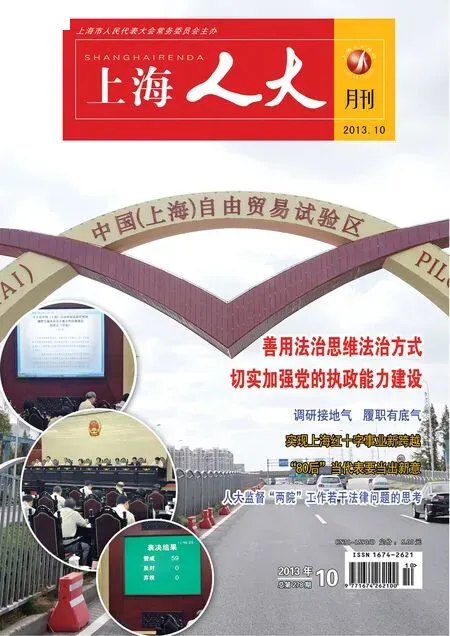人大监督“两院”工作若干法律问题的思考
文/沈志先
人大监督“两院”工作若干法律问题的思考
文/沈志先
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院、检察院的工作开展监督,是人大与“两院”关系的宪法定位所决定的。宪法规定,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人大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从权属、赋权、行使和制约四个方面,明确了我国司法权的运行框架,同时赋予人大履行国家权力机关对“两院”的监督权,以监督和支持“两院”正确行使司法权,确保“两院”忠实履行法定职责。依法充分行使好人大对“两院”工作的监督权,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定职权和法定责任。
人大的监督,在总体上要把握“两院”工作是否坚持了“宪法法律至上”的原则,是否做到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司法以公平正义为依归,公正是司法永恒的主题和最高的价值追求。而追求司法公正,则必须遵循司法规律,必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所谓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必须站在法治的立场上,依法判断和处理周遭一切人和事,其特征是尊崇法律、遵守程序、尊重权利、遵循规律。下面从法律观念层面,就人大监督“两院”工作时,需要关注的若干法律问题,作一梳理。
1、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
前不久,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发表了一篇“如何防范冤假错案”的论文,提出“宁可错放、不可错判”的论点。他说:错放一个坏人,天塌不下来。但错判一个好人,尤其是错杀一个好人,天就塌下来了。这个观点符合“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和尊重、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实际上,这涉及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关系。我们过去长期以来,形成了重实体、轻程序的习惯,程序公正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以为程序仅仅是为实体服务的,只要实体结果可定,程序正确与否无伤大雅。浙江法院刚平反的陈建阳等5人抢劫案,便是这样的典型案例。这是在1995年发生的抢劫并杀害出租车女司机的案件,当时判了4个死缓、1个无期。如今血指纹对上了,真凶项生源终于被抓住了。5名蒙冤者虽已平反但已经被关了18年。冤假错案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具有极大的杀伤力。由于轻视程序公正,导致湖北佘祥林杀妻案、湖南滕兴善杀人案、云南陈金昌抢劫杀人案、河南赵作海杀人案、云南杜培武杀人案、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等一系列冤假错案接踵而至。他们有的被判了死刑并且被执行了死刑,有的被判了死缓,都是因为刑讯逼供而屈打成招,都是在真凶出现或被害人“复活”之后,其冤情方得昭雪。由此可见,程序公正并不仅仅是实体公正的保障,程序公正以其公开、透明、民主、平等、中立等特性而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程序公正强调严禁刑讯逼供,凡用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即使是客观真实的,也必须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而不得采用。这便是“宁可错放、不可错判”。否则,现代版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会源源不绝。从这个意义上说,实体公正是相对的,而程序公正是绝对的。为此,我们强调程序公正优先。人大在监督“两院”工作时,不仅要注重实体公正,更要注重程序公正。
2、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
“两院”办案强调“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如何认定这个“事实”,需要我们运用法律思维的方法。客观事实是指客观发生的事物的本来面目。法律事实,简单地说,就是以公正的程序、查明的证据来证明案件的客观事实,它应当尽可能地接近于客观事实,但并不等于就是客观事实。“两院”办案、老百姓打官司,都必须凭证据说话。比如:张三确确实实借给李四10万元,然而没有借条也没证人,李四不肯还钱还昧着良心不承认。如从客观事实看,虽然不能证明,但确有借款的事实;而从法律事实看,张三口说无凭,缺乏证据,借款的事实便不能成立。所以,以事实为依据,其本质就是以证据为依据。那么,在双方都有一定证据的情况下,又如何定案呢?刑事与民事不一样。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即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必须排除重大疑点,否则就不能定罪。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证明标准是高度盖然性,也就是要看哪一方证据的可靠性超过对方。如果一方所提供的证据证明力明显高于另一方,那么就以证明力高的证据来认定事实,并据此作出裁判。所以,人大在监督“两院”办案是否公正时,必须以法律事实为依据,用证明标准作判断。
3、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两院”办案,要在坚守法律底线的前提下,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兼顾,不可偏废。其实这不是我们独有的观念,西方社会也有这样的价值观。这是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在本质上是应该统一,也是可以统一的。但由于主观和客观上的一些原因,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两者不统一的情况。我们要知道:无视法律效果的所谓社会效果,是站不住脚的,那是人治,绝不是法治;而不讲社会效果的所谓法律效果,也是得不到公众认同的,那不是真正的法治。现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同志,要求“两院”在办案中,既要有利于维护法制的尊严和统一,又要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既要有法律视角和法律责任感,又要有社会视角和社会责任感。这当然是有难度的,也是需要具有智慧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应统一于“两院”依法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全过程,还应体现于司法职能的延伸,如通过司法建议、检察建议、法治宣传等,积极参与社会管理法治化进程。所以人大要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结合的角度,从司法职能本身和延伸两个维度来监督“两院”工作。
4、规则之治与清官之治
规则之治强调制度的重要性。所谓规则之治,是指办事要有规则,要按规则办事,履行规则要严格,违反规则要受罚。它充分体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原则。把这个道理讲得最到位的是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总结了文革的惨痛教训,精辟地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作出这段关于法治的经典论述后,他话锋一转,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往往把领导人的话当做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跟着改变。”35年后的今天,读来依然发人深省。那么,如何落实规则之治呢?其本身也有一套规则。如:在位阶不同的法律之间,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在位阶相同的法律之间,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由于法律的滞后性,当某个具体的法律条文,可能与发展变化的需求不相适应时,可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运用符合立法本意的法律基本原则来妥善处理。当某项法律法规,可能与发展变化的需求不相适应而确实需要先行先试探索时,要由有权决定的机构通过法律手段予以授权,以便待其成熟后修改规则,等等。谈到“清官”,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清官情结。法治社会当然需要清官,遵循规则之治,要求每个法官、检察官都是清官,但同时要求每个清官都能按规则办事。“清官之治”,指的是凭清官的良知和意志办事。其本质仍是人治而非法治,是权大于法,而不是法大于权,那显然是靠不住的。即使能做一些好事,但最终也会随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随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我们曾放弃过规则之治,终于导致了文革灾难性的后果。由此可见,坚持规则之治是如此重要!“两院”办案处事,决不能以言代法,否则将自取其辱,这样的教训颇多。所以,人大在监督“两院”工作时,不仅要关注法官、检察官是否属于清官,更要关注“两院”在履职过程中,包括为大局服务的工作中,是否真正遵循了规则之治的原则。
5、司法质量与司法效率
“两院”的办案质量是司法公正最核心的要素。司法是“两院”为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其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司法的公信力,直接影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办案效率,也是司法的基本价值目标之一。我们常说迟来的公正非公正,便是强调效率的重要性。这次新修订的民诉法制定了“小额诉讼,一审终审”的规定,就是为了顺应公众对司法效率的诉求。为了确保司法质量,提高司法效率,“两院”之间有一套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制度;“两院”的上下级之间也有一套监督制约的制度;“两院”内部还分别建立了一套司法绩效考核的制度。人大在监督“两院”办案质量与效率时,不能只关注数据,关键要看这些监督制约制度是否真正发挥了作用。在分析“两院”所提供的司法数据时,要把握司法数据的内在规律性,要全面、辩证地分析,防止片面性,不能走极端。如调解率高表明“案结事了”做得好,但不能要求它越高越好,否则将违背司法规律;又如在审判质量上,二审改判率低,表明一审的审判质量好,但不可能是越低越好,过低了,可能二审的审判监督职能没有发挥好;再如办案时间短,表明司法效率高,但不可能是越快越好,过快了,工作没有做细做到位,将会影响办案质量。所以人大在监督“两院”的司法质量和效率时,要把握好“度”,这里有一个“合理区间”的问题。在这个“合理区间”内,不分高低,都属正常;对超越“合理区间”的,则须引起警觉。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当质量与效率遇到矛盾时,应当坚持质量优先。
6、司法终局与涉诉信访
进入法律渠道的争议,应该在司法环节终局。这些争议如果终审不终,没完没了,那是司法的悲哀。司法的终局性是法治社会司法公信力的标志。以大家众所周知的美国的辛普森案件为例,该案所有犯罪线索都指向辛普森,因缺乏直接证据,控方只能采用警方所搜集的手套、袜子、血迹等间接证据来指控。但是由于某些程序及证据上存在瑕疵,无法使间接证据形成无懈可击的锁链,法院作出了无罪判决。当时,该案在美国举国上下炒得沸沸扬扬,最终法院一锤定音,也就终局了。从百姓到总统,都说要尊重法院的判决。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法制重建至今,已有三十多年,法治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但司法终局性的问题尚未真正解决。在涉法涉诉信访中,部分群众“信上不信下”、“信访不信法”的观念仍然十分严重。有时,对法院早已终审判决的案件,当事人无理越级上访。为了达到“人要回去、事要解决”的要求,我们有时会无原则地迁就,花钱买太平,可惜买来的只是表面太平,实质是更大范围、更长时间的不太平,信访的功能被异化了。信访是党和国家机关联系群众的纽带、沟通民意的渠道,但不应成为解决利益纷争、决断法律争议的平台。信访要纳入法治的轨道,要把涉及诉讼权利的救济事项,从普通信访中剥离出来。即使需要纠错的,也应当按照法律程序来办。人大在监督“两院”工作时,应尽力促使信访回归本位,既要抓住信访中所反映出来的司法不公问题,加强监督,又要维护司法的终局性和权威性。
7、执行不力与执行不能
破解“执行难”是法院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当然这不是法院一家的事,要靠全社会共同努力。这既和法治环境建设有关,也和社会诚信道德体系建设有关。经过人大的监督、法院的努力、各方的支持,目前执行不力的问题已有较大的改进,但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于因能力不济而拖延执行、因主观原因而怠于执行、因地方保护而难于执行、因害怕出事而不敢执行所导致的“执行难”问题,人大要加强对法院的监督,还要根据新修订的民诉法的规定,加强对检察院发挥监督职能的监督,从而使打赢官司且有条件执行的当事人能及时实现权益。但是强制执行不是万能的,并非所有的判决都能执行到位,总有一部分案件,不管主观上怎么努力,都会基于各种原因而不具备执行的条件。被执行人确实无履行能力的被称为“执行不能”,这是客观存在的市场风险和社会风险。对此,人大监督法院执行工作时,需要实事求是地作出评价,不能求全责备。
8、监督的到位与不越位
如前所述,人大对“两院”工作的监督,是人大必须履行的法定职责,如果监督不到位,便是人大的失职。为此,要从确保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推进依法治国的大局出发,着眼于抓大事、议大事、管大事,在普遍的、重大的、长远的问题上下功夫。要将“两院”工作与全局工作结合起来审议,要看“两院”工作是否发挥了对全局工作的促进和保障作用,是否与国家和上海工作大局相吻合。同时,还要看“两院”在司法改革中是否服从和服务于整个司法体制改革这个全局,是否真正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是否真正有利于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接触到的更多的是具体的事项或者个案。人大监督要真正做到到位而不越位,就必须严格依法办事,正确处理好监督司法与监督“个案”的关系。对于具体个案的审理过程,必须由司法机关按法定的程序走,对此,人大不能越位,不能干预,必须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但是,在监督上的到位,又离不开具体案件,因为司法公正、司法能力与水平都是通过一个个具体案件反映出来的,离开了具体案件,监督工作就难以落实到实处。在这方面,必须根据《监督法》的原则,不搞跨越权力机关与司法机关边界的“个案监督”,而是针对个案中暴露出来的司法作风、司法能力特别是司法不公等方面的问题,督促司法机关改进工作、完善机制,以切实维护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以几年前曾引起全国热议的“彭宇赔偿案件”为例。彭宇将跌倒在地的老太太扶起送医院就诊,老太太起诉称,是彭宇撞倒了她。法院一审判决彭宇败诉。如果是依证据作出的判决,无论结果胜负均与监督无关。但该判决的理由是:从常理分析,彭宇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不是彭宇撞倒老太太,彭宇没有必要送她去医院。这一判断,突破了法律底线,也突破了道德底线。人大所要监督的,就是透过这一具体个案所反映出来的法官在司法思维、司法能力、司法作风上存在的问题。
因此,我们一方面不能盯着具体案件的处理结果开展监督,更不能对涉及特定人、特定单位利益的案件,以监督的形式干扰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另一方面,要善于通过对个案的解剖,从中发现倾向性的问题,从个别上升到一般,提炼出事关公正司法的意见建议,以督促“两院”改进工作。 (作者系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