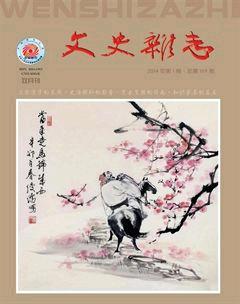试析“蚕丛”名号意涵的多元性
彭元江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蜀,葵中蚕也,从虫”。此议影响广泛。长久以来,人们多视“蜀”为蚕,始祖蚕丛王也与蚕、养蚕、蚕神结缘,其他观点式微。不过,在学界对广汉三星堆遗址和古蜀文化开展一系列研究后的今天,窃以为蚕丛名号的意涵当远不止于此。有关古蜀蚕丛王的文字记载或始于西汉扬雄《蜀王本纪》,该书云:“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亦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
以上资料表明,从时空上看,蚕丛名号应该是一个持续“数百岁”的历史过程,当为若干位蚕丛王所拥有;从意涵上看,蚕丛名号应包括“目纵、纵目人”,“居石室、作石棺”,以及后人盛传的“蚕,养蚕”等内容。但可以肯定,这些看似平淡的记忆在古蜀遗裔的心目中一定十分神圣,否则不会在亡国三五百年后仍铭记于心。
由此看来,在古蜀史上,或许蚕丛应是万民敬仰的复合型神祇:即纵目之神、山石之神、桑蚕之神。现分叙如下。
蚕丛——纵目之神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五十余件青铜头像和若干青铜面具。这些出土物都有眼睛,除其中三件面具的眼睛呈圆柄状凸目,当为特殊的“纵目”外,其他出土物的眼睛多数为丹凤眼式的斜向“纵目”,若与水平线相比较,其眼睛的横轴线约呈30~45度上扬,那件唯一的青铜大立人其眼睛的横轴线也成倒“八”字上扬。[l]《华阳国志·蜀志》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显然,三星堆这些青铜像和青铜面具所象征的,正是始祖众蚕丛王们,甚至可能还包括隶属的亦为“纵目”的部落首领们,用以排成气势磅礴的青铜“纵目”头像、面具阵列。
著名的《羌戈大战》载,戈基人也是“纵目”。不少专家指出:从时代、习性及居住区域看,戈基人就是蚕丛氏,或蚕丛氏后裔。可见“纵目”现象在蚕丛氏族群内是一种人体特征,具有某种普遍性,也是蚕丛王在许多世代里连续保持“纵目”显性遗传的遗传学基础。
眼睛对于刚走出朦胧的古人来说是神秘的,而双眼呈丹凤眼式上扬状(即“纵目”),则更具神秘性。在原始宗教氛围下,三星堆鱼凫氏蜀人铸造了大量的“纵目”青铜头像和青铜面具,体现着他们的“祖先崇拜”理念,也体现着他们的“眼睛崇拜”即“纵目崇拜”理念。这一崇拜可谓达到了极致——那件特大的凸目青铜面具也许就是最高表达形式——它或许象征着古蜀首位蚕丛王,他的双眼被夸张成前凸的圆柱体,这是一种被神化的特殊“纵目”。这位凸目蚕丛王统率着其他蚕丛王和部落的首领们,即大神(巫)统率众神(巫),护佑着他们的子民。蚕丛是“纵目之神”当为古蜀人的精神皈依。
蚕丛氏群体性的“纵目”,即双眼普遍上扬呈倒“八”字,这是人体基因变异的一种遗传学表达,并因上古残余的的血亲婚而得到强化。这一人体特征绝不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消失得无踪无影。试想,若能在古蚕丛氏生活过的区域里,寻找到依旧生活于那里的现代版的“纵目”族群,那将会为“纵目”之说提供可贵的生物学依据。学者董仁威等于2008年上半年在传说的蚕丛氏活动区域,即甘川相交的四川平武、九寨沟及甘肃文县一带,开展了这一田野人类学调查,其结论是:现在于上述地域世代居住的有可能是古氐人后裔的白马人,他们之中许多人双眼的纵目形态明显,与三星堆青铜人头像的“纵目”特征“非常相似”,“在白马氐人中‘纵目存在普遍趋势。”[2]这项调查为“有蜀侯蚕丛,其目纵”之说提供了佐证。
蚕丛——山石之神
古蜀人对巨石、大山有着特殊的情感,这可能源于一个古老传说——“禹出西羌,禹生石纽”,即大禹是西羌人、生于四川汶川县石纽山剖儿坪上的一块大石头,如今民间还有“石裂生禹”的说法。视石为圣物——石能祈福辟灾、石能生子、石能催生、人生活于石、人死葬于石的观念深植在氐羌人及其后裔古蜀人心目中,形成了持久的“山石”信仰,在探讨蚕丛名号的意涵时对此是不能忽略的。
古蜀人与大禹均为帝颛顼之后。蚕丛世代或对应在晚夏,距大禹相去不远,山石信仰丰厚。而且如前所述,他们可能就是被后期南迁羌人所称的“戈基人”族群。除了均有“纵目”的外貌特征外,《羌戈大战》记戈基人“居石洞,葬石棺”;《华阳国志·蜀志》亦载:蜀侯蚕丛“其死作石棺石椁”,“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蜀王本纪》云:“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这些记载都与山石不脱干系。从川西北理县、汶川开始沿大渡河、安宁河流域分布有大石墓葬。岷江峡谷及岷江西岸的广袤区域有“累石为室”之俗,所建石碉楼至今犹在。成都平原曾多有石笋、石阵等大石文化遗存。东汉眉山、乐山、三台等地的土著汉人(即古蜀遗民)建有数量巨大的崖墓群。这都体现着时隐时现的山石信仰。
由此推测,蚕丛名号在古蜀语中或有“石神”、“山神”之意涵,除象征勇武和力量外,还包含生命和生殖——或许蚕丛原本就象征着远古生殖崇拜理念,蚕丛或是女性偶像,而且是传承若干世代的女始祖王。视石为生殖神,对走出朦胧不久的古蜀人来讲是合乎逻辑的。彝族与古蜀族有着族源和文化上的渊源。古蜀人视蚕丛为山石之神的观念很有可能保留在古彝族文化之中——学者易谋远在《彝族史要》中指出——古彝族典籍记载:彝族文明的始祖“武洛撮”,他处的“时间、地点和事迹都与汉文古籍记载的蜀王蚕丛相似”,且“洛撮”二字“彝语义为石人”,其中“洛”为石,“撮”为人。“武洛撮”即“武石人”,“与象征蜀地文化的大石必定有密切关系,而很可能与石室穴居有关。”[3]“撮”字与秦汉以后西南夷的“叟”字音近,均指“人”。再有,“撮”与“丛”音亦近,甚至“武洛撮”加鼻音快读与“蚕丛”音也相似。此似是蚕丛“山石之神”又一证。
蚕丛——桑蚕之神
蚕丛氏部落早期聚居在岷江上游广大区域,其核心地带包括叠溪城(亦称蚕陵城)。对“叠溪”的“叠”字——段渝先生《古代的蜀国·玉垒浮云变古今》记:“叠字应出于先秦金文嫘祖二字合文之省,当为黄帝元妃曾经入蜀的见证”。[4]相传嫘祖正是古代中国蚕业之始祖,享“始蚕”“先蚕”之祀,她必会把养蚕技能传授给居住在岷江上游的土著蜀山氏,况且“嫘祖为其子昌意娶于蜀山氏”。正如段渝先生言:“这支族群早在公元前二千六七百年就已经站在中国蚕桑丝绸业早期起源的门槛上了”[5]。蜀地养蚕时间可谓早矣。
古蜀为黄帝之重孙颛顼的“支庶”之后,封侯于蜀地。作为其后裔的蚕丛氏比前述的嫘祖晚了许多世代。所以,蚕丛虽不算是蜀地养蚕的首倡者,但却是出色的践行者或督行者。这是因为在远古时代,神权和王权合一,历代王者除主持祭祀和指挥战争外,还担负着组织生产的重要职责,以维持部族的生存和繁衍,而渔猎、农耕、养蚕就是重要的生产活动。
总之,或许经过若干位蚕丛王统治的“数百年”,再经过柏濩、鱼凫“各数百年”的经营以及杜宇、开明两代四百余年的治理,蜀地蚕业得到了蓬勃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必将导致意识形态的进化,估计在古蜀国后期,幻化虚妄的神灵观念逐渐淡化——“纵目”的神性和“山石”的信仰逐渐消退或湮没,但人们怀念先祖、颂扬英雄的心理却常在常新,尤其是在西汉扬雄于《蜀王本纪》中将传说中的古蜀始祖名号(很可能就是前述的“武洛撮”——“武石人”),用中原汉字语音直接译成“蚕丛”,加之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写下“蜀,葵中蚕也”,于是蜀国乃“蚕国”,蚕丛乃“蚕神”便不足为奇了。何况袁珂先生在《中国神话大辞典》记:“‘丛之为言,‘神丛也”[6]。所以蚕丛二字原本就是蚕神之意。
蚕——虽不见有纵目巨眼之神性,也不见有大山巨石之雄伟,但柔软的蚕体可结茧、化蛹、变蛾、产卵,孵出小蚕,周而复始,似在暗喻蚕丛的后代永续不绝。蜀人扬雄(前53~后18年)将“武洛撮”对译成“蚕丛”,其用意颇值得玩味。
结语:从原始宗教信仰的角度看:三星堆出土了三具凸目青铜面具和许多纵目青铜人头像、面具,实证了有关“纵目”的记载,蚕丛是“纵目”之神的命题是成立的;由于有“石裂生禹”传说和诸多“石”信仰的存在,蚕丛是“山石”之神的观点亦论出有据;作为部族首领,督行养蚕,民间代代祭祀,蚕丛是“蚕神”之说亦言之凿凿。这种将多种大自然的神奇力量转移到先祖、英雄身上并加以顶礼膜拜,是上古合理的思维。
注释:
[1]钱玉趾:《三星堆纵目与参目头像新考》,《文史杂志》2011年第2期。
[2]董仁威、董晶:《三星堆青铜人面像“纵目”研究》,《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6卷第2期,2008年6月。
[3]易谋远:《彝族史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38、205、208页。
[4][5]段渝:《古代的蜀国·玉垒浮云变古今》,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第23页。
[6]袁珂:《中国神话大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2页。
作者:乐山市科技局退休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