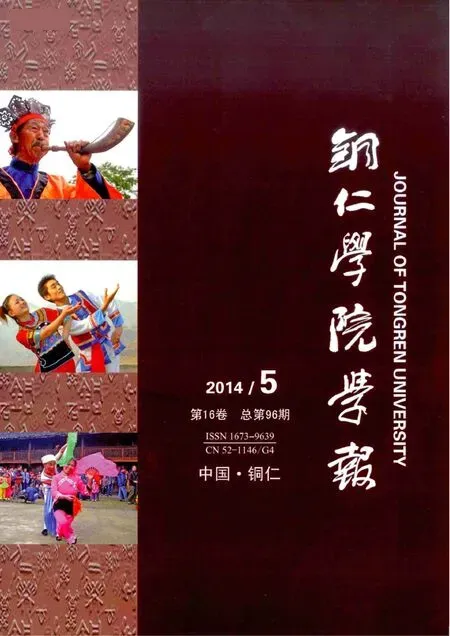村落镜像与神圣砌末
——安徽池州市贵池区梅街镇姚街村荡里姚宗族傩神会的文化生态考察
何根海
( 池州学院 皖南民俗文化研究中心,安徽 池州 247000 )
村落镜像与神圣砌末
——安徽池州市贵池区梅街镇姚街村荡里姚宗族傩神会的文化生态考察
何根海
( 池州学院 皖南民俗文化研究中心,安徽 池州 247000 )
文化生态是指人类的文化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考察池州荡里姚宗族傩神会的文化生态,可以加深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池州傩戏的整体理解。文章透过荡里姚宗族的地理位置、村落镜像、宗族变迁、傩戏传承、演出场地、舞台装置、砌末道具等问题,对荡里姚宗族傩神会的文化生态环境及其跳傩相关事象的深层文化内涵进行了分析,揭示了池州傩文化与宗族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荡里姚; 傩神会; 村落; 宗族; 砌末道具
文化生态指的是人类的文化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荡里姚位于池州市贵池区梅街镇(原刘街乡)姚街村,荡里姚宗族傩戏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池州傩戏”的核心组成部分。每年正月初七至十五,荡里姚宗族在姚氏宗祠等地举行“迎神下架”、“起圣”、“朝青山庙”等傩仪,搬演《舞伞》、《打赤鸟》、《五星会》和《关公登殿》等傩舞,表演《刘文龙》、《孟姜女》等傩戏。荡里姚宗族傩神会是以戴面具表演为特征,以请神敬祖、驱邪纳福和娱神娱人为目的的民间戏曲文化活动,现仍留存着深邃的历史文化信息,“活化石”价值鲜明。用文化生态理念来分析审视荡里姚傩神会,主要是用池州荡里姚宗族生态系统的多元性、系统性、原生性的环境条件来研究分析傩神会这一文化遗产的主体性、多样性、整体性与原真性,这是十分有意义的学术探索,可以进一步探索池州傩文化的存在状态、发展衍变根据和与宗族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深入理解傩神会发生发展的生态动因和文化动因,更准确地理解荡里姚宗族傩文化的内涵,促进傩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一、地理位置、村落镜像与宗族变迁
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Julian Haynes Steward,1902~1972)认为,文化的特征和文化的变迁是环境影响的结果。他的文化——环境适应理论认为,人们对环境的适应是一种重要的创造性过程,可名之曰“文化生态”(cultural ecology),文化与环境是双向互动的,文化适应环境,但也影响环境,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互为因果[1]157-158。荡里姚宗族跳傩文化活动自然也与该宗族所处的生态与社会环境有密切的关联,乡民利用自然、社会与文化条件,搬演傩戏,对宗族跳傩活动进行传承、创新以适应环境,实现宗族跳傩的功能和目的。
(一)地理位置
池州山川秀丽,自然环境优美。池州位于安徽省西南部,地处长江经济带上,北濒长江,东望金陵,南接黄山,西邻匡庐;境内九华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重点风景区,还有秀丽的齐山、秋浦仙境、神奇的地下溶洞群、九华山森林公园、牯牛降国家自然森林保护区;池州是国家生态经济示范区,面积8271平方公里,人口 160万,辖贵池、东至、石台、青阳和九华山风景名胜区,市府所在地贵池,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
池州历史悠久,风物潇洒,素有“千载诗人地”的美誉。夏商周时期,周朝按山川物产分天下为九州,池州属扬州之域;秦统一中国后,大部属扬州之鄣郡;汉时属丹阳郡,今铜陵市、贵池区、青阳县、石台县以及东至县的大部地区均为所属;南朝梁时池州为梁昭明太子封地;唐武德四年(621)始置池州,州治石城(今贵池灌口),隋唐时期池州是江南重要的铜、铅等冶炼基地;宋代以后更为全国重要的铸币基地,经济发达;元至元十四年(1277)改为池州路,隶属江浙行中书省;明代先后改为九华府、池州府,直隶南京;清代如明制,隶属江南布政使司、江南左布政使司、安徽布政使司;民国三年(1914)撤池州府,附属县划归芜湖道;民国十七年(1928)废芜湖道,原池州附属县直属安徽省;1949年新中国成立,设皖南行署池州专区,辖铜陵、贵池、青阳、石台、东流、至德六县;1952年皖南皖北合并,安徽省建制恢复,池州诸县区或废或置,或分或并;1988年池州建制恢复,辖贵池、东至、石台和青阳;2000年撤地建市。池州历史人文荟萃,千百年来,历代文人骚客,俊才名士,流连于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留下了无以数计的名篇佳构。屈原行吟赋骚至青阳之陵阳;陶渊明“日居彭泽,夜宿东流”(今东至县东流镇),吟诗赏菊;李白“三上九华,五游秋浦”,留下大量歌颂池州诗作;杜牧迁池州刺史,登高会友,饮酒赋诗;包拯曾任池州知府,留下了大量爱民故事;明代郑之珍在石台撰著目连戏文;徽剧声腔源头“青阳腔”在民间传唱数百年;九华庙会,梵音绕梁,至今不辍;明清徽商在池州也是形影迭现,商品经济颇具规模。这些历代名家大作,名流盛事,灿若玑珠,为池州增添了夺目的光彩。所有这些自然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环境都构成了池州傩戏发生发展变化的原生性生态条件或文化根据,对池州傩的传承演变具有直接和间接的作用。
(二)村落镜像
村落作为一种传统的人居空间,它是乡民精神内核及其外在表现形式的载体,也表达着乡民对大自然朴素理解的世界观。荡里姚,又称虾(蝦)湖、霞湖,坐落于池州市贵池区东南山区,距池州城区 30余公里,系池州市贵池区梅街镇姚街村一个自然村(原属刘街乡)。姚街村包括上街、下街、梅华、黄岭、新冲、马坦、老屋、坳上等自然村,其中老屋与坳上合称魁山,上街与下街合称荡里姚。荡里姚呈长方形布局,南北走向,村西为南屏山、十八尖,村南有桃花山、小香山和银冲山等,村东白洋河穿村而过。“荡里”来源有二说,据《姚氏宗谱》载:“姚街,古名霞湖,今名荡里。”“地名霞湖,其来有二说。志载村人于山麓取土挖出螺蚌等壳,且多产虾,故名。一说每于雨时,沿雨滴于丹墀,水中见白虾三五,故名。昔时为山间小盆地,潴水为湖,后地壳隆起,湖水外泄而成。志载唐时旧名虾湖,宋改虾为霞。”古代的虾湖,东起青山庙,西至西华姚,南抵桃花山,北达董冲岭,面积约 38平方公里。该村地势低洼,当年汪洋大湖的风貌依稀可见。
荡里姚宗族村落依山傍水,四周重峦叠嶂,白洋河绕村穿过,山青水秀,风景怡人,吸引历代名人游历如此,尤其是唐代大诗人李白五游秋浦,写下著名的《秋浦歌》(共十七首),夜宿虾湖并赋诗一首《宿虾湖》“鸡鸣发黄山(指黄山岭),暮投虾湖宿。白雨映寒山,森森似银竹。提携采铅客,结荷水边沐。半夜四天开,星河烂人目。明晨大楼去,岗陇多屈伏。当与持斧翁,前溪伐云木。”[2]256姚街因毗邻九华山,曾是繁华的“闹市”,当年姚街分为前街、后街和横街三个街道,铺舍林立,有两千多户人家,每天需七筏半米供应客户。该村地处交通要道,交通四通八达,东连青阳、九华山,西过古岭通江西,南越黄山岭通徽州,北顺白洋河经池州达长江。货物运输有肩挑(担子)、驴驮、独轮车推和竹筏水运等方式,以出口金、银、铜锭、木香、蚕丝、银炭等货物为主,现在与外界联络主要以齐石公路(贵池齐山至石门高)陆路为主。
文化遗产自身的发生、发展、延续有着既定的文化法则,其形成于特定的时间、空间里,是人们生产、生活过程中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产物[3]34。从现存村落形貌构图来看,荡里姚宗族村落是自然生态与信仰文化有机结合的范例,该村依山临流,顺乎形势,体现了承天地阴阳之气、循自然五行之道的生态有机观。《宅经》认为,人类建筑是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地)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得如斯,是事俨雅,乃为上吉”[4]16。荡里姚宗族村落遵循着人事活动必须要合于自然规律的生态原则,所以从大的空间格局看,该村村落山水景观是较为和谐自然的,村落布局也是乡民在生产生活中自觉选择的结果。但又正如斯图尔德所说,环境并没有限制文化的发展,而是剌激了文化的发展[5]222-225,从传统风水信仰来说,在荡里姚小格局的村落镜像中,左为青龙,右为白虎,该村左边青龙为白洋河,右边白虎为南屏山、十八尖等山峰,俗信青龙应高于白虎为吉,白虎高于青龙为凶,人们将自然活物化、人格化,在民间信仰中,向有“不怕青龙高万丈,就怕白虎抬了头”之说,那么,从该村自然形势看,右高左低,白虎高于青龙,似有灾厄之象,怎样才能逢凶化吉趋利避害?驱邪逐疫、禳解邪祟的跳傩驱逐活动正好契应了乡民内在祈求,宗族跳傩正是在这种多元性、原生性生态环境“剌激”下赓续不坠,遗留至今。
(三)宗族变迁
荡里姚宗族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族意识为共同体的宗族,这种聚族而居宗族是文化传统的守护者与传承者,许多民族民间文化失去宗族这个载体也便失去依凭而渐趋式微,池州傩之所以千百年来搬演不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宗族在其中起到了凝聚族统、传承信仰、创新文化的作用。光绪三年(1877)重修《姚氏宗谱》载:“姚祥七名胜,由豫章而迁秋浦开元乡,见山水毓秀,携子令公遂家焉。建业灵田,立宅西山,负兑向卯,卒葬西山卯向。娶何氏,生子令……子令,生开宝七年甲戌(974)七月十二日午时,卒北宋明道二年癸酉(1033)四月十九日。”又据《贵池姚氏述源》载:“姚氏肇于重华,立基中州,其后随战乱而北人南下,由豫入浙而赣而皖,其首由赣来皖者,二十二世裔源清公也。公于唐中叶由江西新建迁来皖南绩溪。贵池姚氏溯于赣之新建,于唐末宋初先后三支来贵,曰秋浦西山(今之姚村氏),曰秋浦北冲(今之庄村也),曰秋浦霞湖(今之姚街也),历元明数百年之繁衍,分为六族十三姚,而迁居县外者几布全国,尤以皖北苏北为多,而宗谱之始修也为元至正十三。”①据此推断,姚祥七一支北宋初期从江西迁居贵池,至今已有 1000余年,其后裔居住在今山里姚、山外姚,后来又有荡里姚、南边姚、庄村姚几支陆续迁居贵池,姚氏家庭人丁兴旺。至清代,已分为荡里、楼华、南边、畈里、山里、山外、殷村、毛坦、西华、宋村、蓝冲、庄屋和庄村十三个村落即十三姚②,分别组成永兴社、姚村社、福田社、义兴社和永兴大社[6]91,而荡里姚则成为姚氏一个较大的支族。
姚街村提供的统计资料显示,截止至2008年1月底,姚街自然村共有村民112户,452人,其中姚村49户223人,其他客姓63户229人。在姚姓中又分为荡里姚和西华姚两部,荡里姚又分五个房头,东边房头6户25人,大房6户27人,二房7户37人,三房20户95人,邻房5户19人;南边姚共6户21人。客姓中有吴姓13户,黄姓6户,张姓5户,方姓、王姓、江姓各4户,聂姓、陈姓、章姓、伍姓各3户,夏姓、孙姓、潘姓、汪姓各2户,华姓、徐姓、彭姓、揭姓、叶姓各1户,其中吴、方、张等姓氏多为20世纪初期从江北等逃荒、逃难至此,已成该村永久性居民,现在村中客姓已超过姚姓,但荡里姚仍为一个以姚姓为核心的聚居村落。迄今为止,尽管荡里姚村落宗族内部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荡里姚宗族和宗族乡民的许多生活方式、信仰内容、文化传统、价值诉求等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延续未变,所以姚氏宗族照样依例跳傩,娱神娱人,人神共赏,各姓同乐,一派狂欢!尽管经历了历史的风霜,荡里姚傩神会仍是存在于姚氏宗族群体社会生活中的活的内容,在与自然、历史、现实的互动中较好地保持了傩文化的整体性、原真性,这正是池州傩作为国家非遗活化石的价值所在。
二、傩戏传承、演出场地与舞台装置
(一)傩戏传承
任何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扎根于一个地方的文化传统中,融入地方民众生活中,并体现一个地区的文化特质和价值。荡里姚宗族跳傩活动也是地方文化传统与地方民众生活相结合的产物,是姚氏宗族的标志性文化。安徽池州市的贵池曾是“无傩不成村”的地方,荡里姚宗族搬演傩戏的历史,族人现已难说清,只知是祖辈世代相传。我认为荡里姚傩神会应该是发轫于对梁昭明太子的祭祀活动,在安徽贵池的傩戏祭祀中,梁昭明太子是一个享祀规格很高的大神,被称作“文孝昭明圣帝”,在神坛上的位置甚至高于著名的二郎神[7]164-184。贵池人对昭明萧统的祭祀唐代已十分隆重,并有了专事祭事巫祝。据《杏花村志》引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昭明庙祝周氏杂记》称:“今池州郭西英济王祠,乃祀梁昭明太子也。其祝周氏亦自唐开成年间掌祠事至今,其子孙分八家,悉为祝也。”到了宋代,对萧统的祭祀益加隆重。黄庭坚《贵池诗》自注:“池人祀昭明为郭西九郎。时新覆大舟,人以为神之感也。”陆游《入蜀记》也有贵池祀郭西九郎的记述。两位文人均称萧统为“九郎”。直到近现代,在贵池民间,萧统仍被称为“案菩萨”或“文孝昭明圣帝”,被奉为贵池的保护神,即土主、社神,跻身歌舞祭祀的神坛。荡里姚傩戏源起当与唐宋以来对贵池社神即昭明太子的祭祀这种文化传统有密切关联,或者说正是由于对昭明太子的歌舞祭祀促成了贵池傩的形成与传承,透过祭祀昭明太子与傩文化发生源起的关系,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池州区域特色文化的原生性和原真性,感受到文化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力量。至今荡里姚傩神会在每年正月初七(人日)和十五搬演两天,除举行祭祀仪式外,还表演《舞伞》、《打赤鸟》、《跳财神》、《五星会》、《舞回子》等傩舞,搬演《刘文龙》、《孟姜女》和《陈州散粮》三本傩戏,正月十五还朝拜青山庙。这些祭仪与表演自然也是宗族文化传统的遗存,光绪三年(1877)重修《姚氏宗谱》载:“(傩戏)演时,铳爆鼓乐,喧阗达旦。而元宵清晨,更以卤簿导神至青山庙文孝词,俗谓之‘朝庙’……耆老言,古时朝庙,仪仗外,有秋千、抬阁、高跷诸胜。又选俊童十余,着梨园服,扮故事,立人肩窝上,名曰‘站肩’,其壮丽繁华与江浙等处赛舞无异。”这种“朝青山庙”仪式既是姚氏宗族请神祭社的重大事件,也是民众一种敬祖娱人的狂欢形式。这种传承主体(乡民)的实际参与,既表达了宗族的文化传统,体验了宗族文化的温暖,又承载着族众生活的理想追求。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人们可以在空间中自由漂移,以时间来消灭空间,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了断裂,人们对傩的依存度与热度也越来越低,傩渐渐游离人们生活和文化的视野,逐渐衍变成了一种现代性反思背景下遥远的文化乡愁,走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据姚有志先生回忆,现在的荡里姚傩神会及其傩事活动之所以能薪火续传,也是得益于乡民对宗族文化寻根式的热爱与认同,得益于当代文化环境的宽松和政府的支持,得益于乡贤的倾心整理和对地方知识的坚守。1957年荡里姚宗族姚维中、姚佩仁参加安徽省民间舞蹈汇演,表演傩舞《舞伞》、《打赤鸟》,荣获二等奖,此后该宗族傩戏辍演。20世纪80年代初期,殷村姚、南山刘、山里姚、山外姚、茶溪汪等傩神会相继恢复搬演之际,荡里姚宗族根据姚克水、姚克用和姚庆春等人多方回忆、述录,在 1992年春正式恢复搬演宗族傩戏,并采用手抄方式于 1993年编印成《蝦湖姚傩戏剧曲本》。
(二)演出场地
荡里姚宗族傩事活动主要在宗族祠堂、村口社坛、青山庙址等场地举行。这些演出场地,从表演的视角看,它首先是服务表演的自然空间,是仪式故事舒展的舞台,也是承载观众的自然平台;从社会视角来看,这些场地又是族众公共活动的社会空间,人们藉借傩仪、傩舞、傩戏这种古老的艺术方式表达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活观,这种空间是一种沟通维系族众宗法关系的社会场域,也是族众参与宗族活动的一种社会管道;从文化视角来看,这些演出场地还是一种请神祭祖娱神娱人的神圣空间,通过人为建构或营造,人们赋予了这种空间以神人共处、人神对话的神秘文化义涵,使这种有形的空间和场地蕴藏了无形的文化的实用意义。这些空间场地及其意义,在族众约定俗成的祭祀活动和跳傩表演中自然生成与转换,有时甚至直接构成了荡里姚宗族祭仪和跳傩表演的一部分。荡里姚宗族的演出场地恰恰表明了特定环境中生态与文化的互动过程,同时也表明只有在民众的现实生活环境中,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得到长期有效的保护[8]9。
1.姚氏宗祠
宗祠是族众与祖先对话交流最重要的处所,自然也是祭请祈求最为灵验的地方。姚氏宗祠座落于荡里姚自然村中部,坐东朝西,方向 290度,是一处明末清初时期的建筑。祠堂三进,面阔三间,进深40米,宽17米,高9米,抬梁式砖木结构,梁枋雕刻较少,正中是大厅,两侧为厢房,后进祭祖台两边镶有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来陇碑记和嘉庆二十五年(1816)重修建祠家谱碑刻。祠前广场顶端有半月形放生池,并立有唐代李白到此而作《宿虾湖》诗句现代碑刻。该祠堂为已故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家族支祠。姚氏宗祠是荡里姚傩神会的主要表演活动场所,许多傩仪、傩舞和傩戏均在此搬演,其空间意义自然也不言而喻。
2.村口社坛
宗族社坛位于村口社树旁,老社树已遭砍伐,现有一棵新植的小树。社坛上面是一块石粉红板,南、西、北三面封闭,东面敞开,呈一祭桌式,其下可燃烧纸钱、燃烛,其上也可摆放供品。社坛正面树立“二十四嚎啕神圣之神大显威灵”之牌位,两侧有对联一幅:“傩神在此启圣,社坛大显威灵”。荡里姚村口社坛是举行傩祭傩仪重要的神圣空间,因村口社坛是祖先神灵包括鬼祟常出入之所,在此表演相关仪式表达了直接与祖先神灵对话的行为意向,在此驱邪逐疫效果也应更好。
3.青山庙址
青山庙承载着池州历史文化的传统。青山庙址位于贵池区梅街镇刘街村(原属贵池区刘街乡)一突兀的山岗上,东靠来陇山,西临白洋河,南北为良田。其始建于元朝大德年间,原为昭明太子祠。约从明代起,元二保乡的汪、刘、姚、戴、郑等九社每年正月十五日上午在此举行朝庙仪式,称“九社朝土主”。朝庙时,鸣锣放铳,旗伞仪仗,簇拥着龙亭、“傩神”(面具)仪仗队依次前来。青山庙在“抗日战争”期间遭到毁坏,现仅存庙基。青山庙是荡里姚宗族请神祭社、祈求吉祥的神圣空间,也是族众传承族统交流感情的开放的社会空间,更是乡民舒展筋骨会聚狂欢的自然空间。
4.白洋河畔
该处位于荡里姚村落西部白洋河畔,河段南北为农田,河上有座用水泥板搭成的简易“小桥”,长约10米,宽1米,桥下水流湍急。这里是姚氏宗族每年正月十六早晨举行的“送寒衣”(又称“放河灯”)之处。这种自然空间因白洋河河水有流动放逐的象征意义而被乡民所重视,因而成了送神和逐疫的最佳表演处所,这种逻辑关系反映了乡民模拟巫术的思维特点。
(三)舞台装置
戏台是傩戏表演的场所,具有文化背景的意义,戏台往往又是现实社会的缩影,具有传承文化的价值意义。荡里姚宗族傩戏在宗族祠堂内搭台演唱,舞台设置于祠堂天井与宗族祖辈牌位之间,长8米,宽5米,高1.5米。舞台装置古朴别致,台前檐与台内左右及后侧,分别挂五彩缤纷、形如网状的或飘带式的纸彩。前后台以影壁相隔,名曰“亮匾”,亮匾两侧上下场门楣上挂有绿色或红色帘子,帘子上方各写有“出将”“入相”牌,亮匾前置有一桌两椅,上置桌帏、椅褡,桌上摆放点燃的香炉、烛台。两侧台柱上贴楹联,上联为“古礼犹遵方向(相)掌”,下联为“祚阶如见素王仪”,横批“共庆升平”;中堂设置于对联之间,其内容正月初七与十五不一,正月初七中堂内容为“此日为何日,人辰是此辰。拈香来祖庙,秉烛敬傩神。依旧风光好,居然气象新。年年循古例,同庆万象新。”正月十五换为“乡村无事闹新年,锣鼓声喧接九天。欣逢今宵明月好,神喜人欢大团圆”③。荡里姚宗族跳傩将舞台设置在祠堂天井与宗族祖辈牌位之间,表明搬演傩戏初始动机是出于祭祖娱神的需要,“亮匾”、“出将”、“入相”牌和楹联等是表明乡民对封建社会权威势力的向往与追求,并以此营造乡民心中的社会理想,舞台装饰均是构建舞台社会的实用符号,具有特定的文化承担功能。
三、砌末道具
荡里姚宗祠傩戏砌末道具繁多,有傩戏用具、傩舞用具和傩仪用具,还有普通用具等,一般都自制。除傩戏面具外,傩戏用具有云帚、马鞭、印箱、朝笏、折扇、签筒、惊堂木、喝道板(罗汉竹制成)、文房四宝等,傩舞用具有神伞、古老钱、赤鸟、弓箭、大刀、钺斧、瓜锤等,傩仪用具有神龛、龙床、日月箱、祭桌、香炉、三牲、烛台、火铳、火把、开锣、小锣、鼓、钹以及龙亭、黄龙伞、万民伞、二十四孝伞、各色旗、龙头杖、偃月刀、斧、金锤、笔、蛇矛、月牌、戟、双戟、金抓、矛、朝天盾等仪仗用具等。这些砌末道具表现了傩神会文化生态的多元性、系统性特点。文化生态,一方面指文化与生态之间的互动,另一方面也隐喻着用生态的法则来看待文化,以使文化的整体性、系统性、多样性等能够持续发展[3]31。从文化生态视角来说,荡里姚宗族傩神会的这些砌未道具既发展传承了傩文化,维护了傩文化的多样性、动态性,又深化创新了傩文化,强化了傩文化的整体性、系统性。这些道具砌末及其与傩文化之间的互动关联共同构建了荡里姚傩神会这一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在傩仪、傩舞、傩戏表演活动中,它们既具有表演的实用意义,又具有仪式法器意义,还具有封建文化的符号意义。既是表演形式上的生态性道具砌末,又是表演内容与目的文化性物态载体。这些砌末道具共同构成了荡里姚宗族傩神会表演过程中的文化生态环境,离开这些文化生态条件,乡民跳傩的神圣性与目的性便难以确立与实现。
(一)面具
面具是傩神会的核心符号。戴面具表演是姚氏宗族傩戏的基本特征。表演者扮相,包括冠戴、头饰、髯口均体现在面具上。傩戏面具俗称“脸子”、“假面”,为黄杨木或柳木(枫杨木)雕制,油漆彩绘,形状外凸内凹,眼珠和眼角镂空,戴时头上扎一块布头巾。面具有“全脸子”和“半脸子”之分,分“通用”和“专用”两种。荡里姚宗族傩戏一套脸子共30枚,于20世纪80年代末特请青阳县庙前镇面具制作传承人林中琳先生雕刻而成,有皇帝、皇母、文官、武宫,有财神、土地、关公、和尚,有包公、张龙、赵虎、范杞良、萧贞女、孟姜女,还有童子、宋中、梅香和余娘子等。面具经过开光后,被尊为傩神,具有不可亵渎的灵性,与神灵等同。表演者佩戴之后通过巫术相似律的作用,他们已不再是普通的人,而就是傩神附体的神了,是神本体的表达者、代言者和模拟者,傩戏表演的神圣性也随之具备了。可见,“面具”既有模拟鬼神祖先的符号意义,担负着沟通神界和人界的物态介质作用,同时又是人们现实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工具性道具性反而往往被人们所遗忘和忽略了。
(二)龙亭
龙亭系池州傩戏迎神、朝庙或出巡时抬傩神(面具)专用道具。荡里姚宗族的现存龙亭于20世纪80年代末请当地木匠仿古打制而成,形如“亭”状,上宝炉顶,下分三层,如宝塔状,越上越小。最下层最大,为一活动的方形柜,四面尽是雕花板,为正月十五上庙放傩神(面具)之用。第二层为龙居,上庙时为供关公面具和“龙玺”。四面有四金柱,柱上各有一条金龙盘云,这四条金龙雕得小巧玲珑、栩栩如生。该龙亭玲珑剔透,华丽精巧,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据村民介绍,制作此副龙亭,需花几百担稻谷,费时数年,这足见其技艺之精巧。龙亭应是对封建帝王金銮殿的模拟,在荡里姚宗族傩神会中,龙亭是最为神圣的道具,龙亭造价也最高,雕刻文饰也最为精致,其实用性功能是将“神仙皇帝”的面具供放其中,抬着这种神圣的龙亭参与祭仪和表演本身就有巫术法器意义,因为龙亭是傩神的寓所,龙亭所在就如傩神所在,龙亭所到便如傩神所到。
(三)龙床
龙床系傩戏表演时摆放傩神(面具)的案子,用木板搭架成方形桌子,上面罩有台布。荡里姚宗族傩神会面具中有“皇帝”面具,古代皇帝被尊为“真龙天子”,是龙的化身,所以承放“皇帝”等面具(傩神)的案子也被乡民奉为龙床,对它也是尊崇有加,不敢轻慢。傩神(面具)经开光后,要按祖辈遗传而来的固定次序摆放,不得随意更改,从上至下摆位如下:
大和尚 武官 皇帝 文官 萧贞女
二和尚 财神 皇母 文龙 孟姜女
三和尚 杞良 包公 土地 吉婆婆
大回子 宋中 关公 王大 梅 香
二回子 杨兴 父老 王二 余娘子
赵 虎 赵吏 童子 孙吏 张 龙
荡里姚宗族傩神会龙床上的面具摆位同样也表达了乡民的社会文化观念。面具摆位中的次序位置既与傩神会中的表演角色有关,也是与乡民头脑中傩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等级相似性的观念有关,乡民基于现实环境和生存发展的需要,认为傩神世界的秩序也是对现实世界秩序的一种模似与仿效,通过戴面具行傩仪、跳傩舞、演傩戏就可以摆脱现实困境,实现人生祈愿,追求幸福生活。因此,荡里姚傩神会中龙床上固定次序的面具摆位也是一种文化生态原生性的反映。
(四)荡里姚伞
伞是傩坛的神秘法器。“南边旗,荡里伞,刘锣戴铳汪扎板,山里山外干呐喊”,荡里姚宗族的“伞”形式多样,有神伞、黄龙伞、万民伞和“孝伞”等。荡里姚“神伞”用竹杆和竹篾扎制,上用纸糊成,段长约五尺,伞顶平园,用纸糊密,并绘有蝙蝠图案,伞顶四周用纸层层糊成圆筒状,平年糊十二层,闰年糊十三层,再镶上金色纸边,垂直贴上约60厘米长的彩色纸条,纸条上书“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等吉祥语。荡里姚“孝伞”将古代“二十四孝”中二十四个人物故事,用刺绣的方法,将其绣在四把伞的围幛上,这二十四孝的故事分别为“单衣顺母”、“啮指心痛”、“为亲负米”、“戏采娱亲”、“卧冰求鲤”、“行佣供母”、“扇枕温衾”、“哭竹生笋”、“闻雷泣墓”、“为母埋儿”、“孝感动天”、“鹿乳奉亲”、“扼虎救父”、“拾葚供亲”、“卖身葬父”、“尝药奉母”、“赏粪心忧”、“亲涤溺器”、“弃官寻母”、“乳姑不怠”、“恣蚊饱血”、“涌泉跃鲤”、“怀橘遗新”和“刻木事亲”。荡里姚的“伞”,从功能来看。可分为三种类型:一为降神之伞,即“神伞”。荡里姚傩神会第一个开场傩舞便是《童子舞伞》,俗信以为伞面形为天穹,伞柄类比古代联通天地的“建木”,神伞伞纸平年十二层、闰年十三层表明神伞与时序社会的现实关联,这样傩神可凭依这种符号性的神圣器物从天而降来到人间,而古代信仰中“童子”的身份亦有巫觋的角色意义,故以“童子”按固定程式舞动降神之伞自然会使傩神顺利降临,向神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自然会更加方便。二为仪仗之伞,如黄龙伞、万民伞等,主要是起仪式性氛围烘托效用,同时也有封建执政者宣化德政、彰显威权、号令社会的作用。三为教化之伞,即“孝伞”,荡里姚宗族以“孝伞”为宣传“二十四孝”的道具是别具匠心的,也是荡里姚傩仪器物的一个特色,因乡民认为“伞”是有神性的,因此将它作为传扬“二十四孝”孝道精神和孝文化载体更易让乡民认同和接受,违背孝道精神就是对伞的不敬,对伞的不敬就是对神的不敬。如果从宗法关系来看,不守孝道也就是对父母人伦的不敬,对父母人伦的不敬就是对祖宗的不敬,一个对神对祖宗不敬的人是人神共愤难逃灾厄的,也是无法立世的。封建宗法社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这样以傩坛之伞这种貌似平常的道具器物为生态媒介流露和表达着,并悄悄地流淌到乡民的世俗生活里,渗透到乡民的精神最深处。三种类型的“伞”表现了荡里姚宗族傩文化的多样性,而孝文化与傩文化的涵化结合,表明在文化系统内,各种文化相互作用并受环境制约而达到新的平衡,从而使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1]159。
(五)戏场锣鼓
戏场锣鼓是古代戏曲发生发展重要的文化生态条件,如果没有这些器物,古代戏曲就缺少文化生机和表演法度。荡里姚宗族傩戏武场有大锣、筛金、小锣、铙钹、堂鼓、板鼓、扎板各一。伴奏锣鼓有两种:一是唱腔锣鼓,主要起过门连接、启腔和托腔作用,常用鼓点为长槌、短槌、介槌、底槌、四门净、大批水、小批水等;二是动作锣鼓,配合演员表演。荡里姚宗族傩神会戏场锣鼓类型较为齐全,鼓点也较有艺术特色。从神秘文化视角来看,这些锣鼓一方面是服务于仪式戏曲表演,是娱神敬祖的需要,傩神与祖先要通过这种有节奏的欢娱的演奏与环境,实现自身的“在场”,实现人神共赏、人神对话和天人合一;另一方面,这些锣鼓尤其是荡里姚的“动作锣鼓”是出于驱邪逐疫禁忌巫术的动机[9]108,乡民企图以高亢变化的强烈节奏配合鞭炮火铳达到震慑驱赶邪祟的目的,傩文化驱鬼疫祈吉祥的本质特征在荡里姚的戏场锣鼓中同样也表露无遗。
(六)服饰
服饰是古代戏曲表演中的符号性道具,也是演绎角色的实用物件。荡里姚宗族傩戏服装较简朴原始,一般沿袭明代服装样式。早期服装因陋就简,用土布制成斜襟长袍,用黄山桅染成茶色或用靛兰染成兰色,也有用颜色勾绘花纹图案,乡土气息浓郁;后期傩戏服装逐渐讲究起来,采取集资方式到外地购置一些与戏曲相同的一些服饰,如官衣、蟒袍、洒手衣之类。荡里姚宗族傩神会中,早期的服饰具有皖南民间生活文化色彩,后逐渐讲究服装的外在形式与质量,采购一些官衣、蟒袍、洒手衣之类正统戏曲服饰,表明荡里姚宗族傩神会也在与时俱进,随着社会环境条件的变化也有一些改变,这种现象表明文化与环境是相互利用双向互动的,原真性的文化遗产也会受到现代意义的戏曲文化的影响渗透,也正是由于文化与环境的适应性推动和促进了傩文化的发生、发展、传承和创新。
注释:
① 《贵池姚氏述源》(抄本),2007年荡里姚姚红斌提供。
② “九刘十三姚”是指现居住在贵池区梅街、棠溪两镇的“刘氏宗族”九个村落和“姚氏宗族”十三个村落,“九刘”分别是刘街村的南山刘(上村、下村)、岸门刘、汤村刘,太和村的观音阁刘,双溪村的立山刘、童村刘、前山刘和凤玲刘,潘桥村的观冲刘(现搬迁至刘街村南山)。“十三姚”分别是姚街村的楼华姚、荡里姚、南边姚、畈里姚,姚村的山里姚、山外姚,双溪村的殷村姚(南边姚)、毛坦姚,梅街村的西华姚、宋村姚,长垅村的蓝冲姚,太和村的庄屋姚,棠溪镇的庄村姚。
③ 《虾湖姚傩戏剧曲本》(抄本),2003年11月吴国胜提供,第1页。
[1] 朱以青.文化生态保护与文化可持续发展——兼论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山东大学学报,2012,(2).
[2] 池州市文化局,编.历代名人咏池州[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3] 吴兴帜.文化遗产保护的生态视角[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1).
[4] 王邦虎.人与自然结合的光辉典范——论徽州古村落的生态学价值[J].安徽史学,2008,(1).
[5] (美)斯图尔德,著.张恭启,译.文化变迁的理论[M].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1998.
[6] 姚永昌.贵池刘街“傩”漫谈[M]//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安徽省艺术研究所,安庆行署文化局,编.傩戏·中国戏曲之活化石——全国首届傩戏研讨会论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92.
[7] 何根海,王兆乾.在假面的背后——安徽贵池傩文化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0.
[8] 刘魁立.文化生态保护区问题刍议[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7,(3).
[9] 何根海.崇仰与禁制——安徽贵池宗族跳傩的禁忌事象研究[J].戏剧,2012,(4).
Village Images and Sacred Stage Properties——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a clan Nuo ritual in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HE Genhai
( Research Center of South Anhui Folk Culture, Chizhou Univesity, Chizhou, Anhui 247000, China )
Cultural ecology refers to the natur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in which human culture exists.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a clan Nuo ritual in Chizhou can deepen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Chizhou Nuo opera, a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ased on the village location, village images, clan changes, Nuo opera inheritance, performance sites, stage setting, stage proper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econstructs cul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Nuo opera of a clan and the deep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Nuo opera performance, and reveal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zhou Nuo culture and cl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ngliyao, Nuo opera, village, clan, stage properties
(责任编辑 白俊骞)
(责任校对 黎 帅)
B933
A
1673-9639 (2014) 05-0013-08
2014-6-30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池州傩研究”(12BZW121);安徽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安徽贵池荡里姚宗族傩文化研究”(KS2013A120)阶段性成果。
何根海(1963-),男,安徽枞阳县人,池州学院党委书记、校长,皖南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