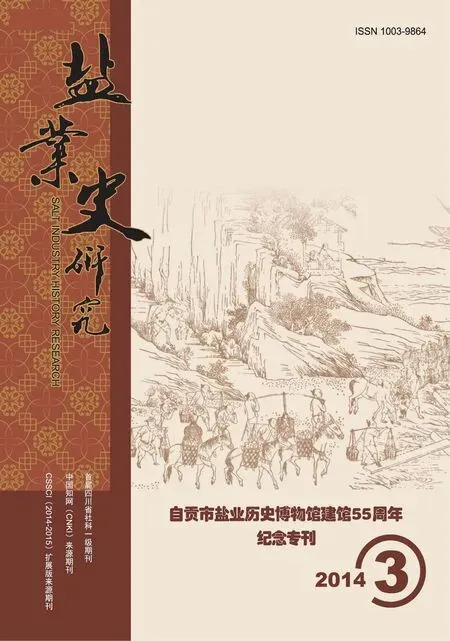怡良与两淮盐政改革
倪玉平
怡良(1791-1867),满洲正红旗人,由刑部笔帖式历任山东盐运使、江苏布政使、广东巡抚等职。咸丰三年,怡良出任两江总督,至咸丰七年因病辞归,在任期间例兼两淮盐政,针对太平天国起义勃兴等新的形势,推行就场征课,并大力抵制以盐济饷,并为后续的改革做了必要的铺垫。本文即就此作一简单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就场征课
太平军虽然没有直接控制过两淮盐区的主体淮南盐场,但却间接地使淮南盐场的食盐生产受到削弱。咸丰三年三月,太平军攻陷镇江,四月攻陷扬州,“不特淮南引地无不被其蹂躏,即商人之居于镇扬二郡者,十有八九亦悉遭荼毒,以致盐务更形败坏”①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朝·财政类·盐务·咸丰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两江总督兼盐政怡良折[Z].(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鉴于此,两江总督怡良随即上奏,请将壬子纲奏销展限,积引暂停。
迫于形势,户部虽然只能同意怡良之不开本年淮盐,但因怡良“于淮南盐务如何设法办理,并未一语筹及”,担心淮南盐政从此不可收拾。况且淮南各场产尚属“完善”,相邻各省人口繁荫,军队需盐亦大,“若藉词军书旁午,任听灶丁私煎私售,而不设法经理,非特尽撤藩篱,不可收拾,即目前自然之美利弃之如遗,于全局大有关系”。经过部议,他们特意将道光十一年(1831)太仆寺少卿卓秉恬之立场抽税、侍读学士顾莼之课归场灶、光禄寺卿梁中靖之就场收税、江西巡抚吴光悦之撤商归灶四件奏折,转抄怡良,希望他在危局之中能别开生面,“不拘运数多寡,不问销路远近,随资本之大小,听商民之贸易,只交一引之课,准运一引之盐”②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朝·财政类·盐务·咸丰三年八月十七日·大学士户部尚书祁寯藻等折[Z].(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怡良很清楚,“以国课支绌,军需浩繁之际,若不于无可筹画之中,急思补救,非独饷需无出,且恐盐务全局从此荡然,将来更难收拾”的道理,故而他立即与署两淮运司郭沛霖等商议后,上奏奏称就场征税的七条办法。
其一,淮南之盐,每正引四百斤,辛亥纲以六百斤出场,作引半纳课。商贩按引呈缴,或缴分司衙门,或缴场官衙门,听商自便。
其二,就场捆运,以六十斤为中包,外加卤耗包索六斤,每大引分捆十包,由运司衙门印发编号,三联大票交分司加印,分别填明发场转给。
其三,盐运出场,于如皋县之许家坝、泰州之滕家坝、江都县之白塔河三处,设卡秤掣稽查,此外出江支港概不准行,并颁发卡员钤记,以凭截票盖钤,否则即以私论。
其四,委员薪水、院司巡缉、赏号经费、通泰分司各衙门经费、书役纸张工食均在四钱五分内提用,如有赢余,即以留备活支,各款如尚不敷,即随时酌筹弥补。
其五,改道运行,除江甘五岸听其行销,如有愿赴淮南引地、楚西安徽各岸销售者,盐船出江后应驶抵南岸,经过浙引地方,不准私自售卖,占碍浙盐销路,违者以私论。
其六,课归场征,若不稍立禁防,难保奸民不藉端影射,积囤济私,应将近场食盐改归就垣拨买,俾灶产之盐颗粒归垣,庶奸贩无从影射。
其七,泰坝上下河停泊各盐船,系已经完课之引,有愿缴就场征课钱粮者,听其在泰坝官衙门完纳解捆六十斤中包,即由泰坝官向分司移取大票,给发护运,俟江路通行,准其照引补运,无须再纳钱粮。①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朝·财政类·盐务·咸丰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两江总督兼盐政怡良折[Z].(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这一方案很快得到清廷的批准。需要指出的是,章程第五条所言之改道,即由长江北岸出江都县属之白塔河等口,渡江经常州、镇江两府所属各口岸,行抵东坝起驳,换船直达芜湖。如果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要绕过已经被太平军控制的南京。
三个月后,怡良奏报淮南就场征税的情况,他称,现在太平军控制长江,其船只“往来游奕靡常”,东坝以上难以通行,“商贩闻风裹足,请运之数甚属寥寥”。他的对付办法,惟有运一引盐,即征一引课,“尽征尽解”②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朝·财政类·盐务·咸丰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两江总督怡良折[Z].(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由于刚开始就场征税效果并不理想,咸丰四年五月,怡良不得不再次奏称,开办半年有余,征课仅止 4万余两,且“皆由认运勒限追缴,并非因畅销而得”,日后征课,必定“更属日难一日”。故本年奏销不能如额,仍不过是不“尽征尽解”。户部对此并不满意,认为怡良等人如果认真补救,实力缉私,“何至片引不行,一筹莫展”?且所收课税本无须拘定商名,但交一引之课,准运一引之盐,“若止责令旧商派认正课,亦非所以广招徕”。另外,现在江南大军云集,“无一非食盐之人,即无一非销盐之地”,为今之计,不如派专员运盐至琦善、向荣等人军营,“计口授盐,俾资抵饷,似于国计、军储两有裨益”③方濬颐.淮南盐法纪略:卷一·就场课税·江路梗阻片引不行未能依限造报奏销折[Z].刊本.淮南书局,1873(同治十二年).。
在淮南一筹莫展之际,淮北的情况亦属勉强。本来,咸丰三年之淮北征课情况还属可以。据怡良奏报,淮北纲食各岸共296982引,而本年份票贩请运335770引,官运24千引,书院经费1千引,皖省借拨10万引,委员捆运新关功盐存坝应贩1130引,青口腌切食盐80引100斤,以上总共请运票盐 461980引 100斤,较之定额仍溢盐164998引100斤④朱批奏折·财政类·盐务项·咸丰四年六月初四日·两江总督兼盐政怡良折[Z].(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但随着军事行动的加剧,淮北每况愈下。
咸丰四年五月,怡良奏称,淮北历票盐,向系预于年前开办,本年份之癸丑纲新课,节经札催海州分司,遵照成案,赶紧筹议开局。但据海州分司运判许惇诗回复称,淮北近日“售价日疲,销市日滞”,加之安徽警报频传,临淮五河一带,还有土匪把持盘踞,“自怀远至正阳,尤为匪徒渊薮,商贩裹足”。因为正阳关为淮北畅岸,向来每年可行盐十余万引,现已片引不行,近闻庐郡失守,正阳关居民纷纷迁徙,湖贩更加畏阻。本年正月间,西坝并未售盐,更兼三河坝因洪水未能堵塞,盐须陆运,上年盘驳费重,并闻浮山口三十里河,均已全涸,以致怀远以下之湖贩,亦复畏累,不敢运盐。通计积引多至一纲有余,“即使运道指日肃清,恐亦不能于数月中销足一纲之盐”。票贩只有一副资本,且银路多阻,借贷无门,开办新纲,实属无可措手。现在西坝卖价,每包仅售7钱数分,核计成本每包亏银2钱有奇,每引即亏银8钱有奇,新纲科则若仍照旧征收,“是驱之倾覆之地,强令完纳,人情不顺,何以招徕”?故而他建议,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减轻成本。当然,成本内如正税杂课,系要上交朝廷,未敢拟减,惟有代纳淮南悬引课银一款,每引征银6钱9分3厘2毫零,原案曾经声明淮北销滞,即当议停。今淮南业已改章,本无悬引名目,淮北疲滞,“万难再令代纳”。即使尽数减免,每包轻本只 1钱有奇,尚虑不敷,故请在场商应得盐价每引 6钱内减银1钱,再减河费1分,以符每引减轻8钱有奇之数。对于许惇诗这一建议,怡良认为所言各条,尚系实情,故应准行,“一俟道路稍通,坝销日起,仍令照旧代纳,或即按引提还,当随时相机办理”①朱批奏折·财政类·盐务项·咸丰四年五月十二日·两江总督兼盐政怡良折[Z].(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但是,户部对此表达强烈不满。他们认为,淮北盐务自道光十二年改票以后,每年行销票盐46万余引,内融销淮南悬引22万,代纳课盐31万余两,并票盐溢课协贴淮南银 36万两,“历经奏报全完”。现在怡良等人所言,并无疏销裕课长策,只冀减免悬引。不过,考虑到所减之经费,均系“外支外用,非如悬引课银拨解攸关可比”,应如所议准其酌减,以轻成本②朱批奏折·财政类·盐务项·咸丰四年五月十二日·两江总督兼盐政怡良折[Z].(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与此同时,淮南各岸亦要求减轻科则。据署运司郭沛霖称,江甘等五岸向因地近场灶,只完报部正课,其余外带杂款概不完纳,但后来被一律扯平,即每引征课1两7钱3分零,另带征经费4钱5分。江甘五岸委员候补大使邹观廷、候补知事褚霖称,五岸销数以江甘为最,计自扬城收复,人民凋敝,食户不及十之二、三,疏民多未归里,较之平时益形狭隘。现在盐价每斤不过数文,计商盐成本即增至一倍,尚不敷钱粮应用。故请照原来办法,每引8钱8分5厘3毫2丝1忽5微8纤,高宝原则每引8钱4分6厘8毫5丝9忽2微3纤,加完一半。况且,江甘等五岸从前每引400斤,现在每引600斤,“自应照引半完课”。加完一半之后,实际上是江甘每引1两3钱2分7厘9毫8丝2忽3微7纤,高邮、宝应1两2钱7分2毫8丝8忽8微4纤5沙,各引仍加带经费银 1钱。既可以缓解运商压力,于正课亦无影响。结果,这一主张得到怡良的同意,并得以推广开来③方濬颐.淮南盐法纪略:卷七·江食各岸·请减江甘等岸科则详[Z].刊本.淮南书局,1873(同治十二年).。
二、抵制以盐济饷
针对两淮盐政的困局,原任侍郎周天爵奏请淮盐10万引,“由官招商运销,先盐后课”,不过效果并不好,很长时间才招运 1万余引,且“尚未销脱”。正在两淮盐斤一筹莫展之际,左副都御史袁甲三又奏请就滞销盐斤筹运济饷。据其奏报,现在商贩均跌价求售,以便脱手,故袁甲三想官运淮盐。他称,听说西坝现存旧盐约三十四五万引,本年能否销完尚未可知。不如令票贩将在坝盐斤,每包按照时价 8钱内外,全部交官运,多出部分算作下纲课银,“如此通融办理,各票贩无须在坝守候卖盐,可省多出旅费,且释其尾欠之追呼,免其新课之称贷”。现在淮南引地悉被阻断,惟淮北引地尚有可销之处,现商贩运跌价相售,该署运司目睹焦灼,不得不议每引减悬引银6钱9分零,又减不关解课之盐价1钱,河费1钱,以冀招新贩而鼓旧贩。至于周天爵之遭遇,袁甲三认为,可照时价先销十数万引,以作水脚,再来周转。这得到户部的高度赞同①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朝·财政类·盐务·咸丰四年六月十九日·大学士户部尚书祁寯藻等折[Z].(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随后,袁甲三再次上奏,谈及让他办理官运之事,淮北一年应销184万包,今时事尚未可知,是以日前折内于 184万包减而又减,至于计销六七十万包。不过,部议称“票贩在坝跌价贱售,实欲收回成本,及早散归,今以盐抵课,所有存盐悉交官运,该票贩视为脱然无累之身,去之更速”等语,他表示,商人零星亏本跌价贱售,“一经售竣,携资而去,无所系恋,谁能禁之”?②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朝·财政类·盐务·咸丰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左副都御史袁甲三折[Z].(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针对袁甲三之以盐济饷计划,怡良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官运只有借助于私商,但官府无钱,则找不到商贩。袁甲三之办法,不但不是两纲之课,甚至连一纲之课也不足③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朝·财政类·盐务·咸丰四年闰七月初四日·两江总督怡良折[Z].(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对此,户部表示,原以为袁甲三之事,“于溢销裕课,洵为有见”,但由于怡良反对,“臣等究未身历其境,难以悬揣”,故“袁甲三著无庸会办”④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朝·财政类·盐务·咸丰四年闰七月二十四日·大学士户部尚书祁寯藻等折[Z].(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在遭到怡良的反对后,袁甲三亦展开反击。他称,怡良行署与两淮相距较远,一切应行事宜,均由自己主稿,“即或有求全之毁,亦断不相尤等语”。他私心窃喜,以为怡良“开诚布公,和衷商榷,不愧大臣风度”。不料怡良忽然有窒碍难行之奏。据他搜集到的资料,怡良所称窒碍难行之处,均系受自己斥责的海州运判许惇诗之意见。许惇诗曾被自己批驳过,该运判无词可辩,遂亲赴泰州面见署运司郭沛霖。郭沛霖原来打算揭参许惇诗,不料许惇诗拜认师生,“遂致通同一气,侵蚀公帑,丧心昧良,至此已极”。至于安徽军饷欠饷,他原奏声明或随同官运,或买回存盐,均听其便,“并非尽人而强以所难也”。若票贩于以盐抵课后,即难再行措银买盐,则该分司何为以旧盐抵旧欠?明系奸商要挟,仍欲曲从减免悬引之议,“漠视课饷,肆意把持”,自己“断难姑容”。至前纲旧盐未能全运,岂不苦累灶丁?乃该分司不催重旧盐而虑停新盐,“试问旧盐未竣,新盐可畅销乎?新课未征,新盐可先重乎”?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欲为灶丁诉苦,与灶丁何益?现在私盐充斥,乡民惟利是视,未有不争食私盐者。即以临淮而论,官盐运到合计成本已在二十六七文,而乡间盐价不及二十文,其为私盐毫无疑义,“皆因顺清河、泗州关稽察委员得钱卖放”。自己于临淮上下设法严查,大帮私枭远在下游,已闻风远避,不敢闯过。但其余奸商夹私,有于定例每包110斤之外,捆至120余斤者,有旧票不缴,累年影射者,有于票内挖补年月者,“即官运委员亦无不公然带私”。此时若因自己不办盐务而稽察之设亦撤,“不惟无此政体,且扪心自问,亦断不忍出此”。若移交怡良照办,无论相距千余里,耳目难周,即精神亦恐难到。故他恳请明降谕旨,将盐船往来并一切售运提课,仍责成自己随时稽查,“俾得尽一分心,即收一分效”。至怡良专司盐政,自有办法,臣未便搀越,致有龃龉。且怡良主减引之说,自己主不减引之说,官商人等,“莫不以怡良为德而以臣为仇”。自揣才力,亦断不敢再担此任⑤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朝·财政类·盐务·咸丰四年八月十七日·左副都御史袁甲三折[Z].(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针对袁甲三所反映的情况,朝廷相当重视,下诏责令怡良彻底清查。朝廷还担心怡良有所顾忌,特意安慰他:“怡良到任后,总在苏常一带驻札,或因未曾亲历,误听其言,亦无所用其回护,著即拣派公正廉干司道大员,驰往淮北,逐一严切根究”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咸丰四年十月初九日[Z].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随即,怡良派署江安粮道赵德辙至常州,询问盐务情形,“该道并非盐务人员,委其查访,可期事事核实”②朱批奏折·财政类·盐务项·缺奏报时间·两江总督怡良折(胶片29,第1707-1708页)[Z].(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不过,可以想见的是,这样的调查不会有什么结果。果然,怡良不久即奏称,郭沛霖与许惇诗两人并未结拜师生,“无勾串影射情弊”,“无从侵渔”。当然,怡良也必须对袁甲三有所交待,故他表示,自己任官四十余年,于两淮盐务从未阅历,专采周谘,不敢稍存大意。袁甲三直节铮铮,自己素所敬慕,“奴才孑肩巨任,目睹时艰,万不敢稍存意气”③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朝·财政类·盐务·咸丰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两江总督怡良折[Z].(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在此争论过程之中,怡良调整了自己的就场抽税办法。在他看来,“今日欲恤灶艰计,惟便小贩,使盐可零售,庶几灶可资生,而欲便小贩计,惟轻税程,使有利可图,庶几招贩较易”。连日以来,自己与部属商量,拟请令各场一体设厂抽税,按盐百斤抽税钱300文,以240文作为报拨正税,以60文作为外销经费,“易引为斤,易银为钱”,无非体恤小贩。核计每百斤成本售价抽钱300文,尚觉其多,断难再为加重。虽然自己也知道,目前之抽税,不及正课之半,“未免过轻”,但当此万灶交困、人心惶惶之时,“势等倒悬,急何能择”?所有抽税之法,厂由场设,各贩于买盐时随时随缴钱,其盐计票不计引,以 100斤起票,拟由司造就大票给分司转发各场,随时填给票根,送司备查。一税之后,即全无税课。原来之向不食引之邻场七州县,因军饷紧急,百货抽厘之际,自应仍令一体抽税,事平即行停止。惟此等零星食盐,究与食岸有别,故拟令每斤抽税钱 1文,作为正税,抽钱半文作为外销经费,另给小票以示区别。当然,所有情况均须先行试办三个月再说。对此,户部表示,三百文较原来之2两1钱8分,不及十分之三,两淮综理鹾务,“并不通盘筹画,惟以核减税程为补救目前之策,似专为便贩恤灶计,并未能筹及裕课之法”。三个月之事,显系因抽税太少,预为诿卸地步。故他们命两淮仍必须每引征银2两1钱8分,即每百斤抽税银5钱4分5厘零,如商贩交纳现钱,仍以钱合银照该处时价核算,以符定章而裕课项④方濬颐.淮南盐法纪略:卷一·就场课税·试办就场抽税折[Z].刊本.淮南书局,1873(同治十二年).。
针对户部要求,怡良毫不退让,他表示课从盐出,盐有销路则课有来源。现在的局势如此,以前讨论过就场征课,以及绕道东坝出江,原冀可上达江广,但刚刚请定章程,而芜湖、安庆、九江相继失守,东坝以上江路仍是不通。旧商勉纳十余万两之课,却因道路未通而无法运盐,新贩惮于冒险,“更不肯认运”。二十场贫灶穷丁有盐无售,“其势岌岌不可终日”。是以酌量变通,议行设厂抽税之法,专为便小贩以恤灶起见,“原未敢议及裕课也”,且“照三百文抽纳,已属未见踊跃”,如今试办将届二月,据各场卡折报税钱一万数千余串,而岸盐税钱仅居其三,是办理毫无把握之明证,“若更议加征,窃恐有名无实”。考虑到不能借道,又要加税,而灶户人等,“平时愍不畏法,值此多事之时,而又为饥所驱,任意透私,屡拿不缉,设竟绝其生路,惨切激变,害何可言”,故仍只能保持 300文之数不变。“淮南盐课为拨解大宗,当此军需浩繁、经费支绌之时,筹课宜在所先。”鉴于怡良的强烈反对,户部只得暂时表示同意⑤方濬颐.淮南盐法纪略:卷一·就场课税·东坝出江岸盐仍照原奏数目就场抽税折[Z].刊本.淮南书局,1873(同治十二年).。
咸丰七年,怡良因病辞归,他的改革就此停止。随着曾国藩等军事将领控制两江地区的实权,以盐济饷这一能够缓解地方军需压力的办法,顺理成章地推行开来。怡良所担心的以盐济饷的种种弊端,则无不成为事实①倪玉平.博弈与均衡:清代两淮盐政改革[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综上所言,怡良在任期间针对国内形势,在两淮地区所推行的盐政改革政策包括就场征课和抵制以盐济饷。所谓“就场征课”,是怡良在当时被动的情况下采取的变通办法,即在淮南20盐场设征盐场所“厂”,商贩自行到灶户处采买食盐,然后到“厂”纳课,自行运销。究其实质,怡良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照顾灶丁,即通过降低成本,吸引小贩运盐,其中的易引为斤及易银为钱,都是出于这一目的。至于随后的坚决反对“以盐济饷”办法,怡良的出发点又在于稳定社会,安定社会,并确保税源掌控在自己手中。
怡良任职期间盐政改革的成效,并无详细统计,这里仅就他离职时留给后任者的成绩单来透视其效果。从咸丰七年四月二十日开栈起至六月初五日,两淮盐区收正税银9220两7钱7分,合钱18441千540文,又收正税钱5587千440文,银钱并计合24028千980文,尚还有未运到之盐若干,综计试行二月有余,已经有 34000余串,较上年通、泰两属一年所收之税,“尚属有盈无绌”,征课大有起色②方濬颐.淮南盐法纪略:卷一·就场课税·泰栈章程详[Z].刊本.淮南书局,1873(同治十二年).。
在清代的两淮盐业史上,相较于陶澍、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大张旗鼓的改革而言,虽然怡良显得较为默默无闻,但他在任期间所推行的这些措施,在客观上却为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改革做好了必要的铺垫。在研究清代两淮盐政改革的历史过程中,怡良这一环节,也理应不能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