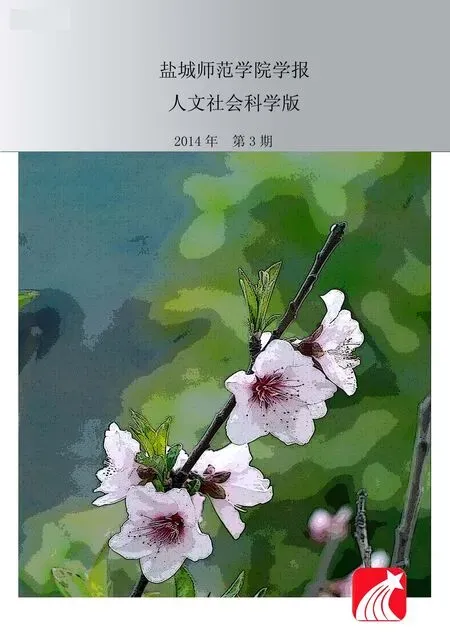“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课程的历史沿革与现实境遇*
郑 艳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116029)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是一门以语文课程与教学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它是教育学下属的二级学科课程与教学论的一个研究方向。作为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重要的并充分体现其专业特色的核心主干课程,它揭示了语文课程与教学规律,引导学生认识语文课程与教学现象,并指导语文课程与教学实践。换句话说,它将告诉学生怎样学做语文教师,如何上好语文课。该门课程的建设与实施的质量,将直接影响学生走向工作岗位之后的教学能力及素质,同时也将深刻而持续地影响他们的教师专业发展之路。
这门课程在不同的师范院校,不同的老师、学生,甚至专家学者口中的名称存在着差异。有的称“语文教学法”,有的称“学科教学论”,有的称“教材教法”,那这门课程到底该叫什么?这门课程的发展历史是怎么样的?在当下这门课程的现状又如何?笔者试在本文中加以梳理。
一、“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课程的发展历史
从世界范围来说,这门学科发端于瑞士教育学家裴斯泰洛齐,他研究的主要方向在“要素教育”的思想,这种思想又具体体现在初等教育理论和实践方面。在裴斯泰洛齐的主张和建议之下,1800年瑞士政府设立了一所公立初等学校。学校内单独开设师范训练班,设置国语教学法、算数教学法、地理教学法等各科教学法课程。这就是近代初等教育各科教学法的萌芽,裴斯泰洛齐因此在教育发展史上被称为“初等教育各科教学法的奠基人”,赢得了“各科教学法之父”的美誉。
我国的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是随着语文学科的兴起,随着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孕育成长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语文的学习是与政治、伦理、道德融为一体的,由于没有独立设科,所以也就没有独立的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古代教育史,就是一部中国语文教育史。所以语文教育的思想可以从古代的如《论语》《学记》《朱子读书法》《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读书作文谱》等论述中找到源头。如《学记》中的“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也其听语乎。力不能问,然后语之。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1];如朱熹的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等。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研究依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到了近代,语文开始独立设科,对语文学科的教学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至今已逾百年。随着这门学科名称的不断变化更替,它也一路在起伏中成长起来。
(一)国文教授法时期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清津海关道、大理寺少卿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特设“师范院”,在师范院首开“教授法”,讲授“各科教授之次序法则”,使用翻译过来的日本人著的《统合教授法》作为教材。同年在盛宣怀的大力支持下,钟天纬在上海创办的“三等公学”(与盛宣怀办的南洋公学的头等、二等学堂相衔接),这所学堂不仅教育内容新,而且使用新的教学法;1898年,他亲自编写了十二册的教材《读书乐》和《教授心术》,《教授心术》可算是早期的讲述语文教育心理学的著作。
1902年,钦定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开设“教育学”课程,该门课程中有关于“各科教授法”的具体论述,在“各科教授法”中我们可以找到“国文教授法”的内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语文课程与教学研究最初是归属于教育学的,并且属于教育学体系中的一个极小的部分。
1903年1月13日(清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清政府又颁布了由张之洞、张百熙、荣禄合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这就是“癸卯学制”,也是我国第一个由政府正式颁布、在全国范围实际推行的学制。其中规定,在初级和优级师范学堂分别开设“教授法”和“各科教授法”。
1913年,《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依然将“教授法”列为必修科目。但是,由于当时教师不够重视,普及程度并不好,效果也不甚理想。
(二)国文教学法时期
从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国的陶行知先生,1918年在任南京高师教务主任期间,提出改革旧的教学方法,1919年2月发表了《教学合一》一文。在文章中陶行知先生对传统教学法“重教太过”“教学分离”的弊端进行了批判,并由此提出了“教学合一”的观点。陶行知认为:“先生的责任在教学生学;先生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先生须一面教一面学。但他的这种观点并没有被及时采纳。”他自言:“自回国以后,看见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有改革之必要。这种情形以大学为最坏。导师叫做教授,大家以被称教授为荣。他的方法叫教授法,他好像拿知识来赈济人的。我当时主张以教学法代替教授法,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会议席上辩论二小时不能通过,我也因此不接受教育专修科主任名义。”[2]尽管这个提议在当时曾遭校方拒绝,但是,在陶行知先生的一再坚持与倡导之下,有识之士纷纷响应,“各科教学法”的名称由此诞生。
1922年11月教育部公布的《学校系统改革令》,又称“壬戌学制”或“新学制”。其中规定,在中等师范分设2学分的“普通教学法”、6学分的“各科教学法”和6学分的“小学各科教材研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科教学法比普通教学法更受关注。这也标志着学科教学开始走向研究之路。此时,一批专门研究语文教学的论著开始产生。1922年,梁启超发表《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该书被称为“我国最早研究中学语文教学法的开山之作”,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教学法》为现代汉语教学提供了很多可资借鉴的方法,成为“我国第一部以教科书形式写成的语文教学理论专著”。此外,还有周铭三、冯顺伯于1926年合著的《中学国语教学法》,王森然于1927年出版的《中学国文教学概要》等。
(三)国文教材教法时期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本学科的研究领域中开始关注教材的研究。1939年教育部颁布的《师范学院分系必修及选修科目表施行要点》规定,各系都要开设“分科教材及教法研究”课,于是“国文教材研究”和“国文教法研究”并列为师范院校中文系(科)的教学和研究的重要内容。
1946年教育部颁布的《修正师范学院规程》进一步规定,分科教材教法研究是专业训练项目,在第四学年开设。内容分课程标准研究、教材选择、课程组织、教具设置、教学研究、教科书批评及应用等部分,还列举了一些研究方法,诸如讲授法、阅读法、参观法等。彼时,一批学科专著相继出版发行,如1936年阮真著《中学国文教学法》、1936年袁哲编《国语读法教学原论》、1941年蒋伯潜编《中学国文教学法》、1945年朱自清、叶绍钧编《国文教学》等。一些专家学者开始有意识地研究国文教材教法了。
(四)语文教材教法时期
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在选用中小学课本时,采纳叶圣陶的建议,不再用“国文”和“国语”两个名称,一律称为“语文”。1952年,《师范学院教学计划(草案)》规定中文系开设“中国语文教学法”和“文学教学法”两门教学法课程。此后随着语文分科教学的终止,两门教学法课程随即相应合并为“中学语文教学法”一门课。1963年《高等师范学院教学计划(草案)》规定,将此学科称为“中学语文教材教法”。
此后的十年“文革”期间,语文教学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就更不要说所谓的语文教材教法的研究了。
(五)“语文教学法”和“语文教材教法”并存期
1978年,教育部委托武汉师院等12所院校编写统一的高师院校中文系(科)语文教学法教材——《中学语文教学法》(1980年4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个时期语文教学法的内涵有所扩大,除了基本技能操作层面的方法之外,还包括一些原理、法则、规律等,在理论研究上有了一定的高度。与此同时,由张隆华先生牵头组织湖南省高师院校语文教学法教师编写的同名教材《中学语文教学法》,于1980年3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至此,各高师院校开设课程、编写教材大都使用“中学语文教学法”这个名称。
1981年4月,《高等师范院校四年制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公布,本门课程定名为“中学语文教材教法”。于是,出现了“中学语文教学法”和“中学语文教材教法”一门课程两个名称并存的局面。
1981—1987年,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专业目录中,一级学科“教育学”下设“教材教法研究”这个二级学科。“语文教学法”或称“语文教材教法”便是其中的一个研究方向。
(六)语文教学论时期
1983年,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召开第二届博士、硕士授权点学科评议组会议期间,顾明远先生建议“把教材教法的硕士授权点拿到教育学组来评议,并把名称改为‘学科教学论’,以提高对它的学术要求,从而提高它的学术地位”[3]。
1986年8月,北京师范学院(现名首都师范大学)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了《关于变更授予硕士学位学科、专业目录中“教材教法研究”专业名称的请示报告》,建议将“教材教法研究”更名为“学科教育学”。同年12月12日,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同志在全国高师师资培训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不但要建立自己的教育学,还要建立自己的学科教育学。这方面工作是大量的,有广阔的天地,大有可为。如果要讲学术性,师范教育的学术性的特点,就在这里。研究如何使人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科学,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门科学,也是学术性很高的一门科学。我们在这方面下的功夫还远远不够。”这段话,给学科教育学的建设工作以极大的鼓舞,也进一步明确了该门学科的理论与实践统一的特点。
198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文将教育学下属的二级学科“教材教法研究”更名为“学科教学论”。于是,以语文这一学科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便改称“语文教学论”。
(七)语文教育学时期
各学科的教学法研究蓬勃开展始于1989年,各个学科几乎年年都要召开自己的教育教学研讨会,无论是规模、人数,还是议题都不断扩大和发展。虽然1987年,国务院学位文件将本学科更名为“学科教育论”,但一些专家学者似乎更倾向于“语文教育学”的提法,很多以《语文教育学》命名的教材陆续出版。语文学科的研究也开始从以知识和能力的研究发展到以学生的发展为本的研究。语文教学法是以语文教学过程为研究对象,以探索语文教学过程的规律和准则为研究任务。而“语文教育学”则以针对语文学科的特点,研究语文学科的教育规律为已任,由语文学科教学法所侧重的具体“法”和“论”,转变成具有系统理论与完整结构的学生的“学”,更加深刻地揭示了语文学科与教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寻求语文学与教育学在教育过程中的最佳结合与统一,是对语文教育进行更全面更科学的研究的理论体系。
(八)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时期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于1997年6月颁发《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在这次目录调整中,我们发现其对二级学科进行了大规模的合并,将“教学论”和“学科教学论”两个二级学科调整合并为“课程与教学论”一个二级学科。所谓课程与教学论,是既包括课程又包括教学的双重理论。虽然两者在研究内容上各有侧重,但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叉与融合,具有很多的共通性。这次调整将“课程与教学论”作为教育学这个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而各学科的课程与教学论便作为课程与教学论这个学科下的一个研究方向而存在,各学科的教育、教学研究类课程都据此定名,于是便有了今天我们师范类院校的本科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课程,和研究生的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专业。
近年来,本学科的研究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深入,一些大学专家、学者,中小学一线语文教师投身到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研究之中。他们或关注课程,或关注教学,或关注教材,或关注学生,或进行更加细化的研究,如阅读教学、口语交际教学、写作教学、教学规范、教学艺术或教学模式等等。与其相关的研究著作非常之多,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均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二、“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定位
“名不正则言不顺”,名称反映的是导向与定位。课程与教学论走到今天几经易名,正是反应了这一学科坎坷的发展历程。由此,我们可对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学科加以简单定位。
(1)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依附于教育学,至今仍然是教育学这个一级学科下属的分支——课程与教学论的一个研究方向。
(2)虽然它归属于教育学,但却无法单独用教育学的理论来解释它,它是教育学,却又不是研究一般教育现象和规律的教育学。它是依托于语文学科的教育学,是涵盖了哲学、史学、美学、文学、语言学、文化学、解释学等多学科的一个交叉性的综合性的学科。
(3)这门学科既要高度重视其理论建构,也要密切关注语文课程教学实践;它既要有先进的坚实的理论作为基础,也要有鲜明的可操作的实践性特点。所以说,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理论学科,理论上的综合性和实践上的应用性是其必不可分的两个基本特征。
(4)它是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所独有的,是最能体现师范院校教师教育特色的一个标志性的学科专业。
三、“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现实境遇
(一)地位尴尬,日渐式微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世纪之交,我国的“师范教育”改称为“教师教育”,从表面上看来内涵更为丰富,更能适应当今世界科技知识的更新加速和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体现与时俱进的时代特点,“但实质上师范教育日渐式微,随着‘三级师范’向‘一级师范’的逐步演进,随着绝大多数师范专科学校升格为地方性的综合性本科学院,随着各地各本专科师范院校非师范专业的蓬勃兴起,过去所谓的‘师范性’不说荡然无存,也是所剩无几”[4],许多师范院校增加适应社会需要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应用性学科,使自己向着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发展。从我国省属以上师范院校来看,越来越淡化“师范性”与“非师范”性的界限,很多师范大学师范专业的招生数量已连年下降。
随着师范教育的式微,作为其标志性课程的课程与教学论也越来越不被重视,并且本门课程是界于语文学和教育学的边缘性学科,很难摆脱尴尬地位。有些师范大学将全校课程与教学论教师进行整合,统一归属教育学专业,这样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就是其教育学下属的课程与教学论这个二级学科中的一个小小分支而已;有些师范大学将其挂靠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但其教育学的性质又决定了它在汉语言文学领域中处于不被重视的边缘地位。
(二)师资薄弱,亟待加强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课程的教师一般由以下三种人员担任:其一是由教育学院的课程与教学论专业教师担任,这类教师对课程与教学论的理论掌握得深入、透彻,但当涉及到语文学科的教学知识、教学经验时,往往很难应对,缺少学科背景的他们在具体的课例及学科专业知识上往往显得捉襟见肘;其二是由汉语言文学的专业教师担任,这类教师对汉语言文学的专业功底扎实,对具体教学内容有深入理解和把握,但在课程与教学论知识的掌握与运用方面缺口较大,往往是满腹经纶,但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其三是由来自中小学一线的优秀教师担任,这些教师有着一线教师丰富的教学经验,可以把很多新鲜的信息带到课堂上,但大学和中小学的课堂毕竟是不同的,他们在讲授课程时习惯于用实践代替理论,对教学案例的分析容易流于肤浅,缺乏理论层面的提升。这样就很难找到既有教育理论高度,又有学科专业背景的优良师资。现阶段国内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博士点一共才六个,其培养的博士生数量很少,难以满足各级各类师范院校的师资需求。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显得薄弱,亟待加强。
(三)理论性创建与实践性探索的结合不够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它的理论是一种应用性的理论,这种理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被证实,才有意义。
从现有的高师院校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课程来看,教师过于强调课程体系的逻辑性、理论知识的学术性,以及教学规律与原则的完整性,在概念、术语上做足了文章,从而使课程变得封闭、枯燥,远离语文教学实践和真实的一线课堂,学生对这样的课程失去了兴趣。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重理论轻实践的现实也很严重,有的时候表现为理论与实践相脱节,重统一要求而忽视个性发展。学生缺乏参与的热情,其教学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得不到很好的培养。用这种方式教出来的学生,将来做了语文教师其思想也必定是僵化的、缺少趣味的,他们可能会按照相关的理论做一个看起来中规中矩的教书匠,但却很难成为教育的思想者,更别提成为教育的研究者和充满智慧的语文教师了。
(四)重视技能的训练而忽视原动力的唤醒
从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课程的实施过程来看,过于强调师范生基本从师技能的培养与训练,以及外在形象的打磨与塑造。这也固然是学生从师很重要的基础,但这却忽视了师范生们作为从教主体的原动力的激发与唤醒。学生可能是具备了听、说、读、写的能力,但是却淡化了他们主动获取知识的兴趣和愿望,很少有学生真正理解语文教师这个职业所带给他们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决定一个教师未来能走多远的,是他的职业理想和信念。这样的学生将来做了教师,会缺少主动性和自觉性,容易产生职业倦怠,就更不要提什么专业发展了。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出路何在?又该走向何方?周庆元先生曾经说过,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发展方向是难以逆料的。三种可能都有。第一,保持现状,不紧不慢,半死不活地继续生存与发展下去;第二,继续衰微,走向消亡,湮灭在“物竞天择”的学科发展生态之中;第三,后发赶超,振兴雄起,在21世纪教育与学科的改革与裂变中浴火重生,走向强大[5]。作为一名多年从事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教学与研究的工作者,希望与有识之士一起努力,不断地加强语文课程与教学研究,迎来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发展的又一个辉煌。
[1]潜苗金,译注.学记[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32.
[2]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2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41-42.
[3]顾明远.学科现代教育理论书系[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1.
[4]韦志成.现代阅读教学论[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3.
[5]周庆元.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博导笔谈[J].语文建设,2009(2):8.
——《教育学原理研究》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