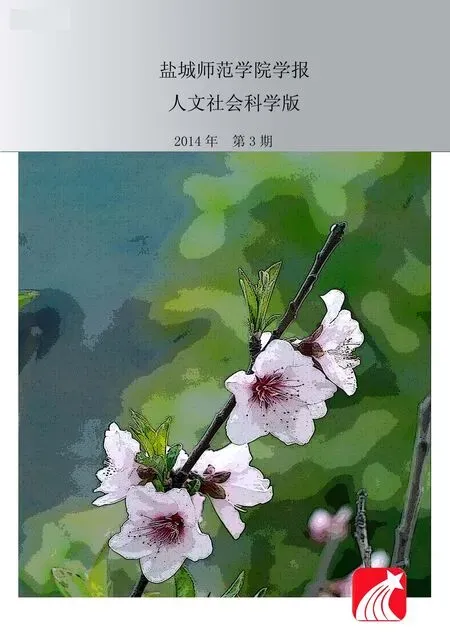论鲁敏小说中的“孤独”与“喧嚣”
——以《零房租》与《隐居图》为例*
李 贤
(蚌埠学院 文学与教育系,安徽 蚌埠 233030)
一
关注鲁敏的小说很久了,从第一次读她的作品《寻找李麦》开始,在新世纪文学的呼喊中,在2001年第2期的《小说家》中,看到那时还属文坛新人的鲁敏有些与众不同,从此留意她的每一篇新作。十几年来,在“文学已死”或“向死而生”的各种议论中,她坚持自己的写作方式,成就百余万字的小说创作。或许目前的她还不适合写长篇,《戒指》、《爱战无赢》、《六人晚餐》三部长篇的创作似乎不及她的一系列中短篇更让人难以忘记。从鲁敏有些成名作《白围脖》开始,她不断地为我们带来期望和惊喜。《转瞬即逝》的青涩已经远去,恰到好处的叙述情感,顺手拈来的故事情节,不拘一格的语言风格,如温润的玉,如新春的龙井茶,耐人寻味。她的创作题材大致可分为“乡村”与“都市”两大类,前者寄托了作家心目中温柔敦厚的乡土情怀,后者则承载了作家对人性的观察与批判,这一点与沈从文很相似。庄重文学奖给鲁敏的获奖评语是:在她的东坝系列小说中,她对人性之善、对一种温暖诚挚的生活作出了大胆的、颇具说服力的书写,而在《取景器》、《博情书》等另一系列小说中,她对喧嚣浮世中的幽微经验和零散的、难以确认的价值,作了富于想象力的表达。笔者从她近期的都市系列作品《零房租》与《隐居图》中来谈一谈她小说中的“孤独”与“喧嚣”。
孤独是一种情感状态,也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母题。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孤独感是一种封闭心理的反映,是感到自身和外界隔绝或受到外界排斥所产生出来的孤伶苦闷的情感,时间久了会产生消极负面的影响。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创作主体还是创作客体,孤独似乎都是一种难以摆脱与言说的情绪。没有孤独或许就难以进行创作,没有创作,孤独的情感或许就难以释怀,“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心绪非亲临其境者不可体会。也时常听到感叹:拥有强大的内心世界的人才能享受孤独。心理学上的“孤独”是一个客观的词,文学中的“孤独”则是一种奇妙的情感,在不同文体的创作中演绎着多面的生活。《零房租》与《隐居图》两篇小说则诠释了都市人的“孤独”,是喧嚣之中的孤独,是隐性的。
二
《零房租》这篇小说叙述的是一个失去孩子和老伴的孤独老人与一个毕业不久的大学生的故事。许小雅因为爱情的背叛而迁怒于自己的工作,为了了断曾经的爱情,她也辞去了她的工作,当然也离开了她和男友杆子共同的小屋。在她生活的城市,离开了那间房子她就暂时地无处可去。可不离开,自尊心又强迫着她那样做。走在人来人往的街头,没有一个可以听她说话的人,报喜不报忧的她更不可能向家乡的亲人倾诉自己的委曲。在她拖着拉杆箱流浪公园36小时倚靠着公告栏歇口气的时候,发现了“零房租”的广告。条件是:“黑头发,单身女性。”真是巧合,小雅因为没钱染头发而保持本色,又因为杆子的背叛而成为单身女性。这一系列的不如意又让小雅在内心深处期待冒险。“当事情恶劣到某个地步,反而像红布一样,会挑动起一股无谓的受虐般的武莽。”[1]
鲁敏像抖包袱一样,先写零房租的房客,这个房客是我们身边常见的,也是媒体所关注的,“漂”在异乡的大学毕业生。小雅是其中的一员,或者说是属于混得不太好的那一类。但她的心境可以看做是她们的缩影。城市、爱情、工作,看上去都很美好,融入自己的生活却很难。于是对于刚走出校园的她们来说,很容易就被自己的情绪打败了。点睛之笔写出了这一群人的生活状态。
我们通过许小雅的眼睛认识了房东胡文伦,一个初看上去很怪异的老人。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我们会感到他的辛酸。他的独生儿子在大学二年级那年因车祸去世,他家的一切摆设都保持着孩子在时的样子,就连日历也永远定格在儿子走的那一天,未曾更新过。他的老伴熬不过,先他而去了。胡文伦想象着儿子在国外安居,想象着儿子在西昌做科研,想象着和儿子说话,每周日都要穿一次儿子的校服。儿子用过的物品不允许别人碰,要找个“黑头发,单身女性”的房客,仅仅是因为儿子小的时候趴在他耳边说的悄悄话。读到这里,谜底也一步步揭开。辛酸的父爱,难言的伤痛,静静的叙述隐藏着最深的凄凉。老人的一切看上去不太正常的行为只源于爱,内心的痛苦与思念无法说出,在一个人的世界中将难忍的孤独转化为无条件的爱。“零房租”的出现实际上是在双方都很无奈的条件下达成的协议。
房客失去的是一份真心付出的爱情,她想以死来结束看上去很惨淡的人生。房东失去的是亲情,是唯一的孩子,是生命中不能再重来的,他以自己的方式为儿子“活着”。相比较而言,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他们之间的不同太多,但唯一相通的是孤独感以及想要摆脱孤独感的努力。不论是外界环境的变化还是内心世界的苍凉所致,孤独感的存在让这份看上去不合理的租房协议变得合情了。不得不承认,鲁敏很善于讲故事,一个伏笔又一个伏笔地吸引着读者。就在谜底揭开后,又出现了“药”,这个药到底是什么?是一张写有“宝贝”两个字的纸。不知道这是胡文伦对小雅的善意谎言,还是另一位父亲老谭的良苦用心。不管怎样,都是一份绝望之中的孤独升华出的无私的爱。胡文伦在拯救自己的同时也给了小雅生活的力量。心理学家认为:情绪情感成分是人际交往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人际交往中的情绪情感障碍常常诱发人际孤独,从而避开与人交往的情境,封闭自我。胡文伦的不愿与人交往是不想触动心底的痛,小雅感觉的绝望与孤独一方面是环境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心理承受力的脆弱。他们的孤独感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生理因素所致,“我们都是没有了宝贝的人”[1],这样的心酸小雅不一定真的能够理解,后来两个人分着吞下了“半片药”。这药能治好他们的“病”吗?有一点是肯定的,胡文伦将对儿子的关心与爱护转移到小雅的身上,让她学会爱自己。
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失去“宝贝”的沮丧或隐痛,时间带来沧桑带不走铭记在心的记忆,记忆有时如毒药,任你怎么努力,都没有解药。也许人与人之间根本就没有相通的心路,总是那么不多不少地离合着。敏感的心会因为自尊而自重,善感的灵魂会因为清醒而痛苦。马克思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将我们每一个人都置于千丝万缕联系的群体中,萨特的“他人就是地狱”则让我们变成无处可逃的个体,在“社会关系的总和”中看别人的精彩,在内心深处孤独着自己的孤独。鲁敏在这个中篇里表达了一个普遍的哲理。与之相联系是内容的丰富性,“失独”家庭与“失业”的毕业生等当下的热点,爱情的忠贞与背叛,独生子女的脆弱心理,人与人之间善意的谎言,等等,很接地气,也很热闹的都市生活。也正因为如此,才令人感受到喧嚣之下的孤独是如此的难捱。也许小雅和胡文伦算不上典型人物,但是通过这两个形象我们可以对这两个群体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三
再来看看《隐居图》,隐向何处?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是看破红尘的潜心还是无可奈何的不甘?故事的情节比较寻常:十多年未见的初恋情人再相见,以男女主人公内心情绪的变化推动情节的发展,在艺术风格上有点意识流的味道。准确地说,隐居者是孟楼,之所以想隐居是因为舒宁。
按照当下的观点,他是一个不算成功的男人,也是一个富有理想主义情结的人。当初学的专业是信息物理,毕业后费尽力气找到了和兴趣相吻合的工作——市话剧团。在“不谙世事的年轻野心里,艺术永远理直气壮”[2]。丁西林以物理学家的视觉写喜剧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孟楼演话剧则没那么幸运了。为梦想而奋斗的壮志在现实生活面前是那么的不堪,心爱的初恋女友因为他的选择而分手,婚后的妻子也因他的选择而离婚,自己为之付出的舞台也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散了架。原本可以留在省城的,他不愿玷污艺术的尊严,不愿为梦想而降低自己的标准。是坚持到底的理想主义还是性格本身的清高呢?到小县城的文化馆工作,他的内心不是没有波澜。当前女友出现时,他不愿意和她相认,故意让自己以一个“谦卑者”的形象出现,甚至明知道她给了他名片也假装不知道。这一切源于他混得不如她,他的骨气助长了他的孤独,好像也只有“超脱”与“我行我素”才能让他对抗舒宁优越的生活状态。从女学生舒宁到文化投资公司老总舒宁,她已经看到两人的不同。女性的微妙心理使然,她渴望孟楼能先和她说话,毕竟她不止一次地设计过与他重逢时的场景。于是,一个想“隐居”,一个想“引出”,最终是一个拥抱结束了这次意外的重逢,想再叙旧已无时间。明明是嘈杂的市井生活,觥筹交错的宴席,年少轻狂的追梦人,衣香丽影的初恋情人,突然之间,就已是昨日的梦,追梦人的失落在初恋情人的光芒之下该有多不甘。越是假装淡然越是不能淡然,相见不如怀念呀,他的生活的表现有多热闹他清醒的内心就有多孤独,他的性格有多清高,他的隐居就有多无奈。这喧嚣下的孤独怎能说出口呢?
四
相比较而言,中短篇小说要想写出深度还是有难度的。它不能像长篇小说那样可以容纳更多的生活,它只是截取生活的一面或一段,但这并不意味中短篇小说的社会价值会降低。在巍峨灿烂的巨大的纪念碑底的文学之旁,短篇小说也依然有着存在的充足的权利,不但巨细高低,相依为命,也譬如身入大伽蓝中,但见全体非常宏丽,眩人眼睛,令观者心神飞越,而细看一雕阑一画础,虽然细小,所得却更为分明,再以此推及全体,感受遂愈加切实,因此那些终于为人所注重了[3]。新世纪以来,有不少作家没有写中短篇的经历而直接写长篇并一举成名,之后再也不见佳作。作为一个年轻的作家,有了十多年创作经历的鲁敏能够执着于中短篇的小说创作,是需要定力的。我们这一代的写作背景,与20世纪80年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常听有同行感叹身不逢时、错过高峰,但我却另有乐观之见。现在这样的时代,当可视作最为有效的过滤器和试金石,混文学的、以文学取名声、以文学求利益,皆可休矣[4]。不是把文学当成名利的工具,而是让生活引领文学。不玩文字游戏,也不追求形式的新奇,是一种认真的写,始终给读者一种可以期待的感觉。小说中的情节以及叙述语言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叙述者的情感像文中的主人公一样有节制,是波澜不惊那种,偶尔的缠绵悱恻也能化作惊鸿一瞥。这应该是她的写作观念所致:她探究人性的多重性,对人性始终保持续尊重与理解的态度,追求向善的品格,在审美观念上是浪漫的也是古典的,不忍心让笔下的人物走上绝境,孤独者能够被拯救,失意者能够有安慰,生活也许是不如人意,但终归有一些希望温暖着喧嚣之中的孤独者。她的文字有着新写实小说的影子,但绝不是新写实。她小说的题材不一定新颖,但叙述的视觉一定是独到的;语言不一定精致,但读起来从容自然;情节不一定惊心动魄,但一定是荡气回肠的。以行云流水般的情感与句子叙述着生活的家长里短,不断破解人生的谜语。
【参考文献】
[1] 鲁敏.零房租[J].小说月报:原创版,2013(7):6-17.
[2] 鲁敏.隐居图[J].大家,2013(2):85-98.
[3] 鲁迅全集:第四卷[M]//三闲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31.
[4] 鲁敏.鲁敏谈《伴宴》艺术的自由与桎梏[N].人民日报,2011-05-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