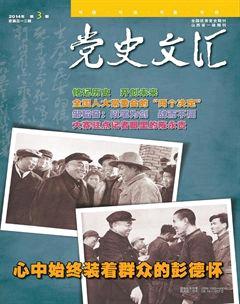邹韬奋:以笔为剑 战而不屈
刘火雄
1926年10月,邹韬奋以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的身份,接办了职教社的机关刊物《生活》周刊。此后,从《生活》到《大众生活》《生活日报》,从《生活星期刊》《抗战》到《全民抗战》,包括开办生活书店,邹韬奋一刊被停,一刊(报、书店)继起,为宣传抗战、团结御辱和争取言论自由、民主政治鼓与呼,在中国近代编辑出版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毛泽东曾说过:“我们干革命有两支队伍,武的是八路军,文的是邹韬奋在上海办刊物,开书店。”
揭露交通部长王伯群穷奢极欲
最初,《生活》周刊内容多集中与青年职业和教育相关领域,发行量只有两千多份,且以赠送为主。邹韬奋接手后,从加强刊物的趣味性入手,“多登新颖有趣之文字”,如撰写“小言论”,编译国外报刊新知趣闻,刊发海外通讯员报道等,文风活泼,可读性强。这一系列举措很快打开了局面,两三年后销数增到4万份以上,5年后发行量达到创纪录的15.5万份,与全国性日报《申报》的发行量旗鼓相当,其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
1931年6月,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交通部长等职的上海大厦大学校长王伯群与本校毕业生保志宁结婚,建造“金屋”,极尽奢华。消息传出,有人讥讽王伯群“位尊多金”,有读者特意写信给《生活》周刊,要求调查并揭露王伯群的“丑行”。
邹韬奋获悉后,基于愤慨,一面将读者来信刊登,一面展开调查,以便弄清事实真相。原来,王伯群所建“金屋”由辛丰记营造厂造就,后者正承建南京交通部办公楼及大厦大学教学楼建设工程。为了讨好交通部长王伯群,造价不下50万元的别墅,最终只收取王伯群约20万元费用即交付使用,有变相贿赂之嫌。
王伯群得知邹韬奋的行动后,害怕丑闻被曝光,于是派人携带10万元前往,企图以此封住《生活》周刊之口。邹韬奋不为利益所惑:“《生活》是一个自力更生的刊物,经费多有困难,但是不受任何方面的津贴,一个小刊物也用不着偌大的巨款。”来人并不死心,接着提出把这笔现金折合股本,作为投资基金。对此,邹韬奋以不符合公司章程为由再度拒绝,并严正相告:“王部长既然这样慷慨,不如替他捐助给仁济堂(当时上海的水灾救济机关——笔者),救救几百万嗷嗷待哺的灾民吧,何奈关心我一人之生活!”来人只得悻悻而退。
没几天,邹韬奋接到匿名信,“警告”他要“小心”。邹韬奋则表示:“我的态度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服的。”他在随后出版的《生活》“信箱”栏目上,刊发了署名陈淡泉的《对王保(君)应作进一步的批评》一文,并配有记者亲往王伯群“金屋”实地拍摄的照片5幅。在《编者附言》中,邹韬奋发表言论,将王伯群痛斥一番:“在民穷财尽的中国,一人的衣食住行四种需要中之一种而且一处,已达四五十万圆,而王君信里犹说‘伯群素尚俭约,虽备员中央数载,自顾实无此多金,我们不知‘多金果作何解?‘俭约又作何解?”王伯群“个人的穷奢纵欲,实为国民的罪人”。“在做贼心虚而自已丧尽人格者,诚有以为只须出几个臭钱,便可无人不入其彀中,以为天下都是要钱不要脸的没有骨气的人,但是钱的效用亦有时而穷……”
迫于舆论压力,不久,有监察委员提出弹劾案,至1931年底,王伯群被迫辞职。只是凭借何应钦这座靠山,他才得以保留国府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头衔。时人戏称王伯群是“娶了一个美女,造了一幢豪宅,丢了一个官职”。王伯群所建“金屋”,后来也被汪精卫等人占有,由“王公馆”变成了“汪公馆”。
创办生活书店,不接受胡宗南游说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进犯沈阳,外敌入侵,国事日蹙。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写道,本周要闻“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记者忍痛执笔记述,盖不自知是血是泪”。《生活》周刊的编辑方针此后相应调整,从“有价值、有趣味的周刊”逐步“成为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据胡愈之回忆:九一八事变之后,“《生活》周刊逐渐改变了方向,关心和议论起国家民族的大事,使刊物和全国人民反蒋抗日的愿望一致起来,刊物更受到读者的欢迎”。
国难当头,国民党当局却宣称“攘外必先安内”。邹韬奋再次严正声明:“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对于暴日的武力侵略,除了抵御之外,不能再有第二个主张。”1932年春,蒋介石派胡宗南到上海,约邹韬奋晤谈。“胡宗南极力为蒋介石游说,软硬兼施,试图拉拢韬奋,改变政治立场,逼韬奋表态拥护蒋介石……韬奋坦率地回答胡宗南,只要政府公开抗日,便一定拥护,在政府公开抗日之前,便没有办法拥护”。邹韬奋还强调:“这是民意,违反了这种民意,《生活》周刊便站不住,对于‘政府也没有什么帮助。”
胡宗南无功而返,前脚刚离开上海,蒋介石又密电发出新指示:在江西、湖北、河南和安徽四省查禁《生活》周刊。此外,蒋介石不惜亲自出面,直接对《生活》周刊主办单位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黄炎培等施压。在“召见”中,蒋介石要求黄炎培责令邹韬奋改变《生活》周刊的政治立场。
两难之际,邹韬奋、黄炎培均不愿职教社卷入政治漩涡。经过权衡,邹韬奋决定“应力倡舍己为群的意志与精神,拟自己独立把《生活》周刊办下去”,自主经营。这一提议获得职教社方面同意。对于编辑出版言论自由,邹韬奋接连在刊物上撰文:“倘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无法维持,那末生不如死,不如听其关门大吉,无丝毫保全的价值,在记者亦不再作丝毫的留恋。”
《生活》周刊虽然独立了,但树大招风。在胡愈之建议下,1932年7月,邹韬奋创办了生活书店,拓展其图书杂志出版、发行业务。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生活书店堪称后起之秀,其在全国各大中城市设立了56处分店,规模一度超过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老品牌。期间,生活书店出版了《文学》《笔谈》《世界知识》《生活教育》《妇女生活》等约10种刊物,图书近千种,为一般民众编行的《战时读本》和《大众读物》,发行量均超过百万册。全面抗战后,生活书店抓住国共联合抗战的有利时机,先后出版了《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数十种著作,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精神食粮。然而,生活书店被查禁的图书同样多达200多种,包括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作品。
后来成为文学家的端木蕻良曾与邹韬奋有过交往,据他在《生活的火花》一文中回忆,两人在聊天中谈及生活书店为什么会不断发展壮大,邹韬奋戏称“这得感谢国民党了”。“我们才出几期,他就要我们停刊。但是,广大读者是支持我们的,一订就是一年。这样,生活书店就越来越大了。所以,生活书店应该是属于人民的!”
八年从不脱期的《生活》周刊被封了
1933年1月,邹韬奋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执行委员。邹韬奋的爱国民主言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仇视和忌恨,邹韬奋的《生活》周刊遭遇的迫害接踵而至。6月,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卓越的领导之一杨杏佛,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消息传来,鲁迅以悲愤心情写下诗句:“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邹韬奋也名列黑名单,被迫于这年秋天出国考察,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流亡生活。
邹韬奋出走并未改变生活书店被查封的命运。1933年12月初,国民党政府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罪名下令封闭《生活》周刊。8年从不脱期的《生活》周刊,编辑出版至八卷五十期停刊。
邹韬奋出国之前已预料到《生活》周刊有可能被查封。最后一期《生活》周刊发表了他早在一年多前就准备好的《与读者诸君告别》一文:“记者所始终认为绝对不容侵犯的是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也就是所谓报格。倘须屈服于干涉言论的附带条件,无论出于何种方式,记者为自己的人格计,为本刊报格计,都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记者原不愿和我所敬爱的读者遽尔诀别,故如能在不丧及人格及报格的范围内保全本刊的生命,固所大愿,但经三个月的挣扎,知道事实上如不愿抛弃人格报格便毫无保全本刊的可能,如此保全本刊实等于自杀政策,决非记者所愿为,也不是热心赞助本刊的读者诸君所希望于记者的行为,故毅然决然听任本刊之横遭封闭,义无反顾,不欲苟全。”
“《新生》事件”爆发后
提前回国创办《大众生活》
《生活》周刊被查禁后,经胡愈之等人斡旋,决定创办新的刊物,以继承、光大《生活》周刊精神,并提议由杜重远出任主编。1934年2月,新刊诞生。刊名原拟采用《新生活》,但因当局的“新生活运动”搞得很臭,很可能引起读者误解,于是最终定名《新生》,意寓《生活》周刊“新的生命”。邹韬奋流亡欧美期间,边走边记,创作了《萍踪寄语》等作品,并陆续在《生活》周刊连载,后因刊物被封中断,如今又得以在《新生》周刊继续刊发。
《新生》周刊出版了一年多,到1935年因刊载《闲话皇帝》一文,引发“《新生》事件”。该文在论述日本天皇时,因有言论把天皇描述为“傀儡”“古董”。文章一经发表,上海的日文报纸以头条新闻宣称《新生》周刊“侮辱天皇”,“妨碍邦交”,有日本浪人举行示威游行,打碎了北四川路上多家中国商店的大橱窗玻璃。此前,国民党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重要城市设立了“新闻检查所”,1934年,当局又成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闲话皇帝》一文虽经当局审查,但最终放行。日方借此大做文章,认为《闲话皇帝》出笼,代表了中国政府的某种意图。
日方咄咄逼人之际,国民党当局不顾国人、侨胞反对,刻意退让,委曲求全。最终,《新生》周刊被封,杜重远被判刑一年零两个月,不得上诉,立即送监。而上海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所有参与审查《新生》周刊的人员,悉数被免职。
1935年7月,邹韬奋在美国《芝加哥论坛报》获悉“《新生》事件”及杜重远入狱的消息后,当即发电慰问,并提前回国。船在上海一靠岸,邹韬奋顾不上跟妻子多说话,转交行李后即雇车到监狱去探望杜重远。两人一见面,话没出口泪已先流。邹韬奋自述:“我受他这样感动,倒不是仅由于我们友谊的笃厚,却是由于他的为公众牺牲的精神。”
当年11月,邹韬奋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他没有因“《新生》事件”而停止“出版救国”的理想和追求。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邹韬奋高度赞扬学生救亡运动,认为“这是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并呼吁凡是确以民族解放斗争为前提的国民,都应“共同擎起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以血诚拥护学生救亡运动,推动全国大众的全盘的努力奋斗”!《大众生活》还刊发诸多现场的照片,一时洛阳纸贵,销售量达20万份。
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
回绝陈济棠“资助”
《大众生活》风生水起之际,蒋介石再次派出要员张道藩与刘健群进行劝说,地点在邵洵美家。张道藩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刘健群为复兴社的总书记。结果可想而知,两人再次碰了“钉子”,没能把邹韬奋“拉下水”。邹韬奋随后在《大众生活》上发表了《领导权》一文,驳斥了刘健群“惟命是从、惟上是听”的“领袖脑壳论”。
蒋介石此时仍未放弃争取邹韬奋的努力,他决定亲自出马,约邹韬奋到南京面谈,并安排杜月笙陪同往返,以便让邹韬奋安心。考虑到邹韬奋彼时已加入全国各界联合执行委员会,是执行委员之一。前往南京与蒋介石面谈,怕双方闹僵,不如不见。第二天,戴笠奉蒋介石之命去南京火车站接人,未果,只能原车返回。不料天降大雨,道路泥泞,半路车子翻了,弄得戴笠满身污泥,狼狈不堪。邹韬奋事后写道:“在他们看来,我大概是一个最不识抬举的人!”三年后,邹韬奋在重庆才得知,蒋介石此次约他“当面一谈”的目的,是要他像陈布雷一样,做“文胆”第二。
“敬酒不吃吃罚酒”。果然,1936年2月,《大众生活》只出版了十几期即被查封了。但是,仅仅3个多月后,邹韬奋即在香港创办了《生活日报》,以“促进民族解放,推广大众文化”为宗旨。胡愈之曾在《邹韬奋与〈生活日报〉》一文中写道:“殖民地的新闻检查,却比在半殖民地的蒋管区要宽大一些。例如‘帝国主义不能公开写出来,写成‘□□主义就可以了。至于要求抗日救亡,要求民主等等,在国民党地区是要作为‘危害民国罪惩办的,而香港政府则置之不问。这也是韬奋决定到香港去办报的一个原因。”
邹韬奋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的时候,广东军阀陈济棠特地派副官接他到广州面谈,事后还要送3000千元,邹韬奋同样谢绝。
由于交通不便,报纸难以及时送达内地读者手中,飞机轮船常常误期,一份报纸到上海有时需7天,时效性不强,还不如迁回上海办报。在坚持出版近60期后,邹韬奋最终决定停办日报。
身陷囹圄仍创作出《经历》等作品
1936年11月22日凌晨,正当邹韬奋仍在为新创办的《生活星期刊》构思社论选题时,一阵急促、凶猛的打门声打破了清晨的安宁。门打开后,5个人一拥而入,邹韬奋被捕了。不久又传来消息,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史良与沙千里这一夜也在上海被捕,由此引发了轰动海内外的“七君子事件”,他们都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要负责人。
“七君子事件”爆发之初,各界即展开营救。延安《红色中华报》以《反对南京政府实施高压政策》为题,报道了邹韬奋等人被捕的消息。文章指出:“这种行为实为全国人民所痛心疾首的,全国人民决不会为南京政府的爱国有罪政策所威胁而坐视中国的灭亡,必须再接再厉,前仆后继来发展正在开展的全国救亡运动。”国民党中央委员于右任、孙科等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此案应“郑重处理”。冯玉祥等在南京征集10万人签名营救运动,“以表示民意所依归,而促南京最高当局之觉悟”。宋庆龄等人还表示要陪“七君子”一同坐牢,直到大家释放为止。罗曼·罗兰、爱泼斯坦等国际人士同样致电国民政府,要求放人。
在法庭审判中传讯邹韬奋时,他昂首阔步,在答复审问时,声调慷慨激昂,仿佛在群众大会上作演讲,驳得法官哑口无言,全场陪审律师则频频起立声援邹韬奋。
邹韬奋被捕后,胡愈之坐镇编辑部,边听同事汇报庭审情况边写特稿——《爱国无罪案听审记》,然后分发给上海各大报刊,生活书店连夜又将“听审记”印制成书,免费发放。
尽管民愤汹汹,当局却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将“七君子”关押了200多天,直到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才释放出狱。虽然身陷囹圄,邹韬奋依然笔耕不辍,接连创作了《经历》等自传性回忆录,编写了《萍踪忆语》《展望》《读书偶译》等文稿,总计30余万字。沙千里后来回忆:邹韬奋“全部时间差不多用在写作方面”,“任何外面的吵扰,对他都不可能发生影响,即使我们在打球的时候,他也在球场旁边一只特制的写作藤椅上运笔如飞地写作他要写的东西”。
拒绝生活书店与正中书局“联合”
邹韬奋刚出狱,又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该刊随后与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合并,更名为《全民抗战》。与此同时,当局对邹韬奋出版言论的压制也更加严厉。
1938年,当局颁布《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和《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要求所有出版物须重新送“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发给审查证,印在封底上,才能出版。根据其规定,除了“本党及各级党政机关之出版物”之外,都不能“原稿审查手续”。针对这些倒行逆施,邹韬奋接连在《全民抗战》上发表了《审查书报原稿的严重性》等文,明确指出:“采取审查原稿的办法,对于舆论的反映及文化的开展实有莫大的妨碍”,“我们所诚恳希望的是在三民主义最高原则下,予耳目以相当范围视听的自由,而不加以过于严厉的限制与束缚。”
在国民党参政会上,作为参政员,邹韬奋接连提出“请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相关议案,但当局并未采纳。“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会”刚成立的时候,邹韬奋一度亲自造访,与审查会负责人理论,并“抢救”出一些被当局认为“应予免登”的文章。后来邹韬奋再去“抢救”稿子的时候,遇到的却总是蛮不讲理的总干事,对于邹韬奋的正当要求,对方每次都官腔十足,百般刁难。邹韬奋不得不“实行了战略上的自动撤退”。
1939年重庆遭日军大轰炸后,邹韬奋从冉家巷搬到学田湾衡舍,和国民党“CC系”代表陈果夫毗邻而居。有友人问他为何如此安排。邹韬奋颇有感慨地说,一来合适的房子难找,二来可以让这类老爷们亲眼看到我们每天都忙着干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韬奋在反动派的诽谤面前,是心怀坦荡、无所畏惧的。”而在大轰炸期间,邹韬奋带到防空洞的随身物品,除了读者来信,往往就是作者稿件。
时局动荡,生活书店的境遇也越来越险峻。1939年4月,西安生活书店被当局查封,财物、现款等被洗劫,有店员遭逮捕。此后,各地生活书店遭搜捕的事件不断发生。邹韬奋一再向当局文化主管部门负责人交涉,都推说是“地方事件,不是中央政策”。在交涉过程中,国民党特务头目徐恩曾、戴笠都找邹韬奋谈话,劝他加入国民党,均遭到了拒绝。
1940年6月,国民党派出3个会计专家突然来书店总管理处查账,检查是否领取共产党津贴,结果毫无所获。来人不甘心,第二天又找生活书店同事谈话,邹韬奋义正词严地指出:“书店的事情一概由我负责,有什么问题尽管问我。在这里服务的同事,我有责任保护他们,不能随便找他们谈话。”对方只好退却。
黔驴技穷之时,国民党主管文化出版的刘百闵出面,提出生活书店应与国民党办的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联合”或“合并”,成立总管理处,请邹韬奋主持,管理所属3个出版机构,各店对外的名称保持不变。但邹韬奋表示,所谓联合与合并,不过是消灭与吞并的别名罢了,绝对不能接受。刘百闵还想以投资入股的方式打入生活书店,并派两个人挂个空职“监督”,让政府放心。此议同样遭到拒绝后,刘百闵摊牌说,这是蒋总裁本人的主意,不能违反,还是接受为利,否则到时将“全部消灭”。邹韬奋毫不退让:“我认为失去店格就是灭亡,与其失去店格而灭亡,还不如保全店格而灭亡。我的主意已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谈判就此破裂。最终,生活书店只剩重庆等地分店仅存,其余50多家分店均遭封闭。
“皖南事变”社论被禁,开“天窗”抗议当局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邹韬奋也为《全民抗战》撰写了社论,指出事变并不是单纯“军令”、“政令”问题,不能否认在实质上是党派斗争,要解决这一问题,要求“从根本上加强民主政治,巩固抗日党派的精诚团结与合作”,国难当头,发生这种事件,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该社论在送审时被“国民党审查判了‘免于刊登的死刑,送进了棺材,只好开个天窗”,以示抗议。夏衍曾在《韬奋永生》一文中写道:邹韬奋办刊物的特点是抓“一头一尾”,头就是社论,尾就是“读者问答”。他主编《大众生活》的时候,每一期的社论几乎都是亲自执笔,并在写作前后在编委会上听取编委们的意见,还广泛咨询不同领域的专家,如国际问题求教乔冠华,经济问题听取千家驹意见等。在邹韬奋看来,“刊物没有社论,等于一个人不讲话,要讲话,那么既不能讲错话,也不该讲得含糊不清。”至于读者来信,“他每一封都看,看了之后挑出一些有代表性的来亲自作答。”
面对刊物屡遭封杀,失望之余,邹韬奋经与周恩来等人商议,决定再次转移阵地,转道桂林坐飞机去香港,继续出版事业。邹韬奋所乘飞机起飞后两小时,蒋介石“坚决挽留”的密令就到了。
然而,随之爆发的太平洋战争,致使香港被日军侵占,邹韬奋的出版理想再次被击碎。在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下,邹韬奋与柳亚子等文化名人混在汹涌的难民潮中离开香港,暂时潜伏于广东山区。此后,国民党特务在广东四处活动,蒋介石的密令内容也变更为“就地承办,格杀勿论”。最终,出于安全考虑,邹韬奋只得避走新四军苏北抗日根据地,开始了新环境下的斗争生活。
(责编 任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