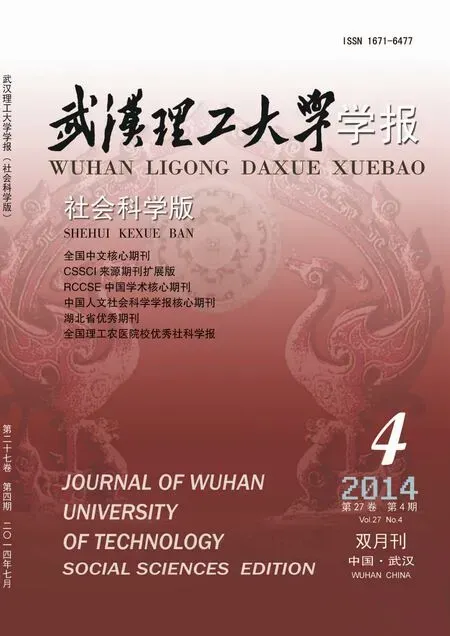唐代贬谪文人与湖湘文化的相互影响
戴金波
(湖南理工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岳阳 414000)
湖湘文化是一种区域性的地方文化,它的孕育及最后形成与地域概念——“湖南”或“湘”的形成有密切关系。先秦时代,今天的湖南大部分属于楚国的版图。秦汉以后,这里的行政区划出现过一些较大的变化。秦汉时代的今湖南中部、湖南东部一带归属长沙郡管辖;到南朝时,开始设置湘州。唐代宗广德二年(763年)设湖南观察使,宋真宗至道三年(997年)设荆湖南路,开始确立潭州(今长沙市)为湖湘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实,在五代时就出现过“湖湘”的地域名称,南宋时在湖南出现的著名的理学学派就被当时学术界称为“湖南学”或“湖湘学派”。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今湖南省行政区划内出现以“湘”或“湖南”命名的行政区域,或将这一地区泛称为“湖湘”,这主要是在唐宋两朝以后的事了。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中国文化重心开始南移,儒学地域化得到较大发展,这就使得外来的中原文化与湖湘的本土文化结合,产生了独具特色并在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湖湘文化。
一、唐代贬谪文人对湖湘文化孕育及形成的影响
唐代贬谪到湖湘地区的文人都是当时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大多数都是进士出身,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素质较高,又都曾经在朝廷为官,有的甚至还是宰辅大臣,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一定的行政管理经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基本上都是当时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只不过是因暂时仕途受挫,被朝廷贬到了当时相对落后且尚未完全开发的湖湘地区,对他们自身来说,是人生的悲剧,但是对广大的湖湘地区来说,则是一大幸事。因为,他们的到来为湖湘地区的开发和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创造了条件,也对湖湘文化的孕育和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他们将中原地区先进的思想、文化带到了湖湘地区,为湖湘文化的孕育和形成积淀了丰富的养分。楚文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源头,湖湘地区一直受到楚文化的熏陶和巨大影响。隋唐以前,关中及中原文化对湖湘地区的影响还是十分有限的,一方面,因远离关中及中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关中及中原文化还很不容易辅射和影响这一地区。另一方面由于湖湘地区地理条件独特,要么是沼泽大川,要么是高山丘陵,道路崎岖,交通不便,外面的人不容易进入这一地区,这里的人们也很少走出大山,去感受外面的世界。因此,在唐代,湖湘地区还属于比较偏僻、落后和相对闭塞的地区。一些文人士大夫因为各种原因,受到朝廷当权者的打击、排斥,为对其进行惩戒,便将他们贬到了湖湘这一远离京城数千里、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他们虽然满腹冤屈,饱受精神和身体的摧残,但他们又不得不调整心态,正视现实,静候东山再起之日。谪居湖湘贬所,客观上又为湖湘地区带来了关中及中原先进的思想和文化。如中唐时期,在王叔文、王伾主导的“永贞革新”失败之后,革新派的重要成员柳宗元、刘禹锡、吕温等三人被贬到湖湘地区达十年之久。他们都是很有思想和抱负的青年才俊,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是生不逢时,命运多舛,朝廷当权者和一些既得利益者容不下他们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们只能被迫远离政治舞台,苟且度日。但他们并没有消沉,他们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传播先进思想和文化的工作,如将关中及中原的哲学思想、文化理念介绍到了湖湘地区,为当时相对落后的湖湘地区的思想启蒙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二,贬谪文人们还将关中及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到了湖湘地区,为湖湘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柳宗元在贬谪永州期间,他将中原地区的耕种技术传授给当地人民,还利用自己的知识积累和实践经验编纂医药图书,介绍医药知识,为当地人求医问药提供参考。吕温贬谪湖湘之后先后任过道州、衡州刺史,他利用自己丰富的管理经验,精心治理自己的管辖地区。吕温在湖湘任职期间,关心百姓疾苦,勤政爱民,大力推动农桑生产,有力促进了这些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赢得了当地老百姓的尊重和爱戴。寓居湖湘十年之久的中唐时元结也是这样,他在任道州刺史期间,也颇有政声,他十分关心百姓疾苦,痛恨贪官酷吏,积极为百姓的利益鼓与呼,在任期间也是一位深受百姓爱戴的地方官。王昌龄在贬龙标尉期间,积极利用自己的管理经验,在充分了解当地民族问题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调整、完善民族政策的方略,在促进各民族和谐相处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第三,贬谪文人们关注民生疾苦及忧国忧民的情怀,极大地丰富了湖湘文化的内涵,使湖湘文化在孕育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关注民生、先忧后乐的品格。张说、王昌龄、贾至、柳宗元、刘禹锡等贬谪湖湘地区文人和因贬谪或其他原因在湖湘地区滞留(流寓)过的李白、杜甫、张九龄、元结、刘长卿等,他们虽然不同程度遭受到政治打击和人生折磨,虽然暂时处江湖之远,但仍不忘忧国忧民。他们在逆境中不断奋起抗争的斗争精神,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忧乐情怀,他们致力革除弊政、振兴大唐王朝的担当和气魄,逐渐凝聚并积淀成为了湖湘文化的基本内涵。如早年怀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远大理想的杜甫,到了晚年因生活所迫,流寓湖湘,虽然自己贫病交加,但他关注的仍然是“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唐王朝烽烟四起,金瓯破碎的景象让他揪心,使他“凭轩涕泗流”。其实个人的孤苦遭遇他早已置之度外,他担忧的是大江南北众多民众不堪战乱流离失所的痛苦境况。他忧虑的是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
第四,贬谪文人们自强不息的品格、坚忍不拔的执着追求,凝聚成为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求实作风和奋发向上的战斗精神。湖湘地区与关中及北方的中原地区相比,经济发展严重落后,文化教育发展尤为滞后,虽然经济文化发展滞后,但是这一地区同样面临着一些尖锐的社会矛盾。与此同时,湖湘地区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空间,落后的农耕技术和社会生产力水平,也较为严重地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贬谪文人的代表人物屈原的许多作品中,他十分关注的就是老百姓的生活疾苦问题,常常因此而焦虑不已。唐代王昌龄贬龙标时,那里的民族矛盾十分突出,他为此殚精竭虑,千方百计积极化解这些矛盾和纠纷。柳宗元贬到永州时,发现当地老百姓的赋敛负担十分沉重,他曾经对孔子说过的“苛政猛于虎”有过一些怀疑,但是到永州后亲眼所见的社会现实使他有了“孰知赋敛之毒有甚于蛇者乎”[1]的深刻感受。吕温在贬谪道州、衡州期间,对当地官员对百姓滥施刑罚的行为十分愤慨,认识到整顿吏治的迫切和必要。这些贬谪湖湘地区的文人,未到贬所之前要么高居庙堂之上,辅佐君王,纵论国事,商讨治国良策;要么侧身“象牙之塔”,故作风流隐士,谈玄论道,模山范水,尽显名士风范。但社会底层的实际情况,他们根本不可能知晓,即使无意间偶尔听到了,他们也觉得肯定是一些人毫无根据乱说的,因此是绝对不会相信的。星移斗转,当他们仕途失意并被当政者无情地贬谪到湖湘地区的社会底层之后,才发现自己原来还真象是井底之蛙,见识太短浅,对社会现实的了解太少了。
因此,这些贬谪文人千里迢迢来到湖湘地区,首先必须面对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社会角色的转变,他们原先大多是达官贵人、风流雅士,现在却突然之间变成了贬谪闲官,落魄文人;另一个是生活条件和环境的改变,生活条件和环境的改变必然给贬谪文人的人生带来一些改变。在新的环境中,他们只能随遇而安,面对现实,自己去求索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像王昌龄,其积极面对湖湘地区复杂的民族关系,推行怀柔安边的民族政策,收效就非常明显。柳宗元初到永州,连居身之所都未得到妥善安排,他只能寄居在潇水东岸的龙兴寺里,后还因生活所迫,几度搬家。但就是在这样异常困难的情况下,他仍不泯灭自己的政治理想与追求,坚持“与山水为伍”,排遣苦闷,缓解病痛,创作了大量的山水游记,为唐代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贬谪湖湘的文人士大夫,他们执着坚韧的品格,自强不息地对正义和真理的追求已经上升为一种人生的新境界。虽失意但不消沉,虽落魄但不颓废,王昌龄、吕温、杜甫是这样,柳宗元、刘禹锡等也是这样,他们体现出的是一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刘禹锡是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到湖湘,谪居朗州贬所十年,历尽人生磨难,备尝万苦千辛,但他却从不向命运屈服。从他在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和大和二年(公元828年)创作的两首游玄都观的诗歌,我们就可非常清楚地看到他性格中执着和倔强的因子,“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体现的是对敌对势力的极大蔑视和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同时,也鲜明体现了刘禹锡乐观自信的心态和精神风貌。贬谪文人的这些优良品格和文化精神,深深地影响到湖湘士人的性格和湖湘文化精神的形成。湖湘文化重实践的经世致用学风和“吃得苦、霸得蛮”,“扎硬寨”、“打死仗”的文化精神与唐代贬谪湖湘地区的文人士大夫之间有明显的历史传承关系。
第五,贬谪文人汇聚湖湘,给湖湘文坛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客观上极大地促进了当时湖湘地区文化的进步和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一方面,贬谪文人们因不同原因走到了湖湘地区,楚文化的氛围、迥别于中原的奇异湖湘山水突然给他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感受。他们纷纷追寻或效仿屈贾的哀怨情怀和悲剧精神,结合个人遭际和感发或直抒胸臆,或相互酬唱,创作了大量的描绘湖湘山水或反映社会现实的佳作,湖湘文学创作也因此出现了离骚以来的又一个高潮期,张说、王昌龄、张九龄、贾玉等都在湖湘期间创作出了具有重要影响的诗篇。柳宗元、刘禹锡、元结等由于在湖湘地区贬谪或滞留时间很长,他们的许多名篇佳作都是在此创作的,因此,他们都是以其在湖湘期间的创作确立自己在唐代文学中的名家地位的。
另一方面,贬谪湖湘的文人还逐渐形成了一些有广泛影响的贬谪文人群体,比较明显的是以岳州、朗州(武陵)、永州为中心的三个贬谪文人群体,岳州地区以张说、贾至、赵冬曦、张九龄为代表,朗州地区以王昌龄、刘禹锡为代表,永州地区以元结、柳宗元、吕温为代表。他们将一批遭际命运相同的贬谪文人紧紧团结在一起,积极扶持提携本地后学新进,切磋传授诗艺,诗酒唱和,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湖湘文学艺术的发展。屈原《楚辞》之后,湖湘文学一度比较沉寂,湖南本土有一些名气的文学家直到魏晋之际才开始出现。三国时期出现过刘巴、蒋琬、黄盖,东晋时期出现过罗含,他们都是以文采飞扬的治世策论而名倾朝野的。南朝时期的阴铿被大诗人杜甫所激赏,并将其作为评点唐代诗歌的范例。唐朝时贬谪湖湘的文人们无疑是湖湘文学繁荣的生力军,湖湘本土出生的文学家也开始在唐代文坛崭露头角。查检《全唐诗》,我们发现这部唐诗总集共收醴州才子李群玉的诗歌258首,收南岳诗僧齐己的诗歌800多首,他们作为唐代湖湘本土诗人的代表,其独特的诗风在湖湘文学史上留下了极其重要的一页。湖湘首位进士及第而被史家称为“破天荒”的长沙人刘蜕,凭借其不假矫饰、文笔古朴的一系列散文,在晚唐文坛大放异彩。湖湘本土文学艺术的繁荣与发展,是与贬谪湖湘文人们的大力扶持、推进和积极倡导参与有密切关系的。
二、湖湘地域文化对贬谪文人的影响
唐代贬谪湖湘地区文人在对湖湘文化的孕育、形成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湖湘自然山水及其独特的地域文化也对从中原地区南下的贬谪文人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相对狭窄单纯的人身阅历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有了较大拓展和丰富,他们感受到了湖湘山水的钟灵秀美和湖湘民风的淳朴。充满浓厚生活情趣的民谣俚语让他们久久回味,欣羡不已。他们的思想认识有了新的变化,他们的创作更加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现实,他们的诗风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们在改变湖湘的同时,湖湘也在悄悄地改变着他们。湖湘地域文化对唐代贬谪文人的影响大致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湖湘贬谪文学的先驱屈原对唐代贬谪到湖湘地区的文人产生了多方面的的深刻影响
首先,屈原的楚辞是唐代贬谪文人在文学创作上模仿和借鉴的主要范本之一。唐代贬谪到湖湘地区的文人不仅追慕和景仰屈原的人格操守,而且还积极学习、借鉴屈原辞赋的表现形式和技巧,并且坚持不懈地进行艺术实践,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贾至、张说、张九龄、柳宗元、刘禹锡等一批贬谪文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旧唐书·柳宗元传》载:“宗元为邵州刺史,在道,再贬永州司马。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数十篇,览之者为之凄恻。”《新唐书·本传》云:“俄尔叔文败,贬邵州刺史,不半道,贬永州司马。既窜斥,地又荒 ,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对照两《唐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柳宗元在贬往湖湘永州时,确实是把屈原作为心中的楷模,并学习和借鉴屈原辞赋的表现形式和艺术技巧创作了一些的骚体诗文。《旧唐书·刘禹锡传》载:“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谷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刘禹锡在谈到读张九龄贬谪荆楚所创作诗文的感受时说:“今读其文章,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州,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辞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2]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刘禹锡、张九龄等的创作也深受屈原的影响。唐代贬谪湖湘文人中,受屈原影响最深的可能是柳宗元,宋人严羽就说过:“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3]。
其次,屈原的“美政”理想也是唐代贬谪文人不懈追求的目标。屈原的“美政”理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敬仰圣君、贤臣,追求国家的统一、富强;二是重民、爱民,有强烈的以民为本思想;三是严明法度,主张选贤任能。屈原的这些政治理想对唐代贬谪文人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中唐柳完元、刘禹锡、吕温等所生活的时代,恰恰正是大唐由盛转衰的过渡时期。经历了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整个唐代社会已处于困境与突破的特殊转折时期,改革、变通、追求大唐王朝“中兴”的思想正逐步演变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变革与发展。贬谪文人以屈原为榜样,“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4]所谓“元元”即芸芸众生,“利安元元”就是要为普通大众谋利益。柳宗元、刘禹锡等把屈原的“美政”理想灵活运用到了观察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之上。在风云激荡的“永贞革新”中,他们就明确提出了内抑宦官、外平藩镇、惩办贪官、选用贤臣、薄赋轻徭等一系列正确的改革措施或主张。如在《贞符》一文中,柳宗元认为为政的根本就是要符合“生人意”,也就是说要坚决限制豪强大地主与官吏的非法掠夺和暴行,适当减轻人民的负担和痛苦,满足老百姓生活的基本要求,使全体百姓都能休养生息,安居乐业。柳宗元的《捕蛇者说》还以永州郊外一家三代为了免除赋役,宁可去以捕毒蛇为生而相继惨死的经历,揭露了当时社会的腐朽和黑暗,发出了“苛政猛于虎”的愤怒呼喊,表现出柳宗元重民、爱民的真挚民本情怀。
再次,屈原还是唐代贬谪文人坚持人格操守、拒绝随波逐流的精神支柱。屈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坚持理想、坚守信念的早期典范。他坚持改革,主张法治,期盼休养生息,国富民强,十分向往“国富强而法立”的尧、舜、汤、禹时代,然而却遭到了来自楚国朝野的多重打击。但屈原不屈从于流俗,仍然深深爱着自己的故国,坚持着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政治追求。屈原的这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意识和不屈不饶的奋斗精神,对那些与其有相同命运的唐代贬谪文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共鸣。因贬谪来到湖湘的张九龄、柳宗元、刘禹锡、韩愈等都将服道守义、穷达不渝的屈原作为自己人生的标杆。与屈原命运有更多相似之处的柳宗元、刘禹锡对屈原的执着意识还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他们已经将其作为了自己坚持人格操守、拒绝随波逐流的精神支柱。
对柳宗元和刘禹锡而言,一方面贬谪既导致了其生命沉沦和心理苦闷,磨练了其意志,加深了其对人生的体悟;另一方面又为其提供了一段回首往事、反思自我的时间。通过深层次的思考和万死投荒般的人生体验,他们已意识到自己的悲剧原来直接与政治的险恶狡诈、特别是与专制君主的严酷少恩有很大关系,自己的问题主要是头脑过于简单、轻率,并不是自己坚持信念、理想出了差错。既然信念、理想是正确的,那就应该像一千年前的屈原一样去坚持,去追求,即使险象环生、浮谤如川、摧残益酷、苦闷日重,也决心初衷不改。柳宗元在赴永州贬所的途中,屈原的身影一直伴随着他,支撑着他,提醒着他:“先生之不从世兮,惟道是就。”“穷与达固不渝兮,夫惟服道以守义。矧先生之悃愊兮,蹈大故而不腻。”[5]这貌似吊屈之文字,实际上是在吊己。柳宗元与千年前的屈原灵魂相通,情感共鸣,不同时代的执着意识在这里融合交汇。表面上柳宗元是在尽情赞扬屈原之气节、人品,其实他的潜意识里是想展示自己与屈原相通的志节和品格,以及对人生忧患的傲视和执著超越的精神。
(二)湖湘民风民俗及湖湘本地文学的表现形式和技巧对贬谪文人的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湖湘地区受楚文化的熏染,巫风盛行,淫祀习俗代代相传。从屈原的《楚辞》中就可以看到楚国先民重巫术、祀鬼神的影子。近千年过去了,这一习俗还在深刻地影响着湖湘人民。贬谪到此的唐代文人士大夫们也很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迥异于中原大地的风俗习惯,在感到新奇之余,他们也开始仔细观察与研究这一民俗的特点和内在文化精神。如刘禹锡就对贬所武陵和朗州的民俗风情十分熟悉,在他的湖湘贬谪诗作中,有一部分就反映了这一内容。如他在朗州所作的《蛮子歌》、《晚岁登武陵城顾望水陆怅然有作》、《梁国祠》等诗就非常生动地描绘了朗州人祭祀鬼神的场景,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当时湖湘地区的巫风盛况。
贬谪朗州时期,刘禹锡还经常收集当地的民间歌谣音乐、故事传说,亲眼目睹了多种多样的民间娱乐活动或当地人的婚庆嫁娶场景,并将其写入自己的诗文之中,在他的贬谪诗里留下了许多表现唐代湖湘地区民俗风情的珍贵资料。唐代的朗州虽地处偏僻荒远之地,但并不缺少青山绿水、平湖秋月,秀丽的山川美景、流传千古的传说故事、迥异于中原的风土人情,一下子就激起了贬谪文人的兴趣赏爱。这里不仅有别具风味的“春江千里草,暮雨一声猿”(《武陵抒怀五十韵》)的景观,而且在“孤帆带日来,寒江转沙曲”的江边夜晚,还呈现出“月上彩霞收,渔歌远相续”(《步出武陵东亭临江寓望》)的如诗如梦般的意境。而成名于巴蜀之地的《竹枝》歌,飘荡于朔漠之上的羌笛却又突然响彻在洞庭湖畔的岳州城边,“荡浆巴童歌竹枝,连樯估客吹羌笛”(《洞庭秋月行》)。四处旗亭酒舍,岸边商船估客与“醉踏大堤相应歌”(《采菱行》)的《竹枝》、《桃叶》曲交相辉映,形成了一组具有湖湘特色的迷人美景。刘禹锡的《堤上行》(三首)就形象地展示了这一风貌:“江南江北望烟波,入夜行人相应歌。《桃叶》传情《竹枝》怨,水流无限月阴多。”(其二)此外,《潇湘神二首》中的“君问二妃何处所?零陵香草露中秋”以及 “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等诗句,也富有鲜明湖湘风韵。
刘禹锡诗歌深受民歌的影响,他用民歌形式创作了许多表现湖湘山川风物、风土人情的作品。他在朗州创作的《竞渡歌》、《采菱歌》就是这类诗歌中的典型代表。采菱一直是富有江南水乡特色的农活之一,南朝开始,一些文人雅士就借鉴湖湘民歌的表现形式创作过《采菱曲》、《采菱歌》之类的诗作。然而,把洞庭水乡采菱场景及采菱女神情风韵表现得最为栩栩如生的还只有刘禹锡的《采菱行》:“争多逐胜纷相向,时转兰桡破轻浪。长鬟弱袂动参差,钗影钏文浮荡漾。笑语哇咬顾晚晖,蓼花缘岸扣舷归。归来共到市桥步,野蔓系船苹满衣。家家竹楼临广陌,下有连樯多估客。携觞荐芰夜经过,醉踏大堤相应歌。”诗歌独特的民歌韵味,流丽的辞采,浏亮的音节,读来声情并茂,确实令人赏心悦目。
贬谪湖湘的王昌龄、吕温及寓居湖湘的元结等也深受湖湘民俗及民歌影响。如吕温在湖湘创作的一些咏物诗、抒怀诗,就带有湖湘民歌的韵味,语言朴实,含蓄蕴藉,感情真挚,其《和舍弟恭惜花绝句》:“去年无花看,今年未看花。更闻飘落尽,走马向谁家。”诗句表面极为通俗浅显,实际上却蕴含深刻,他是在“永贞革新”失败,一片白色恐怖的情形之下,委婉地表达自己内心的焦虑和苦闷,曲折地反映出诗人对遭遇不幸的战友们的深切关注。其《偶然作二首》还明显富有民歌的余韵绝响,节奏明快,朗朗上口:“栖栖复汲汲,忽觉年四十。今朝满衣泪,不是伤春泣。中夜兀然坐,无言空涕洟。丈夫志气事,儿女安得知。”十分形象地为我们勾画出了一位怀才不遇、大志难伸的落寞诗人形象。
元结寓居湖湘期间也积极学习湖湘民歌的表现形式和技巧,创作了一些广为流传的诗歌,如其效仿湘江船歌的表现形式创作的《欸乃曲五首》就很有湖湘民歌风味,“千里枫林烟雨深,无朝无暮有猿吟。停桡静听曲中意,好似云山韶濩音。”(其三)“零陵郡北湘水东,浯溪形胜满湘中。溪口石颠堪自逸,谁能相伴作渔翁。”(其四)为追求地道的民歌风味,元结在这些诗歌创作完后,还“令舟子唱之,盖以取适于道路耳。”[6]由此可以看出,元结确实是在虚心学习湖湘民歌的表现形式和技巧。其《石鱼湖醉歌》也充分运用了民歌的表现形式,一唱三叹,余味悠长:“石鱼湖,似洞庭,夏水欲满君山青。山为樽,水为沼,酒徒历历坐洲岛。长风连日作大浪,不能废人运酒舫。我持长瓢坐巴丘,酌饮四坐以散愁。”在阵阵踏歌声中,一群率性而为的酒鬼们正在豪饮为乐,烂醉如泥的他们已分不清东南西北,三尺水潭在他们的眼中都变成了八百里洞庭。民歌的韵味加之奇特的想象,使这一诗作给人以全新的审美体验,让人回味无穷。
(三)湖湘自然美景及人文景观给贬谪文人们带来了全新的人生阅历和审美体验,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
湖湘地区在唐代还是一片尚未完全开发的处女地,交通阻塞,经济文化落后,与中原地区联系也不很紧密,因此,中原人士还根本就不了解这一片神奇的土地。提到湖湘,在当时人们的印象之中,就是偏僻的“蛮夷”,是遥远的蛮荒之地。其实,湖湘地区是山川秀美、民风淳朴、自然和人文景观极为丰富的地区。这里三面环山,湘、资、沅、醴齐奔洞庭,汇成浩浩荡荡的洞庭湖,滋养着湖湘儿女。湖湘各地自然风光各具特色,美不胜收,湘北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还有“白银盘里一青螺”的湘山(君山岛);湘中有汩汩湘江穿流而过,还有佛道圣地南岳衡山;湘南有清澈潇水环绕的九嶷山、苏仙岭;湘西有多情资水、澧水贯穿,桃花源更是充满着神秘的色彩。湖湘地区还有很多神话传说、历史典故,如炎帝南迁、祝融观天、舜帝南巡、大禹治水等神话传说都与湖湘有关,相传炎帝曾率神农部落一部南迁至湖湘宜章。桂阳县北有湛江,其阳有嘉禾。“嘉禾,故禾仓也,炎帝之志,天降嘉种,神农拾之以耕作,于其地为禾仓,后以置县,循其实曰嘉禾县。”(王应章《嘉禾县学记》)而神农氏之裔“赤制氏作耒耜于郴州之耒山”,故有耒水之河,耒阳之邑。舜帝南巡也充满着传奇色彩,据史料记载,舜帝巡狩曾来到湖湘地区,他令人在韶峰山下演奏《韶乐》,也曾习唱湖湘民间歌谣:“舜弹五弦之琴而歌《南风》之诗,以治天下。”“(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今宁远县九嶷山)。”[7]
湖湘地区不但有一些神话传说,还有许多中古时代真实的历史故事流传,如屈原投江的故事就一直在湘西、湘北地区广泛流传。相传楚怀王时,屈原被任命为左徒,他积极辅助怀王治国理政,主张修缮法度、富国强兵、联齐抗秦,但却遭到了一些奸臣和顽固派的诋毁, 不久即被怀王疏远,并逐出郢都,贬往江南,在湘西、湘北流浪,孤苦地度过了其失意落魄的后半生。在这一时期,他行吟泽畔,继续忧国忧民。当楚怀王被囚,顷襄王无能,楚国都城被秦国大军攻破之时,流浪于洞庭湖畔的屈原,深感亡国之奇耻大辱,在绝望之中,“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自尽于汨罗江。在诗人怀沙自沉的汨罗江畔,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当地人都用赛龙舟、包粽子等形式来悼念这位伟大的诗人。“楚大夫屈原遭谗不用,是日(五月初五)投汨罗江死,楚人哀之,乃以舟楫拯救。端阳节竞渡,乃遗俗也”(吴均《齐谐记》)。五月初五赛龙舟、包粽子的风俗到唐代已十分盛行。
三、结 语
湖湘地区迥异于中原的奇山妙水,令贬谪到此的文人士大夫目不暇接,惊奇不已,湖湘地区丰富而又具有传奇色彩的人文景观,更令他们逸兴遄飞,感慨系之。他们积极把自己在湖湘的所见所闻所感表现在自己的诗文之中,这使得他们诗文的题材、视野和风格有了明显的变化,新的人生阅历及新的审美体验,大大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在湖湘贬所,他们都创作了大量描写湖湘山水,赞美湖湘自然和人文景观的诗篇,为唐代山水诗的繁荣和唐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与此同时,这些贬谪文人们还积极通过自己的创作,热情向中原地区介绍湖湘地区奇妙的山川形胜、神话传说、民俗风情、历史典故,客观上也促进了湖湘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与沟通,从此开始,湖湘地区也逐步为中原人士所认识。
[参考文献]
[1] 柳宗元.天爵论[M]∥柳宗元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79:79.
[2] 刘 昫.旧唐书:卷160[M].北京:中华书局,1975:4211.
[3] 严 羽.诗评[M]∥严羽集:沧浪诗话.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36.
[4] 柳宗元.寄京兆许孟容书[M]∥柳宗元集:第30卷.北京:中华书局,1979:779.
[5] 柳宗元.吊屈原文[M]∥柳宗元集:第19卷.北京:中华书局,1979:515.
[6] 羊春秋.全唐诗:卷241[M]∥传世藏书·集库·总集.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923.
[7] 李超宇.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M]∥四库全书精华·史部.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1179.
(责任编辑 文 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