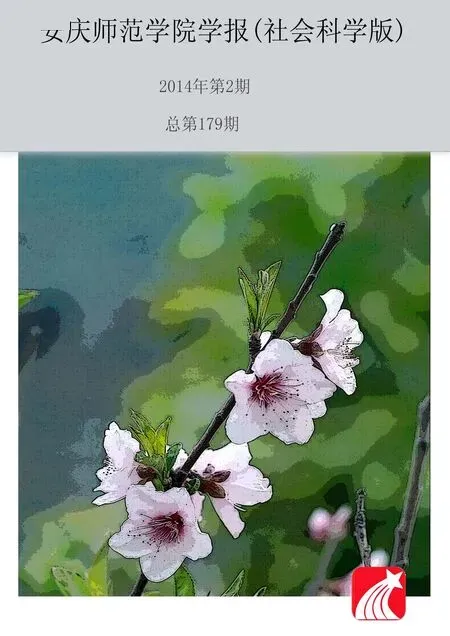刘文典与陈独秀交往考述
黄 伟
(安徽大学历史系, 安徽 合肥 230039)
刘文典与陈独秀交往考述
黄 伟
(安徽大学历史系, 安徽 合肥 230039)
刘文典与陈独秀都是近代皖籍著名的学者,两人一生的关系基本是亦师亦友。在长期的交往中,陈独秀对刘文典大力提携,而刘文典积极呼应和支持陈独秀早期各种活动。刘、陈二人最后因为政治理念的不同,交往疏远。
刘文典;陈独秀;交往;《新青年》
一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刘文典与陈独秀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刘文典于1891出生于安徽合肥,祖籍怀宁,可以说是陈独秀的同乡。陈独秀于1879年生于安徽怀宁十里铺,长刘文典十二岁,刘文典在年轻的时候曾跟从陈独秀学习过古典文学。1917年两人又先后进入北大,成为同事。朱希祖曾言“忆民国六年夏秋之际,蔡孑民长校;余等在教员休息室戏谈:余与陈独秀为老兔,胡适之、刘叔雅、林公铎、刘半农为小兔,盖余与独秀皆大胡等十二岁,均卯年生也。今独秀被捕下狱,半农新逝,叔雅出至清华大学,余出至中山及中央大学;公铎又新被排斥至中央大学。独适之则握北京大学文科全权矣。故人星散,故与公铎遇,不无感慨系之。”[1]
1906年刘文典慕名进入安徽公学,师从陈独秀和刘师培等人学习。安徽公学是1904年2月由李光炯等人在长沙创办的安徽旅湘公学,黄兴、张继、赵声等人曾为该校教员。1904年底安徽旅湘公学正式迁往芜湖,更名为安徽公学,先后有陈独秀、江彤侯、柏文蔚、刘师培、陶成章、苏曼殊等人在此任教。在安徽公学期间,刘文典深得陈独秀的赏识,刘文典曾回忆陈独秀对自己的评价:“陈独秀说我是三百年中第一人。一九一六年,他做北大文科学长,就把我拉进北大,我那时候二十七岁,就在北大教起书来,那真是目空一切,把什么人都不放在眼内,我的权威思想、自高自大,发展发到现在这个程度,真是根深蒂固,很不容易拔掉了。”[2]在安徽公学期间,刘文典从陈独秀那里学习到了运用西方哲学研究中国古籍的方法,为后来校勘先秦诸子打下了坚实的功底。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刘文典还深受陈独秀新思想的影响。1905年柏文蔚、陈独秀等人在芜湖组建岳王会,同年在南京和安庆等地设立分会,刘文典在陈独秀的鼓动下也加入了岳王会。据相关考证,起初的岳王会基本是以安徽公学为基础,除陈独秀和柏文蔚等人外,还有倪映典、郑赞丞、吴旸谷、张劲夫、熊成基和刘文典等四十余人。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随后根据形势的需要,不少革命志士回国发展成员。加入同盟会的原岳王会成员吴旸谷回国后,与柏文蔚和龚振鹏等人商议,建议岳王会加入同盟会,不久岳王会成员除陈独秀外纷纷加入同盟会,刘文典也于此时加入早期的同盟会。
由于岳王会以反清为目的,引起清政府的高度注意,刘师培等人不得不赴日本避难。陈独秀也于1907年春第三次留学日本,不久便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文化。由于两位恩师先后离开安徽公学,于是刘文典决定1908年底前往日本留学。刘文典到达日本后发现陈独秀已经从日本回国,在杭州浙江陆军小学任国文史地教习,而刘师培却又热衷投机政治,因此,刘文典在日本留学期间,经人介绍正式拜入章太炎门下,成为章门弟子,跟随章太炎研究经学和小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刘文典回国在于右任的《民立报》任翻译,笔名天民,陈独秀则应邀回乡,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和安徽高等学堂教务主任。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北火车站遇刺身亡,举国为之一惊。7月14日刘文典与范鸿仙等人齐聚芜湖,决定成立讨袁第一军和第二军。1913年7月柏文蔚正式宣布参加反袁“二次革命”,陈独秀此时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刘文典没有直接参加前线的战斗,但承担了运送伤员的任务,据参与此次战斗的革命党人回忆:“文质彬彬的刘文典已袭长衫,驾着马车穿行于战场之中,四处寻找、抢救、运送伤员,用果敢的行动印证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热血豪情”。[3]8月6日讨袁军内部发生变故,胡万泰在安庆兵变,安徽都督柏文蔚避走芜湖、南京等地。而此时的陈独秀却被驻防芜湖的龚振鹏扣押,龚振鹏此间杀戮无数,引起了陈独秀的极大愤慨,“都督府秘书长陈仲甫因其残暴,痛斥其非;袁市长家声,亦以良心不许,委婉讽劝,均遭绳绑,正拟枪决,而以张旅长永正迫以兵力,稍敛淫威,未下毒手,而陈、袁已饱受惊吓矣”[4]。刘文典闻知陈独秀被龚振鹏羁押后,多方营救,陈独秀幸免于难。知情者回忆:“二次革命,先生(陈独秀)从安庆逃到芜湖,被芜湖驻防军人逮捕。这位军人本是和柏公同立在反袁旗帜之下的,不知因何事与柏不谐,而迁怒于先生,已经出了布告,要枪决先生,先生很从容地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罢!’旋经刘叔雅、范鸿仙、张子纲三先生极力营救得免。”[5]关于此事,程演生曾说:“民二安徽独立反袁,芜湖有军政分府的组织,是合肥龚振鹏主持。省政府命他(即陈独秀)到芜湖说龚取消分府,言语冲突起来,龚即叫卫兵将仲甫绑起枪毙,但龚此时又叫他的秘书写仲甫的罪状,在此一刹那间,寿州张孟起(安徽旅长)得了信,连忙带了手枪卫士,将仲甫救去。同去的人说,当时仲甫被绑时并无屈服表示,但面色亦不能无变了。”[6]
二
讨袁失败后,刘文典于1913年9月再次流亡日本,而陈独秀先是寓居于上海,1914年7月应章士钊的邀请也再次赴日。其间,陈独秀还协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并在该杂志撰文发表对时局的看法,该杂志宣称:“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主旨。欲下论断,先事考求;与曰主张,宁言商榷;既乏架空之论,尤无偏党之怀。惟以己之心,证天下人之心,确见心同理同,即本以立说。故本志一面为社会写实,一面为社会陈情而已。”[7]刘文典应陈独秀的邀请也积极在《甲寅》上发表文章,讨论时局,因此《甲寅》也成为刘文典与陈独秀交往的一个重要平台。1915年夏秋之际,陈独秀回到上海,9月15日创办《青年杂志》,以为“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8]在陈独秀的积极鼓励下,刘文典很快也成为《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
1915年11月15日《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三号发行,在这期的杂志目录中赫然有刘叔雅的名字。该文为刘文典的译文,题目为《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是英国著名哲学家赫胥黎的作品。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采取英汉对译的排印方式便于读者学习,刘文典也在译文前面加了案语:“英国赫胥黎(Huxley),近代生物学大家。生于一八二五年,卒于一八九五年,所著《天演论》,侯官严氏曾译为华言,风行中土。斯篇乃钞自其所著‘Lay Sermon’中之‘On the advisableness of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者也。刘叔雅识。”[9]刘文典此篇文章侧重从语言的角度,让读者更加深刻地了解原文的大旨。1915年12月15日,刘文典又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四号发表《叔本华自我意志说》,从意志学的角度阐释世间万物的因果性,刘文典在文前的案语中说:“盗贼盈国,天地既闭,崩离之祸,不可三稔;而夸者死权,贪夫殉财,邪僻之徒,役奸智以投之,若蝉之赴明火,朝无不二之,野寡纯德之士。齐仲孙曰:‘国之将亡,本必先颠。’今日是也。昔者余杭章先生,闵党人之偷乐,忧民德之日衰,宣扬佛教,微言间作,惟恢心邪执,众庶所同。大乘之教,不可户喻,欲救其敝,斯亦难矣。德意志大哲叔本华先生,天纵之资,既勇且智,集形而上学之大成,(Deussen博士语也)为百世人伦之师表,(R.Waguer教授语也)。康德而后,一人而已。先生之说以无生为归,厌生愤世。然通其义可以为天下之大勇。被之横舍则士知廉让,陈之行阵则兵乐死绥,其说一变而为尼采超人主义,再变为今日德意志军国主义。”[10]由于叔本华的唯心主义哲学比较消极,与《新青年》的创刊宗旨有所背离,陈独秀本人也反对这类消极的文章,因此刘文典后来不少唯心主义哲学的文章就没有刊登在《新青年》上了。
此后,刘文典将翻译的重点转向其他领域,1916年1月15日出版的《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五号刊登了刘文典翻译的《富兰克林自传》。在该篇文章中,刘文典在文前同样加了案语,谓“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为十八世纪第一伟人,于文学科学政治皆冠绝一世。其自强不息、勇猛精进之气,尤足为青年之典型。斯篇乃其七十九岁所作自传,吾青年昆弟读之,棠与高山仰止之思,群效法其为人,则中国无疆之休而不佞所馨香祷祝者也。原书辞繁不可背译,译其青年时代者。”[11]1915年2月15日,刘文典又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六号上发表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伯克的著名演讲《美国人之自由精神》,刘文典在前面的引文中说道:“Edmund Burke(1730—1797 )者,英之Dublin 人也。 幼学于其地之TrinityCollege,得文学士学位。初为William Hamilton之秘书。 后为宰相Rockingham侯爵记室,颇见亲信,两度当选为国会议员,历官陆军主计总监,Wairen Hastings 之七年审讯,实彼所弹劾者也。年六十八卒于家。生平著作有VindicationofNaturalSociety,ReflectionsontheRevolutioninFrance,ThoughtsonFrenchAffairs诸书行世。其在国会演说之辞皆安雅可诵,而“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一篇尤为世所称。 兹所译者即斯篇之精英也。”[12]其实刘文典接连发表两篇关于自由的文章,也是响应陈独秀提出的自由思想。“陈独秀翻译美国的国歌《亚美利加》,就是借美国国歌宣传自由理念‘吾爱土兮自由乡,祖宗之所埋骨,先民之所夸张。颂省作兮邦家光,群山之隈相抵昂,自由之歌声抑扬’。这是陈独秀借美国国歌的自由精神,突出埋葬着祖宗的故土上,高唱‘自由之歌声抑扬’。而刘叔雅翻译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伯克(Edmund Burke)的国会演说《美国人之自由精神》,更是讴歌美国的自由思想的名篇。”[13]很明显,刘文典与陈独秀在宣扬自由与民主思想方面的旨趣应该是一致的,也是两人友谊的重要见证。
1915年12月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国酣战之时,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东西方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对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的思想进行了高度的赞扬,同时也批评了东方民族以安息为本位的精神。“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14]陈独秀希望此文可以激起读者的反思,希望青年人可以振作起来为国家而努力。在陈独秀的影响下,刘文典也开始反思中国民众自身面临的问题,他认为只有从精神上让人们意识到与西方的差距,中国才有希望。为了改造中国民族的劣根性,刘文典于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发表《欧洲战争与青年之觉悟》一文,在该文中刘文典有精确的论述,“好和平之民族,即自甘夷灭之民族也”。“吾国民近代对外交涉,无一非屈辱之历史,甚至以泱泱大国,受人最后通牒而奉命惟谨,其被窃无耻,直为世界诸民族之冠”。“世有意志薄弱者流,谓中国他日兴隆大好,不当侵略他人,但当为世界和平之保障。此盖其脑海中所受‘和平’二字之毒,未易剔除故也。试观史册,自来强盛国家,何一不以侵略为事者。”[15]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上刘文典再次发表《军国主义》一文,高度赞扬军国主义国家,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军国主义以求国家强大,“求生意志乃世界之本源,竞存争生实进化之中心。国家者求生意志构成,军国主义者竞存争生之极致也”,“天下无不能战争之民族,在高瞻深识者鼓舞提倡而已。但吾青年昆弟,能自觉己身之责任,扩观世界之潮流,深知军国主义为立国根本,救亡之至计,振作精神,则吾诸华未必不能化为世界最强毅之民族,中夏犹可兴也。”[16]
三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随后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在陈独秀的推荐下,北京大学还聘请了一大批有新思想的学者,如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程演生、李大钊和王星拱等人,刘文典也是这个时候受到陈独秀的邀请进入北京大学的。陈独秀认为只要在某方面有建树的学者,都可以为北京大学所用。例如袁世凯倒台后,刘师培借住在庙里,身体羸弱,情形甚是狼狈,陈独秀见此情况后与蔡元培商议,聘请刘师培为文科教授。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为扩大影响和便于编辑,陈独秀还将《新青年》从上海迁往北京。而刘文典进入北京大学后,则担任北京大学预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同时在《新青年》继续担任英文翻译和编辑。刘文典刚进北大期间,由于学术上无所建树,因此受到一批老学究的轻视。为了打开这种局面,刘文典决定将更多的精力用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上面,所以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也开始相对较少。但是因为和陈独秀是同事,因此两人这期间有频繁的往来。
1917年12月30日,胡适在故乡安徽绩溪与江冬秀结婚,刘文典与陈独秀等北大教授一起联合给胡适赠礼。1918年1月2日,刘文典在陈独秀家吃饭,与钱玄同等人谈论“红学”。钱玄同日记记载:“午后至独秀处,检得《新青年》存稿,因四卷二期归我编辑,本月五日须编稿,十五日须寄出去也。与独秀谈,移时叔雅来,即在独秀处晚餐。同座者为独秀夫妇、叔雅夫妇及独秀之儿女。叔雅亦为‘红老’之学者,与余辩论,实与尹默多同情。其实即适之亦似渐有‘老’学气象。然我终不以此种主张为然。”同时又记载:“独秀、叔雅二人皆谓中国文化已僵死之物,诚欲保种救国,非废灭汉文及中国历史不可,吾亦甚然之。此说与豫才所主张相同。”[17]1月16日,刘文典与陈独秀等人商议组织大学俱乐部、划分大学区域和制定教员学生服装等事宜。
1918年2月15日,刘文典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二号发表译文《柏格森之哲学》,在译文前加有案语:“柏格森,名安利.路易(Henri Louis Bergson),其先本犹太人。犹太文明旧族,近世哲人,先有斯宾诺莎,后有柏格森。柏氏以千八百五十九年生于巴黎,幼学于利塞康多尔塞,研精数学,试辄冠其曹……其著作甚富,而《创造进化论》一书,尤为学者所宝,盖不朽之作矣。其他著作述,每一篇出,诸国竞相传译,而吾国学子鲜有知其名者,良可哀也。”[18]其实刘文典翻译伯格森的文章也是深受陈独秀的影响的。在《新青年》创刊的时候,陈独秀就在发刊词中先后两次提到法国哲学家柏格森,陈独秀希望用柏格森进化论的观点批判封建主义,企图以此来塑造青年的人生观。柏格森哲学即以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来阐释宇宙间不断向前发展的事实,陈独秀借用生物哲学的理念激励青年舍弃保守传统,奋发向上的意识,唯有如此才能达到保种救国。从某种意义上说,柏格森的哲学实质就是西方的玄学,陈独秀希望以西方的哲学观来批判中国传统哲学。但是,当中国的学者纷纷将柏格森的哲学介绍中国后,强调玄学对科学的独立性,以人文的自觉反对唯科学主义的误导,直接助长了中国玄学的发展。柏格森的人本主义哲学成为中国玄学派人生观的重要依据,这可能是陈独秀始料不及的,于是陈独秀不得不将批判的重点对准玄学。
正当《新青年》在全国宣传新思想的时候,灵学派企图利用西方玄学观攻击《新青年》。1918年5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发表《有鬼论质疑》准备引蛇出洞,打击风行一时的“灵学派”。很快一位自称“易乙玄”的灵学成员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发表《答陈独秀先生〈有鬼论质疑〉》逐一反驳陈独秀的观点。后来陈独秀感到“余作《有鬼论质疑》言过简,读者每多误会;承易乙玄君逐条驳斥,使余有申论之机会,感甚感甚”。刘文典应陈独秀的邀请也在当期的《新青年》发表了《难易乙玄君》做为反击,在文章的案语刘文典说道:“陈独秀先生做《有鬼论质疑》,易乙玄君驳之,辨而无征,有乖笃喻,爰作此文,聊欲薄易子之稽疑云尔。”对于易乙玄提出的问题,刘文典逐一进行了辩驳,如易乙玄质问陈独秀“请问先生何以知鬼之声音笑貌能保其物质生存时之状态?若不之知,骤下一肯定断案,于论理上为不可。夫鬼者,其状貌虽能自现,而发音则必藉他物始能闻于人世。其音貌必不能如吾人。”刘文典驳道:“易子虽明有鬼,而体魄不与众同,谓其音貌不同于吾人。然世之言鬼者,则多谓其能保其物质的生存时之笑貌,故陈先生有此疑问。如易子之说是,则自来说鬼之书,必皆凭空虚造无疑,易子即不能引以为据,奈何上文又引《鬼语》乎?韩非子曰:‘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显学)易子非愚即诬耳!”最后刘文典感慨:“呜呼!八表同昏,天地既闭,国人对现世界绝望灰心,乃相率而逃于鬼。有鬼作鬼编而报资不收冥镪之杂志,有荀、墨降灵而诗文能作近体之乩坛,害之所极,足以阻科学之进步,堕民族之精神。此士君子所不可忽视,谋国者所当深省者也。韩非子曰:‘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前者吾国亡征毕备,唯未有此。今既具焉,亡其无日矣!”[19]
《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的通信栏目刊登了一位名叫张寿朋的来信,信中说道:“柏格森‘直觉’之说,果如贵杂志所谓者,则决不得与程正叔‘德性之知’相附会。必欲勉强附会,只堪拟于佛氏之‘投胎舍’耳。鄙见如此,尚祈知诸君有以审之。(程正叔‘德性之知’是实有此知,不知柏氏之‘直觉’,亦自己实有其觉否?)”作为回复,刘文典的回信就附于该文后面,刘文典说:“仆素不想冒充‘学贯中西’,所以绝不肯‘牵强附会’,所以提及程正叔者,取其‘不假见闻’四字而已。来教问‘不知柏氏之直觉亦自己实有其觉否?’柏氏方在巴黎College de France当教授,请去问他自己可也。”[20]
四
刘文典翻译德国哲学家海克尔的《灵异论》一文刊登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刘文典希望此举可以让国人更加明白灵学的实质,使得民众能够建立起良好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该文也成为刘文典在《新青年》发表的最后文字。由于《新青年》后期基本是宣传社会主义,刊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相关文章,刘文典与陈独秀在政治理念上产生极大差异,因此后来刘文典不再为《新青年》撰文。陈独秀离开北大后,1920年春,《新青年》编辑部正式迁入上海。
1919年3月26日,蔡元培应邀与沈尹默、马叙伦等在汤尔和家讨论北京大学文学长的去留问题,会议一致持续到晚上十二点。其他三人一致主张开除陈独秀,但蔡元培坚持陈独秀仍可以为北大教授,并建议他休假一年。不久,蔡元培在教授大会上宣布废除学长制,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代替学长制,陈独秀拒绝了校方的提议,随后离开北大。对于此事,1935年12月23日胡适在给汤尔和的信中说道:“此夜之会,先生记之甚略,然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了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21]667
诚如胡适所言,陈独秀离开北大后越走越远,基本脱离了学术界,逐步成为当时中国政治中的积极分子。陈独秀自此后将全部精力放在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刘文典对于陈独秀的左倾革命情绪不太赞成,此后两人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刘文典潜心下来做学问,不久校勘了《淮南鸿烈集解》,为刘文典带来了不少的学术声誉;而陈独秀却积极参加革命,最后的局面可想而知。1919年5月4日爆发学生运动后,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刊发了大量的介绍运动发展的文章,而他自己也在《每周评论》发表了7篇论文和33篇随感。虽然,刘文典也参加了五四运动,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但仅仅是为了保护学生。刘文典在回忆此次运动时说:“一直到已故的王星拱教授跑来对我说警备司令部已经派兵包围了北京大学,逮捕许多学生,我才直跳起来奔到学校。在红楼门口遇见了罗文干教授,知道蔡元培先生已经辞职离京,更是大吃一惊。”“我和刘半农教授也参加了守夜的工作,朋友们开玩笑说‘犬守夜,鸡司晨,你们一马二刘是北大的三个守夜的犬’。”[22]
1919年6月12日,陈独秀与高一涵和胡适三人在北京城南一个娱乐场喝茶聊天,陈独秀从他的衣袋里去取一些传单向邻座发散。胡适和高一涵离开后,陈独秀继续散发《北京市民传单》而被捕,传单中明确要求撤换北京政府步兵统领王怀庆的职务,这大大激怒了王怀庆,以致非要处死陈独秀。刘文典在得知陈独秀被铺后,多方营救,还曾亲自找安徽旅京同乡会负责人,说服他们致电政府营救陈独秀。9月16日,经各方努力后,陈独秀重获自由。据9月17日《晨报》报道:“前北大教授陈独秀氏,被警厅拘禁,已历三月有余。近者警厅侦查结果,终不见陈氏有何等犯法之事实……闻陈已于昨日下午四时出厅,完全恢复自由矣。”陈独秀出狱后,躲藏在刘文典的家中,但是仍然有再次被捕的危险,后经过李大钊等人的掩护于1919年底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关于此段历史,马叙伦曾记载:“往在北平,中国共产党领袖陈独秀自上海来,住东城脚下福建司胡同刘叔雅家。一日晚饭后,余忽得有捕陈独秀讯,且期在今晚。自余家至福建司胡同,可十余里,急切无以相告,乃借电话机语沈士远。士远时寓什方院,距叔雅家较近,然无以措词,仓卒语以告前文科学长速离叔雅所,盖不得披露独秀姓名也。时余与士远皆任北京大学教授,而独秀曾任文学院院长。故士远往告独秀,即时逸避。翌晨由李守常乔装乡老、独秀为病者,乘骡车出德胜门离平。十三年,余长教部,内政部咨行教部,命捕李寿长。余知李寿长即李守常之音讹,即嘱守常隐之,守常亦是时北平共产党部领袖也。余时虽反对共产党暴动政策,然未尝反对纯正之社会主义。十五年中华以清党离杭州,亦未知如何竟被逮而致死。其人颇有才,更惜之也。”[23]蒋梦麟也曾回忆:“一天,我接到警察厅一位朋友的电话。他说:‘我们要捉你的朋友了,你通知他一声,早点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我知道了这消息,便和一个学生跑到他住的地方(刘叔雅—文典家里),叫他马上逃走,李大钊陪他坐了骡车从小路逃到天津。”[24]
陈独秀到达上海后,刘文典与陈独秀的往来日益减少,根据现有的史料记载,几乎没有看到他们的往来信函。随后,陈独秀成为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开展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而刘文典走上学术之路,先后在安徽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高校任教,曾编著了《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三馀札记》和《杜甫年谱》等。晚年,刘文典染上了吸食烟片的习惯,陈独秀在四川江津寓居写自己的回忆录时,还在文中调侃刘文典,“烧烟泡的艺术之相互欣赏,大家的全意识都沉没在相互欣赏这一艺术的世界,这一艺术世界之外的一切一切都忘怀了。我这样的解答,别人或者都以为我是在说笑话。恐怕只有我的朋友刘叔雅才懂得这个哲学。”[25]1942年5月陈独秀在四川江津病逝,刘文典闻讯后感叹道“陈是非常好的人,为人忠厚,非常有学问,搞不成(政治)——书读得太多了。”[26]
[1]陈平原,夏晓虹.北大旧事[M].北京:三联书店,1998:140.
[2]刘文典.刘文典先生的第二次检查[J].云南文史,2009(2).
[3]章玉政.狂人刘文典[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48.
[4]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柏烈武五十年大事记[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印行,1986:50.
[5]强重华,等.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G].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19.
[6]林茂生.林茂生自选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6.
[7]章士钊.甲寅杂志发刊词[J].甲寅杂志,1914(1).
[8]陈独秀.敬告青年[J].青年杂志,1915(1).
[9]刘文典.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J].青年杂志,1915(3).
[10]刘文典.叔本华自我意志说[J].青年杂志,1915(4).
[11]刘文典.富兰克林自传[J].青年杂志,1916(5) .
[12]刘文典.美国人之自由精神[J].新青年,1916(6) .
[13]庄森.飞扬跋扈为谁雄[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6:23-24.
[14]陈独秀.东西方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J].青年杂志,1915(4).
[15]刘文典.欧洲战争与青年之觉悟[J].新青年,1916(1).
[16]刘文典.军国主义[J].新青年,1916(3).
[17]钱玄同.钱玄同日记[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503.
[18]刘文典.柏格森之哲学[J].新青年,1918(2).
[19]刘文典.答陈独秀先生《有鬼论质疑》[J].新青年,1918(2).
[20]刘文典.来信答复[J].新青年,1918(6).
[21]胡适书信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2]诸伟奇,刘兴育.刘文典诗文存稿[M].合肥:黄山书社,2008:151-152.
[23]马叙伦.石屋余渖[M].上海:建文书店出版社,1949:133-134.
[24]蒋梦麟.西潮·新潮[M].长沙:岳麓书社,2000:340.
[25]吴铭能.历史的另一角[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45.
[26]刘文典全集补编[M].合肥:黄山书社,2008:192.
责任编校:徐希军
OntheContactsBetweenLIUWen-dianandCHENDu-xiu
HUANG Wei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Anhui, China)
LIU Wen-dian and CHEN Du-xiu, renowned scholars in Anhui province in modern times, established a relationship of both teachers and friends. In their long term contacts, CHEN Du-xiu gave guidance and help to LIU Wen-dian, and LIU Wen-dian also actively supported CHEN Du-xiu’s activities in his early life. However, they became estranged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political ideals.
LIU Wen-dian; CHEN Du-xiu; contacts;NewYouth
2013-08-17
黄伟,男,湖南麻阳人,安徽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时间:2014-4-18 17:23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4.02.021.html
K827
A
1003-4730(2014)02-009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