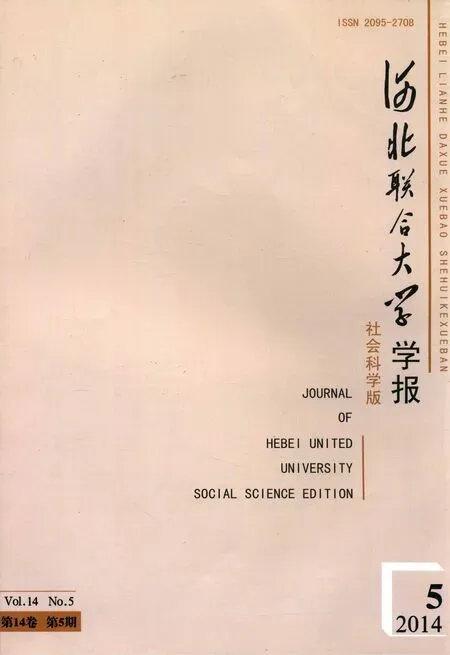《简·爱》的现世性及帝国叙事
邢颖
(蚌埠医学院,安徽 蚌埠 233000)
作为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许多学者把《简·爱》看成作者的生平写照。刘易斯认为《简·爱》是“一部自传,也许所述事实和环境与作者本人并不完全一致,但在磨难和经历方面却完全吻合。“[1]塞西尔声称,“她是我们的第一个写自我的小说家“,作品中的主人公与勃朗特是“同一个人。“[2]自《简·爱》出版以来,这部小说一直被女权主义批评视为崇拜的文本,也因此成为英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经典。[3]223 弗吉尼亚·伍尔芙把《简·爱》看作19 世纪中期前女权主义的愤怒和受挫的典范。她认为小说以作家的自我论断为特征:“我爱、我恨、我痛苦。“[4]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批评对《简·爱》进行了政治与美学意义上的重写,他们把女主人公简·爱看作女性反抗父权压迫的榜样。进入2O 世纪8O年代后,简·爱的叛逆性受到部分批评者的怀疑。玛丽·波维将《简·爱》视为“复杂的意识形态体系“的一部分,把作品解读为一部充满对立矛盾的文本。小说对英国的社会制度提出挑战,表现了叛逆、反传统的一面;同时又呈现出妥协被动、听天由命的一面,作品充满对虔诚、服从、保守的赞颂。[5]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在《简·爱》的研究上则呈现出更多的政治敏感。阿姆斯特朗和斯皮瓦克在《简·爱》的研究上开拓出新的理论领域,把这部小说看成帝国主义的原始文本。斯皮瓦克认为《简·爱》是一部生动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原则“的小说。[3]227本文以赛义德的现世性理论为指导,透过文本的字里行间,探讨勃朗特在文本中帝国叙事。
一、赛义德的现世性理论
在赛义德看来,认为文本具有多种作用,与社会环境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文本是事件、是干预。“文本是千变万化的。文本总是与社会环境和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这些都需要引起注意和评价。正像没有一种理论能解释文本与人类社会之间的所有关系一样,没有人能涉及到全部的问题。文本的阅读与写作从来都不是中立的活动,因为一部文学作品总带有权利与利益、激情与欢快的成分,不管它如何具有美学价值及娱乐功能。”[6]
赛义德把文本看作一种写作行为,并把这种写作行为定位于世界之中。写作通常将各种不同的力量汇合在一起,并有序地把这些力量转化成可以辨认的手迹。赛义德东方主义话语批评揭示了学术性的文本实践与权力关系之间的密切联系。赛义德断言:“世界躯体与文本躯体的密切关系迫使读者将两者都加以考虑。”[7]39就一个文本成为文本的实际过程而言,文本是世界的一种存在物。换句话来说,文本具有物质的在场,它在诉说着一种文化和社会的历史,描述着一种政治、经济的性质,同时还隐含着与其他文本多种联系。[7]33文本无论以多么高深莫测、精妙绝伦的方式存在,它们必定要受到情境、时间、地点和社会的约束。“总而言之,它们是现世性的,因为它们总是处于世界之中。”[7]35
更精确地说,所谓的现世性是指所有文本和再现被多种异质的现实所支配,都处于世界之中。赛义德认为文本是实际的意义的载体,应该被理解成现世的。[8]文本通过言辞表达显现了它们与世界的联系,通过语言的使用表明文本嵌入世界之中的方式及文本与世界复杂交错的联系。这种现世性的情境性就建构在文本之中,文本就是它所谈论的世界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对于认识和把握一个客观存在的世界,文本是极其重要的。“文本是一种被处于统治地位的文化制度化了的力量体系,是一种权力的事实”[7]45
二、文本的帝国视野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率先基本完成,工业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英国国内的资金和销售市场远远满足不了生产高速发展的迫切需求。英国开始对外扩张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掠夺原材料,并倾销工业产品,成为世界工厂。1837年,18岁的女王维多利亚继承英国王位。登基之日,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踌躇满志,她在日记中地这样写道:“我将尽力履行自己的职责。我虽然很年轻,对许多事情缺少经验,可是我确信,几乎无人像我这样怀着为国为民的良好意愿去做合适而正确的事。”[9]女王这里所指的“合适而正确的事”日后证明是英国积极向外侵略扩张、称霸世界的帝国主义。这与女王后来的首相狄斯雷利所见略同:东方,是一项蓬勃的事业。[10]英国社会开始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扩张者渴望的眼睛里再也无法容纳小小的英国版图。要恢复英国古老的霸主地位,女王敏锐地觉察到靠的是实力而不是风雅。这个时代所推崇的英雄是那些富有侵略性和扩张性的商人、传教士和殖民者。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时期,大力推行炮舰政策,争夺海上霸权地位,侵占海外殖民地,大肆掠夺他国财富。
《简·爱》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出版的,男主人公罗切斯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他身上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时代需要威武勇猛、野心勃勃的男人,罗切斯特就代表着这类人物。他曾经“周游过许多国家,有着多变的人生阅历,同很多国家的很多人打过交道,漂泊了半个地球。”[11]151他赞成并积极响应英国的对外扩张政策:他在国外拥有多处地产,在法国、德国等地持有多处产业和别墅,就连他的婚姻也成了跨出了国门,他的妻子就是来自英国殖民地西印度群岛的牙买加人。夏洛蒂将他塑造成了具有殖民扩张性和侵略性的帝国男子,这与英国传统文学中风度翩翩的男性形象截然不同:“他头戴皮毛领,身上裹着骑手披风,系着钢扣子……他大体中等身材,胸膛很宽。他的脸色黝黑,眉毛浓密,面容严峻。“[11]126在他身上,看不到英俊潇洒、温文尔雅,有的只是阴沉严厉、盛气凌人。勃朗特通过对罗切斯特外貌描绘刻画了这个时代理想的男子形象:他胸宽腰细,从运动员的角度看,他身材很好”[11]134。尤其是他那双“圆圆的鹰眼”[11]316使他具有鹰的眼力,这是属于殖民扩张的帝国主义的视力,这种视力一次次越过英国国界,一直延伸到英国殖民地西印度群岛和东方。
文本洋溢着浓厚的海外气息,来自于英国海外殖民地的人物有罗切斯特、疯女人伯莎、简的叔叔,他们都来自于西印度群岛,圣约翰则是去印度传教。圣约翰是文本中除了罗彻斯特之外的二号男主人公,他是个牧师,长相俊美、风度翩翩,举止和谈吐无不透出一种英雄气概。在帝国主义的号召下,圣约翰满怀激情,决定抛弃英国的安逸生活,立志到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印度传教,成就一番事业。他把完成“扩大主的王国,为米字旗赢得胜利。”[11]380这一伟大的使命看作他义不容辞的责任。怀着所谓的崇高的动机,圣约翰准备把光明带给黑暗的印度。作为英国传教士,同时也是大英帝国的殖民者,把英国的宗教传播到无知的王国,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文化侵略,以此来泯灭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殖民者的天性。为殖民地人民引进西方文明、推进人类进步事业等堂而皇之的话语,总是被殖民者用作对殖民地侵略的理由。让殖民地人民相信殖民统治能驱逐黑暗、带来光明是殖民主义者寻求的最终结果。能够让土著民族这样想:如果殖民者离开这里,土著人马上会重新陷入到穷困、野蛮和落后的境地,这就是殖民主义自觉追求的效果。[12]
罗切斯特和圣约翰二人都不留恋英国安逸的生活,而是充满对外拓展的激情。他们的目光早已穿越了客厅窗子,远远地落在广袤的大地上。在文本中勃朗特充分显示出丰富的地理学和博物学知识。文本中多次提到过地球仪,简在寄宿学校所上第一节课,就是谭波尔小姐讲授的地理课,“这位罗沃德学校的校长,在放在一张桌上的两个地球仪前面坐了下来。”[11]49在桑菲尔德府简给阿黛勒上课的图书室里也放着一对地球仪。地理学和博物学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殖民事业的一部分。海外地名更是遍布字里行间,在文本中勃朗特把地理学与博物学知识和海外故事混杂在一起。比维克所著的《禽鸟史》、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以及东方的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都是简小时候最着迷的几本书,这些书都是关于海外风俗、民间传说及风土人情的知识。
女主人公简从小就成了孤儿,姿色平常,虽然处在帝国的边缘,却敢爱敢恨,勇于反抗权威。简以昂扬的斗志、奋发的精神深深地打动着读者,这与大英帝国当年不可一世、雄霸天下的气势完全吻合。从童年时代起,简对外面的世界就充满着向往:“毫不怀疑有朝一日我会去远航。”[11]19罗沃德慈善学校八年封闭的生活并没有阻挡住简对外面世界热切的期盼:“期望那种能超出极限的眼力,不仅能看到繁华的世界,更能看到曾听说过却从未到过的地方。”[11]121在沼泽居,当圣约翰力劝简随其一道去印度传教,简因为留恋罗切斯特,才没有跟随圣约翰去印度。但简并不缺少这种热情:她愿意做他的助手与他一起漂洋过海来到印度,一起在东方的烈日下辛苦劳作。
三、文本的帝国叙事
在维多利亚王朝盛世时期,作为强大的宗主国臣民,勃朗特写作时在身份和道德方面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英国国民的种族优越感。假设为欧洲民族的优越与想象中土著民族的低劣之间的对立是殖民主义社会中权力与利益关系的模式主要表现形式。女主人公简作为生活在大英帝国父权制社会的边缘人物,在她身上,体现出女性在19 世纪工业化社会中逐步脱离了家庭和男权的束缚,追求个性和自我的现代女性意识。简的形象成了女性自尊自强、勇敢理性的精神象征。勃朗特虽然认识到简在父权社会中的边缘地位,但作为大英帝国的国民,她完全忽略了伯莎的生存困境:伯莎处于边缘的边缘。伯莎是来自英国殖民地的女性,她处在父权社会边缘之外。她在赞扬了一位英国女性的同时又毁谤了另一位来自殖民地的女性,这样勃朗特就暴露了她在文学创作时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
在文本中伯莎如同一个鬼影,她的每一次出场都弥漫着恐怖可怕的气氛,就连对她的外貌描写,勃朗特也刻意让人产生毛骨悚然的感觉。文本是借简的目光来透视伯莎的,通过简与她的四次接触,伯莎作为一个正常人身份的遗失以及魔鬼和动物属性在文本中逐渐凸显出来。伯莎的第一次露面是她企图放火烧死熟睡的罗切斯特的一天晚上。简先是听到一阵恶魔般的笑声,随后就闻到一股强烈的焦臭味。伯莎第二次出场是一个深夜,她疯狂地咬伤了前去探望她的弟弟梅森。简先是听见一阵时断时续的、同狗叫差不多的嚎叫声,而后得知伯莎像只母老虎似地撕咬着梅森。伯莎的第三次出现是深夜幽灵般的撕碎了简的婚纱。伯莎面目狰狞的形象通过简的叙述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伯莎野蛮的面孔令简想起了凶恶丑陋的德国吸血鬼,因为这是一张没有血色面孔。至此,伯莎在整个作品中已经出现了短暂的三次,或者以魔鬼、或者以怪兽的形象出现。而对于这个可怕的幽灵,勃朗特从来没有直接对她的身份进行过明确的说明。殖民地人民的主体性被完全抹杀,他们一直处在殖民话语策略的客体的他者地位。
伯莎在文本中最后一次露面完全以野兽的形象直接出现在简的面前:它像是四肢着地趴着,又抓又叫,好似某种奇特的野生动物,只不过有衣服遮体罢了。这条穿了衣服的野狗直起身子来,高高地站立在后腿上。[11]339伯莎被活生生地描写成一只穿着衣服的野兽,斯皮瓦克认为《简·爱》是一部充斥着帝国主义理念的叙事文本,伯莎这一人物是“根据帝国主义原则制造出来的形象……通过伯莎这个牙买加的克里奥人,勃朗特有意混淆了人与动物的界限。”[3]228对于勃朗特来说,伯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他者,充其量不过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一个道具。不过,这个他者刚好是来自英国殖民地的女人,勃朗特这一貌似随意的人物安排却耐人寻味。这个不经意的安排流露出她对殖民地人民理所当然地贬低以及她作为英国臣民对自身无法掩饰的优越感。在构建自己的文化体系过程中,西方知识分子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压制相对于欧洲的无名异己,并且对异己做出同质性空间处理。殖民地女性往往被架构成了一个“无权的同质团体,她们只能充当殖民地特殊文化和社会经济体系潜在的牺牲品。”[13]勃朗特透过简的视觉刻画了伯莎面目可憎的形象,又用罗切斯特的逻辑把伯莎关进阁楼。罗切斯特认为他和伯莎的婚姻受到父亲和伯莎家人蒙骗。由于长兄继承父亲的全部家产,父亲为了让这个次子过上富有的生活,刻意安排让他娶了一个来自牙买加的克里奥女人作为他的新娘,以获取新娘所继承的3 万英镑的陪嫁。牙买加是大英帝国所属的殖民地,这场婚姻以猎取殖民财富为目的。罗切斯特作为一个猎取殖民地财富的殖民者,在物质和欲望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靠伯莎的陪嫁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同时他也被伯莎的美貌、魅力和才艺迷住了。婚后他得知伯莎的母亲是个被关在疯人院的疯子,这对于他的英国身份来说是个巨大的耻辱。他开始对伯莎感到厌恶,作为克里奥人的妻子在他眼里“平庸、低下、狭隘”,她的智力相当于“矮小的黑人”,是个“魔鬼”、“荡妇”、“怪物”。[11]357这与他在桑菲尔德府遇到的“温顺、勤奋、坚定……文雅而又英勇”[11]466的简有天壤之别。这种刻意的鲜明对比完全符合帝国的殖民想象,因为在殖民者看来,统治者天生具有上帝所赋予的美好品质,而殖民地人民野蛮刁钻、愚昧懒惰且品质恶劣。
为了挣脱同伯莎的联系,罗切斯特将她从牙买加带回英国后,就把她禁闭在低矮昏暗的阁楼里。作为殖民者罗切斯特不仅掠夺了伯莎的财富,还像对待动物一般剥夺了她的人身自由,将她置身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之中。十年的禁闭使伯莎完全丧失了自我言说的能力,致使她的人格扭曲而成为一个恶魔般的疯女人。而罗切斯特也因此有了放纵自己的理由,“随便到哪个地方旅游,结识你喜欢的新关系。”[11]360在听了罗切斯特荒唐的诉说后,简居然表示“我怜悯你——我真诚地怜悯你……我感觉到这番话很真实。”[11]409一个秘而不宣的对伯莎进行迫害的合谋隐藏在这种同情的背后:仅仅因为伯莎是来自英国殖民地的克里奥人。
作品结尾女主人公简意外地继承了客居在马德拉群岛的叔叔的一笔可观的遗产,简的叔叔生前曾是伯莎的弟弟梅森制酒业的代理商,频繁往返于英国、马德拉群岛与西印度群岛之间。简所继承的遗产就是从殖民地流向宗主国的殖民财富,也就是这笔遗产使得简实现了改写边缘身份的梦想,成为和罗切斯特平等的人。赛义德认为文学时常表明它自身不断涉及并且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欧洲在海外的帝国扩张,从情感上支持、再现并巩固了帝国的实践。虽然小说并不鼓动人们对外扩张,但小说很少妨碍帝国的加速进程。
文化代表着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文化也是一个社会的知识和思想精华的贮存库。当它与民族联结在一起时,文化便成了一种与异质文化较量的舞台。在赛义德看来,小说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之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联系。“这一联系并不会削弱或毁坏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价值。正好相反,由于它们的‘现世性’,由于它们与其真实的背景之间的复杂的从属性联系,它们作为艺术作品才更为有趣和更有价值。”[14]从某种程度上说,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形式,叙事小说便成了帝国主义的同谋。
[1]Lewes,G.H.Recent novels:French and English [J].Fraser's Magazine,1847 (36),686-695.
[2]Cecil,Lord David.Early Victorian Novelists:Essays in Reevaluation[M].New York:Bobbs-Merrill,1935,121-122.
[3]加亚特里·斯皮瓦克.三位女性的文本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杨乃乔,译.后殖民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Woolf,Virginia.Jane Eyre and Wuthering Heights.In Andrew Mcnellie.(Eds.)The Common Reader (First Series)[M].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29,157.
[5]Poovey,Mary.Uneven Developments:the Ideological Work of Gender in Mid-Victorian England[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126.
[6]Edward W.Said.Orientalism[M].London and Henley:Routledge& Kegan Paul,1978,10.
[7]Edward W.Said.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8]Christopher Norris.Deconstruction:Theory and Practice[M].Lon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2,89.
[9]Gordon S.Haight,ed.,The Portable Victorian Reader[M].London:Penguin Books,1988,20.
[10]Edward W.Said.Orientalism[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9,13.
[11]夏洛蒂·勃朗特.简·爱[M].黄源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4.
[11]法侬.论民族文化.罗钢,刘象愚,译.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78-279.
[12]蹇昌槐.西方小说与文化帝国[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177.
[13]Edward W.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M].New York:Alfred A.Knopf,199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