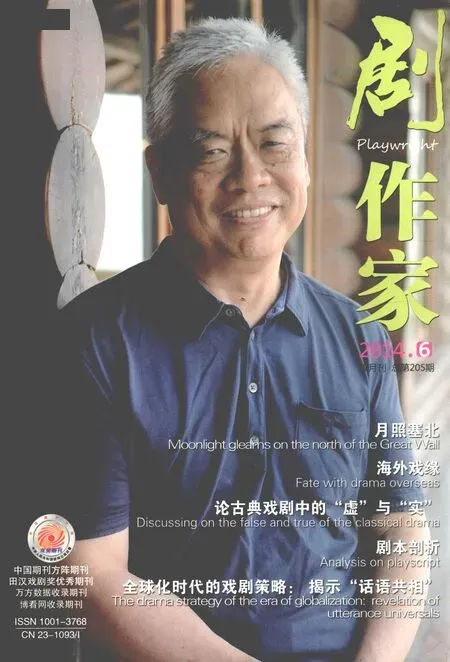论王治普的平民情结
张 阔 尹传兰
论王治普的平民情结
张 阔 尹传兰
摘 要: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牡丹江剧作家王治普借助改革开放这个特殊的时代,以东北的黑土地为背景,从独特的平民视角出发,创作出了一系列平民文学作品,塑造了具有典型性格的底层民众形象,为大众勾勒出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底层的平民生活画面。这种蕴含有丰富意蕴的人物形象及其独特的平民化创作手法是作者内心深处内隐的平民情结的艺术外化,充分展现了王治普朴实平淡的人生态度和对平民审美取向的艺术追求。
关键词:王治普 东北戏剧 平民情结 地域情愫
在中国,“平民”这个概念与文学的真正契合应该是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这个时期“平民文学”作为建设新文学的一个主张和口号被提出,并且得到文学革命者的支持与推广。这个概念由周作人首倡,他认为:“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1]牡丹江剧作家王治普以话剧的文学形态为我们书写了一群生活于底层的民众最为普通、最为本真的生活状态,真实并艺术地反映了他所经历的时代。
王治普生活在文革和改革开放交织的这一特殊年代,长期的底层民众生活让他收获了丰富的人生阅历,这些人生阅历“不仅被经历过,而且它的经历存在还获得一种使自身具有继续存在意义的特征,那么这东西就属于体验,以这种方式成为体验的东西,在艺术表现里就完全获得一种新的存在状态。”[2]也就是说,王治普丰富的人生体验经过长久的积淀,凝构成为一种稳定而又强烈的无意识冲动——平民情结,不断地冲撞意识限阈,最后将其审美艺术化。可以说,王治普的戏剧作品正是深隐于内的平民情结的外化。运用平民化的创作手法剖析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敏锐地抓住了他们身上的时代特色,书写了小人物的命运历程,同时也促使读者对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
王治普在底层环境中积淀下来的生活经验为他平民化的创作走向提供了宝贵素材,对底层百姓命运的关注使其内心滋生出一种平民意识,这主要体现在他所创作的戏剧作品中底层平民形象的择取和地域化的语言风格等。
一、底层民众的群像雕塑
自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剧作家群中的每位作家都本着现实主义的创作基调,塑造了带有地域特点的人物形象,这些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印证了每位剧作家丰厚的生活底蕴和扎实的戏剧功底。如:哈尔滨市的剧作家马风塑造了许多城市知识分子形象;齐齐哈尔市剧作家陈启程、吕明在《魂系鹤乡人》中塑造了铁汉子的工人形象;伊春市剧作家闫洪昌在《归国人的儿子》中塑造了山区林都人的形象。而王治普塑造的平民形象源自于乡土农村,由于受到改革开放的洗礼,生活在乡下的广大农民也逐渐摒弃陈腐落后的守旧思想,开始响应国家政策,积极探求科学致富的路子。然而,他们纯朴耿直的性子没有变,他们泼辣豪气的洒脱没有变,他们还是那群善良质朴的普通人。王治普在东北农村曾有过长达二十一年的平民生活经历,这使他对生活在特殊时期的平民的生活状况及生活环境了如指掌,同时也促使他深切关注这些普通群众的精神心理,因此他以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为原型,塑造了很多纯朴善良的平民形象,比较典型的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一类是淳朴善良的新农民形象。代表人物有《女大十八变》中的喜鹊和得福;《痴心庄稼汉》中的佟柱等。这类人物是改革开放以来新农民的代表,他们不仅在思想上与时俱进,顺应时代潮流,他们在实际的行动中,也起着引领作用,他们带领全村男女老少探索了一条脱贫致富的途径——科学致富,同时也提高了全村人的思想觉悟。在《痴心庄稼汉》中,大学生佟柱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毅然放弃城里优越的工作机会,回到家乡为村民共同致富出谋划策。这个人物形象与作者自身经历有些相似之处,王治普也同样是为了戏剧创作放弃了城里优越的生活条件,而选择了回归小城,静心写作。他们身上体现的不是小人物的热心而是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大义。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善良、淳朴、勤劳能干以及对待爱情的忠贞。作者着重突出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意在发扬普通百姓的性格中向善的一面。他的作品中尽管也有像洋拉子,三丫这类性格直爽和泼辣的人物形象,但他们的内心深处也有着农村人的淳朴和憨厚。除此之外,作者赋予这些善良的人们圆满的结局。在《痴心庄稼汉》中的佟柱最终成为了共浴村的村长,共浴果园的总经理,并如愿以偿地娶了自己恩师的女儿。因此,从王治普的戏剧作品中就可以看出,他的平民情结具有的向“善”的倾向性。这也提升了戏剧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
另一类是市井小民形象。代表人物有《远亲近邻》中的清洁女工翠兰,《当代酒仙》中的“陪酒专员”吴新等。这类人物属于城市中的底层民众,他们一方面抱怨社会无法满足其物质欲望,另一方面渴望通过复杂的人际关系一步高升,摆脱宿命。因此王治普运用反讽的艺术手法将这类人物内心深处暗藏着的投机取巧的小人物心理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物内心道德底线之间的矛盾,凸显了小人物对二者的权衡与抉择。如《远亲近邻》中的翠兰在看到邻家的奢华辉煌,对比自己清苦平庸之时,不禁感叹“真是人比人得死! 货比货得扔! 同住一栋楼! 有富也有穷啊,瞅瞅!这才叫上等中国人的生活呢”![3]一句话展现了其内心深处对金钱物质的渴望,以至于后来继承远亲的大笔遗产时,呈现出了癫疯的状态,肆意挥霍,同时也为自己招惹了祸端。作者将一系列跌宕起伏的情节串联到一起,将小人物内心的矛盾与冲突彰显到了极致,甚为精彩。再看《当代酒仙》中的小人物吴新,将自己的喝酒特长当成了事业飞黄腾达的跳板,在各名利场之间游走,享乐于权欲之下,最终人去楼空。作者以这种荒诞的手法讽刺了生活在城市的底层人物急切的攀龙附凤心理,与艰苦奋斗、憨厚朴实的新农民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正一反的衬托,使这个时代的平民人物形象表现的更加圆润、丰满。
二、平民化语言的幽默构织
王治普在语言上的妙用,还原了平民大众生活的本真状态。这样,一方面凸显了人物形象的个性心理;另一方面,幽默风趣的语言增添了作品本身的喜剧效果。
(一)方言土语的娴熟运用
长期的底层生活经历使王治普对东北地域文化耳濡目染,受其熏陶,他习惯性地选用普通大众的审美习惯来洞观世事、传递情感,尤其是在叙述的语言风格上,具有浓厚的平民文化印迹,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东北方言的运用。在王治普的戏剧作品中,我们发现有很多东北地区的方言和俚语出现,充满了趣味性的同时也有一定的讽刺意味,耐人寻味,令人深思。例如:在《当代酒仙》中,潘半斤喝多后,发出狂笑,并说出醉话“你咋捅咕我嘎纠窝呢”?这里面的“捅咕”和“嘎纠窝”是东北地区特有的方言,意思分别是“触碰”和“腋下”。而这种方言也只有在平民阶层的日常对话中才会出现,将这些带有地域特色的方言加入其中,增加了作品的喜剧韵味,使其更具有通俗性。又如在作品《渤海公主》中,乌氏说:“ 我俩吵架了,哪有这么当哥哥的?要杀亲兄弟、一分钱买个小王八——贵贱不是正经物。”[4]乌氏是渤海国的皇后,一般来说语言应多趋于书面化,可王治普偏偏用了一句歇后语,既生动形象地勾勒了相煎太急的哥哥内心的扭曲与阴暗,也无意中显露了作者内心根深蒂固的平民化叙事格调。
(二)暗含喜剧元素的人物命名
“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第一代职业演员是喜剧演员,最早的戏剧形态是喜剧,最古老的戏剧传统是喜剧传统。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喜剧是中国戏剧的先祖。”[5]在王治普的戏剧作品中,人物名字也成为用来营造喜剧性、构织幽默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元素。比如《女大十八变》中的“喜鹊”,寓意“喜从天来,好事将近”,潜意识中将这个人物的“大团圆”式的结局透露出来,增添了作品的喜剧韵味。再比如“大埋汰”,“埋汰”在东北方言中有“脏,窝囊”之意,从这个名字就可以推测其人必定是一个形象颓废之人,这样的小人物现身于作品中,在“得福”等正面人物的衬托下显得愚钝可爱,不禁令人发笑。又比如“破锣”说明这个人是一个比较爱说闲话,得理不饶人的蛮妇;“洋拉子”本是寄居在树上的一种吐水的毛毛虫的别称,用以命名这个人物,寓意其人满肚子坏水,“喜鹊呀,别站在树底下,那树上净是洋拉子,整天拉坏水,快进屋用面碱水刷刷牙!(向对门啐了两口)呸呸!恶心!(拉喜鹊进了屋)”[6]。在这里,用这个外号形容这个人物,与其人物自身的形象比较贴切,无意中增加了作品的诙谐之意。《当代酒仙》中人物的名字更是以喝酒的多少来命名,如“潘半斤”、“陈三两”、“王一提”。此外还有《白旗屯的老男老女》中的“扁屁”是一个遇到急事就放屁的搞笑人物;“耗子”是一个善于耍小心机,偷奸耍滑如老鼠的小人物。这样的名字设定,一方面是为了让读者更能明确剧中人物的个性,另一方面也展现了作者独特的喜剧创作风格,且不说他们的语言,光看其名字就足可以引人发笑了。另外,王治普善于捕捉平民阶层的心理活动,通过人物的行为方式,将农村人固有的“憨劲儿”和“虎劲儿”表现的淋漓尽致。在《女大十八变》中,作者叙述了多场“洋拉子”和“破锣”之间的拌嘴戏,例如:
“破 锣 (不甘示弱)得福妈呀,还真出了怪事啦......
洋拉子 啥怪事?
破 锣 那老母猪八成要长出两根大牙。洋拉子 真有这事儿?
破 锣 真有就发大财啦!我怕那老母猪嘴里吐不出象牙!是不?
洋拉子 你是指鸡骂狗啊?
破 锣 哪里,我是指狗骂猪!”[7]
二人你不让我,我不服你的刁蛮劲儿,不仅没有给观众留下蛮横可憎的形象,反倒觉得他们很真实,很可爱,这就是王治普表达喜剧效果的高明之处。
三、平民文学创作的现实基调
王治普曾经说过:“作为一个编剧,当然有自己的追求。我追求的是三个字:即真、情、味。所说的真就是不能再凭空胡编乱造了,要反映农民的真实,也就是源于生活。所谓情,让观众和台上演员情感交融在一起,没有情,就扣不住观众的心,所说的味,就是作品的地域性”。[8]王治普的戏剧创作的高潮期是在“文革”之后,此前,他在东北农村经历了长达21年的劳动改造,度过了难以想象的艰苦岁月。他曾在寒冷的冬季参加刨粪比赛,每天都需要工作二十几个小时,但是这段难忘的平民生活经历却为他后来的戏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并且使他的立场、观点、感情等都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因此,丰厚的农村实践经验成为他戏剧创作的源泉,也使他的平民化写作更倾向于现实性和真实性。对于艺术的真实性,鲁迅有过这样一段话,“怎样才能达到艺术的真实性呢?”鲁迅认为,“必须从作家所熟悉的生活出发,从自己的实践和认识的范围中选取创作的题材,如果作家缺乏积累,底子不厚,库存不丰,又硬去描写他所陌生的人物和事件,势必适得其反。”[9]王治普的戏剧创作充分印证了这一点,他大多数戏剧作品的取材都来源于其生活过的东北农村。例如:《女大十八变》中的喜鹊这个人物形象就来自于王治普曾经认识的一个朴实的东北女性“铁姑娘”,这个人物同剧中的喜鹊一样起初是斜视,后来通过动手术修正过来了,而当地的农村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也逐渐走上了致富的道路。时代的进步激发了王治普投身于平民文学创作的积极性,因此《女大十八变》等一系列平民题材的戏剧作品应运而生。此外,在农村改造期间,王治普与很多农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他的散文作品《萝卜和白菜》、《两张油饼》中,描写的张士元、孟昭勤等对他的关心实际上就是那段艰苦岁月的真实写照。可以说,农村的这段生活经历不仅让王治普的生活丰富了,同时也让他更加深切的体会到了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对于平民阶层的思想观念及价值取向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及高考制度的恢复,底层农村百姓也开始认识到人才的意义和价值,由原来的“勤劳苦干”转变为“勤劳巧干”,逐渐认识到科学技术对于提高生活水平的重要性,这为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因此,在王治普的戏剧作品中也体现了平民阶层的这一新的变化,在《女大十八变》中喜鹊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先富带动后富”,并且运用科学的方法养殖木耳,为全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随后随着产业的逐渐扩大,开始引进大学生人才。《痴心庄稼汉》中的佟柱也是作为一名大学生,甘愿放弃城里的优越条件,转而为家乡服务,培育出了一大片果园,带动了全村的致富积极性。
王治普和他的老伴儿之所以选择回归小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想静下心来继续自己的戏剧创作,这种安于平淡,不谙世俗的性格与他的创作风格不谋而合。不仅如此,拥有着丰富人生阅历的王治普还有着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在被下放到农村期间,他密切地联系当地的百姓,贴近他们的日常生活,即使是回到城市以后,他也时刻关注着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生活,将平民百姓的平凡生活与文学艺术融合在一起,为读者提供了更多时代印记,这也符合了文学艺术“为人生”的宗旨。
情感的生成需要特殊的内在驱动力,王治普对底层民众的深切关注,幻化成一种平民视像,他笔下的芸芸众生正体现了他朴实平淡的人生态度和平民审美取向的艺术追求。同时伴随着黑土地成长起来的王治普也为八十、九十年代的东北地区的戏剧创作增添了一抹亮色,极大地促进了东北戏剧的繁荣和发展。
参考文献
[1]许觉民、张大明.中国现代文论[M].安徽教育出社,2010(9):170.
[2](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78.
[3]杨宝林、王治普.远亲近邻[J].剧作家,2008(6):44.
[4]王治普.渤海公主[J].剧作家,2006(5):4.
[5]朱伟明.中国古典喜剧的价值与意义[J].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00(3):84.
[6][7][8]丁汉荣.王治普剧作集[M].北方文艺出版社,1999(3):7-49.
[9]陆贵山.论文艺的真实性和倾向性[J].社会科学辑刊,1982(5):123.
(【基金来源】: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项目《牡丹江戏剧现象研究》,课题号:11E019)
责任编辑 原旭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