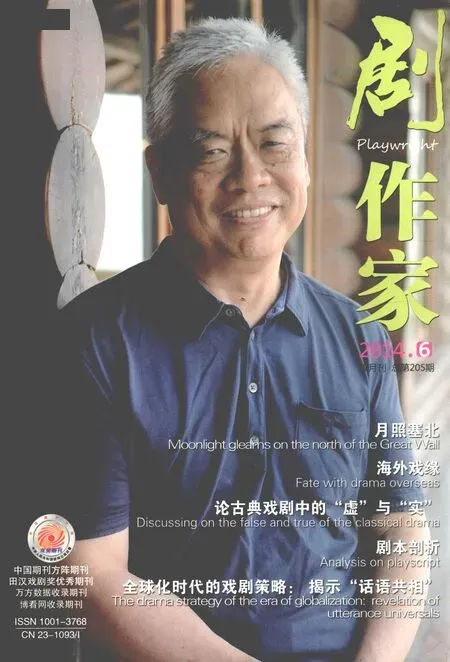谈《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的剧本改编
顾振辉
谈《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的剧本改编
顾振辉
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有点拗口的话剧,有些不明所以。可查过之后才知道,这是根据美国著名纪实性文学作品《相约星期二》而改编的戏剧作品。而且这部作品由台湾“果陀剧场”搬上舞台后至今已经热演了一百多场。该剧讲述了美国米奇在毕业多年后与大学时代最敬爱的“教练”莫利教授再度重逢,可莫利教授患上了“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就是因为最近“冰桶挑战”而闻名的“渐冻症”。莫利教授将逐步丧失肢体的控制能力而最终可能窒息而死。莫利教授与米奇相约每周二下午来他家里上课,直到最后。于是,在莫利教授生命里最后14个周二里,莫利与米奇分享了诸多感悟,关于人生、家庭、婚姻、事业、恐惧、欲望等等,让米奇对人生有了更深的体悟。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确,有了本身优秀的原著为基础,再加之两位演员特别是金士杰的高超演技,保证了人物的表现力,而导演以简洁的舞台形式、灵活的舞台时空配合以恰到好处的声光效果,使全剧透出淡远悠长的隽永感。毫无疑问,全剧汲取了原著本身的精华,将原著对于生命意义的探寻与人性的关怀都浓缩于近两个半小时的演出中。同时在两人的你来我往的对手戏中也不乏幽默的闪光,全场观众也时不时地被逗笑。然而,人性终极的关怀依旧使莫利教授与米奇进行最后道别时,台下观众抽泣声更是此起彼伏。
无疑这是一个上乘的戏剧作品,但并非毫无瑕疵。该剧在内容与演员表演上的优点在早前的各种赞美称颂的剧评中已无需多言。笔者从该剧里,看出一个关于文学作品改编成戏剧的问题。近年来,剧本文学性是在戏剧批评界一直被提起的问题,在不断挞伐那些无视作品的文学性、只知拼贴、靠噱头大撒狗血甚至毫无逻辑的戏剧作品时,笔者们也得认识到,在呼唤戏剧作品文学性的同时,戏剧作品也有其创作本身的规律,在进行剧本改编时,并非以原原本本地将作品搬上舞台就能取得良好的戏剧效果。
在观剧前,笔者就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评论:“本人在剧场中途瞌睡了许久,醒来时还听到有观众的鼾声。”[1]由于演出过于火爆,笔者花了数倍的价格买了一张二楼最后一排的黄牛票。可在整个观剧过程中,笔者也的确发现有睡着的观众,坐在笔者附近的观众有玩手机的,也有时不时在窃窃私语。同时,在观剧过程中,并没有因为笔者的最后一排的位子而影响笔者的视听效果,可笔者也时有走神的情况出现。导演手法简洁明了,演员素质也很高,剧本也不乏妙语哲言。在观剧过程中笔者越发地困惑,问题出在哪儿?在演出结束后的演后谈里,笔者向导演提出了这个问题。导演似乎对这个问题不屑一顾,他认为这是观众素质问题,而在台北、香港从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并且,他强调他只是如实地把剧本翻译过来,如实地把剧本搬上舞台,并没有过多花哨的导演手法。
后来,笔者在演出手册中得知,最早的改编是由美国人完成并搬上舞台的。导演杨世彭教授看中这个戏后,就翻译成中文并搬上舞台。杨世彭导演是戏剧学博士,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戏剧与舞蹈系的荣休教授、系主任及剧场主任,自1990年退休后一直在两岸从事戏剧编导工作,还是香港话剧团荣休艺术总监。
可杨教授这样的回答对笔者来说除了敬佩导演对于文本的尊崇之外,并不能令笔者完全信服。观众看戏玩手机、闲聊甚至看睡着了,笔者认为是不能简单归咎于素质问题的。难道这里面就没有演出本身的问题?因为,就笔者所见,这样的情况在剧场里也并非个例。就好比学生上课睡觉,可能是学生累了,或者调皮赌气。可难道就没有老师本身授课方式的问题?老师水平不够,讲得枯燥无聊,甚至云里雾里,让平时学习压力大的学生们昏昏欲睡,这又怎能完全归咎于学生素质低呢?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就在于对于原著的态度问题,这也是文学作品改编成剧本时始终无法避开的问题。是照着原著来改编,还是有选择地进行二度创作。毕竟文学作品不同于剧本。它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体裁,在改编的过程中自然不能简单地如实照搬。中国话剧史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吴天与曹禺对于巴金小说《家》的改编。吴天的相对“忠于原著”的《家》虽然红极一时,但在历史上终究是昙花一现。但曹禺创造性的改编,却使它被改编成为了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之一而不断上演。
回到这个戏来说,该剧的叙事时序还是按照原著来展开,以一种平铺直叙的方式来表达原著的精神内核。这样的叙事方式下,往往需要相对紧凑的叙事节奏来推进剧情。可原著并非是一个故事性很强的作品,而是以“心灵鸡汤”式妙语哲言来启迪观众与读者的。这样一来,整个剧情基本就沿着整个小说的脉络来推进,米奇自叙前史,介绍人物,然后除了前史中莫利教授与米奇在校园里的交往,就是得知莫利教授开始得病之后,米奇每周二的拜访。可这毕竟是将近二十万字的文学作品,并非仅靠万余字的剧本与两小时的演出时间就能全部承载的。因为在有限的演出时间里,除去“开课”前的交代,留给正式“开课”的时间也不多。在这14堂课里,人生、家庭、婚姻、事业、恐惧、欲望等等内容必然无法像小说里那样气定神闲地一一呈现,所以所谈的内容则多少会有些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的感觉。
在演出过程中,导演也似乎力图通过简洁且形散神聚的方式来向观众诠释该剧。可剧本本身依赖原著的成分太多,也可以说是过于“忠于原著”,以至于在改编成剧本与搬上舞台时,忽略了戏剧性的需要。由于戏剧与小说在容量与叙事方式上的不同,需要在演出过程中,通过叙事者来交代一些观众需要知道,但不必要演出来的前史与情节以避免演出超时。这就需要“叙事者”在演出中尽量简洁明了,并且能够有引导性的内容来使观众始终关注舞台上情节的发展。卜学亮所饰演的米奇在剧中以“叙事者”的身份出场时所叙述的内容,却一直是以介绍性的内容平铺直叙地向观众交代剧情与人物心理。即便演员与导演为此设计了不少舞台动作,可在言语之间还是会在不经意间透出一些散漫与随意,再加之相对之冗长的篇幅,自然会让人感到乏味。
从戏剧行动上来讲,米奇的每次探访本身不带有强烈的动作性,虽然在剧中加入了莫利教授的一句意味深长的德语来做首尾呼应;莫利教授对于米奇妻子简宁的关注来作为花絮,等等。但作为全剧的贯穿行动线,仍显平淡。因为大幕拉开不多久,观众随着剧情的交代,就知道了患上“渐冻症”的莫利教授会因为身体机能日渐退化而去世;同时也大体知晓了剧情的大体架构——米奇共14次每周二的探访。这样全剧后续的悬念就降到了最低,叙事模式也无疑将大大降低剧情本身的紧凑度与其内在张力,松弛与拖沓感自然也随之而来。观众就只能看演员如何在这个架构里诠释人物的能力,编剧将以怎样的妙语哲言来填充这个架构。这样的处理显然是受了原著叙事风格的影响。如此一来便使得该剧在叙事节奏的紧凑度与剧情本身张力上,无法在整个演出过程中都能牢牢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这就需要观众在欣赏的过程中自行调动起注意力,始终全神贯注地投入到舞台演出中去。显然,这就过于苛求观众了。
这里涉及到文学作品与剧本两者不同的审美体验,两者的接受者——观众与读者,显然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接受方式。文学作品的阅读是具有灵活性的,看累了可以过一天再看;在读到妙处时也可通过回读来细细品味;看完了以后,甚至再看一遍,每一遍或许都会有不同的审美感受。而且阅读时的地点与状态也更随意,可以在上班通勤途中的地铁上看,可以在图书馆或书房里正襟危坐,也可以在卧室或者公园里闲适地以自己感觉舒适的姿势进行阅读。同时,读者对于文学作品内容的读取与理解在相对灵活自由的阅读形式间也相对更为主动。
相对于小说阅读的灵活与自由,戏剧欣赏则相对被动。观众首先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剧场空间内与固定的座位上来接受舞台上所呈现的内容。在人群密集的公共场合中,因受到基本的公共道德的约束,人的状态不可能像在自己的空间里那轻松自由,再加之演出在剧场时空中不可逆,故而也不可能颠来倒去地让观众反复品味。这些戏剧欣赏的特性无疑都会影响观众对于演出作品的理解。自然,相比于小说阅读,戏剧欣赏相对更为被动,更需要各部门的通力协作,来保证戏剧作品的接受度。作品的接受度与观众的审美趣味与个体素质有关,剧场里成百上千的观众的接受度自然是参差不齐的。但保持观众的注意力则是戏剧作品在创作或排演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这就要求戏剧作品的编导者在剧情与舞台呈现上保证戏剧作品的张力与节奏以抓住观众的注意力。
在明白了文学作品与戏剧在欣赏上的差别,就不难理解这个优秀作品的瑕疵所在——从原著改编成剧本时,太过忠实于原著,以至于在叙事方式上也承袭了原著的风格,而导致了叙事节奏的松弛。此外,还是应注重浓缩与精炼,着力于剧情的紧凑与张力。倘若能不失原有意味的同时,将剧情设计得更紧凑、更具有张力一些或许会让这个戏剧作品更上一个台阶。即便如此,瑕不掩瑜,这些问题虽然存在,但凭借着原著本身所承载的文学性与精神内核,再加之两位优秀的演员,尤其凭借着金士杰这样的杰出表演艺术家的精湛演出,仍足以撑起这一台好戏。这就使该剧从内容上来看,亦不失为一个上乘之作。
参考目录:
[1]见h t t p://w w w.g e w a r a.c o m/ drama/46010994
责任编辑 姜艺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