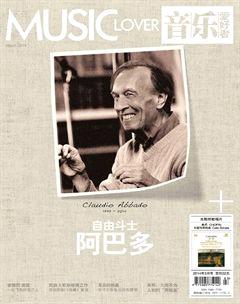何样的灵性与魅力
方向真
如同走近一个可能相爱的人——走进某个大师的音乐,靠的是机缘和内心聆听的渴望,寻觅的渴望。某一天,我突然被肖邦打动,神魂颠倒地一遍一遍播放他的夜曲——《降B小调第一夜曲》《降E大调第二夜曲》《C小调夜曲》《降D大调第八夜曲》——继而是他的玛祖卡曲、奏鸣曲、回旋曲、他的并非舞曲的圆舞曲……这个春天,我的心灵几乎被他的音乐充满。
音乐,甚至比诗歌还要神奇。它越过思想的路径,越过欲望森林的火焰,越过断崖处盘旋的黑鹰,直抵心灵,于生命的呐喊之上搭建起通天的彩虹——连接天空、地平线的无限高远的纯净之邦。意绪、想象或飞翔或凝定于某一空间某一瞬间。音乐唤起的是深切、柔软、勇毅、高贵的情感,难以表述的、无法归类的无尽美丽的情感。那么,肖邦的音乐呢?那看似简单却极富密度与回旋质感的旋律,那明晰而不张扬的和声,那无与伦比的从容、细腻,恰切的舒放与节制,表现出极致的优雅、高贵。与当年贝多芬疾风骤雨般的激情与明媚的柔情打动我,与马勒的沉雄悲悯以及德彪西难以言传的意绪打动我不同,肖邦音乐透出的优雅、从容、高贵的气质令我怦然心动。肖邦的优雅、高贵,需要经历一番世事的磨砺及学会淡定从容地应对人事的烦忧和应对自身的焦灼之后,才能真正发现和体味。“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南宋大家朱熹的《观书有感》在这里可借用来揭示抵达一种境界所需的知识与阅世经验的支撑。到了体悟更多因而内心也愈加敏感的中年再来聆听肖邦,当别是一番滋味——更入心、更彻骨的感动了。年轻时印象里明丽流畅的肖邦,如今听来又添了一层“望尽天涯路”的苍茫了。
儿时常常置身于沙龙演奏的肖邦,他的音乐考究、精妙,明显借鉴了沙龙风格。但他那独具的、肖邦式的范式呈现出绝无仅有的灵魂话语和魅力。舒曼以“藏在鲜花中的大炮”来比喻肖邦音乐的双重魅力,另一位与肖邦同时代的钢琴家莫舍莱斯惊叹肖邦“演奏技巧的独创性极为迷人,最难的转调轻松自如,弱音处理那么巧妙,以至于不需要任何剧烈的强音来表现对比”。
顺着这个春天里瞬间被击中的感动,我开始寻觅肖邦的成长路径,去假想、捕捉他创作的灵感火花,去探寻他奇特的爱情,他的痛苦,他的欣悦,他创作的秘密,甚至,他生活中有意味的细节——
与肖邦同时代的音乐人德·兰茨如此描述他对肖邦的印象:“一个中等身材的年轻人,消瘦,浑身透着忧郁,带有巴黎人最优雅的举止。我从未见过比他更有吸引力的人。”在与肖邦同龄的音乐家李斯特眼里,“他如此高贵优雅的外表和得体的举止,使人们不由自主地把他看作王子”。肖邦天才的音乐及他无可挑剔的贵族般的举止赢得了考究透顶的巴黎上流社会的赞许。
难道是神明的眷顾,特意赋予他超人的才华和脱俗的气质?肖邦的音乐如同其人,极具吸引力。他的音乐有瑰丽的色彩和丰厚的情韵,却从不刻意和夸张;其音乐在冲跃到力量巅峰的呐喊、宣叙、挑战与柔软、隐婉、细腻、遐想、梦幻的两极间行进,于明快流畅中燃烧着裹挟一切的力量。其激情、柔情、忧郁、梦幻,皆于织体的内在平衡中微妙、自然、和谐地、肖邦式地融于一体。
早年能从古典大师巴赫、莫扎特的音乐中获取滋养,是肖邦起步的幸运。他儿时在家乡师从波兰钢琴教师齐夫尼,这位老师只让肖邦弹奏莫扎特的小奏鸣曲和巴赫平均律中最易弹奏的前奏曲和赋格,他认为初学毋需弹奏其他音乐家的作品。他为肖邦规划了一条严整、经典的学习计划,使得肖邦一开始就集中时间和心思从大师的作品出发,绝无旁骛地走上最佳的、经典的学习路径。这之后,肖邦又练习贝多芬的几首奏鸣曲。对贝多芬最后的三重奏之一,肖邦写道:“从未听过如此美的作品,贝多芬真可以傲世天下。”肖邦用自己内心的体验来感应和解读贝多芬,与贝多芬之间的共鸣令他体验到了音乐妙不可言的情状——身心的巅峰状态。早年经典的学习路径启蒙了肖邦高贵的想象力。他矜持地汲取创作的灵感,即便对挚爱的祖国波兰的民间音乐,他也是审慎地取借其中的元素。古典大师的范式已经种子般长成他音乐的根基,他的音乐之树灿烂、葱郁、迷人,却从不漫芜恣肆。
谈到肖邦,就自然想到与他的爱情、创作密切相连的诺昂——他的保护人兼情人的著名作家乔治·桑的庄园。1821年乔治·桑的祖母去世,从小因父亲去世母亲改嫁而跟随祖母生活的她继承了这个庄园。庄园位于巴黎南部三百公里的小镇上,庄园有一个花园、菜园,还有一个茂密的树林与之相连。肖邦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九年。在这个此后被音乐和文学的朝圣者们前来参观凭吊的地方,肖邦创作了他一生最辉煌的钢琴篇章。在与乔治·桑的爱情破裂一年多后的1849年,肖邦被折磨他多年的肺病夺去了三十九岁的生命。
1831年,二十一岁的肖邦从他的祖国波兰来到巴黎。他选择来到法国,既为了他挚爱的音乐创作,也为了他的另一半血统——父系的法国血统。早在两年前肖邦从华沙高等音乐学院毕业之际,他的父亲尼古拉·肖邦就给格拉洛夫斯基部长写信,恳请准获一笔官方经费,使自己很有音乐天赋的、“定能成为国家有用之才”的儿子“游学国外,尤其是去德国、意大利、法国,以杰出的榜样达成自我的完善”。部长同意拨出五千弗朗林资助肖邦国外游学,但政府没有批准。于是,肖邦带着父亲给他的一点钱,短期游历了维也纳、布拉格、特普利兹和德累斯顿。这一次他来到巴黎,正遇上他的祖国遭遇了沦陷,他日夜思念他的父母、姐妹和亲人们。这一时期,年轻的肖邦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他的祖国,他可能进行下去的爱情(因为离开祖国,他与大学的声乐系同学——他心中的女神康斯坦斯彼此疏远)。他的身体和心灵都处于彷徨、漂泊的境地,仿佛一夜之间,他从一个无忧无虑的音乐王子陷入了莎士比亚笔下王子哈姆莱特的绝望。他的《C小调练习曲》及《降B小调谐谑曲》那疾风暴雨式的力量挟着摧毁一切的力量,燃烧着复仇的烈焰——他内心的痛苦已经临近毁灭的境地。
波兰沦陷两年后,肖邦与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相识。年长肖邦六岁的乔治·桑十八岁结婚,十九岁生子,那时她刚离开自己平庸的丈夫一年,正与作家缪塞经历着恋情。又五年,肖邦走进了乔治桑的庄园诺昂,将这里视为他法国的家园,从此融进了乔治·桑及她两个孩子的生活中。
乔治·桑如此描述她的情人:“肖邦是个天使,他的善良、他的温柔和他的耐心有时让我担心,我觉得这是一个太纤细、太美好、太完美的造物,难以持久存在于我们这个粗笨和沉重的人间。在马略卡,他病得死去活来,却创作出充满天堂气息的音乐……”
乔治·桑记录了创作状态中的肖邦。她在《最后的篇幅》里这样描述——
他的创作是自发的,奇迹般的。灵感落到他琴上,突然降临,完整,美妙无比——或者一次散步时某种旋律显现,他会扑到琴上,急不可耐地想要听到它。他不懈努力,犹豫不定,极不耐烦,为的是重新抓住他的旋律的某些细节以及他所构思的主题。为了能记录下来,他对这一切极力追索,为不能清晰地追回灵感而遗憾。他说这种遗憾能让他陷入某种绝望。他能连着几天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流着泪,来回踱步,折断他的羽毛笔,重复或一百次地变动一个小节,一次次写出来再抹去,第二天在坚忍不拔和绝望相混杂的执着中重新来过……
乔治·桑明白,被她呵护的、与她相伴的这个天才“不能屈服于肉体的粗糙。他要寻找的,并非是情妇,而是爱的陪伴”。在与肖邦相伴的九年里,这位小个子、一头浓密黑发的生命旺强的女作家感受着欲望的刺激与压抑,她觉得自己不得不像一个圣女般生活。在一封信里,乔治·桑向友人倾吐:“他病得太重了,以致他的爱只能是柏拉图式的。”
从与肖邦的关系中,我看到了一个比她的作品更令人敬仰的作家乔治·桑。她慧眼识才,将母爱、情爱倾注于年轻的音乐天才,不为占有,而是为了挚爱的音乐,为了彼此心灵臻于幸福和卓越的极限。深切的理解与对天才的爱惜,使一个女人拥有宗教般的奉献行动与力量。乔治·桑热切地将病弱的肖邦迎到了她诺昂的庄园,爱恋着、珍视着、保护着这个过于美好的人,她诺昂的家和她无私的爱成了身处异国他乡的肖邦的家。在这个也是法国文化人荟萃之地,肖邦不仅享有家庭的温暖与呵护,也获得了必要的交流与激励。他的才情,他天才式的灵感在诺昂的时光里凝聚成世界音乐史上绚丽的篇章。在肖邦短暂一生最关键、最富有创作激情和盛产作品的九年里,乔治·桑如同母亲般的情人,迸发出旺强的生命力、创作力及大地般爱的能量。
然而,九年的爱情因为家事的分歧、误解,也因肖邦身体的再度恶化与乔治·桑的倦怠而变为废墟。“如果我能整天闲逛,从安娜家到凯菲家,如果我不吐血,如果我更年轻些,如果我不像眼下这样被友谊压垮,那么我还有可能重新开始生活……”离开诺昂的次年,三十八岁的肖邦在从伦敦写给朋友的信里流露出他深深的无奈。肖邦的元气几近耗竭,他的生活,连同他的生命都末日般沉入黑暗。
李斯特这样描述他:“自1846年开始,肖邦几乎不能行走,每次上楼都要忍受窒息之苦。从此,他只是仗着格外小心才得以活下来。”
肖邦不曾料到,他1847年11月离开诺昂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他身后那扇情爱的门悄然关闭。诺昂不再是他心中的圣地——他病弱身体的、漂泊灵魂的庇护之所。过去的九个夏天里,他在这儿创作出了一系列最动人的篇章。
还有谁能比热爱艺术且会弹钢琴的乔治·桑更能理解、更爱肖邦了?终生不渝的爱情是人们美好的愿望,然而,像画家达利与他的爱侣加拉那样终生炽烈而专一的爱,艺术家里能有几人?曾经迸发出情感的火花,且催生出伟大的作品,已经是彼此的幸运了。试想,如果没有乔治·桑切实赋予行动的多年如一日的关切和爱护,肖邦病弱、漂泊的躯体能负载起他天才的创作吗?靠教课和偶尔向出版商出售作品,肖邦每年的收入远不丰厚。如果不是每年五个月在诺昂的居住生活,为人慷慨、喜欢赠予的肖邦能支付起他巴黎的房租、仆人、衣着、租用轻便马车的庞大开销吗?九年里,被肖邦波兰的家人视为“女保护人”的乔治·桑百般呵护着肖邦,与他相守相爱,她足以使热爱肖邦音乐的人们从心底升起敬仰的目光。
肖邦自离开故乡华沙后,一直与父母、姐妹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他的每一次灵感,每一场音乐会,他在诺昂与乔治·桑及其儿女的生活,他的每一个值得分享的讯息,都会及时通过信件传达给家人。他深知他的音乐生活来自父母姐妹对自己深切的爱和乔治·桑给予他的一切。他的家人也一直感激他的这位女保护人。
离开诺昂三个月后,即1848年2月16日晚八点半,肖邦在巴黎开了一场音乐会。剧场里座无虚席,观众是填了表格后精选出来的。肖邦苍白而坚定地现身。虽然幕间休息时他在休息室昏厥,整场节目完成得无可挑剔。他魅力四射,且延续到音乐会结束之后。让我们存下这场音乐会的节目单——
第一部分
《莫扎特三重奏》,钢琴、小提琴、大提琴,肖邦、阿拉尔、弗朗肖姆演奏
咏叹调,安多尼娅·莫利娜·迪·蒙蒂演唱
《夜曲》《船歌》,肖邦作曲并演奏
咏叹调,安多尼娅·莫利娜·迪·蒙蒂演唱
《练习曲》《摇篮曲》,肖邦作曲并演奏
第二部分
《谐谑曲》、《为钢琴和大提琴谱写的G小调奏鸣曲》的柔板和终曲,肖邦作曲,肖邦与弗朗肖姆合奏
新咏叹调,选自梅耶贝尔剧作《恶魔罗伯特》,罗杰演唱
《前奏曲》《玛祖卡》和《圆舞曲》,肖邦作曲并演奏
这场音乐会是肖邦在巴黎的华丽、完美、最后的亮相。这一次,他为生计所困,是要挣钱的。没有料到法国革命引发的全国一系列事件使他不得不取消了原计划一个月之后的第二场音乐会。通常,肖邦的演奏多在沙龙里进行,他内敛、精致的音乐更接近于倾心的交谈。在一个朋友圈的听众范围里,其音乐才能更自由更放松地真诚倾吐。音乐厅的狂热及陌生的人群令他不安。
两个月后的1848年4月21日,肖邦在两个女学生的殷切邀请下来到了伦敦。他的学生热情周到地迎接了他。在英国的七个月里,他奔走于各个沙龙演奏,却没有得到预期的报酬。再回到巴黎,病痛中的他过着半是隐退的日子。
从1847年11月离开诺昂到1849年10月17日病逝于巴黎,肖邦对已经分手了的乔治·桑始终不曾有过一丝怨言。去世的前一天,他喃喃自语:“她(乔治·桑)对我说过,我只能在她的怀里死去。”肖邦死后不久,乔治·桑让人毁掉了她写给肖邦的全部信件。她曾对肖邦说,你不再爱我了。貌似强大的她,何曾不被痛苦和失意折磨?
肖邦的出现,属于那个时代乐坛的幸运。如同开启了神奇的天窗,令古典音乐的殿堂照进一缕新的光芒,他的音乐引领人们向内心不熟悉的地方去旅行,由此获取一种发现的惊喜。较之于前辈巴赫缜密、繁复的构架织体,肖邦的音乐更具心灵的跃动——情绪的微妙变化,意绪的多重走向甚至是极致的走向。他上承巴赫,深得古典之精妙;下启德彪西,引领现代意绪之繁复。他任凭自己的艺术直觉和纯音乐灵感,放射出较之此前的传统曲式所不曾有的灵性和魅力。他的音乐直抵人心,勾魂索魄,却又从容优雅,有力而不旁逸斜出。他的音乐至今魅力不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