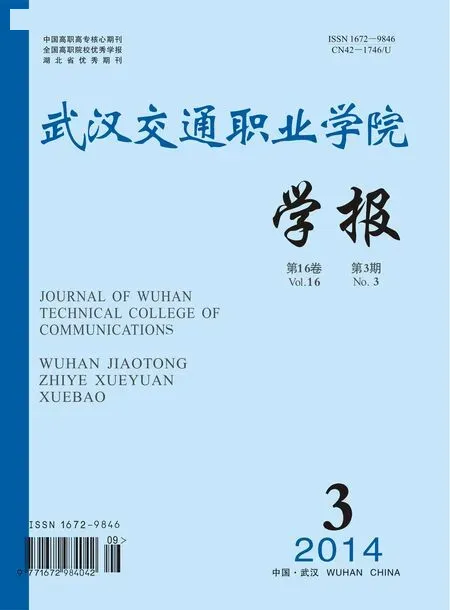商标贴牌加工的侵权问题刍议
——以新《商标法》第48条和第57条为起点*
赵丽莎(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商标贴牌加工的侵权问题刍议
——以新《商标法》第48条和第57条为起点*
赵丽莎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最典型的商标贴牌加工行为不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不会导致相关公众的混淆,因而不侵权。2014年5月1日正式施行的《商标法》增加了2个重要的短语:“容易导致混淆的”和“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有力地支持了以上观点。本文的后半部分通过细分各种“非典型”的商标贴牌加工情形,就加工方和定作方是否构成侵权、如何承担责任进行了分析、罗列和总结,得出“商标贴牌加工并非特殊问题,不需特殊规定或解释”的结论。
商标贴牌加工;混淆;商标性使用;商标法修订;审查义务;侵权责任
一、问题的提出
2014年初,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浦江亚环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环公司”)与莱斯防盗产品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斯公司”)商标侵权纠纷一案存在《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1款第(6)项的情形(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审该案。此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2012浙知终字第285号)认定,被告亚环公司贴牌加工的行为侵犯原告莱斯公司的商标权,因而判决维持一审原判。
关于商标贴牌加工是否侵权的问题,不论在实务界还是理论界,都争议颇大。最高院提审上述案件,也引起了相关方面的热议:这是否意味着司法界将统一认识?与此同时,新修正并施行的《商标法》第48条和第57条分别增加了2个重要的短语:“容易导致混淆的”和“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这对“商标贴牌加工是否侵权”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有何意义?此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的深入,商标贴牌加工的行为呈现多样化趋势。商标贴牌加工的加工方未尽合理的审查义务,贴牌商品未完全出口,定作方事实上无权……这些情形中的贴牌加工是否侵权?谁侵权?侵何权?
商标贴牌加工又称贴牌制造、定牌加工或委托加工,通说认为,贴牌加工是指加工方根据合同约定,为定作方加工使用特定商标或品牌的商品并将该商品交付给定作方,后者依照合同支付加工费的经营模式。为论述方便,本文区分贴牌加工的不同情形,将之分为“典型的涉外贴牌加工”和“非典型的涉外贴牌加工”。典型的涉外贴牌加工(以下简称典型贴牌加工)指:外国定作方仅在其本国享有合法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但并未将该商标在我国进行注册;与该商标相同或相似的商标已由我国的权利人注册并取得;外国定作方委托我国加工方制造商品并贴上该商标;加工完成后商品全部出口。上述亚环公司与莱斯公司商标侵权纠纷案即为典型贴牌加工。与之相对应,非典型的涉外贴牌加工(以下简称非典型贴牌加工)主要有以下情形:①加工方“自我委托”(指虚构委托事实)加工(并销售)商品;②定作方并非是合法的商标权利人;③商品加工完成后,除了出口,加工方也在境内(获授权/擅自)销售。
本文前半部分拟从新《商标法》第48条和第57条新增的两个短语入手,论述“典型的贴牌加工行为不侵权”,后半部分则细分非典型贴牌加工的情形并一一分析。
二、有关典型的贴牌加工是否侵权的争论——终结于《商标法》第48条和第57条
在此前的司法实践中,广东法院(2001深中法知产初字第55号、2006粤高法行终字第22号)、浙江高院(2005浙民三终字第284号、2012浙知终字第285号)等通过判决认定贴牌加工行为构成侵权,理由是:“混淆”不是侵权要件,而是判断是否近似的一个标准,因而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同一种商标(以下简称“双同”)的贴牌加工行为一定侵权,在相同或近似商品上使用近似商标的贴牌加工行为则应根据混淆原则判断是否近似,若导致混淆的,则构成“近似”,进而构成侵权。黄晖博士认为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文义解释,亦持该观点[1]。而福建高院(2007闽民终字第459号)、上海法院(2008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317号、2009沪高民三(知)终字第65号)、商标局机关党委处闫卫国处长[2]等持有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混淆是侵权构成要件,贴牌加工后的商品不在境内销售,产品上贴附的商业标识不是用作识别商品来源的商标,不会导致混淆,不可能产生损害,因而不侵权;加工方只负责加工、不负责销售产品,在此过程中加工方的商标标注行为不是商标使用行为。
可以看出,贴牌加工是否侵权的争议点主要是:①“混淆”是商标侵权的构成要件,还是判断“相似”的标准,这也涉及到如何理解《商标法》第57条第1、2项的规定。②贴牌加工是否是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这涉及到如何理解《商标法》第48条的规定。
对于争议点①,各学者对修正前《商标法》第52条第1项规定的理解不一导致对案件的分析结果大相径庭。王迁教授、吴汉东教授、孔祥俊庭长认为“混淆”是商标侵权的构成要件,不论是双同情形还是其他三种近似情形,不会导致混淆的则不侵权,因而商标贴牌加工行为不侵权:“《商标法》不仅要维护商标权人凝集在商标中的信誉,还要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商标法》要保证商标权人能够排他性地使用商标标识自己的商品或服务的出处,以及消费者能够通过商标将商品或服务与其提供者正确地联系在一起,以充分实现商标的识别功能和品质保障功能。因此,即使在相同商品或服务上使用了与他人商标相同的标志,只要不会导致消费者的混淆,就不构成对商标权的侵权”。[3]黄晖博士、王莲峰教授认为“混淆”只是判断是否“相似”的标准,只要相关公众在视觉上认为商标相同(相似),不论贴有该商标的商品是否会导致相关领域的消费者发生误认,即构成侵权。笔者认为,现行《商标法》第57条将“混淆”明确写入第2项的规定中,因此对于非双同情形,只要被专有权控制的行为不导致混淆,则一定不侵权,以上两种观点在结果上无异。而对于第1项规定的双同情形,可参考国际上的做法:将“导致混淆”作为商标侵权的前提条件,是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其中又以TRIPS协议、美国法(兰哈姆法)和欧盟法最为重要。TRIPS协议第16条第1项明确将“混淆”作为商标使用侵权的前提要件,同时,对于双同情形,认为应推定存在混淆可能。TRIPS协议区分双同与非双同情形,是采纳了欧盟的建议稿,而作出双同情形推定混淆的规定,则是采纳了美国建议稿的建议。我国现行《商标法》似乎采纳欧盟的立法模式,但我国加入了TRIPS协议,在解释上与TRIPS协议的规定保持一致,更符合我国利益。
对于争议点②,《商标法》第48条规定:“本法所称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此条是《商标法》新增,此前,该条规定在《商标法实施条例》第3条中。对比即可发现,现行《商标法》多了“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这一限定语,该条规定亦被称为“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或“商业标识意义上使用”[4]。那么,贴牌加工的行为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吗?笔者认为,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必须是将商标(或者进一步讲,商业标识)作为区分商品来源的商标来使用。对于商标贴牌加工行为而言,因其在境内使用商标并非是为了区分商品来源,因而并非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
此次,最高院以“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为由,提审亚环公司与莱斯公司商标侵权一案,似乎是想借助该案,针对商标贴牌加工是否侵权这一问题作出司法导向。而根据一二审的判决结果——贴牌加工侵权推测,最高院最终的意见,很有可能是“贴牌加工不侵权”,只是最高院打算如何论证“贴牌加工为何不侵权”,仍值得关注。
综上可知,此前由于立法的不明确,导致了对法条用语存在不同的理解,因而出现了结果相反的判决,而现行《商标法》第48条和第57条的相关规定,可为法院得出典型的贴牌加工不侵权的结论,进而终止这种乱象提供有力的依据。
三、加工方是否尽到审查义务对其是否侵权没有影响
同著作专有权和专利专有权,商标专有权也是一项“禁止他人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商标侵权行为根据侵权形态分为直接侵权行为和间接侵权行为。同著作权和专利权一样,商标权的权能也表现为对客体的专有权利,每一项专有权利都控制着一类特定的行为。如未经权利人许可,又无法定免责事由,而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即构成“直接侵权”。[5]这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国际社会认定商标侵权是看有无侵权的行为事实,而不管侵权人主观上是否明知。我国1993年商标法规定“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行为”属于商标侵权行为,2001年修改商标法时,删除了“明知”作为构成侵权的要件[6],从中可看出,构成直接侵权并不以主观过错为要件,无论侵权者的主观状态如何,都应承担立即停止侵权的民事责任。但没有主观过错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所谓间接侵权,是指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的行为。《民通意见》第170条规定:“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连带民事责任。”在知识产权法体系中,间接侵权行为人并未直接实施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但其行为具有可责备性,导致、帮助了直接侵权行为,贡献或扩大了侵权损害后果,因而需要与直接侵权人共同承担责任。判断是否构成间接侵权责任应当特别注意的是,若无直接侵权责任,则无间接侵权责任;若无主观故意,则无间接侵权责任。
我国商标法并未明确区分直接与间接侵权责任。但有学者认为,商标法第57条第4项(原商标法第52条第3项:“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虽然是与其他几种直接侵权行为相并列,容易给人一种直接侵权行为的感觉,但其规定的不是直接侵权责任,而是间接侵权责任。否则,该项规定的行为可以归于第1项情形,无需再另行规定。[7]笔者同意这种理解,这也可由新商标法新增的规定看出——将原实施条例第50条第2项确定为商标法第57条第6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故意为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便利条件,帮助他人实施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的”,从条文表述看,明显可以推定其规定的是商标侵权的“间接责任”,但也是与其他的直接侵权行为规定在一起的。
如上分析,贴牌加工商品不在境内销售,不会引起境内相关消费者的混淆,也不是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因而不侵权,即加工人不构成直接侵权。那么,若贴牌加工的加工方(受托方)未尽到合理的审查注意义务,主观上有侵害商标权的故意或过失,需要承担间接侵权责任吗?要回答此问题,关键是要明确:定作人(委托人)构成商标直接侵权吗?根据商标专有权控制某一种行为的理论,答案很明确:定作人未实施相关行为,因而不侵权,受托方亦不构成间接侵权。
四、非典型定牌加工是否侵犯商标权
如前面第一部分所述,非典型的贴牌加工有3种情形。下面笔者将进行一一分析。
(一)加工方“自我委托”(指虚构委托事实)加工、销售商品
由于委托事实上不存在,故此种情形事实上与普通的商标侵权行为无异。具体而言,可以再分为以下情况进行讨论:
1.加工方仅加工商品,并不在境内销售,涉案商品完全出口。此种情形,由于商品并不在境内销售,故加工方在境内贴上涉案商标的“使用”,并非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同时,也不会使境内相关公众产生混淆:加工方的行为并不属于商标法第57条第1、2项规定的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行为。那是否可以说加工方不侵权?这涉及到商标侵权形态的问题。如前第三部分所述,间接责任作为补偿责任,需要有直接侵权责任的成立和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本情形下,加工方的主观恶意自不待言,惟由于商品不在境内销售,无侵害境内商标权利人专有权的直接侵权行为,故加工方的间接侵权责任亦不成立。有学者认为该行为是假冒仿冒名牌的源头,因而是侵权行为。[8]笔者认为该理由并非基于法理与逻辑,不具有说服力。
综上,加工方既不用承担加工行为的直接侵权责任,也不用承担间接责任。
2.加工方不仅加工,而且销售涉案商品。由于加工方加工产品中使用商标是为了区分商品来源,因而该使用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其也会导致相关消费者产生混淆,因此加工方的行为应当属于商标法第57条第1、2项规定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加工方销售涉案产品的,应当属于商标法第57条第3项规定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此时,加工方不仅扮演了生产商的角色,也扮演了销售商的角色,其两个行为均侵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加工方仅加工商品,另有第三人在境内销售涉案商品。同上,加工方加工产品的,应当属于商标法第57条第1、2项规定的侵权。第三人销售涉案产品的,应当属于商标法第57条第3项规定的侵权行为。此时,加工方和第三人均为侵权主体,应当分别为其行为承担责任。但若第三人不知道商品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商品加工完成后,除了出口,加工方也在境内(获授权/擅自)销售
此种情形,应区分商品的最终销售地来判断加工方在境内从事的贴牌加工行为是否侵权。对于出口的部分,经上面第二部分的分析,应当认定加工方不侵权。对于最终在境内销售的部分,同上述(一)2、3种情形,应当认定商标贴牌加工行为是为了区别商品来源且最终会使相关公众发生混淆——因为商标的主要功能在于区别商品来源,只要其客观上起到了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就应当被认定为“商标法上的使用”,至于加工方在商标贴牌加工当时是否是为了区别商品来源,并不是判断是否构成“商标法上的使用”的要件。加工方的加工行为侵犯了商标权利人的商标专用权。加工方在境内销售行为,分述如下:
1.加工方在境内获“授权”销售。由于国外定作方并不享有境内的商标专用权,故其销售“授权”属于无权处分,授权无效。加工方销售的行为,属于商标法第57条第3项规定的侵权行为。但有关侵权主体为何者,似有争论:有认为侵权主体仅为加工方(销售者)的;有认为侵权主体仅为国外定作方的[9];有认为定作方与加工方承担共同侵权责任的[10][11]。
不论是直接侵权还是间接侵权,如果不存在替代责任的情形(如雇佣、监护),那么责任主体应当为行为主体。具体到本讨论情形中,有人之所以认为直接侵权主体是定作方而不是加工方,是因为其认为国外定作方“通过委托他人制造产品并在产品上标注其注册商标的方式,合法行使了自己对注册商标的使用权……加工方标注商标行为的效果应直接归属于产品的所有人”即定作方。[12]笔者认为此种看法不当。定作方与加工方签订的授权合同,本质上是一份商标许可(定作方许可加工方在境内销售涉案商品)合同,合同的效力暂不论,从许可合同性质上来说,不属于委托合同(若双方签订的是委托合同,〈合同效力暂且不论〉,定作方委托加工方以定作方的名义为销售行为的,由于加工方的行为后果事实上归于加工方,因此,销售行为的行为主体是定作方,责任主体也是定作方。但是由于我国采取商事主体登记或审批制度,双方不太可能签订该种合同。因而本文正文只讨论是授权合同的情形),加工方也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销售行为,该行为的后果并不归属于定作方。对于双方之外的任何人来说,授权销售合同的存在与否、有效与否,都不会影响加工方销售行为的效力。因此,销售的行为主体是加工方,责任主体也是加工方,且类型为直接侵权。从保护我国商标权利人来说,也应当认定国内加工方为侵权主体,方便其采取措施预防、制止侵权行为,挽回损失。那么,定作方是否构成间接侵权?笔者认为,由于定作方不可能不知道(即使真的不知也是因其过失)其在我国境内并不享有商标权,故其主观为故意;定作方无权而授权加工方进行销售,属于引诱的帮助行为,故定作方应当承担间接责任。加工方和定作方还应根据民通意见的规定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因此,商标权利人可以选择只起诉国内加工方,或起诉加工方和定作方,但不能只起诉定作方。至于加工方承担侵权责任后的追偿问题,应根据民法的有关规定(例如连带责任的追责、合同无效的缔约过失责任)另行主张,与商标权利人无关。
2.加工方在境内擅自销售(或第三人销售)。此种情形,与上述(一)2(或3)种情形无异,应当认定加工方(或第三人)侵犯了境内商标注册人的商标专用权,为侵权主体,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定作方无主观过错,不承担侵权责任。
(三)定作方并非是合法的商标权利人
1.“贴牌加工”后的商品全部出口。若定作方并不实际上享有商标权,则其授权境内加工方贴牌加工无效。此行为在性质上与第(一)1种情形无异,加工方的行为既非直接侵权,也非间接侵权,加工方和定作方均不承担侵权责任。
有法院区(2013沪一中民五(知)终字第29号)分加工方是否尽到审查义务(外国定作方是否是商标权利人)而判断加工方是否承担责任的,笔者认为,加工方是否尽到了审查义务属于主观要件范畴,而主观要件并非商标直接侵权的构成要件,因此判断加工方是否尽到审查义务并无实际意义。
2.贴牌加工后的商品有部分在境内销售。对于出口的部分,同上第(一)1种情形,应当认定加工方不侵权;对于最终在境内销售的部分,根据上述第(二)种情形举轻以明重,认定加工方的加工行为侵权。销售行为侵犯了境内商标注册人的商标专用权,若是经“授权”的,则销售者承担直接侵权责任,定作方承担间接侵权责任;若不是经“授权”的,则只由销售者承担直接侵权责任。
五、总结
笔者将本文讨论的情形和主要观点归纳成如下表格(见表1、2):

表1 典型商标贴牌加工行为的侵权认定
从表格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无论贴牌加工中涉案商标是否有外国商标权人授权,该授权是否合法,受控行为的侵权形态和责任主体都是一致的。通过这一结论,也可以得出,(典型)商标贴牌加工的侵权问题与其他商标侵权问题一样,并无特殊性,完全可以用现行商标法和商标法原理予以解释和解决。期望司法实践能早日认识到商标贴牌加工的本质,尽早统一认识。
[1]黄晖,冯超.定牌加工商标侵权问题辨析[J].电子知识产权,2013,(6):49-50.
[2]闫卫国.定牌加工中的商标侵权[J].中华商标, 2002,(7):15-16.
[3][5][7]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479-483,256,500-501.
[4]孔祥俊.商标法适用的基本问题[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120.
[6]王莲峰.商标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141.
[8]赵玉.定牌加工中的商标侵权问题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08:18.
[9][12]朱玲.涉外定牌加工中的商标侵权认定——以法律解释学为视角[J].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3):60.
[10]张熙.定牌加工中的商标侵权问题研究[D].厦门大学,2011:8.
[11]林鸿姣.国际定牌加工与商标权的地域性[J].中华商标,2005,(6):42.
10.3969/j.issn.1672-9846.2014.03.008
D923.43
A
1672-9846(2014)03-0030-05
2014-06-16
赵丽莎(1990-),女,浙江杭州人,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知识产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