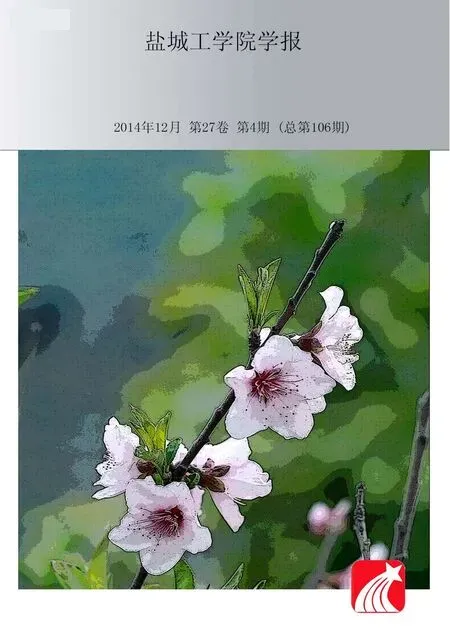文人画:历史起源与重建
方汉文,汤胜天
(1.苏州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2.华东师范大学 艺术研究所,上海 200032)
文人画:历史起源与重建
方汉文1,汤胜天2
(1.苏州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2.华东师范大学 艺术研究所,上海 200032)
“重建文人画”首先要对文人画的历史源流进行梳理。文人画的美学话语起源远比现有的艺术史或绘画史立论要早得多,它起源于仰韶文明陶器绘画中的“象其物宜”的主体性;文人画以线条为重要的手段,进而提倡“书画同源”,将书法与绘画结合起来,形成诗文书画为总体的特性。文人画的美学观念集中于所谓的笔墨,文人画主张笔与墨结合,意在笔先。
中国画;重建文人画;中国美学
“重建文人画”是全球化时代跨文化对话的需要,它是中国绘画转型中具有代表性的体系新建构,而美学话语则是建构的核心,所以必须从历史源流来进行阐释。
一、文人画定义与美学观念“象其物宜”
欲重建文人画,必得先阐释它产生的历史语境是什么?什么是文人画的所指与能指?
文人画得名很晚,明代大画家与书法家董其昌(1555~1636)是文人画的命名者与理论开创者。他在《画禅室论画》中提出:“文人之画自王右丞(维)始”[1]720。这是历史上首次正式命名“文人画”。在此之前,已经有相当多的学者涉及到文人画,如苏东坡曾经提出过“士人画”,但是都没有正式使用文人画的名称,所以董其昌作为文人画的理论肇始者与命名者,也被画史称之为文人画的“殿军”,是当之无愧的。
文人画是与“院体画”相对的,文人画讲究绘画艺术的意义与价值,主张“道法自然”的人文主义,外师造化与内得心源。而院体画除了受到朝廷奉养的宫廷画家的作品之外,则以画艺的技法精美,以纯艺术的追求为中心目标。所以文人画家鄙视院体的“画匠”、“画师”的画法,将其称为“魔渊”。艺术家与“工匠”之间的对立,在世界各国艺术中都普遍存在,并非中国所独有,更不是一个朝代所独有。中国文人画从唐代王维等人提倡起就已经居于画坛的中心地位,使得“画匠”们只有绘画技法,而缺乏思想与美学价值的作品开始评价不高。宋元明清直到当代,文人画一直主导着国画的发展。只有在文化革命中等特殊时期,文人画被贬低和排斥,认为文人画有违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主张以“工农兵画”甚至年画宣传画取代文人画。改革开放以来,如何正确评价文人画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绘画世界化的铁门槛。近年来我们所提出的“重建文人画“是为全球化时代中国画走向世界、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一种观点,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学术关注。
文人画有自己的能指与所指,当然重建文人画,必须对它有一个基本的定义。我们认为,文人画的定义可以简单表述为:文人画是以中国绘画史所特有的人文精神主体性话语(包括所谓“士气”、苏轼的“士人画”、赵孟頫等人的“书画同源”、“聊抒胸中逸气”“逸格”等不同话语所倡导的人文主体性精神),从美学认识论层次来看,文人画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将绘画艺术视为“道之文”(《文心雕龙》语词)的绘画。作为中国绘画的代表,它鲜明区别于西方绘画理论中的理性中心观念,这种理性中心的艺术理论是从古代希腊艺术理论家直到近代美学家黑格尔、当代艺术理论家如康定斯基等人所坚持的传统。
这里必须说明,文人画主体并不是所谓的“封建文人”。当然从文人画的起源来说,提倡者并不排除以王维、苏东坡等“文人学士”为创作主体的认定。这是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提倡“君子之德”,君子是儒家的人格标准,并不具体指个人。《周易》曰:“文明以建,中正而应,君子正也。”[2]29主要是推崇君子的道德与人格。所以君子的美学标准是决定性因素,而不是个人身份,如中国的农民画、年画中也有文人画,而反之亦然,有的人虽然是文化人,但是作画却并不是文人画。如中国绘画史上大名鼎鼎的任伯年等人,虽然也是杰出的画家,但是由于其画中缺少“士气”,所以对他的绘画技法评价相当高,但并不指为文人画。
我们多次在相关论著中指出,中国绘画中的“取象表意”和“以形传神”的美学思想是文人画主体性的表现,并不是汉魏以后才有的,而是在6000年前农业文明时期的中国仰韶文化的陶画中产生,在金石刻纹、战国帛画、汉代砖刻直到汉魏中国绘画的有序历史流传。
仰韶陶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绘画,中国陶画主要载体是仰韶的彩陶文化,仰韶彩陶画中的“半坡鱼纹彩碗”、“河南临汝阎村彩陶缸”和“姜寨遗址陶器”上都有共同的“鸟鱼图”。这些中国古代绘画共同的特点是抽象性绘画,是主体性的突显,主体以象征性的几何体图象来表达形象。“象”是中国艺术的关键词,孔颖达《周易正义序》开篇写道:“易者象也。”[3]6为什么中国人重视“象”,包括诗词中力主“兴象”?据西方学者德里达或是早期的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等人说,这是由于中国的文字是象形表意的汉字的原因,而黑格尔则说是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所致。我们这里先不去考证。《易经》有一段极为重要的话,对文人画起源更适用:“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迹,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4]83。“宜”者意也,圣人对所看到的事物是“象其物宜”而不是“象其物”,就是说要表达其意义与本质,而不是表达这种物体的外形。这其实是中国文人画的精髓,是中国画的美学原则。


图1 姜寨遗址陶器上的鸟鱼图Fig.1 The above are two potteries with paintings of birds and fishes excavated in the Jiangzhai Site
中国的文人画不以形似为主,而以象征与写意传神为特性。笔者认为,早在仰韶文化半坡和姜寨遗址中,就已经出土了鸟鱼图,特别是姜寨鸟鱼图,采用了几何画法,鸟类的尖嘴与鱼类形体都形式化,有时放入人面框中,很有一种现代派的模式。[5]154半坡的鸟鱼图是渔民与猎人的主体性的意象表达,与后世文人画的主体文人与君子的意象表达是同一个传统。
这种画法不是以客观形象再现客体,以相似为目标,而是重视传神写意的表现手段。正因为有这样的主体性,才形成后世苏轼等人主张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超越形似,追求传神的审美观念。这是中国上古绘画就已经表现出的重要特性,与其他民族的古代绘画艺术不同。中国的这种画法经过西亚传到地中海,与古希腊绘画形成鲜明对比。古希腊与米索不达米亚的古代彩陶画基本上是写实风格的,对表现的事物进行细致具体的描绘,以合比例、具象式描绘为主。从公元前3000年起,地中海出现的米诺斯与迈锡尼文化是古希腊文明的起源,米诺斯与迈锡尼文化的陶器绘画主要风格是写实的精确描绘。公元前8世纪的地中海基里克斯彩陶也出现了几何化图案,将鱼与动物几何化与图案化。有人推测这可能是受到“东方彩陶”的影响,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希腊几何纹样的陶绘仍然具有精细的写实风格,与中国彩陶绘完全不同。公元前6世纪前后出现的希腊“红绘风格”与“白地彩绘风格”,据说是融入了东方因素,但仍然与中国彩陶大相径庭,具有后世希腊雕塑与绘画的传统形式。希腊是西方文明的起源,它的彩陶画与西方绘画的源流是显而易见的。
文人画的表象取意性使它以山水画为主体,以主体寄托情志的表达为主。而西方画以理性为准绳,以人物画形象的真实为主流。中国彩陶的取象表意特性与后世的中国绘画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绘画从汉魏时期到隋唐五代经历了初期的演变,其取象表意的特性愈加突出。

图2 董其昌的山水画Fig.2 A Chinese scenery painting by Dong Qichang
南朝(宋)宗炳提出“以形写形,以色貌色”只是出发点,而要作到“畅神而已”。唐代张璪认为应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就是借助自然来表达主体的意象。董其昌认为,王维是中国画的开创者,“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远接衣钵。”[1]720这一段话勾勒出了文人画的历史线索,当然只是明代之前,明代以后文人画风更为炽烈。作为对比,他认为相当著名的画家“若马夏李唐刘松年又是大李将军之派。非吾曹当学也。”作为文人画派的王董巨、李范与“非文人画派”的李思训等之间的区分在于“士气”。
中国古代的“士”主要是文人学士,“士气”就是文人气,画中的士气用现代话语就是文人的主体性。当然文人主体性并不是人文身份,而是这一种阶层主体性的整体性呈现。文人画,从认识论角度、从主客体关系的层次,就是“画中有我”,这个“我”就是“士气”,这样的画才叫文人画,画中有文人所特有的“士气”,有中国人文主义的审美。
二、文人画的以书入画:线条之艺术
中国文人画美学思想根源另一个重要观念是:以书法入画。这就是董其昌所说:“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历代文人画家大多是书法家,而且赵孟頫、米氏父子、董其昌等人的书法甚至远比绘画的名气要大得多。书法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一种艺术。它来源于中国的汉字,汉字具有象形表意特性,书法可以表达出汉字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在文人画的发展中,书法切入的角度也相当突出,书法是一种线条的艺术,正是这种特性,对文人画的形成有重要作用。
我们已经指出陶泥绘画中的几何化形式,其实几何化也是一种线条化,将一幅图形多余的部分去掉,形成一种线体几何图形。我们从半坡的鱼形彩陶就可以看出这一特点。

图3 仰韶鱼纹彩陶Fig.3 A Yangshao color pottery with fish designs
李泽厚指出:“陶器几何纹饰是以线条的构成、流转为主要旋律。线条和色彩是造型艺术中两大因素。比起来,色彩是更为原始的审美形式,这是由于对色彩的感受有动物性的自然反应作为直接基础(例如对红、绿色彩的不同生理感受)。线条则不然,对它的感受、领会、掌握要间接和困难得多,它需要更多的观念、想象和理解的成分和能力。”[6]25简单来说,色彩与线条都是艺术的形式化手段,但是色彩是直接的理性,而线条是第二次的处理,是辩证的理性,色彩被西方理性作为绘画的主要形式,而线条则被中国绘画所选用。
这就形成了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最重要的差异:中国绘画以线条为主要手段,是线条的艺术,最著名的作品如《八十七神仙图》《朝元扙仙图》等,线条最为突出,无论是人物山水花鸟还是宗教画(只要看一下敦煌壁画就明白),中国古代绘画最初的画风起自于线条是无可怀疑的。文人画来自于一种以线描为基础的艺术,线条是最基础的。
西方绘画则不然,西方绘画主流是以色彩为主的。西方绘画并非不重视线条,相反,线条也相当重要。但是西方画更重视色彩与形式(包括被中国画的古典阶段所逐渐扬弃了的几何形式)。西方现代绘画的重要理论家康定斯基说:“马蒂斯的色彩,毕加索的形式,——这是两位指向伟大目标的伟大的指示标。”[7]28这一论断不仅只局限于现代西方绘画,也是全部西方绘画历史的总结。只不过在西方绘画中,现代绘画的转型更为突出,从理性精神的形式精确描绘到主体性的内心观念表达,经历了令人触目的拐点,这就是从印象派之后艺术的转型。这可能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印象派绘画仍然是西方艺术的颠峰。因为它代表了西方绘画主体精神外化,这是一种理性精神的形式化变形。而文人画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形式化,这是人文精神的代表,主体的“空纳万境”与自然之道是山水人文精神之美的呈现。
但是线条在西方绘画中主要是为抽象与写实两个原则服务。而在中国绘画中,线条成为书法,又通过书法进入绘画,成为文人画的笔墨。

图4 方汉文 中国画,八宝图之金银国宝,纸本设色Fig.4 A Chinese painting with ink and color on paper "A Golden and Silvery Panda among Eight Paintings of the National Pet" by Fang Hanwen

图5 方汉文书习近平词《念奴娇 追思焦裕禄》并配兰考焦桐中国画Fig.5 A Calligraphic and painting work created by Fang Hanwen, featuring "A Poem of Nian-nu-jiao in Commemoration of Jiao Yu-lu" by Xi Jinping, with Jiaotong trees in Lankao painted in it
所以书法对文人画极为重要,是认识文人画的钥匙。其表现相当丰富,首先是书画同卷,体现了一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地。诗人的思想如果表达不完全,可以通过画来从视觉艺术的层次来表现。如著名诗人画家书法家赵孟頫的作品中,这种书画同卷,最为突出。通过对《尚书 洪范》中箕子与武王的对话,他将这一段历史故事在画中表现,文徽明跋曰:“画既古雅,而小楷精绝,殆无遗恨。”这幅画中所表达的“君子之道”,其实正是文人画的思想观念,所以很受重视[8]。文人画的提倡者董其昌就是杰出的书法家,他的画从草书入手,受到历代画论的赞扬。
文人画的技法中,点线面的观念,各种皴法笔法都来自于书法。其中最著名的是所谓“米点”。书法家米芾父子根据书法原理,创造了米点的画法。董其昌对二米的画法予以充分肯定,他说:“唐人画法至宋乃畅,至米家又一变耳”。虽然对米家画法历代都有批评,如鲁迅就有过相当尖锐的批评,但仍然只是从技法方面的,而并不否定米氏画法的整体贡献。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笔意”的表达,这是历来文人画家对绘画的最高评价,充分体现出对书法的重视。赵孟頫在论竹石画时说:“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这里已经将绘画作为书法的原理呈现了,虽然有不当之处,仍然可见古代文人画对书法的“法”与“意”的重视。
三、笔墨的美学起源
笔墨是中国绘画的生命,也是文人画的核心,为什么笔墨有如此重要的作用?
这必须从中国绘画的起源来理解。中国画起于取象表意的美学观念,使用了线条等多种艺术手段,结合为一个整体,这就是文人画的笔墨。在古代彩陶艺术中,已经将线条与色彩结合,构成写意性的构图。河南临汝阎村彩陶缸鸟鱼图是一件中国艺术史上的珍品,给予我们的美学启示无限丰富。这幅图上以鸟鱼和斧柯为物象,线条优美,色彩斑斓,构图给人以视觉艺术冲击力。这幅图中的线描与色彩相结合,预示着中国画的笔墨艺术的形成。笔墨二字就是强调有线条书法的用笔,也有濡染甚至设色的用墨,这二者缺一不可。

图6 方汉文书毛泽东词《卜算子·咏梅》并配画Fig.6 A Calligraphic and painting work created by Fang Hanwen, featuring "A Poem of Bu-suan-zi in Praise of Plum Blossom" by Mao Zedong
汉代以后,纸笔成为中国画主要的工具,从而为笔墨的审美作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文人画家们尤其重视“笔”的运用,董其昌甚至提倡所谓“一笔画”,可见他对笔法的重视程度。他在《山水小景册》的自题中说:“此所谓‘一笔画’大轴能尔,亦自佳。”[9]27一笔画就是强调意在笔先,笔可以创造出点、线、面,笔服从于主体的意,通过笔的运用创造出主体独具的意境。因此,全画只是主体的一笔,全画的无数笔是统一的一枝笔,这就是“一笔画”的真正含义。这里所说的一笔画,就是画家的主体性的笔法。
此外,对于笔墨的互补关系强调也是中国文人画的传统。荆浩在评论前人画时说:“吴道子画山水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吾当采二子之长,成一家之体。”[10]足见对于笔墨二者不可偏废,早已经受到重视。
对于文人画笔墨的各种手段,董其昌也有极深刻的体会,他主张笔墨的精妙,甚至认为笔墨可以超越真实山水。但是更为重视意义超越技法,重笔墨而不唯笔墨论。笔墨服务于主体精神,要求运用笔墨达到苏轼“空纳万境”的境界,这是文人画主体性表达的境界,也说明文人画中笔墨与主体的关系。文人画对皴法、染色和构图都有独特的看法,总体来说,文人画家们并不排斥青绿与金绿的技法,董其昌强调的“墨润”、“秀润”、“秀气”、“滋润”、“惜墨”、“淡墨”等笔墨理论,都对中国绘画有重要影响。其中相当多的观念甚至对院体画家也有影响,如对青绿设色重视淡染,淡墨为主等,都是文人画家的主张。这些技法的主张无论如何重要,我们都必须明白,它们是为了“象其物宜”服务的,美学的总原则是“道法自然”的传统观念,以“不似之似”作为审美标准。
文人画从宋元到明清,一直统治着中国画坛,近现代又有重要的传人,直至吴昌硕、齐白石、溥濡、启功等当代名家。它的历史作用早有定评,虽然有不少负作用,但是贡献更大。在中国绘画史上,对文人画的评价远远高于院体画、宫中画或是其他画派。
[1] 董其昌.画禅室论画[M]∥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57.
[2] 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M].(上),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79.
[3] 孔颖达.周易正义序.《十三经注疏》上,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79.
[4] 《周易正义序》,《十三经注疏》上,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79.
[5] 方汉文.陶泥文明[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8.
[6] 李泽厚.美学三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7] 康定斯基.艺术中的精神[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8] 张丑.清河书画舫[M].出版地不详,出版时间不详.
[9] [清]卞永誉式古堂画汇考.卷五,明独册[M].出版地不详,出版时间不详.
[10]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M].卷二.纪艺上·荆浩.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沈建新)
Literati Painting: Its Origin and Reconstruction
FANG Hanwen, TANG Shengtian
(1. 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Jiangsu 215123,China; 2. Art Research Institute,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32,China)
A survey of its history is required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literati painting. The origin of its aesthetic discourse can be actually dated back much earlier than the present arguments about it in the history of art and painting, which derived from the subjectivity of “symbolizing the essence of the universe” found in the paintings on Yangshao pottery. It uses lines as the main method, while advocating the combination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nd characteriz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poetry, pro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Its aesthetics emphasizes the combination of line and shade, as well as the ingenuity of strokes.
Chinese painting; reconstruct literati painting; Chinese aesthetics
2014-06-20
方汉文(1950-),男,陕西西安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J222.2
A
1671-5322(2014)04-005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