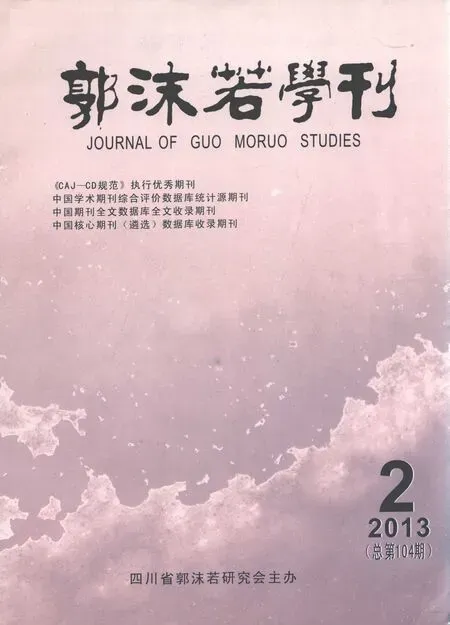《静晤室日记》中的郭沫若
李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 郭沫若纪念馆,北京 100009)
《静晤室日记》共10册169卷,1993年10月由辽沈书店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高度重视。很多史学家从中发现重要史料,撰写了一批相关论文。《静晤室日记》中有多处跟郭沫若相关的资料,展现了日记主人跟郭沫若的交往,对郭沫若的评价。这些资料对郭沫若研究饶有价值,但尚未引起学界注意。笔者不揣浅陋,将其勾稽出来,做相关解读,以就正于方家。
一
《静晤室日记》有关郭沫若的最早记载,跟日记主人金毓黻的身世之感有关。
《静晤室日记》作者金毓黻(1887—1962),原名金毓玺,字静庵。辽宁辽阳人。1913年入北京大学文科就读,师从著名文字学家黄侃。1916年毕业后,赴沈阳文学专门学校任教。后曾任黑龙江省教育厅科长、辽宁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九·一八”事变后,主持编纂《奉天通志》。此后曾担任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研究员。他在建国前的行事方式与治学路径都比较守旧,对新文学作品不大欣赏,长于旧体诗创作,在史学史、东北史,近代人物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著。编著有《东北通史》(上编)、《中国史学史》、《渤海国志长编》等。
“九·一八”事变后,时任辽宁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的金毓黻为日军拘捕。1932年夏,金毓黻为伪奉天省长臧式毅保释出狱,此后曾担任伪奉天公署参事官、伪奉天图书馆馆长、奉天通志馆主纂等职。1936年7月,借访日之机,金毓黻化名逃回上海,经蔡元培介绍,任中央大学史学教授。担任伪职务的经历让金毓黻承受了不小的精神压力。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当天,《静晤室日记》载:“吾国之文学家,如鲁迅、郭沫若皆有左倾色彩,受青年学子之欢迎。鲁迅与日人内山完造交谊极笃。其卒也,内山氏为主丧人之一,值中、日国情严重之日,而吾国人不以为病,盖以私交与国事判然两途也。郭氏娶日妇,久居日京,不啻籍于日本,而国人甚爱读其著作,不以为病。闻其每年著述所得约数万金,而日本文化机关且以奖学金予之,而国人亦不以为病,何也?吾国不可解事极多,岂止鲁、郭二氏而已乎!”
显然,鲁迅、郭沫若跟日本人之间的关系让金毓黻想到了自己的经历。鲁迅虽交好日人,但属“私交”,郭沫若“娶日妇”,也属私事,都与属“国事”的金毓黻任伪职不同。鲁迅、郭沫若未受谴责,但金毓黻的经历则足以为人诟病。金毓黻希望国人对他少些责备,以减少压力,亦属人之常情。日记说郭沫若“每年著述所得约数万金,而日本文化机关且以奖学金予之”,显然属于谣言。但金毓黻信以为真。这一方面可见中日关系紧张之时舆论对郭沫若处境的关心和涂饰,另一方面也表露出国内部分知识分子与郭沫若之间的隔膜。值得注意的是,金毓黻将鲁迅郭沫若并列,说明在他这样离新文化运动稍远的知识分子心中,郭沫若足以跟鲁迅比肩。
二
1940年4月,郭沫若参与发掘了重庆江北岸培善桥汉墓,在这次发掘过程中,时任中央大学教授的金毓黻第一次跟郭沫若见面,并进行了诗词唱和。
4月初,上海美术大学重庆分校美术教授吕霞光告诉考古学家卫聚贤,在生生花园有一条用汉砖彻成的小路。卫聚贤很感兴趣,偕郭沫若于4月7日前往生生花园觅汉砖,未果。于是渡江到嘉陵江北岸培善桥头吃茶散步,无意发现了汉砖,并由汉砖发现汉墓。卫聚贤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于右任、张继、吴稚晖及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中央大学教授常任侠、金毓黻等,引起了重庆文化界的轰动。卫聚贤约大家10号前往调查汉墓。
4月10日,郭沫若、卫聚贤、马衡、常任侠同到培善桥调查汉墓。他们从当地联保主任处获悉,附近还有同样的墓。尽管常任侠“观此两古墓,恐非汉而为后代者”,但马衡认为墓砖确属汉砖。卫聚贤决定4月14日同时发掘这两座古墓,并邀请相关人士前来参观。
14日发掘古墓,金毓黻前往参观,这是有文献可征的他跟郭沫若的第一次见面。《静晤室日记》当日载:“午前诣牛角沱生生花园,渡江之培善桥董家溪,一名胡家堡,发现一汉墓。其一部因建房破坏,一部尚存。始发现者为郭沫若、卫聚贤二君,雇工掘之,余在场监视。”并在日记中手绘了汉墓图形。但这次发掘除了一些刻有“富贵”和“任文”字样的汉砖外,没有其他有价值的发现。
卫聚贤坚信发掘的是汉墓,继续工作,终于在4月18日发现了铢钱、灵剑、土俑等珍贵文物。4月20日,郭沫若将汉砖拓墨。4月21日,卫聚贤在桐油公司开了一个小型展览会,除展出出土文物外,郭沫若的汉砖拓墨也参加了展出。参观者大概有两千多人,郭沫若、常任侠、金毓黻都参观了这次展览。
重庆多家报纸报道了这次展览盛况,有“题有诗句,悬之壁间”之说。这里的诗句,从当时的报纸报道分析,包括了郭沫若的《题富贵汉砖(一)》。题富贵砖,郭沫若共有四首诗,均为五言古风,押鞭字韵。其中第一首最为有名,唱和者最多。
1979年,宋丛从《静晤室日记》勾稽出此诗,断定此诗作于1944年4月20日。王继权等《郭沫若旧体诗词系年注释》从其说。1988年,曾凡模作《郭沫若〈题富贵砖拓墨诗〉时间地点补正》,纠正宋丛之说,将时间提前到1940年。文章举证说:“重庆各报报道4月21日‘题有诗句,悬之壁间’的展览盛况”,认为此诗作于1940年4月“20日晚上筹备展览会拓墨之时”。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从曾凡模说。但常任侠在《永念考古学家郭沫若先生》一文中,却说这首诗作于郭沫若发掘汉墓(1940年4月14日)“劳作休息”之时。当时常任侠请郭沫若将这首诗写在了他随身携带的《花边文学》底页上。常任侠步郭沫若韵,和诗一首,也写在《花边文学》底页上。1999年后,关于此诗的两幅手迹先后公布。一为《郭沫若书法集》(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所载拓本右侧所题,隶书,落款“五月十二日晨沫若自题”。一为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0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32页后所附拓本的左侧所题,楷书,落款“廿九年五月十日沫若”。有学者据两处墨迹,认为该诗或作于1940年5月10日,或作于1940年5月12日。可见,关于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有如上几种说法:①1940年4月14日,②1940年4月20日晚,③1940年5月10日,④1940年5月12日,⑤1944年4月20日。上述五种说法,究竟谁更准确呢?
这种情况,一般时间在先的应该更为准确。但我们从《静晤室日记》中能得到比较可靠的证据。常任侠1940年4月22日日记载:“观音岩遇郭沫若,出晨间所作步其汉富贵砖拓文诗八韵示之。”23日载:“金静庵来谈,并为延光砖文题字。”《静晤室日记》4月23日日记载:“郭君沫若有咏汉砖诗,任侠和之。余见而心喜,亦作一诗,录存于后。”4月25日,《静晤室日记》录存了郭沫若原诗和常任侠、金毓黻和诗。所录郭沫若诗题为《题富贵砖拓墨》,全文为:“富贵如可求,尼父愿执鞭。今吾从所好,乃得汉时砖。上有富贵字,古意何娟娟。文采朴以殊,委婉似流泉。相见仅斯须,逖矣二千年。贞寿逾金石,清风拂徽絃。皓月来相窥,拓书人未眠。嘉陵江上路,蔼蔼生苍烟。”这正是《题富贵汉砖(一)》。可见此诗作于1940年4月22日之前,第③④⑤种说法均可排除。
现在剩下第①②两种说法。事实上,这首诗随拓墨参加了4月21日的展览会,被人们广为知晓。郭沫若对这首诗非常珍爱,他又于当年5月10日,12日两次将这首诗题在富贵砖拓墨上,一为楷体,一为隶书。这两次题写,对原诗有少量修改。其中,“尼父愿执鞭”中的“尼父”改作“尼叟”,“皓月来相窥”中的“相窥”改作“窥窗”,“蔼蔼生苍烟”中的“生苍烟”改作“竖苍烟”。常任侠《永念考古学家郭沫若先生》一文中所举的题于《花边文学》中的该诗,跟5月10、12日两日所书字句相同,说明郭沫若为常任侠题诗的时间应该比较靠后。且据诗中“皓月来相窥,拓书人未眠”一句来看,该诗写作的情景不会是常任侠所谓的发掘现场的“劳作休息”之时,故第①种说法可以排除。
从“皓月来相窥,拓书人未眠”一句来看,该诗应该写作于郭沫若拓墨之时,结合《郭沫若书法集》所收拓本左下角“廿九年四月廿日晨郭沫若手拓”字样分析,郭沫若拓墨时间应为从19日晚至20日晨。他深夜未眠,将富贵砖拓墨,诗兴大发,在1940年4月20日晨创作了《题富贵汉砖(一)》。也就是说,第②种说法比较接近,但应提前二十来小时。
三
常任侠4月22日晨和郭沫若诗,在常任侠日记、常任侠《永念考古学家郭沫若先生》、《静晤室日记》中都有披露。《静晤室日记》所录题为《发掘汉墓纪事次沫若韵》,全诗为:“巴水碧如油,渝柳软如鞭。晴郊趁游屐,荒垅拨残砖。研古集多士,振奇来群娟。长剑出幽墓,覆瓿结败泉。剔辨‘昌利’字,作此延光年。欣获盘与豆,快比剑脱弦。洗拓能忘疲,摩挲行废眠。既返城市路,犹恋墟里烟。”跟郭沫若原诗一样,该诗歌咏了发掘汉墓情况,及墓中砖、剑、覆瓿等古物出土情景,并赞美了郭沫若在嗜爱出土文物时所体现出的超脱。
金毓黻4月23日和郭沫若诗,《静晤室日记》所录题为《参与巴蜀文物发掘,和沫若韵,并呈聚贤、任侠》,全诗为:“搜奇到岩穴,让君著先鞭。宝剑光耀眼,岂但俑与砖。冢中骨已朽,不辨豸与娟。拭得‘昌利’砖,媵以五铢泉。再出人间世,垂及二千年。姓字昧金石,事业空管絃。汤汤西汉水,不肯护牛眠。成坏本一例,过眼如云烟。”这首诗在附和郭、常诗中的发掘情景之外,另辟新境。所谓“姓字昧金石,事业空管弦”,所谓“成坏本一例,过眼如云烟”,都融入了传统文化中的“齐生死,等富贵”这一豁达、超然的老庄境界。
除常任侠、金毓黻二人和诗外,郭沫若的诗还引来了另一位诗词大家的兴趣,他就是汪辟疆。汪辟疆(1887—1966),号方湖,别号展庵,江西人。清末入京师大学堂攻中国文史。1912年毕业,至上海,结识邵力子、于右任、叶楚伧、苏曼殊、张继等。1927年执教于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更名国立中央大学)。1937年随学校迁入重庆。汪辟疆在诗词创作和研究上成就卓著,影响颇大。
汪辟疆的第一次和诗见《静晤室日记》1940年4月27日。该日日记载:“汪辟疆先生以诗见贻,因昨以延光砖拓片赠之,故以诗来答谢,又以和郭沫若汉冢诗一首写示,皆佳制也。”并全文录下署名“方湖”的汪辟疆和诗《和郭沫若汉冢诗》:“延光去千载,咄哉羲和鞭。不谓陵谷移,乃出剑与砖。埋幽者谁子,绝代岂婵娟。不然累世士,玩志甘林泉。我闻江州彦,多出元初年。贤守好荐士,永歌蜀国弦。岂其归山丘,爱此吉祥眠。松楸不可见,怅望空云烟。”重庆在汉代时曾名为江州,元初为汉安帝的年号。汪辟疆这首诗,在郭、常、金诗外,另辟一境,遥想出汉墓主人所在时代当政者重视人才,人才辈出的繁华景象。末一句“松楸不可见,怅望空云烟”,不胜今昔之感。金毓黻除在该日日记中赞汪辟疆诗为“佳制”外,4月29日再次在日记中称赞:“汪方湖之诗,评以八字曰:典重高华,风神绝世。”
几天后,汪辟疆再次和郭沫若诗,见于《静晤室日记》1940年5月1日条,该诗题为《再题延光砖拓本和沫若韵》,署名“方湖”,全诗为:“昔贤集砖文,珍同七宝鞭。岂期异代后,又见延光砖。昌利与富贵,法体和便娟。波磔出真朴,静穆如沍泉。千华嗜奇古,缅想二千年。手拓传万本,奚翅朱丝弦。一纸张素壁,累我清夜眠。谁谓置眉睫,不见玉如烟。”这首诗跟上面几首的不同,在于歌咏了砖上文字的艺术之美,即“昌利与富贵,法体和便娟。波磔出真朴,静穆如沍泉。”同时,“一纸张素壁,累我清夜眠”也是对郭诗“皓月来相窥,拓书人未眠”的较好回应。
5月2日,《静晤室日记》录下了汪辟疆和郭沫若第三首诗,即署名“方湖”的《再题富贵砖,用沫若韵》:“养生如牧羊,虽贵视后鞭。世人昧生术,营圹竖作塼。此墓砖上字,吉语何连娟。昌利人所尚,富贵渴赴泉。想其固幽扃,所愿万斯年。冢中骨已朽,世事亦改弦。空令后世人,摩挲夜未眠。何如任造化,万古横苍烟。”这首诗在诗意上是回应金毓黻的和诗,体现超然旷达的人生境界。墓主人渴望“富贵”“昌利”,但到头来不过是“冢中骨已朽”而已,这是回应金诗中的“姓字昧金石,事业空管弦”。而“何如任造化,万古横苍烟”,则跟金诗中的“成坏本一例,过眼如云烟”所表达的思想情怀高度一致。
《静晤室日记》同日载:“汪方湖要余再押鞭字韵作一诗,勉为应命,属无佳句。方湖凡作三诗皆押此韵,可谓嗜古不倦矣。”“勉为应命”所作题为《题汉砖用沫若韵》,全诗为:“晴郊罥丝影,侧帽复扬鞭。来种蓝田玉,忽睹粉水塼。昌利媵富贵,有文秀而娟。大地不爱宝,那得闷黄泉。华阳志巴士,延光识汉年。手拓比操缦,所愧未安弦。珍重逾拱壁,废食兼忘眠。疑有神呵护,拂拭生尘烟。”这首诗在思想意境上超不出上述几首和诗之外,确有些“勉为应命”之感。
汪辟疆与金毓黻跟郭沫若在此之前均无交集,但从汪辟疆三和,金毓黻两和郭沫若诗来看,他们对郭沫若的文采风流相当敬重,尤其是郭沫若“今吾从所好,乃得汉时砖”,“皓月来相窥,拓书人未眠”中所体现的嗜爱古物,悠然超脱之境,深得金、汪等人赞誉,并发自内心地多次作诗唱和。
在金毓黻、汪辟疆唱和郭沫若《题富贵砖》诗这段时间,金毓黻跟郭沫若有过两次交往。
4月30日,《静晤室日记》载:“午前,郭沫若、卫聚贤二君来访,因与同观江边之崖墓,又尝一洞门之右角有马形之花纹,他无所得,遂同至校内,导观掘得各种明器及拓片,并邀晚饭于沙坪坝,作半日之聚谈,入夜别去。”三位史学家穷半日之功,寻访崖墓,参观出土文物,他们的兴趣爱好跃然纸上,的确值得一记。
5月5日,金毓黻邀请郭沫若、卫聚贤到中央大学演讲。《静晤室日记》详细记录下了郭沫若这次演讲的主要内容:“郭君略谓考古学与文字学本为两途,而有相互为用之处。考古学者往往成见太深,对文字学加以轻视,实则研究文字学者,惟缺乏科学方法为可议耳。考古学者过于拘于形式、花纹,以记载之文字居于次要地位,亦属偏见。若能取斯二者打成一片,使其相得益彰,则其效为尤宏也。研究文字者不因考古学之藐视而灰心短气,再加以科学之整理则善矣。例如今日发见之延光四年汉砖,即由文字以证明年代,此于花纹、形式之外,又须文字之证明也。郭君又谓,嘉陵江北岸之地实为一汉墓群,倘再努力考求,必有伟大之发见,此不过见其端耳。”演讲完毕后,金毓黻招宴郭沫若、卫聚贤于生生花园。
郭沫若要求考古学与文字学相互为用,尤其是在传统考古学之外,通过出土文物上的文字来判明其所属时代,这正是他在治学上的夫子自道。此一治学方法,在判明出土文物的年代上助益不少。郭沫若在建国后判明《明妃出塞图》《文姬归汉图》的创作年代时就使用了这一方法,这给后辈学者良多启迪。
四
1945年春,金毓黻跟郭沫若还有一次诗词酬唱,后来两人对该次酬唱都曾反复修改。
《静晤室日记》载,1945年3月24日晚,“张申府及其夫人刘清扬女士来饭于佑儿寓,闻郭沫若寓于对面楼上,因并邀来小饮,鬯谈而散,遂撰一诗赠之。”佑儿指金毓黻长子金长佑,40年代在重庆创办五十年代出版社,这家出版社在当时比较有名。1942年曾出版过郭沫若、高地合译的《战争与和平》。
金毓黻所“撰一诗”题为《邀郭君沫若过寓小饮,赋赠长句》,《静晤室日记》1945年3月24日录全诗如次:“寰海知名一作家,立言自足息纷拏。著书百万才未尽,脱手千金贫更加。智者大声不入耳,哲人辨味岂由牙。关心七件开门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哲人辨味岂由牙”句下有小字注:“君患重听,又小饮而不进食。”“柴米油盐酱醋茶”后有小字注:“时值物价飞涨,因论及之。”并有眉注:“此诗已修正,别录于后,余嫌茶字韵率易故耳。”所谓“别录于后”,见《静晤室日记》3月27日,诗题改为《邀郭君沫若过寓小酌赋赠长句》,内容略有增删:“寰海知名几作家,如君卓卓自堪夸。著书百万才未尽,脱手千金贫更加。智者大声不入耳,哲人辨味岂由牙。定庵诗句应移赠,一字真能奠万哗。”诗后有注:“君微患重听,又小饮而不进食。”首联赞美郭沫若是当时屈指可数的大文豪,其相关研究中所下的学术判断大都可成定论。颔联称说郭沫若著作之多,性格之豪迈,处境之贫困。颈联将郭沫若的重听,不大进食,说成是“智者”、“哲人”。修改前的尾联,说郭沫若关心日常生活琐事,以此反映战时知识分子生活的艰难。但这大概跟郭沫若的“智者”、“哲人”形象不符合,于是修改成赞美郭沫若的影响力:“一字真能奠万哗”。
3月28日,金毓黻到天官府访郭沫若,郭沫若和诗一首。据《静晤室日记》载,此诗名为《静庵教授邀饮,席后谈将修清史,用原韵却酬》,全诗为:“平生四海以为家,亡命险经被捉拿。求学粗通风雅颂,立身愧短乘除加。不辞尝尽苦中苦,忧信能堪牙以牙。何意当筵逢太史,一番清话胜清茶。”《静晤室日记》为该诗加眉注:“后有改作”。其改作见于《静晤室日记》4月2日条。诗题改为《静庵邀小酌并有诗,依韵合之》,全诗改为:“平生四海惯为家,刻鹄不成未敢夸。折节粗通风雅颂,立身幸短乘除加。微怜已失耳为耳,忧信能堪牙以牙。畅喜当筵话班马,无心取宠向谁哗。”此诗后以《和金静庵》为题收入作家出版社1959年11月初版《潮汐集·汐集》,文字略有改动,改后为:“平生四海惯为家,刻鹄未成不敢夸。折节粗通风雅颂,立身幸免乘除加。微憎已失耳为耳,犹信堪能牙报牙。秉笔相期学司马,无心取宠向谁哗”。郭沫若的和诗,首联道出自己多经流落、“四海为家”的经历,后将“亡命险经被捉拿”改成“刻鹄未成不敢夸”,是为了回应金诗在首联中赞美的“寰海知名几作家,如君卓卓自堪夸”。颔联中的“折节粗通风雅颂”回应金诗中的“著书百万才未尽”,“立身幸短乘除加”回应金诗中的“脱手千金贫更加”。郭沫若基本认同金诗对自己的评价,但不满足于金诗仅为现象之描述,而补充道出造成此现象的部分原因。他不是为了著书而著书,著书实出于“折节”,即迫不得已也。其“脱手千金”,也并非仅仅是出于豪迈,也源于不会理财,即“立身幸短乘除加”,对于不会理财,郭沫若最初感到“愧”,后来改为“幸”,一字之改,更为真实的体现了自己对于财物的态度。颈联“微憎已失耳为耳,犹信堪能牙报牙”,以风趣的口吻谈到自己的生理缺陷,在金诗的评价之外另辟一境:重听虽然稍感遗憾,但并不影响自己的气节和风骨。尾联是与金毓黻共勉,希望同为历史学家的金毓黻和自己学习司马迁等中国古代史学家不为权贵折腰,秉笔直书的崇高气节。
郭沫若和金毓黻的诗词唱和内容以郭沫若的丰硕成果和身世之感为核心,金毓黻的两次修改,越发雅致。郭沫若的三次修改,精益求精,淡然超脱。
五
1949年3月6日,在政权更替之际,金毓黻在北京见到了郭沫若。《静晤室日记》载:“午后在于思泊宅晤郭君沫若,因与马叔平、陈梦家合邀郭君饭于森隆,颇能畅所欲言。郭君新自沈阳归来,于东北考古工作谓为有必要性,且重于华北。同座又有于君名瓒,亦自沈阳来平。”于思泊即于省吾,与陈梦家均在甲骨文研究上有突出贡献,马叔平即马衡,曾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在金文研究上有贡献。几位历史考古学家相聚,“畅所欲言”,说明当初的氛围之融洽民主,这为他们后来在学术上的合作打下了基础。金毓黻长期从事东北地方史的研究工作,郭沫若谓东北考古工作重于华北,当然给他以鲜明深刻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后,《静晤室日记》提到郭沫若的比较重要的有四处,分述如下。
第一处为1949年9月3日。这天,北京大学史学系邀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杜国庠四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召开座谈会,讨论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之长。时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教授的金毓黻出席了这次座谈会,并在《静晤室日记》中详细记录了郭沫若的观点,还谈到了自己的体会:
今日郭沫若发表意见如下:史学与史料配合起来,应以实事求是为整理方法,自然与马克思主义接近。新旧交替之时应掌握新方法以创通条例。现在尚难言创通条例,即使新方法亦要有丰富之史料配合之。治古代史患史料太少,治近代史又患史料太多,凡史料太少及太多皆不易得结论。吾人应尽量搜求史料,又须求其正确。如有方法掌握则史料不患其太多,若无掌握之方法则必被困于史料之中而无法自脱。
愚按既贵有正确之方法,又贵有丰富之史料,掌握正确之方法以整理丰富之资料,则得之矣。
本日郭沫若参加史学座谈会事,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不载,其他郭沫若研究资料也未见提及。《静晤室日记》留下的这条资料弥足珍贵。从金毓黻记录来看,郭沫若虽强调史观与史料都很重要,但谈得更多的是史料,尤其是谈到“即使新方法亦要丰富之史料配合之”,这对于长期从事史料搜集整理,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观还不大熟悉的金毓黻来说,无疑是非常容易接受的。所以座谈会四位史学大家发言,金毓黻唯独记下了郭沫若的观点。强调史料,这是郭沫若在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的突出特点,这也成为他在文革期间受保护的理由。《顾颉刚日记》1967年3月20日载:“静秋得一印刷品,记毛主席与林彪、陈伯达谈话,谓郭沫若、范文澜讲历史,亦是帝王将相派,但他们注重史实,当保,与处理翦伯赞、吴晗、罗尔纲不同”。
第二处为1956年1月23日。这次为听郭沫若等访日归国报告。《静晤室日记》载:
午后二时诣天桥剧场,听郭沫若院长、茅以升、翦伯赞三教授访日报告,傍晚始毕。大抵此次访日之收获有二:日本人民与其政府有矛盾,日本政府与美国亦有矛盾,美帝国主义者高压于日本人民和政府之上,此为日本全国人民所最感不快者。但日本政府掌握于资产阶级,亦不愿与属于社会主义类型接近;而其人民则正与之相反。此次系科学家名义访日,极为其广大人民所欢迎。而日本之知识分子亦极不同意美国之把持其政府,转而欲亲近于我。由于我科学界访日,对其广大人民及有权威之知识分子与以巨大之影响,则两国人民之友谊更能大进一步。此其收获一也。日本知识分子由于受美英方面之反宣传,颇怀疑社会主义不能自由,又虑将来亲身履受之时不能堪受。此最为制度不同国家不能和平共处之障碍。经过此次访日,举出种种实例,说明惟有社会主义国家之人民才有真正的自由,并以证明日本人民在美帝国主义者控制之下,绝无所谓自由。且美、蒋两方制造种种谣言,以污蔑人民民主国家,经过此次访日,正可缩小此类谣言之市场,以至得到逐渐澄清。此其收获二也。
1955年5月,日本学术会议会长茅诚司先生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率领日本学术会议代表团访问了中国。他邀请郭沫若访问日本。1955年12月1日至25日,郭沫若率领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当时中日两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在意识形态上分属两个阵营。作为重要的赴日公事访问团,此次访问受到中日两国的高度关注。《人民日报》多次予以报道。
代表团归国后,向中国科学院同事做报告。据《人民日报》1956年1月14日报道:“据新华社23日讯不久以前回国的中国访日科学代表团团长、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团员茅以升、薛愚、翦伯赞,今天在中国科学院主办的报告会上,作了关于访问日本的报告”,“他们在会上,报告了代表团访问日本的经过,介绍了日本学术文化界以及日本人民的生活、工作等情况。他们在报告中还列举了很多事实,说明日本人民要求进一步促进中、日两国文化、学术、经济交流和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迫切愿望。”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顾颉刚在当天日记中也记下了前往听报告的情景:“与李俨、尹达、昌群同车到天桥剧场,听郭沫若、茅以升、薛愚、翦伯赞讲科学代表团访日经过,自二时至六时。”《静晤室日记》所记这次报告内容,比《人民日报》《顾颉刚日记》都要详细,栩栩如生地展示出郭沫若等人对于加强中日两国人民交流合作的迫切愿望,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新中国成立后《静晤室日记》有关郭沫若的第三次记载是郭沫若关于知识分子的发言。
1956年1月31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受政协常务委员会的委托,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报告从五个方面谈到知识分子问题,认为,党和政府希望知识分子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对于知识分子是“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知识分子需要提高水平,进行自我教育,加强团结。郭沫若提出了知识分子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说:“个人主义、宗派主义、本位主义的思想,在不少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还存在着,因而在业务上不能做到充分的相互尊重,相互切磋,相互协助,而往往各自为政,不通声息,不求分工,不相配合。本位主义相当严重的人,甚至对于领导上的统筹规划也发生抵触,这些人只愁自己人手的分散,不考虑国家建设的需要。有的人习惯于单干,不能从事集体工作;孤芳自赏,坐井观天。这些现象的存在必然地影响业务,影响国家建设事业。克服这些现象的关键所在依然是思想教育问题。”
金毓黻看到发表于1956年2月1日《人民日报》上的这一报告后,对于郭沫若有关旧知识分子“孤芳自赏、坐井观天”的形容深有感触。《静晤室日记》2月4日载:
郭沫若院长在政协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形容旧知识分子有“孤芳自赏、坐井观天”八个字。孤芳自赏即为高自位置,睥睨一切。坐井观天即为积非成是,故步自封。往岁余肄业北京大学,所遇诸师,多不出此八字风气,背后则互相诋鍍,当面则肆口谩骂。当时以此为贤,不悟其非。盖由宗派之见使然,非一朝一夕之故;今提出此语,可谓片言居要。今日知识分子中间,虽知掌握自我批评武器,改正自己缺点,但不能谓千百年遗留之士风已为之扫地无余,每人或多或少残存潜伏于脑际,遇有机会则故态复萌。惟有用曾子三省吾身之法,时时检查自己,庶能彻底克服。
不仅仅是金毓黻深有感触,参加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也大都有所触动。傅抱石在发言中说:“不可讳言,旧知识分子的许多缺点,尤其是自高自大和宗派倾向的缺点,更集中地、突出地表现在我们这些人的思想意识和言语行动上。古人说过:‘文人相轻,自古皆然’,而‘画人相轻’(主要是国画家)我看也决无逊色的。例如:老一辈的看年青的不起,同辈的也未必看得上眼;画花鸟的很少喜欢山水,画工笔的对写意却很难引起好感。既然如此,就形成了种种无原则的纠纷,加上‘拜师’‘门’,搞个不清,给人以极不愉快的印象,妨碍了团结,也阻碍了国画的提高和发展。我们必须痛下决心,赶快把这些严重的缺点坚决予以克服。”沈从文发言说:“这几天,在大会中我听过了各部门负责首长的报告,我学习了一生没有学习到的许多事情。内中周恩来总理的政治报告,和郭沫若院长关于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都特别提到祖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结成一体的光荣责任,和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迫切问题。我理会到这个责任的光荣,同时也明白责任的重大。从我自己说起,就是必需更好的自我改造,才够得上做个人民时代的知识分子。”林焕平发言指出:“正如郭沫若副主席所指示:‘问题要想得到彻底的解决,责任的至少一半,还要依靠知识分子自己的努力。’我们肯定了我们知识界6年来的进步,同时必须正视我们的缺点。我们应自觉地响应郭副主席的号召,每日以三问来反省自己,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业务的实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以继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严格地鞭策自己,克服一切非工人阶级思想,使自己真正成为周总理所说的‘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也只有如此,才能够符合祖国对我们的要求,才不辜负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殷切期待。”这体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真诚的自我改造态度。
2月15日,金毓黻在《静晤室日记》中再次思考郭沫若提出的“孤芳自赏、坐井观天”:
孤芳自赏为自尊感之一种表现,含有好坏两面。努力向前,不肯随人俯仰,具有独特之造诣,此属于好的一面。高自位置,目空四海,结果脱离群众,成为踽踽独行之人,此又属于坏的一面。我谓不能因为有坏的一面,而否定好的一面,故孤芳自赏正有可取之处。大抵卓荦不群之士,独居深念,仰屋而思,每觉当世无一知己,而思尚友古人而自慰遣者往往而有。然由此产生一病,即脱离群众是也。脱离群众之极,即为坐井观天。孤芳自赏者只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即使其人有二三友朋及其门信从之人,亦必互相称重,成为标榜声气之徒,因而造成宗派,以与其他宗派对立,是之谓自有一小天地。古人讥公孙伯阳为井底蛙,即为坐井观天之另一譬喻。此为孤芳自赏向坏的一面作极度之发展,人而至此,则一无可取矣。凡孤芳自赏之人,其缺点即在脱离群众,一经矫正之后便可成为通才,以其尚肯努力向前,具有独特之造诣故也。如果不肯矫正其缺点,一意孤行而不已,久之则一变其自尊感而为自卑感。觉得自己百无一成,事事落后于人,如臧获之歧路亡羊,形神惧丧,因而否定自己所有之一切。此又脱离群众一往不返所应得之结局也。总之孤芳自赏之士尚有好的一面,故可进一步而成通才,但一达到坐井观天程度,则为不可救药之人。二者密切相关,而实各有分际,此为应知之义。吾以郭沫若先生提出此八字,最为警切,并触及本身之病痛,故一为申言之。
2月19日,金毓黻结合郭沫若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在《静晤室日记》中反省自己说:
知识分子而不甘寂寞,必不能安心读书,治学有所成就,以至贪利忘义,堕节败名。往在旧社会中,如此二徒触目皆是,不值一论。持此以省察自身,亦未能免此。例如余在三十岁后至六十岁之三十年中,往往一方治学,一方从政,兼营并骛,两两相妨,以致年将迟暮,学无一成。探其病源所在,亦由不甘寂寞所致。不甘寂寞之正面名词,即为热中,热中之徒,苟利于己何所不至。故不甘寂寞之人,究与热中之徒有别。余居常以顾亭林先生“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自勉,自问尚非热中之徒。特以旧社会中除教读外,曾无他途可以安于读书治学,只有循孔子之教,出乎学优则仕之途,以收士优则学之效,故有类于不甘寂寞耳。此实缘余生也早,未遇明时,以至虚度光阴也。解放以还,环境大异于昔,生活已有保障,正宜安心治学,以弥往日之缺。然以旧染仍在,触及又生,痛自检绳,仍有不甘寂寞之病。以为人皆竟爽,我独向隅,愧怍在躬,怨尤萌念。曾不悟及治学以实事求是为归,向声背实乃真可耻之尤。谨记于简,以当息壤。
跟傅抱石侧重于批评“帮派意识”,沈从文侧重于与工农结合,林焕平侧重于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不同,金毓黻痛自反省“孤芳自赏”、“不甘寂寞”之病,准备在大好环境下,与群众相结合,实事求是,勤奋治学,这既体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真诚和责任,也体现了金毓黻精神气质中的传统文人节操。尤其是他对自己大半辈子治学从政两两相妨的反思,今天读来,仍字字跃然,令我辈如芒在背。郭沫若的讲话,对于金毓黻的痛自反省,无疑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这也说明郭沫若在当时知识分子心中的巨大影响力。
第四处是对《甲申三百年祭》所用材料提出疑问。《静晤室日记》1957年1月7日载:
郭沫若先生前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论叙李岩甚详,许为富于人民思想之一人,所论诚当。惟所引资料,如《明季北略》、《剿闯小史》,多属民间传说,而《北略》一书雅俗并传,真伪杂揉,实为一种可疑之作,不知郭先生何以不加别择,是为一短。吾所引证,于此一概不收,以示严于别择。昔者,《阜阳县志》及《豫变纪略》载《李公子辨》,谓李岩之事,出自《樵史》。如所谓《樵史》即为孟心史刊印之《樵史通俗衍义》,则亦为剿寇小说之流,而品更劣下,其应慎于引用,不问可知矣!
此时金毓黻正在编写《李自成传笺证》,故查阅《甲申三百年祭》,提出不同看法。关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的史料运用问题,历来都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我认为,这样的批评有一定的道理。郭沫若当时身处重庆,资料难得,而且他的主要精力在先秦的思想与社会研究。他研究明末历史,属偶一为之。资料上有所不足,在所难免。但郭沫若在当时的条件下,于史料搜集解读上,也算尽力为之。何况,《甲申三百年祭》与其说是一部严谨的史学著作,不如将其看成是有学问的革命家,在革命需要的紧急关头所发的战斗檄文。如斤斤计较于《甲申三百年祭》的史料不足及史料运用问题,而不去分析郭沫若写作该文的动机和心态,无疑会因小失大。金毓黻对此理解,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代表了较为普遍的观点。不过,金毓黻以纯学术的角度来看《甲申三百年祭》,其提出的问题弥足珍贵。
小结
综上所述,从1936年到1957年,在治学方法和行事方式上略显守旧的历史学家金毓黻,对于郭沫若有一个从不理解到相与过从,诗词唱和,低首学习的过程。虽然直到1957年,金毓黻对郭沫若部分学术成果仍有微议,但总体上说,金毓黻赞美郭沫若的学术品格,人格精神,对于郭沫若在学术研究上的勤奋耕耘和不断创获表示钦佩和赞誉;郭沫若对于金毓黻的友谊亦非常珍视,多次与他唱和并畅谈学问。这从一个侧面呈现了郭沫若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和份量。金毓黻、汪辟疆、常任侠与郭沫若的诗词唱和,涉及当时知识分子的处境与念想,金毓黻阅读郭沫若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后几次痛自反省,更是牵涉到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心态和作用。从这些记载中,我们亦能管窥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世界。
(本文修改过程过中得到王锦厚先生、郭平英女士、蔡震先生指正,谨此致谢。)
[1]常任侠.战云纪事[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
[2]宋丛.郭沫若题富贵砖拓墨诗[J].社会科学辑刊,1979.
[3]曾凡模.郭沫若《题富贵砖拓墨诗》时间地点补正[J].社会科学辑刊,1988(3).
[4]顾颉刚日记.(卷十)[M].北京:中华书局2011.
[5]顾颉刚日记.(卷八)[M].北京:中华书局,2011.
[6]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傅抱石的发言[N].人民日报,1956-02-08.
[7]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沈从文的发言[N].人民日报,1956-02-10.
[8]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林焕平的发言[N].人民日报,1956-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