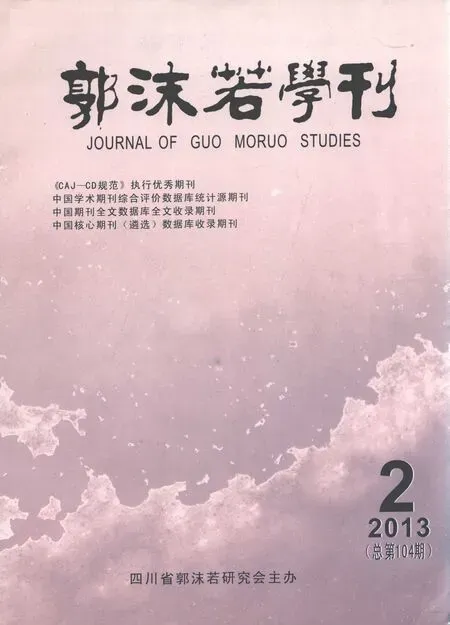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版本问题
孟文博
(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山东威海264209)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在新的世纪正与时俱进,向着更加纵深的方向发展,这种纵深发展的方向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中一个便是以往从某种现实需要出发,以具体思想或者观点筛选史料、提炼史料、阐释史料的研究方法正逐渐退出学术舞台,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从意识形态的固囿中蜕脱出来,以更纯洁客观的眼光去审视历史、考察历史,从历史最原始的面貌出发进行研究,以期能够得出更为真实公正的结论。这种研究方略显然更科学、更客观、更合理,但要做到这一点,对史料的进一步搜集、校对与整理就显得极为重要,而长期以来,这也恰恰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点。时至今日,已有相当多的学者注意到了这个薄弱点,他们以极为认真的态度细致入微地从原始文献中搜集整理各种有价值的文本,加以考查分析,为学科做出了巨大贡献。不过众多学者们所从事的这一个工作是一个面的扩充和量的积累的过程,而在纵的历史流变方面,针对众多现代文学、文论作品在不同时期不同版本所进行的考证、汇校工作,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研究,却是非常欠缺。最能标志这一工作成绩的现代文学作品汇校本,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总共只有七部出版,分别是《〈女神〉汇校本》(郭沫若著,桑逢康汇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文艺论集〉汇较本》(郭沫若著,黄淳浩汇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棠棣之花〉汇校本》(郭沫若著,王锦厚汇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死水微澜〉汇校本》(李劼人著,龚明德汇校,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11月版)、《〈围城〉汇校本》(钱钟书著,胥智芬汇校,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5月版)、《〈女神〉校释》(汇校本兼注释本,陈永志校释,华东师大出版社2008年9月版)、《边城》汇校本(沈从文著,金宏宇、曹青山汇校,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7月版),另外还有两部关于鲁迅作品的校读研究,即《〈鲁迅全集〉校读记》(鲁迅著,孙用校读,湖南人们出版社1982年6月版)和《〈两地书〉研究》(鲁迅 许广平著,王得后校对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
自然,由于一些作品在最初发表之后,没有再版或者收入到其他文集中去,因此不存在版本考证和汇校的问题,但是也必须承认,在现代文学领域,确实是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在再版或者收入不同文集时曾被作家修改过,甚至是多次的、较大幅度的修改,其中还不乏大作家的经典代表作,像《雷雨》在学界公认就有初刊本、初版本、开明选集本、“剧本选”本、“戏剧二版”本等众多版本,而巴金的《家》甚至有十个版本。在现代文学领域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早有学者指出“这是因为我国的近现代社会,曾长期处于动荡不定的、不断变革的状态中。作家的思想必然受社会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对自己的著作加以修改,这是极其自然和无可非议的事情。”而除了这“社会的影响”之外,作家自身阅历的增加,对某一问题的研究有了新发现,或者是为了使作品更趋完美等,也都可能是其进行修改的原因,巴金就曾这样说过:“作家写东西又不同学生的考试卷子,写出来后不能改。作家经过生活,有些事情过去不了解的,现在了解得比较充分了,就有责任说出米。为什么不能改?为什么不让我进步?”
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浩繁的历经修改的作品来说,这七部汇校本和两部校读研究真可谓凤毛麟角。究其原因,客观方面大致有二:一是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历经战乱动荡,作品出版后散佚流失较多,搜集整理工作难度很大;二是1993年由《〈围城〉汇校本》引出的一场官司和一场论争,对学界和出版界产生很大影响,使之后十几年内对作家作品的汇校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另外主观方面的原因更不可忽视,目前学界在相当程度上还弥漫着某种浮躁的氛围,许多学者依然习惯于从宏观上进行长篇大论,却对自己立论的文本材料不加以严格地考证和认定,结果就很容易造成引用的错误或研究结论的偏差。可以说,像汇校本这种研究资料的欠缺只是制约学科向纵深发展“瓶颈”的表层反映,而更为基本的层面,则在于学者们缺乏版本考证意识。
在这七部汇校本和两部校读研究中,有四部是关于郭沫若作品的,比鲁迅还多出两部,这源自于他自身的创作特点。郭沫若是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上的巨匠,他一生所涉猎领域之广泛,成就之斐然,为平常作家学者所难望项背,因此被誉为“球型天才”。同时,郭沫若在历史纵向上又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善变”的作家,他横跨晚清、民国、新中国初期和文革四个历史阶段,其思想观念总是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的变化,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他不同时期所创作的作品上,同时还体现在他对同一篇作品在不同时期的修改上,尤其是其对自己文艺论著的修改,相对于其他作品的修改来说更为频繁,而且幅度更大。郭沫若在修改自己的文艺论著后,从不加以具体说明,而篇尾却依然延续最初版本所注明的时间,因此如果要研究郭沫若的文艺思想,就必须首先对其文艺论著的版本加以严格考证,否则便很容易造成各种失误。对此我们不妨先看下面这个例子:
学者鄂基瑞、王锦园于1981年在《文学评论丛刊》第8辑发表《郭沫若“五四”时期美学思想初探》一文,是文革结束后较早研究郭沫若文艺思想的文献,在当时影响较大,后来此文又被收录到上海书店出版社于2012年7月出版的《郭沫若研究文献汇要》。在这篇论文中两位学者这样论述郭沫若关于艺术功利性的问题:
和艺术无目的论相反,他认为艺术本身是具有功利性的,真正的艺术必然要发挥艺术的功能。但是,假使作家纯粹以功利主义为前提来从事创作,功利的效果反而有限。因为作家惯会迎合时势,虽能收到一时的成功,而在艺术上却未必真正有所建树。相反的,“文艺如由真实的生活源泉流出,无论它是反射的或创造的,都是血与泪的文学。”都会有功利主义的效果。“由灵魂深处流泻出来的悲哀,然后才能震撼读者的魂魄。”这些话写在距今五十八年前,今天读起来仍然富有生命的活力。只有联系郭沫若当时整个文艺思想和创作的实际进行全面的考察,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如果仅仅凭借片言只语,轻易断定他是为艺术而艺术者,那是既不公平也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由注释可以看出,两位学者所引用的材料来自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文艺论集》中的《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郭沫若这篇文章最初发表的时间,据当时推算,确实是“五十八年前”。然而在“五十八年前”的1922年8月4日,这篇文章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时,其内容与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文艺论集》所收录的这篇文章的内容却有着相当大的不同,也就是说,当这篇文章在被收入到解放后的《文艺论集》时,郭沫若对其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两位学者所引用的内容,在最初版本中是这样的:
假使创作家纯以功利主义为前提以从事创作,上之想借文艺为宣传的利器,下之想借文艺为糊口的饭碗,这个我敢断定一句,都是文艺的堕落,隔离文艺的精神太远了。这个作家惯会迎合时势,他在社会上或者容易收获一时的成功,但他的艺术(?)绝不会有永远的生命。
这种功利主义的动机说,从前我也曾怀抱过来;有时在诗歌只中借披件社会主义的皮毛,漫作驴鸣犬吠,有时穷得没法的时候,又想专门做些稿子来卖钱,但是我在此处如实地告白:我是完全忏悔了。文艺本是苦闷的象徵,无论他是反射的或创造的,都是血与泪的文学。
正如两位学者所强调的:“只有联系郭沫若当时整个文艺思想和创作的实际进行全面的考察,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而他们所引用的材料,恰恰并非郭沫若“当时”“创作的实际”,两位学者是在没弄清版本问题的情况下,错误的引用了材料,其结论自然与实际情况有偏差。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学者以郭沫若的《文艺论集》为例,提出过“现代文学研究需要注意版本”的问题,只是一直未能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结果从90年代到新世纪,很多学者在研究郭沫若文艺思想时,还在因忽视版本考证工作,造成错误地引用资料而得出错误的研究结论,不能不说十分遗憾。对此,我们可以再看以下几个例子。
1994年,《郭沫若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初版,其中收录了刘纳女士非常富有创新意义的论文《重读〈李白与杜甫〉》,这篇论后又被收录到文化艺术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的《郭沫若评说九十年》,被看作是九十年来郭沫若研究最重要的论文之一,影响自然非常大。然而就是这样一篇被广为称道的论文,其中也存在着材料引用错误的问题。刘女士在这篇文章里就郭沫若“对李白‘附逆’的罪名做了充满理解的开脱”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在这里所注意的是郭沫若熔铸进了个人情感的评论立场。他不能容忍一个诗人在民族灾难面前没有切实的表现,他却宁愿为一个诗人因天真的热情站错了队辩护。这使我想起在写作《李白与杜甫》四十多年前,年轻的郭沫若曾经论证过艺术家与政治家可以‘兼并’:‘一切热诚的实行家是纯真的艺术家,一切志在改革社会的热诚的艺术家也便是纯真的革命家’”,然而实际上郭沫若“在写作《李白与杜甫》四十年前”发表于《创造周报》第18号上的《艺术家与革命家》原文中所写的这句话是这样的:“一切热诚的实行家是纯真的艺术家,一切热诚的艺术家也便是纯真的革命家”,只是到了解放后的五十年代后期编篡《沫若文集》时,郭沫若才在下半句“热诚的艺术家”前面加上了“志在改革社会的”定语。刘纳女士对这句话的引用是基于她在前文中所讲到的:郭沫若认为李白“从永王却是出于‘报国忧民的诚意’,即使投错了门槛,也该以‘天真’原谅”。显然,“出于‘报国忧民的诚意’”而“从永王”的李白,正属于“志在改革社会的热诚的艺术家”,因此在这里引用这样一句话也是非常恰当的。但是倘若刘纳女士再仔细读一遍郭沫若在“在写作《李白与杜甫》四十年前”所发表的论文原文,会发现他在当时所着重强调的,并非艺术家的“志在改革社会”,而是艺术家“藉以宣传的是不是艺术”,他认为“无论若何艺术没有不和人生生关系的事情。更无论艺术家主张艺术是为艺术或是为人生,为什么都可以不论,但总要它是艺术。刀说是杀鸡的也可,说是杀人的也可,我们总要求它是刀然后才能承认,这是易明的事实。”郭沫若进而论到:“艺术家要把他的艺术来宣传革命,我们不能论议他宣传革命的可不可,我们只能论他所藉以宣传的是不是艺术。假使他宣传的工具确是艺术的作品,那他自然是个艺术家。这样的艺术家以他的作品来宣传革命,也就是实行家挚一个炸弹去实行革命是一样,一样对于革命事业有实际的贡献。”在这种论调的基础上,郭沫若得出“一切热诚的艺术家也便是纯真的革命家”的结论,就很自然了。当然,刘纳女士此处材料引用的错误对于整篇文章来说是无伤大雅的,但是这样不经严密考证的资料引用毕竟有违学术规范的严谨,且与其论述本身也并不能完全相契合,不能不说是一处令人遗憾的瑕疵。
再有一个例子是来自于学者魏红珊的《郭沫若美学思想研究》一书中,这本书于2005年8月由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出版,是较新的研究成果,在郭沫若学界也具有很大影响。魏女士在论述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文艺思想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他以表现主义的表现“自我”而自然地将艺术和人生联系在一起的美学思想为指导,提出了艺术和人生天然联系的理论主张:“艺术与人生,只是一个晶球的两面,和人生无关的艺术不是艺术,和艺术无关的人生是徒然的人生”“文艺是人生的表现,它本身具有功利的性质,即是超现实的或带些神秘意识的作品,对于社会改革和人生的提高上,有时也有很大的效果”他所要求和用以衡量艺术及艺术家的标准是“要看你的作品到底是不是艺术,到底是不是有益于人生”。在这里,郭沫若不仅认定艺术和人生具有天然联系,而且强调艺术作用于人生的特殊规定性。他主张遵循艺术本身的规律,以艺术自身特殊的功能,有效地实现艺术为人生的使命。艺术不仅要反抗丑恶、反映现实,而且要表现理想、指导人生,尤其是要去鼓舞人们的反抗意识。查看注释,这段话三句引文中的第一句和第三句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版《郭沫若全集》中的《文艺论集·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第二句出自《文艺论集·儿童文学之管见》。事实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版《郭沫若全集》是根据1957年至1964年陆续出版的《沫若文集》扩充编印的,来自于《沫若文集》的部分均未加以变动,内容相同。也就是说,《郭沫若全集》中所收录的很多作品也并非郭沫若最早在各个报刊上所发表的原文。魏女士在此处所引用的这三句话,都不是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的“理论主张”,而是他在50年代经修改而得的。这三句话在最初版本中的原文分别是:
我认定艺术与人生,只是一个晶球的两面,只如我们的肉体与精神的关系一样,他们是两两平行,绝不是互为君主臣仆的。(《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1922年8月4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文学自本身具有功利的性质,即彼非社会的Antisocial或厌人的M isanthropic作品,其于社会改革上,人性提高上有非常深宏的效果,就此效果而言,不能谓为不是“社会的艺术。”《儿童文学的管见》(1921年1月15日《民铎》月刊第2卷第4期)
可见,郭沫若在“五四”时期所强调的是艺术对“人性提高上有非常深宏的效果”,而到了五十年代才改为“对于社会改革和人生的提高上,有时也有很大的效果”,无论艺术所作用的对象,还是语气,都发生了变化。因此魏女士在郭沫若修改之后的言论基础上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时期的郭沫若作品的重要特点是表现心灵冲动。冲动不仅是创作的一种内驱力,也是表现对象本身。但这些冲动并不源于抽象的人性,而源于现实的刺激和时代的感应。”就有些欠妥,毕竟郭沫若在当时的言论中出现了“人性”一词。事实上,“人性”是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经常用到的一个概念,只是到了解放后显得不合时宜,才在修改中多改为“社会改革”“人生”“革命”等词。
以上几个例子均属于较为典型的情况,除此之外,其他几乎绝大部分论述郭沫若前期文艺思想的论文都是引用建国后出版的《沫若文集》和《郭沫若全集》中的材料,而没有注意到这些材料都经过了郭沫若不同程度的修改,并不能完全代表其当时的文艺思想。有少数学者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采用《〈文艺论集〉汇校本》中的材料。但是这本《〈文艺论集〉汇校本》只是近三十年前黄淳浩先生参与编辑《郭沫若全集》的副产品,他依据“至于一般文字变动,为避免繁冗,则不一一录出”的原则,并没有对全部的异文加以标注,自然也就没有完全反映历史文献最初的真实全貌及后来不同时期的流变,对此笔者曾将《〈文艺论集〉汇校本》中未标注出的异文加以辑录,并形成了论文发表,希望对郭沫若研究有所增益。另外更需要注意的是,收入到《文艺论集》中去的文艺论文也只占郭沫若前期文艺论文的很少一部分,其他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在被收入到此部《沫若文集》时,都经过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但至今却都还没有通过汇校等方式加以标明。可以说,这是郭沫若文艺思想研究中纠结已久的一团乱麻,而这一团乱麻的存在显然不利于学界对郭沫若的深入研究。事实上,从对比的角度来看,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左翼文学界和史学界公认的领袖,其涉猎范围之广,存在时间之长,都超过了鲁迅,其留下来的各种史料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并不亚于鲁迅,然而正如有学者所论:近年来关于郭沫若的研究虽然“收获是很可观的,但与规范成熟的鲁迅研究相比仍存在一段较大的距离”,“与鲁迅研究相比,郭沫若研究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当代性仍显得不够,郭沫若研究迄今还是一个尚未成熟的领域。”这当然都与郭沫若这个历史人物的成就、地位及贡献很不相符,而这种“尚未成熟”显然又与史料的相对欠缺与混乱不无关系。像近年就有学者指出:“《郭沫若全集》非但不是‘完整的第一手资料’,反而极有可能是世界上最不全的作家‘全集’之一”,仅“‘文学编’遗漏的文学作品至少有1600篇以上”此外相对于郭沫若多次、不同程度修改过的大量文艺论著,仅仅一部并不全面的《〈文艺论集〉汇校本》,也明显是不够的。有鉴于以上方面,笔者正在搜集郭沫若前期所有曾被其修改过的文艺论著的原始版本和各种再版本,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文艺论著进行系统的整理汇校工作,希望在此工作完成以后,能为学界考察研究郭沫若文艺思想的流变提供一个更直观而准确的研究资料。
我们都知道古之学者治学,资料版本的考证校勘便是最为基本的功底之一,尤其是到了清初,经学大师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主张“无信不征”,极为注重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开朴学之先河。时至清末民初,国学大师章太炎、王国维等均有着深厚的考证校勘功底,并把治学之道建于此基础之上,而在此之后现代文学领域的大家像鲁迅、郭沫若、胡适等,同时又都是大学问家,他们有着上一辈学者审慎严密的治学态度和考据功底,从而成就了其卓越的学术成果。然而当历史发展到了新中国时期,尤其是从文革结束直至今天的这三十多年,我们的学者却在相当大程度上抛弃了这一治学传统,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最为基础的原始资料考证工作,而多习惯于在提出新观点、表达新思想方面高歌猛进,这样的偏颇显然不利于学科的进一步健康成长。在新世纪已经进入第二个十年的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正向着更加纵深方向发展,如何让这样的发展更科学、扎实、客观,是摆在我们所有学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目前学界的研究现状,学者们应该首先进一步强化重返历史现场的意识,注重文学文本资料的版本问题,所有研究工作都要以资料考证详实、真伪辨析明确为前提,否则便很有可能像本文上面所列举的例子一样,不仅违背了学术规范的严谨性,而且得出了与事实不符的研究结论。正由于此,笔者谨以这篇小文抛砖引玉,希望和广大学者在日后的研究中共同更加注重各种资料文本的版本考证工作,共同维护学术规范的严谨性,增强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并以此努力突破“瓶颈”,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扎扎实实地推向前进。
[1]黄淳浩.现代文学研究需要注意版本——从郭沫若《文艺论集》的版本说起[J].人文杂志,1986(2).
[2]魏红珊.郭沫若美学思想研究[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
[3]孟文博.郭沫若《文艺论集》汇校本·补正[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6).
[4]温儒敏,李宪瑜,贺桂梅,姜涛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魏建.郭沫若佚作与《郭沫若全集》[J].文学评论,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