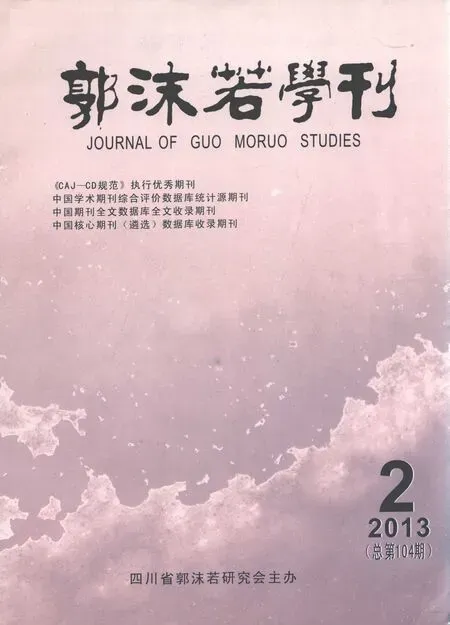《在轰炸中来去》一文的误传
蔡震
(中国社会科学院 郭沫若纪念馆,北京 100009)
1937年7月底,流亡海外十年的郭沫若秘密从日本归国,投身到民族解放战争的滚滚洪波之中。在回到上海之初的两个月内,他陆续撰写了几篇散文记述在这期间的活动:往淞沪战事的前线寻访,拜会北伐时期的老朋友等,应召到南京去见了蒋介石。其中,《在轰炸中来去》是篇幅最长的一篇散文,共有14节,详细记述了他从上海到南京去见蒋介石又返回上海的经过。《在轰炸中来去》列入阿英主编的《抗战文艺小丛书》,1937年由《救亡日报》社以单行本形式,又由上海抗战出版部1937年11月1日初版发行(阿英为编辑者),次年1月,又再版印行。1937年上海文艺社、1938年汉口新人书店出版单行本。
《在轰炸中来去》未见有其他版本。该篇作品后来曾先后收入汉口星星出版社1938年2月出版的《前线归来》、上海北新书局1946年5月出版的《归去来》。1958年编订《沫若文集》时,该篇辑入第8卷,现收《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所有这些关于《在轰炸中来去》出版情况的记录文字都表明:《在轰炸中来去》是以单行本的出版面世的,所以《郭沫若全集》为其所作的篇注道:“本篇最初收入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抗战出版部出版的《在轰炸中来去》。”
然而史实并非如此,《在轰炸中来去》是发表过的,先在《申报》连载发表,之后才结集为单行本出版。
为什么这一最基本,当然也是关于该文很重要的信息,至今未被厘清,甚至根本没有被注意到呢?
首先,大概由于该文写成后,郭沫若并没有署写作时间。以后《在轰炸中来去》的发表,出版单行本,收入《前线归来》集,收入《归去来》集时,都没有署写作时间,直至1958年,郭沫若自己编订《沫若文集》第8卷,才在文末署写作时间为“1937年9月下旬”。《沫若文集》仅注有写作时间,没有关于该文发表的说明,后来的《郭沫若全集》和其他有关郭沫若著作撰写、发表、出版的文献资料,便都循此记录该文而未再注意其是否发表的情况。
其次,应该说这是在郭沫若文献资料整理中时有出现疏漏所导致的问题。
实际上,从一篇所谓与《在轰炸中来去》相关联的文章的信息,原本是早就可以理清此事的。那是在《郭沫若著译系年》(上海图书馆编)的1937年内,所记载的郭沫若的一篇散文作品,题为《谒见蒋委员长》。其相关信息记录为:
载1937年9月下旬上海《申报》;
收入广州战时出版社版《抗战将领访问记》;
注:此篇系《在轰炸中来去》之第十节,收入《抗战将领访问记》题名《蒋委员长会见记》。
从这些文字可知,这应该是一篇无写作时间,而依据发表时间系年的文章(按照《郭沫若著译系年》的编写体例)。但是最关键的发表时间不详,遂使其实际上成为一条无出处、无根据的资料。
《郭沫若年谱》(龚济民、方仁念编)也作了相似的记载。其在1937年9月24日条目中,于郭沫若见蒋介石一事的记述后写道:“接见后曾作《蒋委员长会见记》,内容与《在轰炸中来去》第十节大致相同,收战时出版社版《抗战将领访问记》。”
事实上,在1980年代的时候,曾在郭沫若研究者之间有过打问寻看这篇文章的事情,因为据说最初在《申报》发表出来的文字,与后来录入《在轰炸中来去》的文字有异(指关于对待蒋介石的态度)。之所以如此,一是因当时查找资料不及如今方便,二是在那时的郭沫若研究中,凡涉及带有负面涵义的文献资料会比较引人注意。但这样的事情不曾见诸在文字中,也就一直没有人对于所谓的《谒见蒋委员长》一文说出个所以然。
《郭沫若著译系年》会记到“1937年9月下旬”这个时间信息,显然是因为郭沫若后来将《在轰炸中来去》的撰写署为这个时间,而郭沫若应召去南京见蒋介石是在1937年的9月24日。但是从这一天起的整个9月下旬,直至10月10日(《在轰炸中来去》开始刊载),上海《申报》上并未刊载过一篇题为《谒见蒋委员长》的文章,也即是说《郭沫若著译系年》的这一条记载其实是子虚乌有的,又或者是对于《蒋委员长会见记》一文的误传(战时出版社出版的《抗战将领访问记》确实收录有《蒋委员长会见记》一文)。
出现一篇子虚乌有的文章,只能说明《郭沫若著译系年》,以及《郭沫若年谱》的编写者,还有《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的编辑,都没有对于有无该文进行查考,没有对于《在轰炸中来去》原始文献资料进行查考。郭沫若自己编订《沫若文集》第8卷时于文末署作于“1937年9月下旬”,其实已经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时间线索,惜未被注意。这里就便把《在轰炸中来去》发表的情况作一记述:
《在轰炸中来去》自1937年10月10日起开始在上海《申报》连载发表。连载按文中小节,每日一节(其中只有23日停载一次),至10月24日连载完毕。
《申报》为连载发表《在轰炸中来去》,还特别提前作了宣传介绍,于10月8日、9日两天连续刊发了预告,可谓隆重推出。其中10月9日的预告采用了郭沫若手书的篇题、作者署名(后连载时一直使用这一手迹)。预告中写道:
郭沫若先生在淞沪战事爆发前夜返国,于上月十九日应蒋委员长电召往京,本篇即郭先生在敌机轰炸中往来京沪途中的纪行。作为归国后第一长文,书中对敌机轰炸的暴行、抗战期间的京市、首都军政的当局、淞沪的前线苏州,及其张(一麐)李(根源)二老,皆以极酣畅生动之笔,一一加以描写。我国抗战胜利的前途,从所叙的各方面,亦可获得充分的保证。发表权现为本报获得,即将开始在本报刊载,尚希关心抗战及爱好郭先生作品者注意及之。
《在轰炸中来去》的第十节是写郭沫若面见蒋介石,两人谈话的情形,被单独抽出来,以《蒋委员长会见记》为题收入《抗战将领访问记》一书,那么《郭沫若著译系年》中所谓《谒见蒋委员长》一文,有没有可能也是将《在轰炸中来去》第十节单独成文而在其他报刊又发表过呢?从《申报》的预告可以看到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申报》得到的是“发表权”。所以《在轰炸中来去》连载于《申报》后再面世,就是抗战出版部出版的单行本。
《在轰炸中来去》发表情况的信息理清了,其文本,主要是在第十节的文字,在初刊本和初版本(《申报》发表的文本与抗战出版部出版的单行本文本相同)与作者编订《沫若文集》第8卷时勘定的文本之间,是有所不同的,作了一些文字的删改。以下将该节删削到句子和段落部分的初刊文本节录出来,可与收入《沫若文集》的文本有个比较,其中括弧内的文字为删削部分。
我也同样地感觉蒋先生的精神比从前更好了,眼睛分外的有神,脸色异常红润而焕发着光彩,这神彩就是在北伐的当时都是没有见过的。我见过些西安事变后的蒋先生的像,觉得很有憔悴的神情。[抗战以来的局面不用说是异常繁剧的,念到蒋先生的健康,我自己是暗暗地怀着几分的忧虑。但这忧虑,完全是杞忧。由我自己的眼睛已经证明了。]
“目系而道存”,储蓄在脑里所想说的话顿时也感觉着丝毫也没有说的必要。因为蒋先生的眼神充分地表明着钢铁样的抗战决心,[蒋先生的健康也充分地保证着钢铁样的抗战持久性。]……[蒋先生是我们最高的领袖,他既有持久抗战的决心,那他对于抗战必如何能持久的物质条件。(例如孙总理三大政策所暗示),必已高瞻远瞩,成算在心。不然,他是不会有那样的清明,那样的宁静的。]
在蒋说到郭不必出席会议,只消做文章,研究学问一段后:
[这样的恳切实在是使我感激。而且在这简单的几句话里面还给予了我一个今后工作的途径:学行兼顾。我看,在凡百方面这个途径恐怕都是必要的。]本节最后一段文字:
[又是一次暖和的握手,依然是满面的喜色,分外发着光彩的眼睛。]
此外还有个别词字,以及有些将“蒋先生”改作“蒋”,将原称呼人物的表字,改作姓名或官衔等文字易动。
两相对比而言,初刊文本那样的文字,在抗战期间其实是很寻常的,那一时期的时势使然,说不上是多么恭维,甚至阿谀蒋介石(如有些人所谓)。而到了1958年,当编订《沫若文集》时,作者删改这些文字,也是势在必然的。
在记述《在轰炸中来去》发表于《申报》的情况之外,还须顺带说一下郭沫若两篇与《申报》有关的文章:《全面抗战的再认识》和《惰力与革命》。
《全面抗战的再认识》发表于1937年9月17日《申报》,《惰力与革命》发表于同年10月10日《申报》。《惰力与革命》是郭沫若应约为《申报》撰写的专论。《申报》在抗战爆发之初的那一阶段,特别延请了郭沫若、邹韬奋、章乃器、胡愈之、郑振铎、金仲华、张志让、陈望道、沈志远等一批文化界著名人士为该报写专论,所论涉及抗战期间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郭沫若的两篇文章即是在这种情况下撰写的。所有这些情况,在《郭沫若著译系年》《郭沫若年谱》《郭沫若全集》等有关郭沫若创作活动的文献资料中,都是尚未被记载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