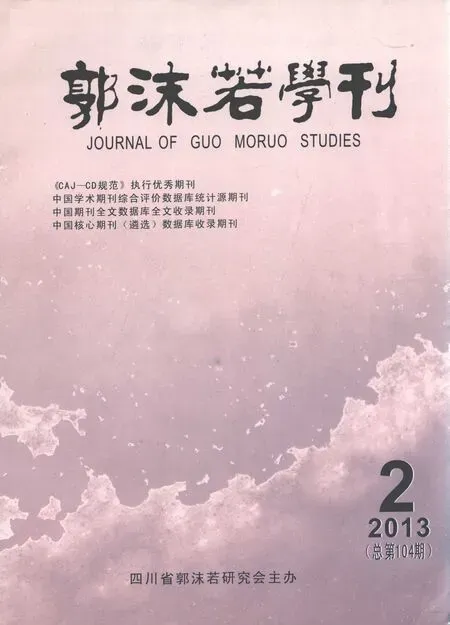试析郭沫若对《周礼》态度的转变
付瑞珣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00)
试析郭沫若对《周礼》态度的转变
付瑞珣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00)
郭沫若对《周礼》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周官质疑》一文,郭老用金文对比官制的方式得出:《周礼》一书是战国时期荀子的后学参考“遗闻佚志”加以己见所著。后来学者提及郭沫若对《周礼》研究的贡献时也只提及《周官质疑》。因此,郭老便成了《周礼》成书“战国说”的代表。其实,郭沫若对《周礼》一书的观念不是静态的,其对《周礼》成书年代的看法更为复杂。本文以时间为尺度,细心考察郭老的专著中有关《周礼》的材料,发现郭老对《周礼》的态度是动态的,其历程大体可用冯友兰先生的“信古·疑古·释古”来概述。而这一历程则是郭氏的学术理路与近代“周礼学”史的内在发展互相交织的体现。
郭沫若;《周礼》成书年代;《周官质疑》;《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郭沫若是中国学术转型时期的文化巨匠,其涉及领域之广泛已是众人皆知。不仅如此,在各个领域之中,郭老也大有一席之地,甚至开创之功,是后人同领域学术研究难以绕过的重要人物。在“周礼学”上,郭老亦成就斐然,郭沫若对《周礼》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了《周官质疑》一文中。《周官质疑》收录于《金文丛考》,最初由日本文求堂书店于1932年影印,1954年经过修正与整理由人民出版社刊行,2002年科学出版社依1954年版收录于《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五册》,其间关于《周礼》的一些基本观念并无变化。此外,郭沫若有关于《周礼》一书的论述与引用还散见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批判书》和《奴隶制时代》等论著中。
在《周官质疑》中,郭老列出金文所载的卿士寮、大史寮、三左三右、作册、宰、宗伯、大祝、司卜、冢司徒、司工、司寇、司马、司射、左右戏繁荆、左右走马、左右虎臣、师民、善夫、小辅、鼓钟、里君、有司、诸侯、诸监等官职,分二十条进行研究,发现这二十项“周代官制之卓著者”,“同于《周官》者虽亦稍稍有之,然其骨干则大相违背。”由此,郭老以金文对比官制的方法——二重证据法否定了《周礼》出书于西周。之后,郭老从古人著书立说的特点分析:“且古人并无专门著书立说之事,有之盖自春秋末年以来。其前之古书乃岁月演进中所累积而成也。《周官》则有异于是。今考其编制,以天地四时配六官各六十职,六六三百六十,恰合于黄道周天之度数,是乃准据星历智职之钩心结构,绝非自然发生者可比。仅此已足知其书不能出于春秋以前矣。”进而,郭老认为“古人并无以天地对立之观念,金文之在七国以前者,纪时之事亦无确证。其以天地四时配六官之说始见于《管子·五行篇》……《周官》者乃周末人也。”最后,郭老得出结论:“《周官》一书盖赵人荀卿子之弟子所为,因袭其师‘爵名从周’之意,纂集遗闻佚志,参以己见而成一家言。其书盖为未竣之业,故书与作者均不传于世……”
彭林先生总结《周礼》研究的方式有三:其一,从文献到文献的方法;其二,运用金文材料的研究方法;其三,研究《周礼》思想的时代特征进而推断成书年代的方法,张国安先生将第三条“概括为思想史的方法”。而这三种研究方式在《周官质疑》中都有成熟的运用,因此可以说《周官质疑》奠定了《周礼》研究的基本方法。可见《周官质疑》在周礼学史上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后来学者提及郭沫若对《周礼》研究的贡献时也只提及《周官质疑》,因此郭老便成了《周礼》成书“战国说”的代表。然而通过考察郭老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批判书》和《奴隶制时代》等论著中对《周礼》的运用,我们可以发现,郭老对《周礼》的态度是动态的,其历程大体可用冯友兰先生的“信古·疑古·释古”来概述。
一
1930年,郭老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出版,震惊了学界,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是发扬。但是这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并非一时之作。“第一第二两篇关于《诗》《书》《易》的研究,从去年(即1928年)九十月间到最近,在杜衍的化名下蒙《东方杂志》连续地登载了出来,这是应该感谢的一件事……第四篇《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乃新近之作”。这些时间相近的文章,对《周礼》的态度有着潜在的不同。
本书的第一篇“《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发表于1928年,其对《周礼》的态度是直接引用,不加辨析与解释。在说“铁”被称为“恶金”时,引《周礼·秋官》的“职金掌凡金玉锡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美恶”,其后又说“铁的发现,论理应该是在周初,不然那农业发达的原因便无从说明了”。在《豳风》《豳雅》《豳颂》中专有咏农事的诗时,便引用《周礼·春官》的“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昼,击土鼓,吹《豳诗》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国祈年与田祖,吹《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緩;国祭蜡则吹《豳颂》、击土鼓,以息老物”。在讽刺《楚茨》中“诸宰君妇”和“诸父兄弟”快乐时,说“这就是一些‘公子’们的生活,这虽然是一些比较原始的公子们,虽然只是一时的快乐(照《周礼》看来当在仲春),但却是怎样的快乐呢”。在说周时有郡县的时候,竟直接举例“《周官》有乡、遂、县、鄙之分”。以上例证虽然不能完全确定郭老认为《周礼》是可靠的史料,但是可以肯定,郭老不考证地运用《周礼》为史料,体现了一种对《周礼》的信任。当然,这种信是一种潜在的,并非理性的。若然,在论及殷周社会制度之时,必有“《周礼》时代的社会生活”一篇了。
本书地三篇为“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发表于1929年9月,其对《周礼》的态度是委婉的,亦或说是矛盾的。在论及盘庚时期的“评议会”现象时,郭老引《周礼》的外朝之政来证明。其后,直言“《周礼》大约是纂成于晚周的文献,在晚周犹有遗存的评议会制,在殷代当然存在,惟惜卜辞过简,实不能寻出积极的证明”。在这里,郭老已经委婉地说出《周礼》成书于晚周,然而在后文论及同姓不婚之制度并非始于周初时,又说:“《周礼》有仲春同淫之习,地官媒氏掌万民之判,‘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此习于春秋时代犹有残存,如《鄘风》之《桑中》,一人而御孟姜、孟弋、孟庸三女,《郑风》之《溱洧》,男女殷盈,相谑而乐,所歌咏者均即此事”。由此窥见,郭老已经自觉地意识到《周礼》的成书时代问题,并委婉地说“大约是纂成于晚周的文献”,这表现出了其对《周礼》认知的自觉,但是这种自觉还不明晰,也未经过考证,因此语气委婉地用了“大约”。在后文运用《周礼》为史料时也未进一步的考辩与解释。
本书第四篇为“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发表于1929年11月。此时。郭老对《周礼》的观念已经大不同于以前,态度是强烈的怀疑。在论及“井田制问题”时,郭老说:“井田制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最大的疑问。其见于古代文献的最古的要算是《周礼》。然而《周礼》便是有问题的书”。如此强烈的质疑态度在之前的文字中是难以见到的,而之后在论及周代无五服五等制度时,语气更甚:“《周官》又分为九畿。国畿方千里,此外侯畿、甸畿、男畿、采畿、卫畿、蛮畿、夷畿、镇畿,均各方五百里(《夏官·大司马》之职)这同样也只能算是一种纸上的规模。周代并没有那样广泛的疆域,而周代彝铭中连畿字都还未见。五服九畿是虚造,五等六瑞也同样是虚造。《周礼·春官·大宗伯》之职: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除王之外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禄……《周礼》是出于刘歆之所表彰”。这里,郭老不仅说《周礼》所载的九畿制度是“纸上的规模”,更说五等爵制度不可信是因为“《周礼》是出于刘歆之所表彰”。这便体现了郭老对《周礼》的强烈怀疑。
二
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几篇论文中,可以看出郭老对《周礼》的态度是有变化的,即从不考辨的使用《周礼》(且称“信古”)到强烈的怀疑《周礼》(且称“疑古”)。而1932年,《周官质疑》的发表可看成郭老对《周礼》态度的又一次转变。这是郭老综合运用从文献到文献、金文对比官制以及思想史三种方式对《周礼》进行客观理性的研究,认为《周礼》为战国时期荀子的后学参考“遗闻佚志”加以己见所著。从此郭老对《周礼》的使用就比较谨慎了(且称“释古”)。
1945年郭老出版了《十批判书》,其中写于1944年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对《周礼》就有了更为成熟的态度。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郭老是以《易》《诗》《书》为主要的传世材料对殷周社会进行研究的。所以,《批判》一文中,在批判文献处理时,郭老对《易》《诗》《书》的篇章年代进行了修正,并未直接提及《周礼》一书(《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所用的《周礼》材料并不多)。但是他也认为传世文献“时代混沌,不能作为真正的科学研究的素材”。这样的认知明显是在《周官质疑》这类文献考证的研究基础之上得出的。在其后的“关于井田制”的批判中,郭老先说:“周室治野的办法在《周官·遂人》职文里面还保留着,那是纯粹十进位的办法……这项资料我觉得同样值得宝贵,并不是出于刘歆的杜撰。因为《周官》尽管是有问题的书,但只是经过刘歆的剪裁添削,割裂改编而已,其中自有不少的先秦资料。故《周官》和《左传》一样,固不可尽信,然亦不可不尽信,使用时须得一番严密的批判”。这里,郭老使用《周礼》为史料时,不仅交代了《周礼》的成书时代有问题,而且还指出其保留的史料价值,足以彰显郭老对《周礼》态度的成熟。
在之后运用《周礼》为史料时,就比较注意其真实性。1951年《关于奴隶与农民的纠葛》一文,在谈及人可以当牲畜买卖时说:“周代的人民是可以买卖的,而且同牛马一样买卖。《周礼·地官》质人有下列的执掌……《周礼》虽然是有问题的书,但那问题是在刘歆把一些后代的成分和自己的意识掺杂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里面而加以改编。质人这项材料,我认为就是原始资料。即使是后代成分吧,也好,因为后代如果都还是这样,周代也就可想而知了”。在1952年出版的《奴隶制时代》中,我们可以发现相似的文字,同样是论及周代人民可以当牲畜来买卖时说:“《周礼》地官有质人一职便掌管着贩卖人口牲畜等事项……《周礼》虽然是有问题的书,但那问题是在刘歆利用了许多先秦的原始材料而加以改编,并搀杂了一些杜撰进去,故《周礼》仍然有丰富的先秦资料存在。这项质人,照它的性质看来,我认为应该是先秦资料……西周也是奴隶社会,据今天所有的资料看来,我认为是不成问题的”。两则相似的材料的关系也许是后者对前者的直接抄誊,但是在细节的文字处理上并不相同,所以更有可能是面对同一问题,运用同一材料而进行的相似的写作。从这里可以发现,郭老对《周礼》的态度是辩证地看待,客观地运用。
经过以上的论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郭沫若对《周礼》的态度是变化的,其历程简单地可以用“信古·疑古·释古”来概括。
三
郭沫若对《周礼》态度的变化是其自身的学术理路与近代“周礼学”史的内在发展交织而成的,而这一历程正体现了中国近代学术思想的剧变。
郭沫若生于1892年,此时正值清末民初,旧时代的学术风气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而各种新的思想也在中国大地上蓬勃生长。郭氏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开启了自己的学术生涯。正如他自己回忆所说:
我是生在过渡时代的人,纯粹的旧式教育在十二三岁时便开始结束,以后便逐渐改受新式教育。尤其在一九一三年出国,到日本去留学之后,便差不多完全和旧式教育甚至线装书都脱离了。在日本的学生时代的十年期间,取得了医学学士学位,虽然我并没有行医,也没有继续研究医学,我却懂得了近代的科学研究方法。在科学方法之外,我也接近了近代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尤其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我才认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亡命生活又是十年,在日本的刑士与宪兵的双重监视之下,我开始了古代社会的研究。为了研究的彻底,我更把我无处发泄的精力用在了殷墟甲骨文字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的探讨上面。这种古器物学的研究使我对于古代社会的面貌更加明瞭了之后,我的兴趣便逐渐转移到意识形态的清算上来了。
从郭老的自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其学术理路的展开:由启蒙时期纯粹的传统式的读经诵典,到接受新式的科学方式,将新的研究方法(二重证据法)与科学的理论(辩证唯物论)相结合对中国古史进行探究。这一学术思想的进展无疑会使郭老对《周礼》态度的变化产生影响。
此外,郭老对《周礼》态度的转变也与近代“周礼学”史的内在发展相契合。郭老对《周礼》态度的转变大体经历了“信古·疑古·释古”三个阶段,而近代“周礼学”的发展也可以用这三个阶段进行表述。
传统研究《周礼》的方式无非两种:其一,针对《周礼》一书进行文字解诂、音义注疏、文献辨伪、有关名物制度的考据;其二,以《周礼》为依据,进行社会政治改革。这两种方式激荡在今古文经学的争执之中,构成了传统《周礼》研究的基本范式,从西汉经学的确立到清季民初的学术大转型,一直是占据主导地位。晚晴的巨儒孙诒让可谓是传统《周礼》研究的集大成者,以《周礼正义》为基石,《周礼政要》为发挥,传统《周礼》的研究可谓登峰造极了。郭沫若从小接受传统教育,熟读经典,其中必然包括《周礼正义》,这一阶段的“周礼学”研究的“信古”特征可以与郭沫若对《周礼》的信任相契合。
清末民初之季,中国的历史学界在西方史学理论的传入与新材料的发现双重刺激之下发生了巨变。这一巨变的主要推动力便是“罗王之学”与古史辨派。他们的史学理论也深深影响了《周礼》研究的方法论。古史辨派以顾颉刚、胡适、钱玄同为代表,他们以“疑古惑经”的态度,对中国的古史问题进行了讨论,其成果体现在1926年至1941年出版的《古史辨》七册。古史辨派的一个重要理论是顾颉刚于1923年《致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其内容是:1.可以说明了为什么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2.可以说明了为什么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人物愈放愈大;3.我们在这上面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至少可以知道那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胡适便以“疑古惑经”的精神对《周礼》发难,他说:“《周礼》屡说祀五帝,其为汉人所作似无可疑,其中制度似是依据《王制》而大加改定的……我们说《周礼》是王莽用史迁所见的《周官》来放大改作的,似乎不算十分武断。但我们不能因此便说刘歆编伪群经。”胡适说《周礼》成书于汉代的原因是祭祀五帝,其论虽然简短,但已经有了以制度思想考察《周礼》的萌芽。与疑古思潮相契合的是,郭老对《周礼》的态度由信任到怀疑。
而对于古代文化过分的怀疑,引起了当时许多学者的反对。1925年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二重证据法”,以此来应对古史辨派的过分疑古。简单的说就是用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相互结合来研究中国古史问题。这一方法的提出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然而对待《周礼》,王国维仍旧遵循孙诒让的观点,认为《周礼》为周公所作,其遗文见于先秦。真正开始运用二重证据法于《周礼》研究的人是顾实和杨筠如。1926年,顾实的《重考古今伪书考》出版,其中便有对《周礼》的研究,他所运用的方法是考察《周礼》所运用的文字,列举出诸多其他古书所不用的古文字,并比较出了《周礼》的一些文字与当时新出土的甲骨文相近,而其他古书却没有,以此来证明《周礼》产生于西周初年。虽然顾实的结论未必正确,但是他所运用的方法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比顾实更进一步的是杨筠如,1928年,他发表了《周代官名考略》。首次运用金文对比官制,证明《周礼》的一些官制符合金文的记载,但是由于金文研究的不成熟,他在材料运用上有很多的错误,但是,其金文对比官制的方式对后来的深入研究有开创之功。正是在这种学术进展的推动下,1932年,郭沫若发表了《周官质疑》,综合运用从文献到文献、金文对比官制、思想史三种方式对《周礼》进行考察,虽然其名为“质疑”,其实郭老以金文对比官制(二重证据法)为主要方法对《周礼》的性质进行考证与解释。与以“二重证据法”来考察《周礼》相契合的是郭老对《周礼》的态度由疑古到释古。
可见,郭老对《周礼》态度的转变是与近代“周礼学”史的内在发展紧密相连的。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郭沫若对《周礼》态度的转变大体经历了“信古·疑古·释古”三个阶段,这一过程反映了郭老自身学术思想的进展与近代“周礼学”史的内在发展。而这些线索,共同交织成一幅中国近代学术变迁的画卷。
(责任编辑:何刚)
注释
:①当今学者普遍依据《周官质疑》认为郭沫若赞同《周礼》成书于战国晚期,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彭林先生对《周礼》成书年代各个观点的分类。详见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1]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五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2]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3]张国安.《周礼》成书年代研究方法论及其推论[J].浙江社会科学,2003(2).
[4]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5]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7]胡适.论秦畤及周官书[A].顾颉刚主编.古史辨(第5册)[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
[8]刘起釪.古史续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9]杨筠如.周代官名考略[J].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2(20).
K05
:A
:1003-7225(2014)02-0045-04
2014-03-19
付瑞珣,(1990-),男,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