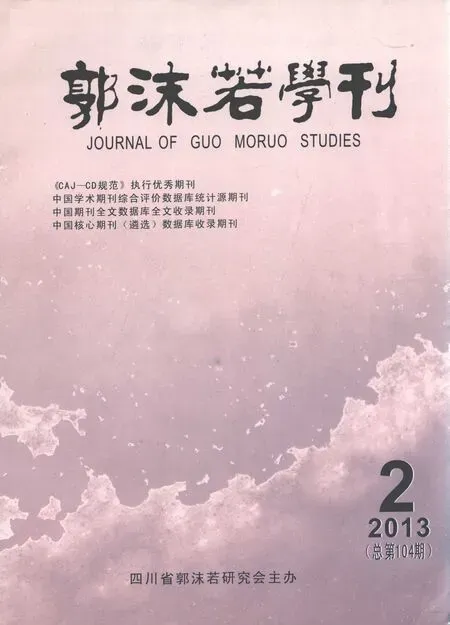威廉·舒尔茨的《郭沫若与浪漫主义美学》译介
杨玉英 廖 进
(乐山师范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
1978年前英语世界研究郭沫若的学术期刊论文共有四篇,发表在《东方文学》1955年第2期上威廉·舒尔茨的《郭沫若与浪漫主义美学:1918-1925》是其中较早的一篇,也是英语世界研究郭沫若诗学与美学思想最早的文章。文中所阐发的关于郭沫若的创作背景、思想状态、诗学与美学主张以及对所涉及的诗歌文本与诗学文本的全文或部分英译,有些已经成为其后郭沫若研究学者所了解的常识。对于这些相关的内容,笔者权作精简或省略。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本文作者会在行文时将其观点,包括文后的注释中那些新颖的有价值的理念、错误或值得商榷之处一一指出。
这篇长达33页的文章从“简介”、“传略”、“1918-1925年”、“观念的构成”与“诗学理论与实践”五个方面对郭沫若浪漫主义美学思想的发生、发展及其在诗歌创作中的体现进行了翔实的阐发,文本涉及到对《天狗》《创造者》《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笔立山头展望》《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和《我是个偶像崇拜者》等7首郭沫若诗歌的全文翻译。文后注释翔实,有91条,共8页,是论文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简介”部分有两处值得注意。一是作者认为,郭沫若灵巧的、时刻准备好的笔常常以诗歌的形式来号召同胞们关心国家和民族大事。他现在的政治地位使他在政治和文化宣传方面的杰出才能得到了体现,但也正是这个政治地位阻碍了他从政早些年在学术上的发展。二是浪漫主义的文学理想在1925年的时候突然遭到遗弃,代之以“应该积极为社会的进步服务”的申明,但这只不过是包含在辩证唯物主义术语中的“革命文学”的短暂前奏而已。
“传略”部分指出,郭沫若在最初充满热情的创作岁月里所信奉的浪漫主义,是结合了他自己的充满激情的观点,他所阅读的中国作家,以及泰戈尔、年轻的歌德和惠特曼的作品的。在这种精神与影响下创作的郭沫若诗歌和戏剧,正是本文所研究的主题。郭沫若的激进倾向和当时弥漫在20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学家中的那种思想的漂移不允许他保持一种将艺术本身当成目标的艺术信仰(即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信仰)。
“1918-1925年”一节有多个需要注意的观点。作者认为,1925年郭沫若戏剧性地背离自己的浪漫主义的信条,被好些批评家认为是其所谓的早“期”结束的标志。由于对郭沫若生平和创作的最初的调查研究以及对他已经出版的作品的批判性的研究版本都还没有确定,这个必须得等待他停笔为止,将其生活进行分期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而且,这样的事更多仅依赖于观念的转变。郭沫若1925年后的戏剧和诗歌继续在总体的语气和感觉上反映出那种潜在的浪漫主义的气质,这就使得将其创作进行分期变得更加的牵强。
要是郭沫若从医学院毕业之后选择文学和公众生活没有反映他的气质和心理性格的话,它们是不会引起文学研究者的关注的。他在不同的时候对此选择给出了两种不同的理由。是少年时代就有的耳疾阻碍了他的医学实践吗?还是因为他相信文学能够为中国的需要提供更好的服务呢?前一个理由会引发对后一个理由的真实性的质疑,而且两个理由本身都不完全正确。作者在文后的注释第19中指出,在《郭沫若选集》第一卷第152-166页的《歧路》中,郭沫若有力地谴责了那个繁殖连医生也不能治愈的疾病的社会体系。这种疾病只能通过社会行动和社会改革才能根治。这个观点也被如白英和袁家晔(Yuan Chiahua)这样的批评家所引用。然而,这更多似乎是对过去行为的一种辩护,而非对在经过几年的学习之后为什么要放弃学医这个问题的回答。
舒尔茨在提及郭沫若读中学时被《史记》所吸引时的表达不太清楚:“在他自己对学生时代的记叙中,郭沫若回忆起年轻时被《史记》《屈原列传》所吸引,(屈原)对他此后登上共产党的文化英雄万神殿是有帮助的。还有项羽、伯夷及其他人物的传记。《史记》中的《刺客列传》对郭沫若也有很大的吸引力。除了反映出郭沫若对古代典籍的兴趣之外,文中他列举的这个清单还试图反映出他自己的精神特质。”原文在《史记》(Shih-chi)之后紧跟着的是对《屈原列传》的英译(biographies of Ch’u Yuan),让读者一看以为是对《史记》的英译。将其改为“the Biographies of Ch’u Yuan in Shih-chi(史记,The Historical Records)”更准确,也不易引起读者的误解。关于《史记》,郭沫若在《我的童年》中是这样记叙的:“把《史记》读了一遍的也怕就是在这个时候。那时候我很喜欢史太公的笔调,《史记》中的《项羽本纪》《伯夷列传》《屈原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信陵君列传》《刺客列传》等等,是我喜欢读的文章。这些古人的生活同时也引起我无上的同情。”舒尔茨紧随其后评论道,只有极个别例外,所举的这些历史人物,包括出现在《刺客列传》中的那些,都是以他们对无望的事业的支持和与《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感伤情绪相似的悲观厌世而出名的。这或许也是对中国时代精神的反映,这种精神要求人们对民族的觉醒和年轻祖国的复兴作出无私的奉献。
“观念的构成”一节主要梳理了郭沫若诗学和浪漫主义美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对其《王阳明礼赞》《创造十年》和《文艺论集》中的诗学和美学观点进行了引用,对《湘累》中的两处屈原自白进行了引用,并对《天狗》《创造者》《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笔立山头展望》《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和《我是个偶像崇拜者》等7首诗进行了全文英译。
舒尔茨认为,从整体的思想发展来考虑的话,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是个异常的现象,它的产生是对艺术与非艺术需求的回应。它是对早期的那种秩序井然的自满的反对,是对逐渐灌输的新鲜感、活力以及艺术世界之意义的寻求。分离与对美学价值的奉献对其存在来说是必要的,但是一种要求艺术完全自治的生活方式却发现社会理想在喧嚣的现代中国是被限制了的。中西思想相融合的遗产能够明显地在郭沫若创作于日本时期的诗歌和文章中看出来,在他的自传体作品中这两种不同的思想来源甚至更加显而易见。
在舒尔茨看来,郭沫若接近王阳明哲学在本质上是基于感性而非理性。而郭沫若在他说到自己对泰戈尔和歌德诗歌的喜欢,指出是通过这两个诗人,他发现了哲学上的泛神论之后讲,“或者可以说我本来是有些泛神论的倾向,所以才特别喜欢有那些倾向的诗人的。”他在情感上依附于一种理想的自然的体系。有人认为,他的思想,正如在他的诗歌和戏剧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更适合与19世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感性的泛神论相比较。舒尔茨在文后的注释第37中提及,朱自清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8卷《诗歌卷》第5页上指出了郭沫若诗歌的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泛神论思想;二是20世纪的反抗精神。这两个特征都是与中国的传统和诗歌相异的,也即是它们都是从外国引进的。
作者认为郭沫若的《天狗》反映了他的创作思想——将那个完全可以理解的自我与无限的、唯心主义的、在诗中甚至有些自我本位的“我”进行了诗意的认同,将宇宙看成是包蕴了个体的宇宙灵魂的世界。舒尔茨在注释第40中提醒读者,不能将郭沫若的“天狗”与弗朗西斯·汤普森(Francis Thom pson)的“天堂猎犬”混为一体。在英国诗人汤普森那首作于1893年的著名诗歌《天堂猎犬》(The Hound of Heaven)中,诗人将天主比喻成天堂里的一条高贵的猎犬,它是一个不屈不挠的追求者,一直在猎取人心。
在舒尔茨看来,尽管《天狗》一诗在诗学高度上没有可比性,但蕴含在创作于《天狗》之前和之后的那些诗中的诗人的观点却可与威廉·华兹华斯诗学的泛神论的表达相比:“在所有人都与上帝同在的那种内在生活中,人自己就是上帝,存在于一个强大的整体中,正如正午时分,当整个半球都呈现一片天蓝色时,无法分辨出无云的东方与无云的西方一样。”或者与《创造者》一诗中想要表达的创造社的诗学宣言相比。郭沫若自己称受到了惠特曼的影响而创作的《凤凰涅槃》一诗,表现出了与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和惠特曼的超验主义的烙印相同的几个基本的构成特征。“一切的一,一的一切”的重复,反映出了作者郭沫若的现实的一元论的观念。那群聚集在濒死的伟大凤凰四周的贪得无厌的小鸟,象征着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瓜分衰弱、一盘散沙的中国之企图。而重生的凤凰则预示着一个崭新的、现代的、辉煌的中国的再生。民族主义在郭沫若的诗中,同时也在中国的时代精神中有着强烈的共鸣。从总体的效果来看,《凤凰涅槃》一诗的乐观多于悲观,但是受浪漫主义的鼓舞而对贫穷、疾病和肮脏的抨击仍然是存在的。19世纪的欧洲浪漫主义作家大都是贵族,他们远离下层阶级,发现用他们的信条来批判人类的贫穷以及造成贫穷的原因是必要的。同样的显而易见的矛盾也在郭沫若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相互作用的宇宙灵魂,现在表现为人同时也表现为自然,在郭沫若的诗《笔立山头展望》中被呈现为“自然与人生的婚礼”,而在《地球,我的母亲》中则是在对地球母亲说,“我的灵魂便是你的灵魂”。人的个性、自我的超越和自我的肯定在如《地球,我的母亲》和《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可找到表达。⑧(p66)
舒尔茨在英译《笔立山头展望》时将原放在诗末注释中对“笔立山”的说明“笔立山在日本门司市西。登山一望,海陆船廛,了如指掌”放在了诗的正文之前,但是他对“海陆船廛”和“了如指掌”的翻译都不准确:“船、陆地和海洋,像手掌一样明亮,一目了然。”“廛”在古代指的是一户平民所住的房屋,这里可通指岸上的房屋。“了如指掌”意为对情况非常清楚,好像指着自己的手掌给人看。
在舒尔茨看来,郭沫若在歌德的影响下创作的三幕剧《湘累》,不仅表明了他在观念的强调上的转变同时也显示出他气质的变化。现在,他不再让自己不停歇地狂喜地高歌,而是以一种更加克制但仍然充满感情的口吻来述说:“我又盼不得早到天明,好破破我深心中不可言喻的寥寂。啊,但是,我这深心中海一样的哀愁,到头能有破灭的一天吗?哦,破灭!破灭!我欢迎你!我欢迎你!我如今什么希望也莫有,我立在破灭底门前只待死神来开门。啊啊!我,我要到那‘无’底世界里去!”此外,郭沫若作品强调的重点也变了。他从在惠特曼的影响下赞美和陶醉于自然的善与人的进步,到现在对人与人类社会给予更多的批判。
诗人仍然是乐观的,因为他呼吁人们起来反对他自己,祛除世界的邪恶。偶尔,在他的作品中女性扮演了男人邪恶行径的拯救者或精神的复仇者。《女神之再生》这部神秘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浪漫结合之作,描绘了女神们对美丽新世界的摧毁。舒尔茨在注释第66中指出,郭沫若曾说《凤凰涅槃》是中国之新生的象征,《女神》这部诗集中的其他诗歌,如《匪徒颂》和《晨安》,都是对这种精神的委婉的颂扬。
郭沫若的诗集《瓶》中的那种压抑的、忧郁的味道或许反映了他正在经历的思想变化。它们似乎与《瓶》之前的诗篇中的那种青春活力和《瓶》之后的诗篇中的“革命文学”的精神完全不同。《瓶》或许暗示了这些诗歌是写于他与合法的决裂和与另一个相结合之间的低谷时期。
“诗学理论与实践”一节阐释归纳了郭沫若的诗学理论和美学思想在其诗歌创作中的具体体现。作者指出,在郭沫若的折衷主义诗学主张中,艺术是天才诗人以韵律的形式对情感的自然表达:“文艺也如春日的花草,乃艺术家内心之智慧的表现。诗人写出一篇诗,音乐家谱出一支曲子,画家绘成一幅画,都是他们感情的自然流露……”空间艺术和时间艺术都倾向于音乐性,在这种运动中,音乐是最重要的:“音乐、诗歌、舞蹈都是情绪的翻译,……一是翻译于声音,一是翻译于文字,一是翻译于表情运动。”舒尔茨对郭沫若《艺术的本质》中对诗的三个特征的归纳做了引用:“1.诗是文学的本质,小说和戏剧是诗的分化。2.文学的本质是有节奏的情绪的世界。3.诗是情绪的直写,小说和戏剧是构成情绪的素材的再现。”“诗不是‘做’出来的,是‘写’出来的”意指艺术是不能设计的,它是诗人情感以韵律和表达的形式之即时的、自然的投射。
新词也丰富了郭沫若的创作。诗中现代科技术语被借用,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他长期呆在日本和其间接受的医学方面的教育并不是完全无用的,如“大都会的脉搏呀!生的鼓动呀!”、“我是X光线底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等等这些诗行构成了中国新诗的新起点。日本的术语,尤其是关于科技方面的,被引入中国的诗歌中,成了郭沫若的外援。上面这些表达带给他的诗一种现代的科学文化气息,这与中国想要将自己从一个落后的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的愿望是完全一致的。
丰富的、变化多样的修辞手法可在郭沫若的诗歌中找到。“典故”在其诗歌中有高度的发展,因为对他而言诗歌不是一种技巧的精心之作,而是内心冲动的自由的、不受束缚的表达。郭沫若文学作品的典故主要源自汉朝及之前的经典,如《楚辞》《史记》《山海经》《列子》《说文》、儒家经典等。
在象征性的语言方面郭沫若对中国的诗学语言并没有什么令人惊异的创新。他采用标准的象征体,如“荷”与“梅”象征纯洁与高贵,“凤凰”象征国家,“群鸟”采用的也是它们通常的含义。
《湘累》中最有趣最令人喜欢的一处明喻是诗人将“脑袋”比作“灶头”,将“心脏”比作“土瓶”,将“眼耳口鼻”比作“烟筒的出口”。在《天狗》中他则将自己比作可以吞下整个宇宙的“天狗”,比作“月底光”、“日底光”、“一切星球底光”、“ X 光线底光”和“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在该诗的第三诗节,诗人把自己比作“大海”、“烈火”和“电气”。
郭沫若从西方的文学经验中借用了十四行诗来满足自己的个体需求。变换不定的诗行长短、不均匀的诗节、跨行的诗句是他诗歌的显著特征。这些诗明显地不注意诗歌的形式,其中大多是试验性的,但有的也被证明是相当成功的。郭沫若最好的诗是用自由体形式创作的,只是基本的韵律、语言的流畅和内在的张力将他的诗结合为一体。
重复是郭沫若诗歌自始至终用来表达自己情感的技巧。对词语、诗行的重复使用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使他的诗产生了一种音乐的效果,远远超过了他诗歌的抒情特征。《凤凰涅槃》即是运用这种技巧的典型。《天狗》中每一行的开头用的都是第一人称代词“我”。《地球,我的母亲》中每一诗节都是以标题“地球,我的母亲”开始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和《我是个偶像崇拜者》中重复技巧的使用也是很明显的。
平行诗行的使用多到不用提醒大家注意,相反,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晨安》中对中国传统诗歌技巧的运用。
如果对郭沫若诗歌进行历时的考证的话,可以看出其越来越背离松散的自由体诗的形式,相反,增加了对诗歌形式细节的关注。诗集《瓶》中的诗歌就呈现出了这个事实,从中可看出诗行长短的规律性、每个诗节中数量相同的诗行以及更多运用的是每个诗节是四行的形式。同样需要给予高度关注的还有他在美学原则和个人气质方面的转变。他的诗学才能的这种束缚或许是其诗歌力量总体上下降的原因。
在总体的风格上,郭沫若的诗歌表现出两个明显的极端:一是早期诗歌中那种急迫的、强有力的语言上的冲力与《瓶》中平静的、克制的诗行;二是所谓的“惠特曼”时期的诗歌中丰富的、充满活力的语言与后期诗歌中忧郁的文字。
郭沫若这些年的诗常常是诗人情感冲突的直接的阐述。这些诗表现出了一种风格,这种风格即是他的强有力的美学思想的直接结果:“我效法造化底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我萃之虽仅限于我一身,放之则可泛滥乎宇宙。”
他的诗歌是一种轻率的感情的冲动在诗的外衣下的表现,具攻击性、傲慢无礼、自信、独断而且具有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他的这些自吹自擂的诗只不过是他气质的反映而已。
郭沫若的诗,尤其是他所谓的“惠特曼”时期的诗,总体上不如他后期的诗和戏剧那样在问题的判断和风格上具有批判性。《女神之再生》中赋予几乎所有戏剧人物的夸张且言不由衷的话,使得这种方式几乎完全不适合现代戏剧或诗歌。而且,诗人在这方面的不足似乎充分地表现在人物肤浅的对话中,尤其是在共工和颛顼之间你来我往的空洞语言上。
总体说来,正如郭沫若这个时期的作品所证明的,读者可以在其早期诗歌中读到一些他最好的诗。与散文体作品相比,他的才能更适合诗歌,尽管对话在散文体作品中的使用效果更佳。郭沫若在美学原则上的逐渐转变,或者在根本上更是气质和个人性情的问题,与灵感和有效的陈述的衰退是并行的,表明了一种因果关系。他早期的作品中所表现的那种精神和语言上的新鲜感,在后期作品中完全没有了。后期的作品在总体上可比作是他自己对“屈原”,即诗人自己的“他我”的描绘,是一个“在外表和特征上苍老、形容枯槁之人”。(12)(P74)
尽管存在诸多不足,文中指出的仅是其中的一些,但他并非完全配不上他所自称的那些大师。如果不从各个视角去考察去研究他整个的生活和创作的话,要对他真正的地位作出全面的评价都将是不成熟的。然而,下面这个建议或许不算是太早,那就是,郭沫若在世时国内批评家和读者对他的赞誉在某种程度上是应得的。或许,更可能是他对时代和其他作家的影响比他自己的创作本身使他居于中国现代文学最杰出的作家之列。
注释:
①除舒尔茨的《郭沫若与浪漫主义美学:1918-1925》外,另有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哈佛中国研究论文》分别在第4期和第11期上刊载了关于郭沫若的研究文章。其中一篇是克拉伦斯·莫伊的《郭沫若与创造社》,发表于1950年。另一篇是戴维·罗伊的《郭沫若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时期:1892-1924》,发表于1958年。斯洛伐克著名汉学家马立安·高利克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系列之四《郭沫若的无产阶级批评》于1969年发表在《亚非研究》第5期上。其出版信息为:
William R. Schultz. “Kuo Mo-jo and the Romantic Aesthetic: 1918-1925”. Journal of Oriental Literature, 6.2 (April, 1955). pp.49-81.
David Tod Roy.“Kuo Mo-jo: The Pre-Marxist Phase: 1892-1924
”. Papers on China, 1958,No.11. pp.69-146.Marian Galik. “Studie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Part IV. The Proletarian Criticism of Kuo Mo-jo
”. Asian andAfrican Studies, No. 5, 1969. pp.145-160.Marian Galik. “Studie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Part IV. The Proletarian Criticism of Kuo Mo-jo
”.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No. 5, 1969. pp.145-160.②威廉·舒尔茨(W illi a m R.Schu l tz).《郭沫若与浪漫主义美学:1918-1925》(Kuo Mo-jo and the Romantic Aesthetic:1918-1925),前面所引书,第74-81页。
③同上,第75-76页。白英一书的出版信息为:袁家晔(Y uan Chia-hua)、白英(Robert Payne).《中国当代短篇小说》(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伦敦:卡林顿(N.C a rri ngton)出版社,1946年版。共 146页。
④同上,第54页。英文原文为:“:“In his own accounts of his lower and middle school years, Kuo recalls his youthful attraction to the Shih-chi (史记) biographies of Ch’u Yuan (屈原),whom he has since been instrumental in elevating to the pantheon of Communistcultural heroes, Hsiang Yu(项羽),Po I(伯夷),and oth er s.”
⑤郭沫若著.《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
⑥威廉·舒尔茨.《郭沫若与浪漫主义美学:1918-1925》,前面所引书,第54-55页。
⑦同上,第77-78页。英文原文为:“The Chinese figure must not be confused with Francis Thompson’s ‘Hound of Heaven,’which in that famous poem symbolizes God, the inexorable pursuer.”p.78.
⑧同上,第78页。注释第41条解释该观点引自朱利安·罗斯((Julian L. Ross)的《文学中的哲学》(Philosophy in Literature
)一书第183-184页。书中注明是选自华兹华斯未出版的手稿片段,后收入《序言》(应指华兹华斯(W illi a m W o r dswo r th)为其与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合著的《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第2版)所写的《序言》(The Prelude),本文作者注)。⑨同上,第68页。其英译为:“Mount Fudetate lies to the west of the Japanese city of Moji. Climbing the mountain, this mark for ships of land and sea, as bright as the palm, is seen at a glance.”
⑩同上,第70页。引文涉及郭沫若的《文艺之社会的使命》和《艺术的本质》。
(11)同上,第71页。引用的诗行涉及郭沫若的《笔立山头展望》和《天狗》。作者在注释第84条指出,该观点参照了闻一多的《女神之时代精神》。
(12)同上,第71页。中文原文为:“从早起来,我的脑袋便成了一个灶头;我的眼耳口鼻就好像一些烟筒的出口,都在冒起烟雾,飞起火星,我的耳孔里还烘烘地只听着火在叫;灶下挂着一个土瓶——我的心脏里面的血水沸腾着好象干了的一般,只迸得我的土瓶不住地跳跳跳。”
(13)同上,第74页。舒尔茨在注释第91条中例举了闻一多的《女神之时代精神》、冯文炳的《谈新诗》和黄人影的《郭沫若论》几种国内对郭沫若诗歌的褒扬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