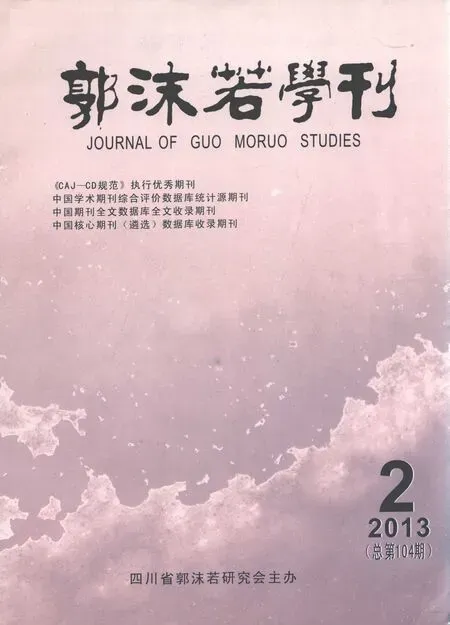《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发表前前后后
翟清福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所,北京 100732)
余英时在《互校记》一文上的失误,教训是深刻的,《真相》一文已发表18年,该文发表前后有些经验也值得总结,特写此文求教于方家。
我和耿清珩同志在1996年发表在《中国史研究》第3期的《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副标题是《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以下简称《真相》)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与支持。一些利用余英时《互校记》攻讦郭沫若的人,有所收敛。但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还在利用此文,对郭沫若进行攻击。他们有的撰文,有的利用现代网络,在网上对郭沫若污蔑,原因是有的人孤陋寡闻,既然写有关郭沫若的文章,特别是与《互校记》有关的信息,就应当多加留意,但他们知之甚少,很少关心不同观点的论述。更有甚者,他们有的明明知道已有不少揭露《互校记》为政治攻讦的论文,有些文章也读过,但采取谎言重复三遍便是真理的自欺欺人的手法,继续制造混乱。对于少数有政治偏见的非学术文论,我们主张及时消毒,净化空气。有鉴于此,我们回顾一下《真相》发表前后的历史,一来可以总结一下郭沫若研究的经验,二来或许能起到一些消毒的作用。
缘起
郭沫若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前,郭沫若研究学会负责人黄烈同志让我查一下已发表的有关郭沫若研究的论著和资料。我从目录中发现1954年香港《人生》杂志第7-8期,连载有余英时的《郭沫若抄袭钱穆著作考——〈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以下简称《互校记》)一文,觉得此文与众不同,决定有时间找来进行研读。但因工作忙,加上这一杂志只有在北京图书馆才能查到,就暂时放下了。适值耿清珩同志退休,向我要事做,于是我就向她推荐此文。用了三天的时间,她从图书馆将该文抄回后,并精读数遍,提出“郭老与钱先生史法各异,观点不同,一个是唯物史观,一个是考据者”的初步意见。之后,因为都较忙,就搁下了。1990年,我参加在四川乐山举行的郭沫若学术会议时,对余文做了一个简单的评论,发表在《郭沫若学刊》1990年第4期。
1991年和1994年,余英时将该文略作调整后,先后收入纪念钱穆的《犹记风吹水上鳞》集子与《钱穆和中国文化》一书,要在社会上产生此文第一次发表时未能产生的影响。为了推销其观点,余英时还专门写了《谈郭沫若的古史研究》一文,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1992年十月号上,否定郭沫若的古史研究成果。由于《互校记》最初在香港发表,读者不多,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大。在大陆出现后,读者倍增,在学术界影响极坏,丁东等人的追随文章相继出现在一些期刊上。我和耿清珩对《先秦诸子系年》和《十批判书》都没有什么研读,更未对两书进行过比较研究。只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开始读两书。
《真相》是怎样完成的
我们在对照余文读郭、钱两人的书时,首先对余文“抄袭”的铁证依据,明人王世贞的著作,做了查对。我们发现在王世贞的著作中,既没有钱穆所讲的《读书后辨》,也没有郭沫若所说的《读书后记》,但是有《读书后》。这一发现,证明包括余先生在内,郭沫若、钱穆三人都未看到王世贞的原书,他们所用的王世贞文字,是转引自清人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一书,而该书版本多达十几种,不难借到,并不像余英时所讲的那样玄乎。两书所引书名不同,钱书为《读书后辨》,并在其后加了一个“说”字,成为“《读书后辨》说之曰”,这显然是断句时误断,而且他还加上一个“说”字,仍然不通,既有“曰”,还加个“说”,是不应出现的问题;郭书在引王世贞的文字时,可能觉得书名不全,才加了“记”字,也不应该;余英时不会看不见郭、钱二书所引王世贞的书名不同,由于先入为主的思想占了上风,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只想着我抓着了抄袭的铁证了,你还有什么话说,所以他的错误较钱穆的错误更为严重。铁证被推翻后,我们延着这条路对余文的所谓抄袭证据一一查校,发现所谓的抄袭证据是站不住脚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在林甘泉研究员的帮助下完成了《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草稿。初稿打印了30份,分送有关专家学者征求意见,并于1996年4月15日,邀请近20位专家学者对初稿进行了一天的讨论。
在讨论中,大家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使本文作者受益不浅,对改稿帮助极大。这不仅充实了文章的内容,也对作者给予了很大的鼓舞。如钱穆的《系年》只是将材料整理了一遍,没有多少观点。而且不少观点是前人的,比如稷下学,不是他的发明,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又如郭沫若和钱穆两书性质不同,一个是分析思想体系,自己形成诸子的体系的专著;一个是考订诸子年代,对材料分类排比。有学者指出,《十批判书》对《先秦诸子系年》有些看不起,钱穆有些不服气。有的明确说,余英时的文章是为了政治的目的,不是学术。国际上反鲁、反郭有一个思潮,中国有大事,余英时肯定有评论。有的专家指出,攻击郭沫若的人几乎都没有对他进行认真的研究。
研讨中,大家的认识都有所提高,有的参加会议前,认识不甚明确,认为抄袭的问题很麻烦,对反驳《互校记》觉得很难;受《互校记》影响,基本上是接受其观点的,口头上虽然没有说初稿对《互校记》反驳得占理,但从其发言中已知,通过对初稿的讨论,认识有了转变。
《真相》发表后产生的反响
初稿修改中,,吸收了专家们的意见,又查对了一些材料,充实了内容,已经很难说此文是那个人的研究成果了,因为甚至连标题都是听取意见后改的。定稿后得到一级学术杂志的支持,《中国史研究》把此文放在首篇发表,《郭沫若学刊》同时全文转载。稍后,全国发行量较大的颇有影响的《新华文摘》也全文转载。截至2013年止,已有十几个报刊、文集或摘登或全文转载,引用此文观点的也不少。甚至一位美国学者从美国打电话给姜广辉研究员,询问中国学术界是否要发动一场批判运动。当被告知,这只是一般学术讨论时,他表示赞同此文。一些知名老教授、老专家也纷纷表示支持《真相》的观点,作者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其中八十高龄的就有于光远、吴江、邓广铭等好几位。于光远向吴江推荐登载在《博览群书》的该文文摘后,吴老不知作者在什么单位,几经查询,找到了作者,他不只一次地表示,同意作者的观点。之后,他以曹剑的笔名,编辑了《公正评价郭沫若》文集,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文集有评论《互校记》和《郭沫若总论》等歪曲事实,攻击郭沫若的论文,也有《互校记》的文摘。吴老为文集还专门写了前言。他揭露余英时的人品,强调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持公正立场,尊重历史。邓广铭先生是经过考古学家宿白教授推荐才阅读《真相》的,也不知道作者是谁,因为作者没有什么知名度,他误认为作者用的是笔名,当通过他的学生(研究员)了解到作者的情况后,让他的几位学生向作者转达他的话说,“看来一桩不好翻的公案,被他们给翻过来了,钦佩!钦佩!”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刘大年和《求是》杂志副总编苏双碧都表示,希望多发表《真相》这样的文章。时任中国史学会会长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戴逸和西北大学原负责人张岂之教授都肯定了此文。王戎笙研究员在一次社会科学院会议上推荐此文。台湾学者来大陆访问时,对林甘泉研究员说,《真相》一文写得好,击中了余英时的要害。2006年,该文荣获“第一届中国社会科学院离退休人员优秀科研成果”论文一等奖。值得一提的是,《互校记》的作者余英时,对《真相》一文没有反映,这不是他的一贯做法,过去曾有过,他与中山大学冯依北教授在中国文学史问题上进行争鸣的事,每当冯先生发表一篇评论余英时观点的文章时,他就会写不止一篇文章进行辩论。《真相》问世后,未见其动作。
几点体会
经过反思,我们认为有如下几点体会。
一、事实证明,一篇论文或专著,经过多人研讨,反复认证,多方征求意见,远比一两个人的成果好得多。而且在讨论中,无论是执笔人还是参与讨论者,都会通过研讨,从中受益,有所提高。集思广益,确实是推进学术发展的重要方法,值得推广。其实,这一做法是郭沫若和尹达等老一辈学者的治学方法,早在1959年《中国史稿》就在全国史学界征求过对该书的意见,参加讨论的有史学工作者、高校师生,可谓盛况空前,多以能够参加《中国史稿》的讨论为荣。没有参加讨论的学人,有不少将个人意见,写成书面材料,寄送该书编写组。收集到的意见多达八千多条,对书稿的修改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通过此次活动,参加讨论者,也从中受益不小,因为参与讨论,必须认真研读书稿,在听取他人发表意见时,也会受到一些启发。
二、做学问要防止先入为主,应扎扎实实地求真求实,尽可能地使用第一手材料。余英时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明人王世贞的著作书名问题,值得借鉴。又如方舟子先生也发表了评论《互校记》的长文,文章有理有力有节,驳得抄袭说者无话可说。然而,由于他评论《互校记》时使用的是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钱穆和中国文化》的版本,不知道该书有所删节,结果有学人对此提出批评。《真相》所用的《互校记》是《犹记风吹水上鳞》港台的本子,而且还参照1954年《人生》半月刊的原文,就避免了麻烦。可见,在资料的使用上一定要慎重。
三、政治与学术很难分开,应当像郭沫若那样,妥善处理好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坚持真理。不能为了政治的目的,歪曲事实,篡改历史。余英时就是为了政治目的,被政治蒙着了眼睛,由于政治的偏见,才铸成《互校记》这样的错误。
四、做学问不能意气用事。钱穆先生因为对郭沫若不服气,所以暗示让还在上学的余英时将《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两书比较阅读,并写出《互校记》这样的文章。
五、做学问切莫为了名利而歪曲事实。一些利用《互校记》攻击郭沫若者,除了政治目的外,无非就是为了名利。其实这种追求名利的后果是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六、关系到个人声誉的结论,要慎之又慎,防止轻易做出结论。
七、做学问要谦虚,防止骄傲。余英时在《互校记》的问题上,就是成名后,产生了骄傲的情绪。学生时代的作品,未认真研究,轻易地一而再地发表,就是很好的证明。其晚年在台湾的自以为是是出了名的。不过他对自己的错误虽然未明确表态,沉默也是一种表态,远比那些仍在利用《互校记》在作文章的先生们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