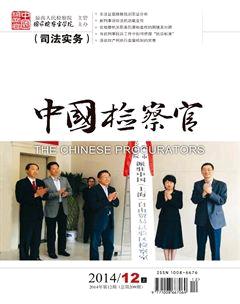事出有因伪造民事证据的行为定性
文◎高蕴嶙周玉玲
事出有因伪造民事证据的行为定性
文◎高蕴嶙*周玉玲**
一、基本案情
2008年,犯罪嫌疑人张某、王某、陈某、李某作为刘某的下线相继加入刘某的传销组织,每人入会时各交纳了21万元的入会费。2010年初,该传销组织无法继续进行并予以解散,张某等四人便要求刘某赔偿损失或让刘某交出其上线。刘某既无法找到其上线也不愿意赔偿张某等人损失,于是刘某更换了电话号码及住址以躲避张某等人。张某等四人在无法联系上刘某的情况下,为了迫使刘某出面,于是共谋伪造了一份刘某向张某借款50万元协议书(张某等人认为刘某作为其上线大约从他们84万元的入会费中提成了50万元,并且四人认为只能选其中一人作为出借人才符合常理),见证人为王某、陈某、李某。2010年4月6日,张某将刘某作为被告向重庆市某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并向法院提交了借款协议书复印件。张某等四人还就诉讼费用的分摊以及胜诉后效益的分配另外签订了协议。2010年7月2日,重庆市某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王某、陈某、李某便以证人身份出席法庭证实刘某向张某借款的经过,但刘某当庭辩称借款协议上的手印并非其本人所留,并申请司法鉴定,张某却以借款协议书原件遗留在家中为由申请延期审理。当日庭审后,张某等四人便不让刘某离开,并以协商解决为由,要求刘某一同协商,刘某考虑到该经济纠纷系传销引起,也不愿司法机关知道该经济纠纷的真相,于是答应前往某酒店协商,协商未果后,张某等四人强行刘某留宿于该酒店,并共同居住于一房间内。2010年7月3日凌晨四时许,张某等四人趁刘某睡觉之机,强行将刘某的大拇指在他们事先准备好的伪造的借款协议书上按捺鲜指印,并向法庭提交了该份证据用于司法鉴定。2010年9月28日,该区法院据此判决刘某偿还张某借款50万元及利息。刘某以借款协议书上的手印系被强迫所按为由,向重庆市某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2012年3月29日,刘某拿到终审判决书后,便向重庆市公安局某区分局报案,同时向重庆市某区人民检察院申诉。后张某、王某、陈某、李某、刘某等五人如实向公安机关交代了上述事实。2013年6月18日,重庆市某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撤销了一审判决和二审判决,并驳回了张某的诉讼请求。
二、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该四人的行为应认定为诈骗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张某的行为应认定为妨害作证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该四人的行为皆不宜认定为犯罪。
三、评析意见
笔者赞同第三种意见。
首先,张某、王某、陈某、李某的行为不宜认定为诈骗罪。2002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中明确指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不宜以诈骗罪论处。”该答复遭到很多学者的质疑,认为其误解了诈骗罪的构造,但笔者却赞同该答复。因为诉讼欺诈行为和诈骗罪中的三角诈骗虽然很相似,但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典型的三角诈骗如:B上班后,保姆C在家,A敲门后欺骗C说:“B让我上门取他的西服去干洗。”C信以为真将西服交给A。B回家后得知C被骗。[1]三角诈骗中行为人之所以能得逞,是因为行为人对财产处分人进行诈骗时利用被害人不知情或者被害人来不及与财产处分人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如果被害人知情或者被害人能够及时与财产处分人进行沟通,那么三角诈骗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了,行为人更不可能骗得财产。诉讼诈骗中行为人(原告)对财产处分人(法官)进行诈骗时,财产处分人(法官)与被害人(被告)同时在法庭上,被害人当然知情,也清楚行为人在对法官进行欺骗,更能及时与法官进行沟通,但被害人是明知有诈却苦于反证,最终导致法官以判决的形式强迫被害人交付财产。因此,诉讼诈骗并不符合三角诈骗中行为人对财产处分人进行诈骗时被害人不知情或者被害人来不及与财产处分人进行沟通的要求。行为人在被害人完全知情且能及时与法官进行沟通的情况下以虚假的证据欺骗了法官,被害人财产的转移更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审判机关的裁判,甚至是强制执行。因此,诉讼诈骗中行为人的行为并不符合诈骗罪的基本构造,从而不能以诈骗罪论处。
更何况诈骗罪的成立,不仅要求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诈骗行为,而且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本案中,四名嫌疑人之所以要伪造借款协议,是因为他们四人参加刘某的传销组织而遭受了经济损失,他们想拿回在刘某领导的传销组织中损失的钱财,尽管传销活动不受法律的保护,但不能就此认定四名嫌疑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刘某钱财的目的。同理,四名嫌疑人在酒店以强迫的方式使刘某按捺借款协议手印的行为,也不能成立其他侵财类犯罪,因为其他侵财类犯罪在主观上也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其次,王某、陈某、李某的行为不宜认定为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是指在诉讼活动中,唆使、协助当事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行为。该罪的成立必须是行为人帮助诉讼活动的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即行为人所毁灭、伪造的必须是他人作为当事人的诉讼案件,刑法条文之所以使用“帮助”一词,主要是为了表明诉讼活动的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不成立该罪,因为毁灭、伪造自己是当事人的案件的证据的,因为缺乏期待可能性,而没有被刑法规定为犯罪,使用“帮助”一词更是为了表明行为人是为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对于本案中的借款协议,从民事诉讼的角度而言,由于民事诉讼采取的是形式真实主义,因此,王某、陈某、李某只能被认定为形式上的证人,张某一人是形式上的诉讼当事人。但从刑法意义的角度来看,该借款协议的当事人还能如此吗?笔者认为该借款协议是张某等四人共谋的结果,选择张某作为出借人(原告),其余三人作为见证人(证人)是四人分工配合的需要,目的是为了更易骗得法官的信任,并且四人还就诉讼费用的分摊以及胜诉后效益的分配另外签订了协议,诉讼的胜败不仅关系到张某的切身利益还关系到其余三人的切身利益。因此,从刑法意义上来看或者说从实质意义上来看,该伪造的借款之诉的当事人应当是他们四人。既然四人都是实质意义上的当事人,那么四人共谋伪造张某一人为形式上的当事人的证据的行为也只能认定为四人皆为自己伪造证据的行为。所以王某、陈某、李某不能以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论处。
最后,张某的行为不宜认定为妨害作证罪。妨害作证罪是指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行为。尽管该借款之诉中王某、陈某、李某与张某共谋后以证人身份作伪证,但这是他们四人为了取得胜诉而精心谋划、分工合作与配合的结果。王某、陈某、李某作伪证是在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奋斗”,既然涉及到自身利益,可以推定他们是自愿的行为,而非是受到张某的指使。因此,张某不能以妨害作证罪论处。
注释:
[1]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94页。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检察院[400060]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40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