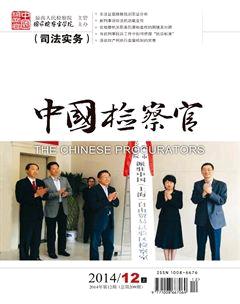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检察工作
金依 张孚雄
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基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对法治建设提出的要求,法治思维强调思想转变,从思想层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法治方式强调行为实践,从执行层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法治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必须树立法治思维、善用法治方式。
一、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案件时,要保持谦抑的心态,要有一种法治的理性
就是我们用法律手段处理老百姓纠纷的时候,要奉行谦抑、平和、宽容的原则。用1991年柏林围墙守卫案主审法官的话来说,“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1厘米的权利,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法官所说的良心义务,类似于王阳明“致良知”所提倡的“良知即是天理”精神。在这个世界上,良知是最高的准则,是不允许用任何借口来无视的。自然法学认为,良知和正义是至高无上的,它是指导社会基本结构设计的根本原则,是衡量社会制度和法律合理与否的根本标准,自然法永远高于社会法。2009年,贫困小伙王某因无钱火化而将母亲沉尸河底“水葬”,福建警方以涉嫌“侮辱尸体罪”将王某刑拘的事件。2012年“温岭虐童案”,温岭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其采取刑拘措施并报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这两起案件都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从刑法谦抑性的角度来看,对这两起事件当事人采取刑事处罚的行为,显得过于刚猛、严厉了。日本学者川端博认为,“刑法的发动不应以所有的违法行为为对象,刑罚限于不得不必要的场合才应适用的原则。”当我们在执法办案或处理社会问题或矛盾时,不能动辄适用刑法,一定要保持谦抑、平和的理念,要有谦卑、宽容之心。当我们有多种方式可以处理违法犯罪的时候,有柔性方式可以解决的,决不采取刚性措施,用平和的方式可以处理的,绝不能选择极端方式,用行政处罚、民事救济等手段可以处理的,绝不能使用刑事手段,要把刑法视为众多处理方式中的一条底线,不能轻易动用。
二、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并且让公平正义以老百姓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法治思维是法治方式的前提和思想基础,法治方式则是法治思维的执行和外在表现方式。在西方法制史上,对法治方式的理解上,曾经有过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争,后渐趋于融合;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曾出现了朱熹的“性理”与叶适的“事功”之争。形式法治强调把法律的规则与程序当成思维根据,法治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这种过于简单化的思维可能导致机械执法,法律与价值之间会产生冲突。“由于规则具有强制性,因而人们在规则已经明确的范围内无需做出价值判断与选择。”更由于“简化的规则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诸如社会趋向于平整化、道德判断能力下降,以及社会生活质量降低等成为了亟待解决的新问题。”由此可见,一方面作为法治方式的重要工具的法律并不是万能钥匙;另一方面法律职业法律思维和公民一般的法律意识不同,公众本身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习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的指示,要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在老百姓眼里,检察机关的执法办案行为具有一定的神秘性和封闭性。现在打官司的老百姓赢了也不认为公平正义,输了更不认为。赢了说这是我找了好多人,输了就说对方找了人。怎么让老百姓感受到公平正义呢?就是要以法治思维更新执法理念,摒弃人治思维,用法治思维观察事物、思考问题、处理案件,尊重司法规律,秉持司法理性,信守司法规则。把纸面上的法律法规投放到司法实践中,把静态的法律以动态的形式展现给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的处理过程当中,而不仅仅在结果当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三、正确处理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关系,要有整体性思维
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是司法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从价值层面来看,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间是灵魂与血肉的关系,实体正义是对“真”与“善”的追求,而程序正义则是对“美”的坚守。运用法治思维就是要求我们在执法办案时要坚守法律规则的意识,坚持宪法、法律至上,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等法治精神和原则,充分认识到程序正义的价值,坚持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重的理念,把程序正义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法治的实现不能仅靠一套完备的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使法治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模式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我们要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深根植于执法办案过程中,使权利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成为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以法治思维作为执法行为内在化的指引,全面提升法律监督能力,更好地履行保障法律实施、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责。影片《深度谜案》通过一系列连环谋杀案的侦破过程告诉我们:因果关系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逻辑原来并不可靠,理性也有失算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说,依据所谓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构建一个足够复杂的情节或证明体系,既可以捉拿到真凶,也可能使无辜的人坐牢。这是因为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办案思维中奉行是一种“拉普拉斯信条”,“拉普拉斯信条”也称为决定论,这是一种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客观规律和因果联系的理论和学说。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以三段论为基础的形式法治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情结,因为现实问题复杂多变,仅仅依靠逻辑与理性是根本无法解决的。“一百多年来法律推理大前提的可靠性受到了批判,自此以后逻辑学的发展走向了多元,面向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并驾齐驱,逻辑思维规则对法治的捍卫也出现了新的形式。”在法治建设向纵深发展的情势下,我们要正确认识作为理性决策模型之法律的局限性以及执法者的能动性问题,重新释读和准确把握“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站在执法办案的角度,当你参与案件时,案件也参与了你,你与案件就一体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心无所住,方可于事实、法律而从容。
四、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强自身建设,以响应司法体制改革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核心在于法治,法治的核心在于以规则和程序来扼制权力的无限扩张。卢曼认为,法治的维持“不是简单地依靠强有力的政治支持而被或多或少地实施。只有能够规范地预测时,法律才是法律。而且,在这方面,法律不是由从上到下的等级决定的,而是不同中心并行地处于相邻的系统中。”可见,提倡法治并非排斥政治,法治从来不是脱离政治之外而单独存在的产物。但是法律不再仅仅是政府做出的命令,而是社会约定的东西,是共同表达的理想、信念、共同规则。孙谦副检察长2013年在第九届高级检察官论坛上指出,“作为一种治国理政的方式,‘法治强调法律作为社会治理工具在社会生活中的至上地位。强调法治,标志着我们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重要转变。”今年8月,《上海检察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由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推进小组原则通过,标志着上海检察改革先行试点。与此同时,上海检察院出台了22项配套制度,以推进检察官专业职务序列、分类管理、司法责任制、健全检察人员职业保障、推动各级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五大试点工作。但对于我们基层检察院来说,目前主要是做好三件事。一是加强与上级、兄弟县区院的协作,推进侦查一体化建设,实现侦查资源统一调配,减少地方干扰。二是探索分类管理,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人员分类改革框架方案(试点试行稿)》的规定探索建立检察官类,书记、技术等事务官类,司法警察、行政等行政人员类。三是加强教育培训力度,防止司法幼稚化。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