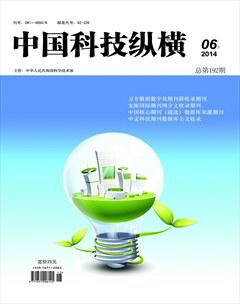拙政园
——东亚农耕生活样态之典型
郭轩佑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北京 100083)
拙政园
——东亚农耕生活样态之典型
郭轩佑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北京 100083)
借江南名园“拙政园”的细化分析,试图体现汉文明典型农耕文化的样态,及扼要梳理代表此一生活样态的族群之精神视域。
拙政园 文明 农耕 生活样态
中国江南,自古迄今,文人喜称:自然形胜之地域,人文荟萃之渊薮。其地偏于欧亚大陆最东南一隅,自南宋以后千余年来,此一地域所形成诸多文化样态,始终是东亚文化最典型的代表。此地域远离欧亚大陆的文明发源中心——两河流域、西亚文明,以自身地域的独特造就了东亚自成一格的生活样态,其形成之江南私家园林,正是这一生活样态具体而微的体现。
早期东亚文明中心基本在黄河流域的中游地区,其向北向西,形成至今我们所知的夏文明及商文明,夏商文明余绪沿至秦汉隋唐,无论生产方式还是生活状态,都带有颇多源于欧亚大陆东西交融的痕迹:从人种的羌戎狄等混合,到青铜冶炼业之发达,再到农业以小麦燕麦种植为主……这一切都说明,上至夏商、下至秦汉隋唐,东亚文明还未最后步入圆熟期。最能说明彼时东亚文明情态的,莫过于汉武帝时张骞凿空西域之举及盛唐时丝绸之路空前之盛况。简言之,直到南宋偏安江左之前,东亚地域文明——我们今日习称之汉文明,还处于其上升时期,族群生活样态,属于吸收交融状态,诸多方面都表现出族群的勃勃生机,文化形制未臻圆熟当在所难免。通过考察中国古典园林历史,从商周园林置囿、台以期旷远,到明清江南私家园林小桥流水自足于尺境之乐,我们看到了一种文明从上升的勃勃生机到圆熟的自盛而衰,这一过程是否预示着一个族群的毁亡之路。当然,物极必反,势盛必衰。此世界任一文明都有其圆熟极美之境,亦有其衰亡自毁之途。在此,笔者借江南名园“拙政园”的细化分析,试图对汉文明典型农耕文化的样态体现,及代表此一生活样态的族群之精神视域做一扼要梳理。
人类自上古,最重要的发明就是农业和畜牧业,它们一直是人类生活最基本的经济基础,由农业和畜牧业依存的自然环境及生产生活状态,衍生出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框架。
自宋以后至元明清初,江南私家园林的成熟兴盛,从自然环境及生产方式关照,应与农耕稻米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指出:“水稻最初在印度种植,后来,约在公元前二千至二千一百五十年间,经海路和陆路被介绍到中国南部。它以我们熟悉的传统形式慢慢在那里普及。随着水稻的推广,中国生活的重点完全颠倒了过来:新兴的南方代替了历史悠久的北方……”。这里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到的“慢慢在那里普及”和“推广”在时限上正符合宋以后汉文明进入精致的圆熟时段。而也正是在南宋偏安江左,以至元明清初,江南成为了代表东亚圆熟文明样态的场域。隔海东洋亦步亦趋的学习吴地文化的精致,亦是指称这一时期的中国江南。在这样的文化场域中,兴盛而圆熟的江南私家园林,与由农耕稻米文化所形成的生活样态必然有千丝万缕的牵连。
位于苏州城内东北方的“拙政园”,初建于明代中期,原是明朝御史王献臣的私园,王曾受东厂宦官之害,感叹拙于从政,营建此园以自况明志,后数度易主,清代曾作为太平天国忠王府,再后改为八旗会馆,历经四百余年变迁,基本仍保存初建时之山水布局。全园占地4.1公顷,分西部“补园”、中部“拙政园”、东部“归田园居”三部分。为现存江南私家园林之代表。
江南水道交织,湖泊众多,稻田密布,江南私家园林以小居多,拙政园虽占地仅4.1公顷,已算江南私家园林中之大园,陈从周有言:“以有限面积,造无限空间”。而此种造园法则也可以从另一角度理解。耶稣会神父杜哈德于一七三五年写道:“所有的平地都被耕种,见不到任何沟渠和篱笆,几乎没有一棵树,他们十分珍惜每一寸土地。”另一位杰出的耶稣会神父拉斯戈台斯在一个世纪前曾说过同样的话:“没有一寸土地……没有一个角落不被耕种”。在江南水乡,自然环境的局限,衍生出私家园林的样态,在小的空间中悠游、堆砌:园之主门设于宅邸之曲巷,自腰门以入,黄石假山列于目前,有挡景之功用,运用藏露技巧,绕过山后水池,景始有所开阔,迎面见到的是“松风亭”,透过亭上开窗,可看到局部水面。出松风亭,经过一座跨于水面的廊屋“小沧浪”,远处可看到一座廊桥,名为“小飞虹”,这些围出一个更小的水院。绕过小飞虹廊桥,就到了园中部核心建筑“远香堂”。远香堂为一座四面厅建筑,在廊桥另一端,还有旱舟“香洲”。远香堂之北为水域,水域中有两座凸起的岛山,将水域分隔成南北两部分,岛上分别建有“香雪云蔚亭”及“待霜亭”。东边岛有小桥通向水池东面的“梧竹幽居亭”。水池中央还有“荷风四面亭”,水池西北亦有“见山楼”。这里简要的述说了拙政园中部的主要建筑。正如知者所言:往往于无可奈何处,而以无可奈何之笔化险为夷……当然亦有无可奈何之美:庭院深深深几许。以曲折得之。如若真能“三五步行遍天下”,也是盆栽中的天下,小飞虹,小沧浪,在尽情把玩小之趣味中,汉文明达于圆熟。但最终失去了秦时明月汉时关的力量。
江南私家园林其文化样态的圆熟,还表现在宋元以来,文人文学情思的圆融通透,它的展开表达了一种文明发展到圆熟状态时的必备之纤巧精致。它也将一种文明的遥远过去带到了当下的情境中,使得生活在局促水乡的人们,在此一文化样态中体认到时间的进程,自足于某种当下存在的满足感,其深层族群心理机制,源于人们世代被固化于稻田的辛劳耕作,此一种耕作的特性潜在地决定了这一种精神视域:“种植水稻意味着人和劳力的大量集中,意味着专心致志地适应环境……”。制作于十三世纪的《耕织图》即展现出这一农耕景象。
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去细心的品味——一种虽已逝去,但依然魅力无穷的精巧的文字游戏。其实质也是此一种圆熟的农耕文明的时空游戏,它支持着对历史的想象。拙政园“卅六鸳鸯馆”以西,步过一小巧曲桥,有“留听阁”一景,在汉文明浸润过的任一文士,当行次处,必会想到在历史悠远的往昔曾有一诗人,哀婉低吟于秋日荷塘前“:竹坞无尘水懢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晚唐诗人李商隐的《宿骆氏亭寄崔雍崔衮》诗句,表达了思念,孤寂之情。而在时光的进程中,在未来,在拙政园“留听馆“,另一个人,又一次,在他的诗句中找到了同样的思念和孤寂,当然还有依托文学之魂,在时空中实现的又一次回望的志得和意满。在园林中达成了又一次当下者和往昔诗人的精神契合,由此,江南私家园林使得孤独和寂寞,物化为一种文化样式的美感体验。
拙政园的其他几处景致亦有这样的范例。“远香堂”,取宋理学家周敦颐咏莲句:“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另一处“得真亭”取左思《招隐》诗句:“竹柏得其真”。而西部补园有一处临水扇面形小亭,凭栏可环眺三面景色,题名:“与谁同坐轩”,是宋代诗人苏东坡名句:“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当人们流连于这带有文字暗示的景色中,过往逝去的名士风流萦绕于江南文士局促的精神视域中。
从原始的农耕历千数年,形成圆熟的东亚农耕文明,通过最直观的天象、气象、物象诸方面观测判断时令节气是农耕生产的基本环节,不能准确把握时节,就意味着不能保障生存所需的基本食物,一年两至三次种植收获的稻米,更是如此。所以,汉文化中关于天文的诸多意向,同时也存在于文学艺术以致园林中,它们交融影响,深入到东亚生活的方方面面。顾炎武《日知录》即言“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我们亦可说,在园林中遍植各色植物花草,寄情草木四季之荣枯,亦是文人雅士于园林中的天象节令之谣。拙政园于园中山上植落叶树间以常绿树木,岸边散植灌木藤蔓,垂柳,亭馆间并种植柑橘、梅花、山茶花等各色花木,山茶花又名曼陀罗花,拙政园亦以花名命一馆为“十八曼陀罗厅”。另一名为“香雪海”的景致更是冬末春初踏雪寻梅之佳境。而“待霜亭”却让雅士们体认到生命苦短的悲情。使四季纷呈各色,荣枯变迁,岁月流逝,以园林花木为依托,展于目前,正是东亚江南私家园林的诗情体现。
园林艺术代表了一种文化的综合样态,当它达于成熟期时,它所蕴含的远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形态,更深层地昭示出此一文化样态创造族群的生命消息。从古波斯的水法绿洲,疏朗庭院;到欧陆对称布局之嵯峨城堡。其旷远雄健,蓬勃生机,展现出此世界的另一美境界,其中的华丽,超凡,严谨,哲思,标明出一类上升的生命样态,是外展的。以此反观江南私家园林,于局促之水乡,产生自足之稻米文化,文人雅士,流连于逼仄之四壁六合,臻于极度精巧纤细后,必将堕入颓败一途,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自然法则的必然。江南水乡,私家园林,只能是一个如风逝去的魅影,连同东亚农耕文化,留存于回望的哀婉低吟中。
[1]陈从周.《书带集》.
[2]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3]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