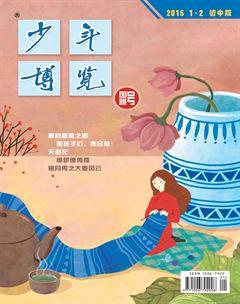姹紫嫣红的花之国
莫幼群+潘小娴
中国式的精雅生活,与草木联系得十分密切。人们从花儿草儿当中,提炼出了一种君子人格,营造出了一种天人合一的氛围,真是:树影花径,直指仙境;与草木共舞,胜似闲庭信步。
四季皆有花神来
春:解语之棠
许多人到了海棠面前,开始怀疑人生,突然觉得:缺憾,是人生最大的主题。
大诗人杜甫见着海棠,满腹诗才无处施展,苏东坡叹道:“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无他,皆因杜甫母亲小名海棠,为避讳计,诗人只好对这花儿说声抱歉了。
大名士李渔见着海棠,激赏之下,是深深的遗憾,无他,“杨梅无香,与海棠齐恨”也。后来,张爱玲在《红楼梦魇》中又进一步“饮恨”道:“一恨海棠无香,二恨鲥鱼多刺,三恨红楼未完!”可见,世上完美的花儿是不存在的,正如从来没有完美的人一样。
林黛玉大约是不喜欢老杜风格的,喜欢的恐怕是李白、李商隐一路,所以她张罗着弄了个诗社,偏叫做“海棠诗社”。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正经的活动还没办过几回,大观园连带林妹妹,便频遭劫难了。或许,海棠之名,本身就是一个不吉利的征兆?
鲁迅以他前无古人的犀利,为这种缺憾定格了一幅最经典的画面:孱弱的才子像林黛玉那样害着肺病,怏怏地由丫环扶到阶前去看海棠,吐半口血,看半天花——多美啊,能否为我停留一下?
但海棠实在是美,引得无数人都痴了,连旷达如东坡居士,也未能幸免。想起苏轼的那首《海棠》:“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此诗一出,海棠也就有了“解语花”的雅号。
海棠,蔷薇科落叶小乔木或灌木,花姿潇洒,花开似锦,自古以来就是雅俗共赏的名花,素有“国艳”之誉。据明代《群芳谱》记载:海棠有四品,皆木本。这里所说的四品指的是:西府海棠、垂丝海棠、木瓜海棠和贴梗海棠。其中后三种海棠花无香味,只有西府海棠既香且艳,是海棠中的上品。北京故宫御花园、颐和园和天坛等皇家园林中就种有西府海棠,每到暮春季节,朵朵海棠迎风俏立,花姿明媚动人,楚楚有致。
夏:水墨之荷
数年前看《辛德勒的名单》,很佩服导演斯皮尔伯格在色彩上的创意。前面所有的镜头都是黑白的,只有最后一个场景——当劫后余生的人们相拥着走向新生活的时候——才是彩色的。整个电影也就这一点五彩缤纷,但却完美地留出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完美地诠释了历史的厚重和人性的斑斓。
在我的想象中,荷花也应该是这样,它周遭的一切都是暗色调的,下面的淤泥是墨黑,身边的潭水是近乎透明的淡黑,身上的叶子是墨绿,而只有顶上的花朵,是唯一的彩色——所谓的彩色,也只是从白底之中沁出一丝粉红,但就是这一点粉红,把所有的一切都点亮了,于是荷就成了一盏明灯,成为某一种珍贵的人格的象征。
在我的编排中,“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这群在初秋季节采莲的小姑娘穿着白衣就好,否则色彩就有些多了,纤手也是近乎透明的鲜白,只有粉面与花朵相呼应,构成一幅和谐的画面。
从莲蓬里剥出莲子,再从莲子里剥出莲肉,是色彩递减的过程:深绿到黄绿再到粉白,但别忘了粉白中还藏着一针深绿——莲心。白融化在纤纤玉手的掌心,最终又跳进一碗银耳羹里;而深绿宛如一枚茶叶,最终又融在一盅八宝茶里。
从墨泥里起出莲藕,是色彩突变的过程,就像那部经典电影。初看污浊不堪,洗净,又是一番色彩,这种色彩不可复制——藕色,是如许的淡雅,又是如许的清凉。
荷花,从头到脚的每一个部件,都合力营造出一种氛围。就像茶壶上的“可以清心也”,从任何一个字开始读,都是一句妙语。叶、花、蓬、籽、藕,每一个字,都从你的眼眶流进去,洗过你的五脏六腑——可以清心也。
秋:工笔之菊
如果花神是一位国画家,那么他画起兰花来最潇洒,寥寥两笔就行了,画菊花时最耐心,因为那一瓣一蕊,都像是用极精细极精细的工笔画出来的。
严格地说,这画家是那些古往今来的花卉巧匠们。牡丹是古代花匠们面对的最重要攻关对象,接下来大约就是兰花、菊花了。
菊花在我国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菊花传入欧洲,约在明末清初。国人极爱菊花,从宋朝起民间就有一年一度的菊花盛会。
菊花最早是单一的“黄花”品种,经过历代许多人对菊花的培育,使菊花的品种不断增加。宋朝刘蒙泉《菊谱》记载有35种,到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已有900多种。千百年过去了,菊花在我国已有3000多个品种。光开封就有1200多个品种。
如今的菊花色彩极为丰富,有红、黄、白、墨、紫、绿、橙、粉、棕、雪青、淡绿等。又有复色、间色等不同色系。花序大小和形状各有不同,一般以花的大小可分成大菊系和小菊系;依花瓣形态分类,可分为单瓣、桂瓣、管瓣几大类;依花型分又可分为宽瓣型、荷花型、莲座型、球型、松针型、垂丝形等;依栽培形式和整枝方法的不同,则可分为一株一花的“独本菊”、一株多花的“多头菊”、一株有数百朵甚至一千朵花的“大立菊”、小菊整枝悬垂状的“悬崖菊”,还有将各式品种嫁接在青蒿上的“高接菊”等等。
“春日见山”“墨荷”“绿牡丹”“绿云”“凤凰振翅”“帅旗”“西湖柳月”“国花金大壮”……单看这些名贵品种的名字,就可以想象花匠们酿出了怎样的创意,付出了怎样的匠心,搭下了怎样的工夫,进而可以想象他们怎样前赴后继,进行着一场至今尚未结束的接力赛。
冬:凌波之仙
一棵大蒜不开花,它还是大蒜,一棵大蒜开了花,它就是水仙。
水仙既是中国老百姓喜闻乐养的冬季花卉,也是中国文人案头上的清供。虽小,却能让你在整个春节期间都沉浸在它的香氛之中。
它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显出了中国人对于花卉的创造性改造之功。
先是技巧之功。水仙球茎的切割大有讲究,花开得怎样全靠“刀工”,历代花匠反复琢磨,终于研究出了最鬼斧神工的“刀法”,也使得水仙和大蒜的区别越来越大了。
再是文化之功。经由文人们的想象,水仙被赋予了仙气。其中宋人黄庭坚“功勋卓著”。宋元以来千百年间歌咏水仙的诗词歌赋甚多,而写得最早、最多的首推他,写得最精彩、最耐人寻味的也非他莫属。“借水开花自一奇,水沉为骨玉为肌。暗香已压酥糜倒,只比寒梅无好枝。”这首诗便是黄庭坚咏水仙诗中的代表。
另一位不太出名的宋代诗人刘邦直也写有一首好《水仙》:
得水能仙天与奇,寒香寂寞动冰肌。
仙风道骨今谁有?淡扫蛾眉篸一枝。
水仙最重要的便是借了水的灵气,正是暗合了“女儿都是水做的”。在青花瓷的矮盆里,洁白的鹅卵石隐住了不算好看的根,下面是浅浅的清水,几株绿茎亭亭玉立,顶上是白玉般的花瓣,围着中央金黄色的花蕊,仿佛灿烂的笑脸。没有一种色彩不是美的,组合在一起,更是美上加美。
既是凌波仙子、绝世美女,身形必须适中,最好是“九头身”之类的美女,即头(花冠)和身(茎)必须有一个黄金般的比例,太矮了成了武大郎,太长了成了姚明,都不够好看。
但谁也没有养过完美的水仙,只能是接近完美。球王贝利说:我的下一个球最精彩;花匠们得说:我的下一株水仙最美丽。
满城多少插花人
花在中国民间,最早是代表一种男女互赠花束以表达思念的风尚。《诗经》中有记载:“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而插花的最早出现,则始于南北朝时期,最初用于佛教的供花。《南史》中就记载了最早的佛前供花情景:“有献莲花供佛者,众僧以罄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六朝时的北周诗人庾信在《杏花诗》亦有对插花的两段描写:在花开满园的春天,“依稀映村坞,烂漫开山城。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小船行钓鲤,新盘待摘荷,兰泉绕悦架,何处有凌波”。金盘即是铜盘,诗中的“金盘衬红琼”和“新盘待摘荷”都是盘花。可见此时插花已不仅仅用于佛前供侍,民间已有采折花枝涪花与荷花入盘待客会友的习俗。
插花初始仅是将花“放”或“养”在花瓶或花盘中,还谈不上“插”的艺术匠意。到了唐代,君王把二月十五定为花朝,视作百花诞。君王提倡,文士尚雅,仕女爱花,处处呈现一派争奇斗艳的盛况。插花开始讲究花要插得好、配得妙,插花形式不仅有瓶插、盘插,还有吊挂插花以及专门供插花朵硕大的牡丹、芍药等花卉的缸插。而且还讲究花器,并对花木赋予个性与格调。比如讲究将花器置于精美台座或几架,并在背后挂名人字画,形成或清新高雅或富丽华贵的“书画插花”风格。此时的插花,已从早时的寺庙供养,延伸为宫闱或诗人雅客书房内的装饰品。
到了晚唐,插花风气更盛,从诗人杜牧在《杏园》诗中所说的“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可见当时社会插花之盛景。五代十国时南唐国君李后主于每年的“花朝日”2月15日定时举办盛大的插花展览会,在梁栋、窗户、墙壁、柱子上等能利用的场地都插上花,有悬吊的、摆放的、挂置的,琳琅满目,锦绣灿烂,还题名曰“锦洞天”以吸引观众。
宋元时期,插花之风盛极一时。除宫廷、寺院、民间盛行插花用以陈设外,甚至连茶馆、酒楼、商店、游船等,为了招徕顾客,还按四时更新插花。一般的民众往往出外郊游时也还“中置桌凳、列笔床、香鼎、盆玩、酒具、花樽之属”,可谓是一尊插花不离身了。而且,插花艺术在当时还上升为专门学问,与“烧香、点茶、挂画”并列为宋代的“四艺”,被视为宋代人自小就应具备的修养,纵使仆役也不例外。至此,插花已发展成为普罗大众生活的必需品。
至于讲究情趣的文人雅仕,更是常以插花影射内心世界,比如,喜用高雅韵致的“梅、兰、竹、菊、杉、柏、水仙”等花材插花,以表达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愿望和抱负,同时还将插花艺术分成不同欣赏层次,比如,有酒赏、香赏、曲赏、茗赏、琴赏等,其中以唐代之酒赏、五代之香赏、明代之茗赏最具特色。
酒赏,即边饮酒边赏插花。插花酒赏源自唐代,流行到宋代,被列为文人生活的情趣美谈,并留下了大量赏花醉歌之作。例如,“曾插花百瓶,醉饮其间”的欧阳修有诗《谢判官幽谷种花》云:“深红浅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我欲四时携酒赏,莫教一日不开花。”
香赏,即把对插花作品的欣赏与焚香结合在一起。插花燃香源自五代时期的文人韩熙载,他在《五宜说》写道:“对花焚香,有风味相和,其妙不可言者:木犀宜龙脑,酚糜(蔷薇的一种)宜沉水,兰宜四绝,含笑宜庸,桐葡宜檀。”韩熙载依照不同的花材配制不同香料的焚香,形成花香相和的“香花”风格。这种赏插花方式,追求花朵天然香味与燃香的巧配,将插花发展为诉诸嗅觉之美的“香赏”,更见趣致的境界,在宋元两代文人中十分盛行。到明朝时,文人们还将插花与品茗相结合,开创了“茗赏”的新方式。赏花品茶兼得花与茶的清香幽美之情韵,成为文人雅士间赏插花之最高雅境界,正如明代被誉为花道专家的袁宏道在《瓶史》中所言:“茗赏者上也,香赏者次也,酒赏者下也。”
袁宏道还曾将花比作“天地间一种慧黠之气”所凝成的东西,认为它们具有与生俱来的天生丽质,人见人爱。而大凡阅读过清代文学家沈复的《浮生六记》,一定会为沈复文中所描绘的妻子芸娘所倾倒。芸娘聪慧洒脱,与沈复默契温存过日子,无论案头雅供、静室焚香、赏菊东篱、设计花园等,她和沈复一样都是行家里手,让每天的日常生活都在艺术化的人生里悠游。尤其书中对芸娘关于插花的一段描写,其所显示出的“慧黠之气”,更让人望尘莫及:“余闲居,案头瓶花不绝。芸曰:‘子之插花能备风晴雨露,可谓精妙入神。而画中有草虫一法,盍仿而效之。余曰;‘虫踯躅不受制,焉能仿效?芸曰:‘有一法,恐作俑罪过耳。”余曰:“试言之。曰:‘虫死色不变,觅螳螂蝉蝶之属,以针刺死,用细丝扣虫项系花草间,整其足,或抱梗,或踏叶,宛然如生,不亦善乎?余喜,如其法行之,见者无不称绝。
爱花成癖的沈复,喜欢摘花插瓶,所以总是不断地更换新鲜桌上的瓶花。芸娘说沈复的插花十分精妙传神地体现了风晴雨露,但她觉得还可以仿效画画中画草虫的方法:“虫子死后颜色不变,你可以捉来螳螂和知了、蝴蝶之类的昆虫,用针把它们刺死,用细丝系住虫的颈部绑在花草当中,整理它们腿的姿态,或者抱梗,或者站在叶上,就像活的一样,不也很好吗?”沈复采纳芸娘的办法,结果看到插花的人无不称口叫绝。虽然把虫子刺死有些不地道,但芸娘的聪慧可见一斑,也足见中国古已有之的插花,在清代已经发展成社会上一种普及性的技艺,并成为了诸如芸娘等聪慧女子的必学之道。爱花,爱美,爱人,都同是日常生活中缺一不可的美好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