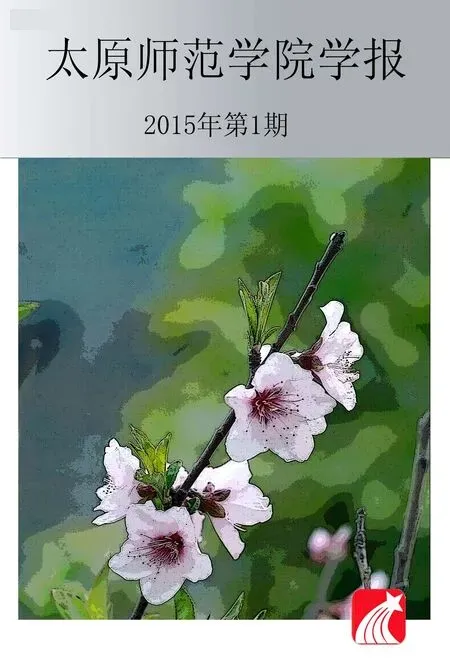论隋文帝、隋炀帝与天台宗
段知壮
(1.南开大学 法学院, 天津 300071; 2.日本爱知大学 中国研究科, 日本 名古屋 4618641)
【文化学】
论隋文帝、隋炀帝与天台宗
段知壮1,2
(1.南开大学 法学院, 天津 300071; 2.日本爱知大学 中国研究科, 日本 名古屋 4618641)
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隋唐佛学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隋唐佛学兴盛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佛教八宗在此时期的陆续出现。虽然佛教宗派的兴衰受制于诸多因素,但在君权至上的中央集权封建社会当中,最高统治者——皇帝个人的喜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天台宗为例,其创始人智顗与陈、隋两代王朝的皇室都保持着密切的来往,并且天台宗的思想也基本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与当时的政治理念也有着某种潜在的暗合。
隋文帝;隋炀帝;天台宗;智顗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自两汉传入中国,经过了漫长的融合与发展,时至隋唐已经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隋唐佛学更是继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之后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一巅峰,并对之后的宋明理学、清代朴学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是君权至上的中央集权封建社会,所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组织都必须完全地处于国家权力的严密统摄之下。但是作为一种宗教存在,尤其是一种相对而言比较系统性的、经过长时间与本土社会融会贯通的佛教,民众的心理向心力是巨大的。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同样是人而不是神明,其个人对于佛教的态度关系到整个佛教的发展与兴亡。就隋唐时期的帝王而言,大多数的皇帝对佛教都是持大力弘扬的态度的,这也就直接导致了隋唐时期佛教八大宗派陆续出现的鼎盛局面。
关于佛教的主要宗派,古往今来有着许多不同的说法,但现如今关于佛教八宗的通说主要是指律宗、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密宗八个宗派。虽然各个宗派从宏观上讲都是佛教的支流,但其相互之间,尤其是在佛教义理思想上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与对抗。各个宗派的出现与兴盛虽然有着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是国家权力,也就是封建王权对其的影响则极为关键。在本文中,笔者选取了隋文帝、隋炀帝与天台宗的智顗之间的人物关系进行分析研究。
一、天台宗的基本思想
在隋统一全国之前,佛教也同国家的分裂一样,在南北地区有着“南义”、“北禅”的差异。南方佛教偏重于义理,强调讲解;而北方佛教偏重于修禅,强调禅定。之所以形成这种差异与当时南北方的社会状况是分不开的。南方玄学盛行,随着晋室的南迁,在士大夫心中南方就成了“正朔”的所在地。与士大夫一同南迁的还有大量的“义学沙门”,如东晋名僧道安就“与弟子慧远等四百余人渡河”南迁。[1]178而北方由于战事连连,人们生活在兵荒马乱之中,“申述经诰、畅说义理”的环境自然也就要差得多。再加上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国传统文化氛围并没有太多的融会,相比之下他们更关注实际,在佛教方面也就更重视“坐禅”、“修行”等“修福行善”的活动。天台宗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产生的,与这种背景相应,“统一”的理念自然就成了天台宗隐性的思想基调。
天台宗的师承谱系为龙树—慧文—慧思—智顗—灌顶—智威—慧威—玄朗—湛然。之所以将龙树推为天台宗的“初宗”,原因主要是天台宗大量引用和阐发了龙树“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的偈语。实际上龙树与天台宗的关系并不是很大,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应当是智顗。
不过这里要特别提及一下智顗之前的慧思,虽然不能说慧思是天台宗的创始人,但是慧思是南北佛教统一进程中非常重要的过渡性人物,其为天台宗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一段言论非常能体现慧思的思想,“沙门(慧思)问曰:‘汝当闭目忆想身上一小毛孔,即能见否?’外人忆想一小毛孔已,报曰:‘我已见了也。’沙门曰:‘汝当闭眼想作一大城,广数十里,即能见否?’外人想作城已,报曰:‘我于心中了了见也。’沙门曰:‘毛孔与城,大小异否?’外人曰:‘异。’沙门曰:‘向者毛孔与城,但是心作否?’外人曰:‘是心作。’沙门曰:‘汝心有大小耶?’外人曰:‘心无形相,焉可见有大小?’沙门曰:‘汝想作毛孔时,为减小许心作、为全用一心作耶?’外人曰:‘心无形段,焉可减小许用之,是故我全用一念想作毛孔也。’”[2]这便是天台宗“一心三观”、“一念三千”的雏形。
(一)天台宗的认识论——“一心三观”、“一念三千”
天台宗创宗的经典为《法华经》,所以天台宗也称为法华宗。天台宗最主要的理论便是来自《法华经》中的“会三归一”,《法华经·方便品》:“舍利弗!如来但以一佛乘故为众生说法,无有余乘,若二,若三……舍利弗!十方世界中,尚无二乘,何况有三……诸佛以方便力,于一佛乘分别说三……无有余乘,唯一佛乘。”“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佛乘,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3]这里明确指出,世间只有“一佛乘”,其他的只是为了适应不同情形而出现的权变而已。那么这个“一佛乘”在哪里呢?《法华玄义》:“世界无别法,唯是一心作。”[4]这便是智顗提出的天台宗的基本认识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天台宗所说的“心”,并不是每个人的“凡心”,而是一种独立存在的精神体,即“佛性”。如前文所述,天台宗非常重视龙树的一句偈语:“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名中道义。”意思是因缘际会所产生的一切,归根结底都是“空”的,也就是“假”的,但是其所现实出来的“相”却是非空非有的,也就是“中道义”。天台宗认为,“空”、“假”、“中”“三谛具足,秖在一心……若论道理,秖在一心,即空,即假,即中……三谛不同,而只一念。”“虽三而一,虽一而三,不相妨碍。三种皆空者,言思道断故。三者皆假者,但有名字故。三种皆中者,即是实相故……一念心起,即空,即假,即中。”[5]也就是说,三谛是相互通融的,因为它们都“秖在一心”。这便是天台宗的“一心三观”、“一念三千”。
(二)天台宗的方法论——“止观”
之所以说天台宗在统一佛教南“义”、北“禅”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标志就在于天台宗“止观”学说的提出。简单来说,“止”与“观”就是“戒定慧”三学中的“定”和“慧”。智顗说道:“泥洹之法,入乃多途,论其急要,不出止观二法。所以然者,止乃伏结之初门,观是断惑之正要;止则爱养心识之善资,观则策发神解之妙术;止是禅定之胜因,观是智慧之由籍。若人成就定慧二法,斯乃自利利人,法皆具足。”[6]本来,“止观”只是一种修持方法,主要是“修”,而不是“说”。现在智顗把它们改造成了“说”的东西,就是说,他把“止观”也“义理”化了;止观“学”,变成了止观“学说”。[7]156智顗正是通过这种“止观”学说将南北佛教的“义”和“禅”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
二、隋文帝、隋炀帝与佛教的渊源
隋文帝杨坚与佛教的渊源极深,根据记载,杨坚是在寺庙里出生的,并且他十三岁前的整个童年时期也都是在寺庙中长大的。《隋书·高祖上》:“皇妣吕氏,以大统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于冯翊般若寺。有尼来自河东,谓皇妣曰:‘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尼将高祖舍于别馆,躬自抚养。”[8]1《续高僧传·道密传》:“太祖乃割庄为寺,内通小门,以儿委尼,不敢名问。后皇妣来抱,忽……惊遑堕地。尼曰:‘何因妄触我儿!遂令晚得天下’。及七岁,告帝曰:‘儿大当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而尼沉静寡言,时道成败,吉凶,莫不符验。初在寺养帝,年十三始还家……及周灭二教,尼隐皇家,内着法衣……帝登祚后,每顾群臣,追念阿闍黎……乃命史官王邵为尼作传。”[9]从对太祖和皇妣的描述中可以看到,杨坚生于一个笃信佛教的家族,杨氏家族与佛教之间的关系由来已久,这与当时北方世家大族中佛教盛行的史实也基本相符。与此同时,隋文帝杨坚的皇后,隋炀帝杨广的母亲独孤伽罗也是虔诚的佛教徒,独孤氏是魏时期名将独孤信的第七女,独孤家族历来有信佛的传统,独孤氏去世时,史官王邵上书云:“伏惟大行皇后圣德仁慈,福善祯符,备诸秘记,皆云是妙善菩萨。”[8]1608在这样一个父母皆与佛教有如此渊源的家庭中长大,隋炀帝杨广自然也与佛教有着特殊的情感。在其师从智顗受菩萨戒时,他就在《受菩萨戒疏》中说道:“以此胜福,奉资至尊、皇后,作大庄严,同如来慈。”“弟子即日种罗睺业,生生世世还生佛家。”[10]
三、隋文帝、隋炀帝与智顗
智顗(538—597),俗姓陈,祖籍颍川(今河南许昌),后迁往荆州华容(今湖北监利县西北)落户。他的父亲陈起祖,梁元帝时为散骑常侍,封爵益阳侯(亦说封孟阳公)。[7]106可见智顗出身官宦门第,十八岁出家之后,智顗前往金陵,从那时起其与陈王朝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不过关于智顗于陈、隋两朝的关系远近,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如潘桂明教授等认为智顗“对于陈朝,他是积极支持、主动拥护;对于隋朝,则阳奉阴违、消极回避。”[11]94董平教授对此也持类似观点,“智顗与陈国君臣的深相结纳也出乎其主观上的自愿,但他对隋王朝的态度实际上却若即若离,始终未有一种主观上的亲和感。”“智顗虽周旋于陈、隋帝王之间,却总在为佛法之真理,为众生之救度,其间略无一毫私意之掺杂;故终不失其一代高僧之人格风范。”[12]23-25再如包兆昌先生提出的:“陈、隋王朝与智顗的关系是相似的。无论陈朝宣帝、后主还是隋朝文帝、炀帝,对待智顗的态度都没有超出东晋以来形成的帝王与名僧之间互相尊重、互相支持的关系模式。而智顗对于两朝君臣的态度也大体相同,在遵守沙门律仪的前提下,出于弘法化众目的与世俗王权相周旋。”[13]相比之下,笔者更倾向于包兆昌先生的观点,虽然智顗对两朝君主的态度不能说是极尽谄媚,但是其努力与皇室搭建良好的关系网络,并在特定事件上利用这样一种优势发展佛教,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
《国清百录》里收录了大量陈朝君臣给智顗的敕、书等,如《太建十年宣帝敕施物》:“智顗禅师,佛法雄杰,时匠所宗,训兼道俗,国之望也。宜割始丰县调,以充众费,蠲两户民,用供薪水。”[10]再如后主陈叔宝也曾经向智顗下发过大量的敕文,除了表示问候,还赐赠了大量的钱粮等物。由此可见,陈王朝时智顗已经具有了相当大的声望,并且当时的统治者对他也是非常礼遇的。
隋文帝杨坚与智顗之间的第一次联结是在平陈之后的开皇十年,隋文帝向当时已经颇具影响力的智顗下发了一道敕文:“皇帝敬问光宅寺智顗禅师:朕于佛教,敬信情重。往者周武之时,毁坏佛法,发心立愿,必许护持,及受命于天,仍即兴复,仰凭神力,法轮常转;十方众生,俱获利益。比以有陈虐乱,残暴东南,百姓劳役,不胜其苦。故命将出师,为民除害。吴越之地,今得廓清,道俗人安,深称朕意。朕为崇正法,救济苍生,欲令福田永存,津梁无极。”杨坚首先表明了自身坚定的立场,其对于佛教是“敬信情重”的,绝不会出现周武灭法那样的事件,并且他也知晓智顗与陈王朝之间的关系,所以特别提出出师平陈,统一全国是“为民除害”,自己登基为帝也是“受命于天”。但在向智顗投出橄榄枝的同时,敕文还说道:“师既几离世网,修己化人,必希奖进僧伍,固守禁戒,使见者钦服,闻即生善。方副大道之心,是为出家之业。若身从道服,心染俗尘,非直含生之类无所归依,仰恐妙法之门更来谤读。宜相劝励,以同朕心。”[10]如果说前半部分的敕文还算是比较亲密的话,后半部分多少带点“恐吓”的味道。
不过总体来说智顗的表现并没有让杨坚失望。当时身为晋王,总管原陈国属地的杨广到扬州不久,曾遣使修书与智顗,希望智顗接受其供养并作他的菩萨戒师。“法师抗志名山,栖心慧定,法门静悦,戒行熏修,籍甚微猷,久承音德,钦风已积,味道为劳。”[10]智顗没有立刻应允,《天台国清寺智者禅师碑文》中记载他回信说:“虽欲相见,终恐缘差。”[10]此后还进行了一年的观望,但最终于开皇十一年十一月,欣然出山为杨广受“菩萨戒”,并一反之前态度,表示“我与晋王,深有缘契”,杨广在《受菩萨戒疏》中也说:“弟子基承积善,生在皇家,庭训早趋,胎教夙渐”[10],再一次强调了其整个家庭对佛教的亲近之情。那么为什么智顗没有立刻答应而是等待了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呢?王光照先生的一段论述可以说一语中的:“智顗自金陵城破之后即避居匡庐,借隐学之名,实则坐山以观形势之变化:一看新政权能否巩固;二看新政权对佛教的态度;开皇十年,接文帝一书,知新朝对佛教有控制但又想利用之政策,迟疑观望之间,南方豪族大规模反隋之事已起,因即顺势‘安坐匡岫’;杨广至镇之后,频频致书智顗,至此,智顗对南北统一,新朝政治强大之势亦已了然”[14]。而智顗也精准地把握住了杨广虔诚地请求这一机遇,成为杨广的受戒师父,这极大地拉近了其与隋皇室的距离,在之后的时间里,智顗每遇难事,多告请杨广出面帮助解决,甚至有些寺院的维持,也经他请杨广帮忙。杨广的妃子(萧妃)患重疾,智顗急赴扬州亲自主持“金光明忏”,为其治病祈福。智顗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一再表明对隋王朝的效忠与维护,《发愿疏文》:“幸值明时,栋梁佛日,愿赖皇风,又承众力,将劝有缘,修治三处:先为兴显三世佛法;次为拥护大隋国土;下为法界一切众生。”虽然这里的用词不免显得有些谄媚,但智顗所说的“明时”、“皇风”也确实不假,隋王朝对佛教的确是持大力扶持的态度的。智顗对隋文帝也确实是带着一种感恩的心态,“若塔像庄严,则绍隆不绝,用报佛恩;若处处光新国界,自然特殊妙好,则报至尊水土之泽。”[10]直至其临终前,还一再表示对隋王朝的感恩戴德,《遗书》:“生来所有周章者,皆为佛法,为国土,为众生……命尽之后,若有神力,誓当影护王之土境,使愿法流行,以答王恩,以副本志。”[10]不过情感抒发归情感抒发,智顗在临终前也没有忘了要为天台宗谋福利,他在《遗书》中向杨广请求:“乞废寺田,为天台基业。”杨广对此也是满口应允,《答遗旨文》:“所求废寺水田,以充基业,亦勒王弘,施肥田良地。”[10]智顗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从整体上加强了隋皇室与天台宗之间的关系。如在智顗去世之后,杨广夺得太子之位时,天台宗人智越等立即上书致贺,《天台众贺启》:“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门智越一众启:伏惟殿下,睿德自天,恭膺储副,生民庆赖,万国欢宁,凡在道俗,莫不舞抃!况复越等,早蒙覆护,曲奉慈惠,不任悦豫之诚!谨谴僧使灌顶、智璪等,奉启以闻!”[10]为此在贺礼之后,杨广还专门派员外散骑侍郎张乾威送他们回天台山,还“施物三千段,毡三百领……设千僧斋。”次年杨广还特意下令邀请智顗的高足、天台宗的传人灌顶入京,《天台九祖传·灌顶》:“禅师既是大师高足,法门委寄,今遣延屈,必希霈然随使入京。”[15]再如杨广登基为帝时,天台僧人又在第一时间上表致贺,《仁寿四年皇太子登极,天台众贺至尊》:“天台寺沙门智越等一众启:窃闻金轮绀宝,奕世相传,重离少阳,时垂御辨。伏惟皇帝菩萨,圣业平成,纂临洪祚,四海万邦,道俗称幸,越等不任喜踊之至!谨遣僧使智璪,奉启以闻!”[10]
综上所述,佛教的发展虽然取决于诸多因素,但在中国古代君权至上的中央集权封建社会,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对于佛教的支持与否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存在,也无法摆脱宗教哲学与宗教社会学的二律背反。作为宗教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超凡脱俗,但作为宗教组织,其存在与发展必然要受制于社会各方力量的博弈与权衡,而绝不可能成为乌托邦式的理想净土。千年前的高僧大德绝对不会认识不到这些事实,所以佛教僧人对当朝政权的亲近也绝不是什么谄媚之相,相反,中国佛教恰恰是在这种与当朝政权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的关系中成长、兴盛起来的。
[1] (梁)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2] (北魏)慧思.大乘止观法门(卷二)[G]//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6册).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
[3] 王彬(译注).法华经[M].北京:中华书局,2010.
[4] (隋)智顗.法华玄义(卷二)[G]//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3册).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
[5] (隋)智顗.摩诃止观[G]//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6册).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
[6] (隋)智顗.修习止观坐禅法要[G]//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6册).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
[7] 郭朋.隋唐佛教[M].济南:齐鲁书社,1980.
[8] (唐)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9] (隋)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六)[G]//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
[10](唐)灌顶.国清百录[G]//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6册).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
[11]潘桂明,吴忠伟.中国天台宗通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12]董平.天台宗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3]包兆昌.智顗与陈、隋王朝关系新探[J].台州学院学报,2007 (5).
[14]王光照.隋炀帝与天台宗[J].学术月刊,1994(9).
[15](宋)士衡.天台九祖传[G]//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册).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
【责任编辑 张 琴】
1672-2035(2015)01-0021-04
G122;B946.1
A
2014-06-26
段知壮(1988-),男,吉林四平人,南开大学与日本爱知大学联合培养在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