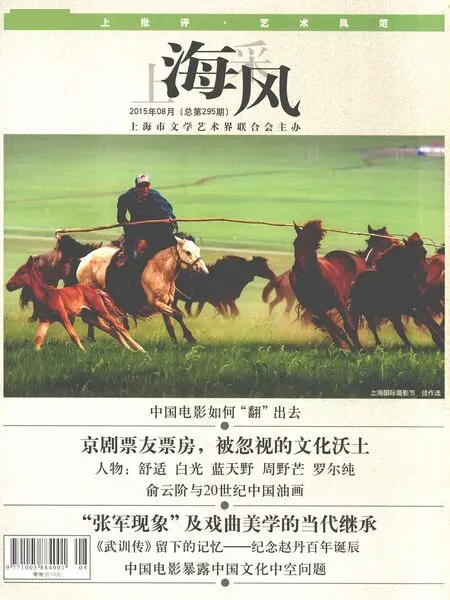上海这座城,有灵魂么
文/刘再复
上海这座城,有灵魂么
文/刘再复
壹
二十二年来,我走过三十多个国家,欣赏过一百多个城市,每到异乡的一城一池,总会联想起故土大地上的北京与上海。这才知道“北京”与“上海”这两个名字已在自己的血液深处扎下根了。我在北京居住了二十七年,在上海则逗留不到二十七天,然而,拉开时间与空间的长距离之后,这两个城市在我的记忆中却同样深刻,同样难忘。不管世道如何沧桑,人生如何曲折,“上海”再也挥之不去了。
我常用“是否有灵魂”这一眼光来看城市。因此,总是把城市划分为“有灵魂的城市”和“没有灵魂的城市”,或“灵魂微弱的城市”。《忏悔录》的伟大作者、中世纪宗教思想家奥古斯丁写过《上帝之城》一书。在此书中,他说上帝之城包括精神之城与世俗之城。我引伸一下说,凡是精神之城非常发达的地方,都可称作有灵魂的城市。香港可以说是地球上最繁荣、最发达的世俗之城,但其精神之城却不够灿烂,以至让人们视为“文化沙漠”。我虽多次为香港辩护,但也不能不承认,它是一个灵魂微弱的城市。至于澳门、拉斯维加斯(美国)等处,尽管赌场的灯火格外辉煌,但我还是把它划入没有灵魂的城市。分类,本身就是一种话语权力操作,不免独断,因此朋友之间聊起来也不免会有争论。可是,对于巴黎、罗马、伦敦、北京、京都等城市,朋友们总是一致认定这是有灵魂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历史文化积淀太丰富了,那些教堂的尖顶、先贤的墓地、天才的名字、博物馆的珍品,样样都不容你否认这个城市是个巨大的精神存在。对于上海,则常有争论。
“上海是伟大的世俗之城”,这一点没有争议。早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上海就与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大都市“齐名”,成为地球上稀少的“城市恐龙”之一,世俗生活丰富多彩到了极致。可惜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上海却陷入了萧条与贫困,霓虹灯下只有哨兵而没有夜市,甚至连霓虹灯本身也失去了斑驳的色彩。恐龙失落了血肉,只剩下了空疏的骨架。一九八〇年我首次来到上海时,只拜访了我的散文诗习作《雨丝集》的责任编辑谢泉铭先生。他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可是他的住房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狭小和简陋,特别让我惊讶的是床下还有床,其拥挤可想而知。谢先生就在这一小“蜗居”的灰暗灯光下一页一页地阅读那些无名作者的手稿,包括我傻乎乎地投给出版社的十分幼稚的诗集。我与他素昧平生,可他却在阅读中发现我有写作的“底气”——他在信上这样激励我,让我高兴得彻夜难眠。没有谢泉铭,就没有我后来的《读沧海》和《再读沧海》等,所以我到海外浪迹天涯时,总是对友人说,上海有个默默无闻无私的“神瑛侍者”,他的名字叫做谢泉铭。可是他在破落的上海却几乎没有安居之所。从他身上,可知上海这一城市恐龙已消瘦干瘠到何等地步。幸而转机来了。一九八五年我到上海参加“文化战略”讨论会,看到的还是恐龙骨架,但那时恐龙之魂已经觉醒,正在翻身重吟之中。那之后的二十年,恐龙的肉身又再次丰满起来。如今上海再次成为强大的世俗之城,其辉煌绝不在香港、东京、纽约、伦敦之下。
“那么,上海是不是伟大的精神之城?”关于这一点,朋友之间则总是争论不休。说“不是”的,理由很多。上海没有罗浮宫,没有先贤祠,没有大英帝国博物馆似的博物馆,没有罗马斗兽场似的历史遗迹,没有西敏寺那种埋葬着牛顿、达尔文、狄更斯的大教堂,没有剑桥、牛津、哈佛那样的现代大学,甚至没有北大、清华这种老牌大学。原先比较深厚的圣约翰大学已经消失,一九四九年后才浮上地表的“华师大”等校,历史毕竟太短。“交大”资格较老,可是分身一半到西安。上海虽然曾经“阔”过,但没有建设国家博物馆与城市博物馆的传统,艺术的珍品善品只是个人收藏,私藏者的“家”也许有魂,但公共的“城廓”还是没有魂,比不得北京故宫博物院那种长悠悠、沉甸甸的气象。
争辩中我总是属于“保海党”的一方,总是竭力论证上海乃是有灵魂的城市。一九八五年我到上海时曾接受上海电视台的采访畅谈上海。那时我就说,上海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先打破海禁即最先打开门户的城市,是聚集着管理精英和工艺精英的中国现代化先锋城市。上海“敢为天下先”,所谓海派文化便是敢开风气之先的文化。这一基本认识,我一直坚守着。在海外与朋友的争论中,我还说,别小看上海的“租界”与“十里洋场”,没有这些租界与洋场,就不会有张爱玲,甚至也不会有完整的鲁迅。不是吗?鲁迅的《且介亭杂文》,就得益于半租界。整个左翼文学之所以能蓬勃发展,也完全是借助上海的生存夹缝、社会氛围和心灵的温热。鲁迅被誉为“民族魂”,而这一魂魄最后十年是在上海磅礴跳动的。鲁迅时代上海那么多文学刊物,其辐射的时代光芒覆盖全中国。这些刊物为什么能生存?因为有读者。那时的上海聚集着无数苦闷而有理想的中国青年,他们渴望读书,渴望新知,渴望真理。这种渴望,便是灵魂的骚动。在论辩中我也承认,上海的灵魂在上世纪下半叶之初的二十多年里受到改变,“左”祸逐渐猖獗,连原先左翼文化的首领潘汉年也被送进牢狱,而我的写作课老师(厦门大学中文系)、原上海市首任宣传部长彭柏山也被送上十字架,至于张爱玲彷徨无地迁居海外恐怕亦与之有关。上海呵上海,我能理解你,大有大的难处,大就让人注目,让人不放心,让人不能不看得更严,管得更紧。可是一旦严紧,灵魂就难以拥有活力,才子才女们就难以拥有天马行空的精彩了。
贰
我所以竭力为上海辩护,还因为我和上海文艺界尤其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有着一段富有诗意的“因缘”。“因缘”里蕴藏着我终生难忘的激励之情。
前几年,我应《东方早报》所属的“上海书评”陆灏兄的邀请,前去上海参加由“早报”主办的十年文化成就奖颁奖活动。很荣幸,我被尊为“颁奖人”,给文化英雄们颁奖。除了参加颁奖活动之外,我还到上海图书馆讲述“红楼梦的哲学阅读”,到华东师大文学院讲述“红楼梦与西方哲学”,到译文出版社评述李泽厚的答问录新书。就在出版社的座谈会上,我和阔别了二十三年的好友、前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郝铭鉴相逢。这一相逢真让我喜出望外,高兴了好久。
郝铭鉴兄是改变我命运的一个上海出版家。让我“暴得大名”(胡适语)的《性格组合论》正是他推动出版的。他当时身为出版社的负责人,亲自来到北京,向我约稿。说他正在组织一套名为“文艺探索书系”的丛书,以探索为手段,以开拓为目的,一定要让我的论著打先锋,作为丛书的开山之作。他还运用手中的“权力”,说出版社租了旅馆,可让我在上海躲藏起来写作几个月(我果然也到上海躲着读清样),其真诚的态度令人感动。在他的敦促下,我很快写就最后三章,完成了这部理论著作。从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六年之间,我接到郝铭鉴兄许多电话和信件,每封信都是“你可放开写”一类的鼓励与叮咛,那两年,我从铭鉴兄身上,得到最多的温暖和力量,并通过郝铭鉴,我感受到来自上海的助我思想飞扬的暖流。除了铭鉴兄,还有一个让我永远难忘的已故的友人,这是徐启华。他那时在《文汇报》担任副刊主编。出国后他英年早逝,真让我的伤感伤到心底。我在二〇〇四年所作的悼念文章《文学殉道者的光明》中有一段这样的纪实文字:
……正是这个低调的《文汇报》副刊主编,在八十年代用他的全副心力支持我的探索,毫无保留地为我推波助澜。他对我说:“你的文章,无论是理论文章还是散文诗,我都一律发表。”这种绝对态度,使我深受鼓舞。一九八五年六月,我应他所约,写了“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他接后立即打电话给我,说他将立即发出,并加编者按语,组织全国性讨论,声音是兴奋的。果然,七月八日,文章就见报,接着便是牵动人心的热烈讨论。在他的推动下,我进一步把中心论点学术形态化,写了《论文学主体性》,进一步引发更大范围的论争。今天国内外学界都知道我是八十年代“文学主体性”学案的主角,却很少人知道是启华拉开了“文学主体性”讨论的序幕。一九八六年秋,文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新时期文学十年”大型研讨会,我做了“论新时期文学主潮”的报告,篇幅一万字,他竟然决定要在《文汇报》全文刊登,我说《人民日报》已决定刊登了,他却说,他们登他们的,我们登我们的。就这样,出现了南、北两大报同时刊登我文章的特异现象,而制造这一现象的正是那个腼腆的上海编辑。读了《文汇报》我才明白,这个说话声音柔和的启华很有大将风度,很有独撑灵魂的内在力量……
《性格组合论》刚一出版,《人民日报》就第一时间报道“一抢而空”的消息,这之后,便一版再版,直至第六版,发行量近四十万册,成为一九八六年的十大畅销书,还得了几个主要报刊联合颁发的“金钥匙奖”。对于奖项和外部评语,我历来不在乎,觉得自己不受批判便是凯旋,最重要的是能够发出自己内心真实而自由的声音,但“金钥匙”这一名字实在很美,也很切合我的喜欢打开思想门窗的心灵走向,所以就记住了。
《性格组合论》第一版发行时,郝铭鉴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郑煌等其他负责人,特在上海举行发布会,还要我作个“讲话”。面对一千多个好学的听众,我以最坚定的语言颂扬巴金所作的“忏悔录”(原书名《随想录》)。说明忏悔乃是民族新生的第一步。我们曾共同创造了一个错误的时代(文化大革命),在错误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份责任。对这份责任的体认,便是良心。“受蒙蔽”而进入“共犯结构”没有法律责任,但有良知责任。演讲后我收到几百张字条,其中那些感人的语言除了给我震撼之外还让我感到上海这个伟大城市显然跳动着一颗集体性的伟大的良心。演讲后,我开始签名,队伍排得很长,一些拥到讲台上的性急的年青朋友差些把桌子挤倒。签书半小时后“拥挤”现象愈来愈烈,我坐不住了,郝铭鉴诸兄怕我不“安全”,竟把我“架走”,匆匆逃离会场。那一天,我感到八十年代的上海真是一团火,烧得我浑身是热,也烧得我思想更为动荡更为活泼。所以从上海返回北京之后,我便立即撰写《论文学主体性》,一发不可收了。
一九八六年十月的一天,钱钟书先生急着找我,说他得知《性格组合论》印数已超过三十万,让我要“知止”,说“显学很容易变成俗学,不要再印了”。钱先生一言九鼎,我立即写信给郝铭鉴兄,请上海文艺出版社不要再增印了。出版社尊重我的意见,也就止于第六版。钱先生是个极有智慧的大学者,他深明“知止不殆”(《道德经》)的真理,劝阻我完全是为了保护我。
《性格组合论》让我“暴得大名”之后果然也让我进入多事之秋。而在此“秋季”里,又是上海把我推得愈走愈远。首先是《文汇月刊》记者刘绪源带着梅朵和肖关鸿的好意到北京采访我。开始时我还是逃避,但最终扭不过绪源兄的“执着”,从而对他回应了姚雪垠先生的批评。姚先生在《红旗》杂志写了两篇数万字的长文,对我进行“炮轰”。此事非同小可,一旦回应,便会演成一件大事。果然,刘绪源的采访录在《文汇月刊》(1988年2月号)以头条的显著位置发表之后,引起了姚先生的愤怒,他声言要到法院起诉我。剑拔弩张之势形成了,事态严重化了。尽管那时我收到无数“声援”的电话与信件,包括律师的“自告奋勇”,但我还是略感不安,觉得自己可能犯了和姚先生一样的错误:上纲上线。文化大革命的毒汁固然在姚先生身上有所反应,在我身上也有所反应。姚先生说我“反马克思主义”,我还以姚先生“顺四人帮路线”。尽管双方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各显“政治正确”的姿态,但都没有在学术上进入真问题。不过,由上海《文汇月刊》发动的这场半论争半官司的戏剧,却让我更深入地思索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即让我更彻底告别文学顺从意识形态的悲剧,也更清楚地认清了把文学变成意识形态的转达形式,丧失审美自性,正是当代文学最根本的伤痛。出国后我和林岗合写的关于“广义革命文学”的论著,其论说主题及其彻底性的审美判断也得益于这场论争,所以我还是要感谢绪源兄,感谢梅朵、肖关鸿兄主持的《文汇月刊》和它立身的大上海。
出国十年之后,又是上海最先记起了我。出版社的高国平兄在电话上对我说的话,让我落泪。他说:上海一直怀念你,你的书已长存在上海的心里了。这几句话出自一颗朴实而憨厚的心灵,在我内心激起强大的思想波澜。近十年来,我每天黎明即起,笔耕不倦,思想进入新的飞扬时期,这箇中有许多原因,但有一原因便是上海助我——上海的朋友助我。天地人间,情感毕竟是最后的实在。上海友人们给我的正是最值得珍惜的助我思想飞扬的真情感。此刻我想起给我激励之情的国平兄、启华兄和谢泉铭、梅朵先生已经去世,再也无法向他们说一声感谢,实在难过得难以自持,写不下去了。不过,最后还想说,倘若此刻我站在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门口,那我一定会面向东方充满感激地说:“上海,助我思想飞扬的上海,你是一个有灵魂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