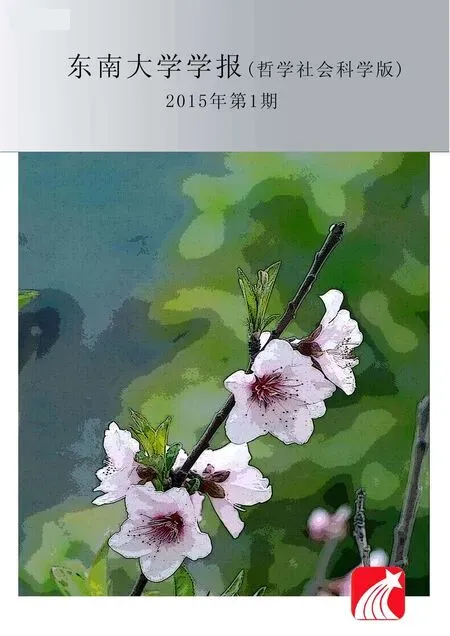个体化倾向及其阶层差异
洪岩璧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210096)
中国向来以“文明礼仪”之邦自称,然而近年来的一系列事件,如小悦悦事件、广场舞争论、扶摔倒老人被讹等,却给这一称号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此类事件貌似家长里短,但其影响却至为深刻巨大,不仅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道德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整个社会和文化的危机,并进而可能“影响到意识形态安全”[1]。但也有学者认为所谓的“道德衰败”只是一个神话,“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都不可避免地出现对所谓道德滑坡或者道德崩溃的担心”[2]。此类宏观层次的讨论和争鸣为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现状提供了借鉴,但宏观论断若不能建基于微观研究之上,就不免会流于空疏。时至今日,大量的新闻报道和研究侧重从应然角度进行批判性检视,而欠缺基于实证数据的分析。
2011年,《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指出“焦躁疑惧、迷茫失落、愤青思维、拜金主义……在急剧转型中社会心态的失衡之势,是我们正在面临的挑战”[3]。社会心态是“一种社会共识和共同的情绪体验汇聚形成的社会心境状态”[4],它也是个体价值观形成的一般心理基础。所谓社会心态的失衡也是社会伦理道德出现问题的一个病兆。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诸多维度都处于急剧的现代化转型中,现代化过程往往会导致传统与现代在价值观、道德判断和行为规范方面的冲突。这一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核心现象就是个体的崛起[5]。那么这一“个体的崛起”与我们日常所目睹的道德事件存在何种关联?个体的崛起是否导致了当前社会的道德衰败?以往有关中国个体化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引介西方个体化理论,并厘清中国是否也正在经历西方社会那样的个体化进程[5-6];二是以定性调查和对策研究为主[7-9]。涂尔干指出,研究道德和权利科学有两种方法:一是比较历史学和比较民族志的方法;一是比较统计学的方法[10]3。在讨论“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一类应然问题之前,首先亟需明晰实然问题,即当下的道德现状到底如何,否则,相关的批评和分析往往会陷入隔靴搔痒的窘境。因此,本文尝试利用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希冀对已有研究起到补充作用。
本文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勾勒和剖析中国个体化进程之现状;二是分析不同社会群体(尤其是阶层)在个体化倾向上是否存在差异。因为以往分层研究主要关注物质资源,而相对忽略了伦理道德层面的阶层分化。本文属于探索性研究,为了融合理论探讨和数据分析,本文并未遵循一般的社会学定量分析文章的结构,而是首先介绍本文所使用的数据;然后,在分析部分,理论探讨和数据分析并行,分别讨论了个体化现状、个体化的类别以及个体化的阶层差异;最后对本研究进行总结和讨论。
一、数据与模型
本文所使用数据来自2013年“居民生活状况与心态调查”,该调查受江苏省委宣传部国家重大项目组委托,由东南大学国情调查中心和社会学系具体实施。本调查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抽取了南京、无锡和连云港三个地级市,然后利用PPS方法分别抽取区县、街道/乡镇和社区(居委会/村委会)。随后,根据社区常住人口名单进行系统抽样,每个社区抽取50-60户进行调查。最终抽中了3个地级市中的6个区县、12个街道/乡镇、24个社区。入户问卷调查于2013年9月5日-15日、11月9日进行。最终完成1281份调查问卷,其中南京446份,无锡443份,连云港392份。调查结果可以基本推论到江苏省境内的常住户籍人口。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职业阶层、教育和收入,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宗教信仰、党员、户籍。①由于年龄平方在所有模型中都不显著,出于简洁性考虑,所有模型都删除了年龄平方项。有关上述变量的具体操作化参见表1。本调查对伦理道德判断的测量主要采取三种方式。一是直接询问被访者对某一表述的态度(从“完全同意”到“完全不同意”)。二是假设某个情境,让被访者决定在该情境中会做出什么选择。三是询问被访者对社会上发生的某个事件的看法和评价。本文的因变量有5个,分别是个体—国家/家庭关系、是否会救助陌生人、对香港老太阻碍工程的判断、对广场舞扰民的看法,以及对社会道德状况的总体判断。有关因变量的具体描述笔者在下文的数据分析中会提及。由于因变量皆为分类变量,因此采用了logistic模型(二分类因变量)和多分类因变量logit模型。在logistic模型中,建构两个相互嵌套的模型,即不包括教育和收入变量的简单模型,和纳入所有变量的完全模型。通过这两个模型之间的比较,探讨阶层间的差异是否主要由教育和收入水平的分化引起。在分析中,删除了存在缺失值的个案,剩下的个案数为1097,本文的统计分析结果皆基于这些个案所得。

表1 自变量特征描述(N=1097)
二、个体主义盛行?
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不仅在社会学中举足轻重,是公民道德的重要维度[10],在伦理学中也是核心议题之一。阎云翔认为,在当前中国,个体崛起的证据俯拾皆是,包括生活理想中对于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强调,社会实践中更多的个人选择,以及个体从涵盖一切的家庭、亲属关系和社群等社会藩篱中脱嵌[8]。什么是个体化?阎云翔指出个体化命题中的三个主要观点值得特别关注[8,11]。一是个体从社会性中“脱嵌”(disembedment),或吉登斯所说的“去传统化”(detraditionalization),即个体日益从外在的社会约束中脱离出来,包括文化传统、家庭、血缘关系和阶级地位。二是鲍曼所说的“强迫的和义务的自主”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即现代社会结构强迫人们成为积极主动和自己做主的个体,对自己的问题负全责。但由于排除了传统、家庭和社区的保护,现代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影响事实上不断在增加。三是“通过从众来创造自己的生活”,即倡导选择、自由和个性并不必然会使个体变得与众不同,相反,对社会制度的依赖决定了人们最终得到了相当一致的生活。但个体化理论和命题主要基于西欧社会的历史经验和现状发展而来,其在非西方社会的适用性尚无定见。
就中国社会而言,其个体化存在诸多不同之处。贝克夫妇认为个体化进程有赖于“文化的民主化”,即民主已经作为一个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原则被广泛接受和实践;其次,福利国家体制的存在也是中西一大差异[8]。这两个制度特征无疑是当前中国社会所不具备的。但贝克等人的个体化命题强调一种新的张力,一方面是不断增长的对个性、选择和自由的要求,另一方面是个体对社会制度的复杂而不可避免的依赖[8]327。这对于理解当前中国社会中的个人与社会制度(尤其是国家)极具借鉴意义。
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家庭和国家是至关重要的两种制度。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上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所谓伦理,就是社会关系,“就是要人认清楚人生相互关系之理,而于彼此相互关系中,互以对方为重而已”[12]87。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梁漱溟指出西方的团体和个人是两个实体,家庭无足轻重;但中国的伦理本位是从家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从而消融了个人与团体这两端。所以他说:“是关系,皆是伦理;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12]79。这和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近似,即个体根据与他人的亲疏关系来确定交往准则。边燕杰进而提出“关系主义文化”,即一套关于伦理本位、关系导向,以“熟、亲、信”为准则的行为规范。与之相对的是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个体主义是利益本位、个人导向,以“权、责、利”为准则的理性主义文化。集体主义是价值本位、集体导向,笃信“集体利益高于一切”这一信条。[13]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集体主义文化在社会伦理道德中占统治地位。国家通过一系列运动推行集体主义道德,从而破除了以家庭为核心的伦理本位社会,使得国家可以直接控制个体,从而形成个人对社会制度和国家的组织性依赖。但由于“天高皇帝远”,国家能力自有其限度,所以伦理本位社会的破除也为个体的兴起提供了条件[5,7]。改革开放之后,个体主义如出笼猛虎,一发不可收拾。现代经济竞争的急速扩展,对旧有的社会文化传统形成摧枯拉朽之势。一方面,由于对自由流动的劳动力的需求,市场促使个体打破社会团体的约束,寻找自己的发展之路;另一方面,国家也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刺激经济发展和改造社会结构,体制改革给个体、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松绑,激发底层的工作热情[8]330。因此,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利之间亟需一种新的规范加以调节和润滑。
中国社会个体化这一转变的核心是崛起的个体与包括国家在内的多种形式的集体之间正在进行的协商和抗争[5]。此类集体形式包括国家和家庭。可以说家庭和国家是个体化崛起所面对的两个重要“集体”制度。从这一角度出发,本调查用下面的题器来测量被访者的个体化“脱嵌”倾向:
C6.您认为家庭和国家对于个人存在的意义是
1.家庭和国家只是工具,个人最重要
2.家庭和国家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基地,比个人更重要
3.其他(请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结果显示,83.5%的被访者选择了选项2,选择选项1和3的比例大致相等。把选项1和3合并,形成二分类变量:家庭和国家比个人更重要=1,个人更重要=0。这一比例分布表明大多数被访者依然认同“集体”比个人更重要。由此,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全面转向个体化社会的判断是值得商榷的。正如阎云翔所说,到目前为止,个体仍然被国家和社会视作达到更远大目标的手段,且大多数个体也认同这一看法[7]。
那么这种个体化倾向在不同的阶层群体中是否存在差异呢?对美国社会的研究表明,不同社会阶层的道德倾向存在差异[14]。我国的一些研究也指出不同社会群体在伦理道德的价值判断上存在冲突和矛盾[15]。我们通过回归模型来看阶层差异,以及教育和收入的影响。由表2的logistic模型结果(模型M1和M2)可知,个体化倾向在阶层之间基本不存在显著差异。在简单模型 M1中,所有阶层系数皆不显著。在完全模型M2中,收入对个体化倾向有显著影响。相比于无收入者,月收入2000-3999元和4000元以上者更认同个人更重要这一说法。Piff等人的研究指出,在动荡时期,富人更倾向于依赖财富,而穷人更可能依靠社群[14]。在变动频仍的中国转型社会,富人更认同个人比国家和家庭更重要。
在完全模型M2中,底层比管理人员的“脱嵌”倾向更强一些,但系数只在0.1水平上显著。因此,一个基本的判断是职业阶层间的“脱嵌”倾向差异不显著,但高收入群体的“脱嵌”倾向更强。这也表明仅以职业来划分社会群体,难以较好地反映观念和态度的分化。此外,由这一测量也难以较好地反映个体化倾向内部的复杂性,所以本调查还采用了情境题来测量被访者的个体化倾向。

表2 个体“脱嵌”倾向的logistic模型
本文以下面的题器为情境,来测量个体在涉及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时的抉择:
B8.2010年,港珠澳大桥修到香港段时,香港66岁的朱老太认为,工程的环境评估不充分,因而是不合理也是不合法的。于是就大桥香港段环评报告申请司法复核,最终法官裁定香港环保部门存在疏忽。因这位老太的诉讼导致工程停工,预算增加了很多。对此事,存在以下不同看法,您更同意哪种:
0.老太不应该因担心自己身体受影响而叫停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
1.老太的行为在道德上无可指责,因为真正该负责任的是香港环保部门。
选项0反映被访者更注重集体或国家利益,而非个体利益。选项1则表明被访者更看重个体的权利,认为这是道德的基点。有21.6%的被访者选择了选项0,78.4%选择了选项1(N=1097)。这说明,相对于集体或国家而言,接近4/5的被访者认为个体的权利和利益更重要。这显然与C6题的结果存在很大冲突。如何理解这一矛盾现象?家庭和国家虽然同为个体之上的“实体”,但对于个体而言,其意义差别甚大。在当前中国社会,家庭仍然是个体崛起最好的资源,同时也是个体自我身份认同的基础[5,7]。在道德领域,本调查询问被访者C32,“您认为在自己的成长中得到道德训练的最重要场所或机构是?”答案的比例分别是家庭38.9%,学校26.9%,社会(包括职业生活)25.3%,国家或政府5.8%,媒体1.5%。换言之,中国的个体已经逐渐从国家这一曾经无所不在的集体范畴中解放出来了,但并未抛弃家庭这一传统归属范畴。涂尔干认为“家庭生活曾经是,也依然是道德的核心,是忠诚、无私和道德交流的大学校”[10]22,这一判断在当前中国似乎并未过时。当然,这里所说的家庭已经不是梁漱溟的伦理本位社会中所说的“五服”家庭了,而是现代的核心小家庭。
表2的模型M3和M4分别是对B8情境题看法的简单回归和完全回归结果。在M3中,城镇居民显著地支持老太太的行为,而蓝领和底层显著地不支持其行为。在M4中,加入教育和收入变量之后,城镇居民依然是显著正效应,但阶层差异已不再明显,说明阶层差异被教育和收入差异所解释。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支持老太太的行为,即更注重个体的权利,而非国家利益。
三、何种个体主义?
个体化被认为是中国正在崛起的一股思潮,并从方方面面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9]。但个体主义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包含了不同的类型,甚至充满了内在矛盾。一方面,随着市场繁荣和民众富裕,原有的秩序和道德观念日益淡漠,中国社会步入了一个缺乏善恶感的时代。曾几何时,我们认为为了“摆脱贫困”,一切的道德评价都是苍白无力的。现如今,“摆脱贫困”已不再是时代主题了,但我们的道德水平似乎并未有所提升,日益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便是明证。生产者不食用自己的产品,但并不在乎陌生人食用这些有毒食品,从而形成“易粪相食”的可悲局面。这种极端自我的个人主义显然和贝克等人个体化理论中的个体存在很大差别,但却是中国社会的无情现实。为了进一步了解个体化的不同维度和侧面,本调查通过把被访者置于事件情境中来获得其道德判断,并分析相关的影响因素。两个相关情境分别是广场舞扰民和是否救助陌生人。
广场舞扰民问题广为媒体报道,各方往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此作为一个情境题,它可以较好地测量被访者的个体化倾向。题器如下(括号中数字是选择该选项的比例):
B4.入夏以来,晚饭后,很多中老年朋友喜欢在广场上伴着录音机播放的音乐跳舞。但小区里有人向物管投诉,嫌跳舞者放的音乐太吵,扰乱了社区的安静环境,要求物管阻止她们的跳舞活动。对这件事您怎么看:
1.在广场上跳舞是居民的自由,继续跳 (21.2%)
2.跳舞自由如果妨碍了别人的清静自由,就应该停止 (15.8%)
3.大家在一个社区生活,即便跳舞活动构成干扰,也应该尽量容忍,免得伤了和气(15.7%)
4.当大家的权利相互冲突时,应该通过协商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 (47.2%)
这四个选项分别代表了不同形式的个体主义。选项1“继续跳”是一种极端自我的个体主义,他们只关注自己的“自由”,而不顾及他人的“自由”。选项2“应该停止”代表了另一种个体主义,注重相互间权利,认为如果自己的“自由”侵犯了他人“自由”,那么就该停止该行为。选项4“合理协商”代表了第三种个体主义,在关注个体自由的基础上,认为个体之间发生冲突时应该以理性协商方式解决矛盾。选项3“尽量容忍”则代表了传统的集体重于个体的观念。
结果显示,近一半(47%)被访者展现出了一种较为成熟的个体主义观念,近1/6的人秉持的依然是传统的“和事佬”观念。还有1/6的人注意到个体的自由不应妨碍其他个体的权利,但他们还没有形成通过个体间理性沟通来解决争端的意识。值得注意的是,有超过1/5的人认为应该继续跳,这也揭示了为什么各地因广场舞而争端不断。这正是学者所批判的只强调权利而忽视义务和他人权利的个体主义,或称之为“无公德个人”[7]。社会上存在数量庞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者,无疑会使整个社会的道德面貌江河日下,难以提升。因此颇有必要检视哪些因素影响了被访者倾向于不同的个体主义。
由于存在4个不同选择,笔者采用了多分类因变量logit回归,以“合理协商”为参照类,结果如表3所示。相对于“合理协商”,年纪大的人和信仰宗教者更可能选择“尽量容忍”。而城镇居民更不可能选择“继续跳”这一选项,因为广场舞扰民问题主要发生在城镇地区。性别和党员身份没有什么显著影响。就阶层变量而言,在控制教育和收入之后,除了办事人员更倾向于“尽量容忍”外,其他阶层间无显著差异。教育水平越高,越不可能选择“继续跳”。而收入水平都没有显著影响。最后,“脱嵌”变量系数显示,相比于“合理协商”,个体“脱嵌”倾向高,就更可能选择“应该停止”,也更可能选择“继续跳”,但后者仅在0.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个体的“脱嵌”倾向与个体间相互关系也息息相关。

表3 多类别因变量回归(B4广场舞)
第二个情境是对陌生人求助的态度。中国以往的志愿者工作都由政府及其委托机构组织和领导,在某种程度上属于集体行动。但2008年5月的汶川大地震之后,个体志愿者迅速兴起,阎云翔认为这种个体自愿活动主要基于一种对陌生人的同情,是一种非相关个体之间的互动,促使中国社会的道德价值和信任文化也变得更为个体化[8]339。
与经典社会理论家面对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的社会不同,新近的个体化研究者试图理解当前身处高度不确定性社会中的个体化本质[11]13。在贝克的个体化理论中,“利他个体主义”是促进社会团结的重要伦理因素,其核心原则是“给予却不必牺牲自己”[6]。为了测量此类“利他个体主义”态度,本调查询问被访者是否同意下面的表述:B7A“如果上街碰到陌生人求助,最好对其置之不理”,选择结果是“完全同意”11.2%,“比 较 同 意 ”26.5%,“不 太 同 意 ”46.3%,“完全不同意”13.3%。多数被访者会选择帮助陌生人,但不容忽视的是有超过37%的被访者会选择对陌生人的求助置之不理。这在现代社会并不乐观,因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需要接触陌生人。
表4的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相比于管理人员阶层,在简单模型M5中,蓝领阶层的正效应仅仅是边缘性显著,且在加入教育和收入变量的M6模型中不再显著。但在模型M5和M6中,底层都呈现显著正效应,说明相对于管理人员,底层更可能对陌生人的求助置之不理,而且这一阶层差异不能由教育和收入水平所解释。

表4 对陌生人求助(B7A)的Logistic回归
四、讨 论
作为影响中国人道德生活的重要维度,个体化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而非一味的污名化。①个体化往往被等同于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个体化进程展现了丰富的多样性,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也呈现出差异。首先,就个体与家庭和国家的关系而言,个体已基本脱离国家的控制,日渐把个体利益置于集体和国家利益之上。收入越高、教育程度越高的被访者,此种个体化倾向就越强。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已经从所有的集体范畴中“脱嵌”。就现阶段而言,家庭依然是中国人归属感和生活的重要指向,同时也为个体化提供了资源。第二,就个体化的类别而言,教育程度越高,个体秉持“无公德”个人主义的可能性就越低。相对而言,底层更不太可能认可“利他个体主义”,这一阶层差异也不能被教育和收入差异所解释。贝克夫妇的个体化理论强调制度在个体化进程中的作用,阎云翔的研究也展示了国家在中国当前个体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所以在个体化进程中,我们能够通过一些政策措施,包括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和减少底层的比例,尤其是无业失业者的比例,来抑制“无公德”个人主义的流行,激发负责任的个体主义和“利他个体主义”,从而增强社会团结。
转型社会过程出现的“中国问题”既具有普世性,又反映中国社会的独有特征,个体化进程亦不例外。贝克夫妇提出了四种现代性的理想类型,分别是欧洲式现代性、美国式现代性、中国式现代性和伊斯兰式现代性(前言:个体化的种类)[8]4-5。中国的个体化是一个发展的进程,同时展现了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状况[8]345。要了解这一复杂迭加的图景,就需要更多基于经验性调查的定性和定量研究。在西方学术界,通过实验来研究个人在特定情境下道德行为的实验伦理学(experimental ethics)已悄然兴起。这弥补了当下伦理学主要关注应然问题的局限。相形之下,社会学对伦理道德问题的关注依然不足,除了在“社会心态”问题(包括信任问题)与个体化命题之外,定量分析鲜有涉及其他伦理道德议题。本研究仅是实证伦理学领域的一个初步尝试,因而也存在诸多局限,尤其是操作化问题,如对道德态度的测量还很粗糙,都有待未来研究的进一步检验和发展。
[1]樊和平.伦理道德问题影响意识形态安全[N].中国教育报,2014-03-14.
[2]晏绍祥.道德衰败:一个神话?[N].南方周末,2013-06-14.
[3]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N].人民日报,2011-04-21(14).
[4]王俊秀,杨宜音.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3-2013)[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5]Yan Yunxiang.The Chinese Path to Ⅰndividualization.[J].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2012,61(3):489-512.
[6]李荣荣.从“为自己而活”到“利他个体主义”——乌尔里希·贝克个体化理论中的一种道德可能[J].学海,2014(2):106-111.
[7]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M].龚晓夏 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8]转引自 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M].陆洋,等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9]贺美德,鲁纳.“自我中国”:现代中国社会中个体的崛起[M].许烨芳,等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10]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M].渠东,付德根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1]Howard,Cosmo.Ⅰntroducing Ⅰndividualization[C]//Cosmo Howard ed.,Contested Ⅰndividualization:Debates about Contemporary Personhood.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1-33.
[1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949].
[13]边燕杰.关系社会学及其学科地位[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1-6.
[14]Piff,Paul K,Daniel M Stancato,Andres G Martinez,Michael W Kraus,Dacher Keltner.Class,Chaos,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12:103(6):949-62.
[15]樊浩.当前我国诸社会群体伦理道德的价值共识与文化冲突:中国伦理和谐状况报告[J].哲学研究,201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