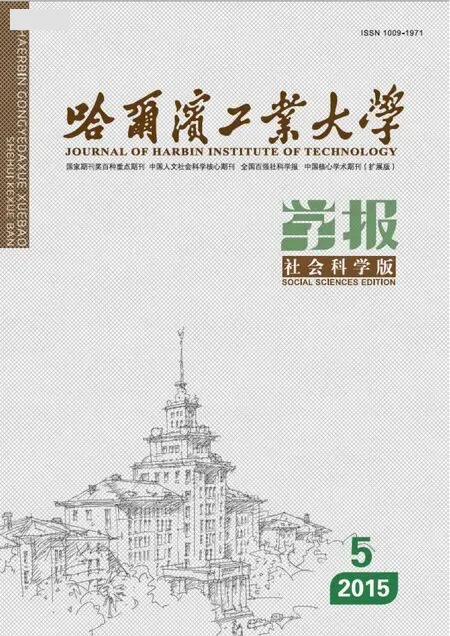“权利政治”语义分析及其范式
范进学
(上海交通大学 凯原法学院,上海 200240)
·政治文明与法律发展·
“权利政治”语义分析及其范式
范进学
(上海交通大学 凯原法学院,上海 200240)
摘要:“权利政治”这一术语自20世纪90年代晚期引入中国,即成为政治哲学界、国际政治学界、法学界等颇流行的话语。当其进入中国的学术语境后,由被批判的对象摇身变换为批判的武器,即用来批判传统的政治法律理论和制度,权利政治的对手从公益政治变换为权力政治。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所使用的分析工具即概念范式却是共同的,这就是“权利政治”。可见,“权利政治”作为一种分析问题的范式理论,获得了不同学术领域学者的共同承认。
关键词:权利政治;公益政治;权力政治
收稿日期:2015-05-2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权利与政治研究”(12JJD820001)
作者简介:范进学(1963-),男,山东临朐人,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从事权利政治哲学、宪法学、法解释方法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志码: A
文章编号:编号: 1009-1971(2015)05-0001-05
Abstract:The term of “Politics of right” has immediately become popular discourse in political philosophy,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legal science and so on since its introduction into China in the late 1990s.After entering China's academic context,it was transformed from the object of critique to the critical weapon, which is used to criticize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system and legal theory, and the opponents of right politics transformed from public politics to power rights.The academic analysis tool used by different scholars in the field,that is the concept paradigm is common,that is “politics of rights”.So “politics of rights” as a kind of paradigm theory to analyze the problem got common recognition from different academic fields and scholars.
“权利政治”这一术语自20世纪90年代晚期引入中国,即成为政治哲学界、国际政治学界、法学界等颇流行的话语。然而,“权利政治”的语义在不同的学界中是不同的。黄文艺曾分析说:“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英美学术语境中的权利政治与中国学者所理解的权利政治,就会发现权利政治的语义发生了实质性的转折。”[1]78因为在英美的政治哲学和法哲学领域中,权利政治是社群主义者批判新自由主义者时给后者所贴的政治标签;而当其进入中国的学术语境后,由被批判的对象摇身变换为批判的武器,即用来批判传统的政治法律理论和制度,权利政治的对手从公益政治变换为权力政治。事实确实如此,不同的理论语境下,权利政治的内涵是有差异的。循着这一差异,笔者欲因而澄清不同语义的“权利政治”的含义以及作为一种范式的权利政治话语的意义。
一、西方政治学语义的“权利政治”
“权利政治”(politics of rights)这一术语被引入中国,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俞可平199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的《当代西方社群主义及其公益政治学评析》一文以及随后于2000年出版的《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是权利正义优先于善即公共利益或公共善,还是善优先于权利正义,是政治哲学领域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争论之焦点。主张权利正义优先于善的政治就是“权利政治”,而主张善优先于权利正义则是公益政治[2]235-242。2003年俞可平在《政治与政治学》中明确指出:“自由主义者认为正义的原则是绝对的和普遍的,因而个人权利也是绝对的和普遍的,一个公正的社会必须遵循下列这一原则,即‘不能为了普遍利益而牺牲个人权利’。自由主义者倡导‘权利政治’,他们的理论便被称为‘权利的政治学’。社群主义者则相反,断定普遍的善始终优先于个人的权利,公共利益必须优先于私人利益,如果必需,国家为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的私人利益。他们强调公共利益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其理论被称为‘公益政治学’。”[3]
西方政治学中的“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是一对范畴与矛盾。主张权利哲学的政治理论由来已久,近代自由主义者如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密尔等主张个人权利是政治权力的来源与最终归属,权利是基础与本源,权力源自权利,这种权利哲学属于自然法哲学与人学哲学。而以罗尔斯、诺齐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则主张把个人权利作为政治学说的唯一基础。对于这样一种哲学,现代社群主义者进行了批判。社群主义者所说的权利不是抽象意义上的自然权利,而是社群中的法律权利。按照社群主义观点,“每个人都应当努力追求美德,在追求美德的过程中实现一种善良的生活。个人生活在社群之中,社群给予个人共同的目的和价值,因此,个人的善势必与社群的善结合在一起,真正的善就是个人之善与社群之善的有机结合。”[2]242-243也就是说,不是个人权利具有优先性,而是社群的公共道德具有优先性。因此,社群主义不是反对权利,而是反对自然权利,主张法律权利、集体权利和积极权利。
可见,西方政治学语义的“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相对,是社群主义者在批判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时的一种理论范式。他们都倡导“权利”,然而他们之间的权利是不同的,即自然权利与法律权利、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之间的差异。如果在“权利”在场的情况下言说“政治”,那么“公益政治”也是一种“权利政治”。
二、国际政治语义的“权利政治”
北京大学的梁守德教授则较早从国际政治的视角论及“权利政治”。2000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把国际政治的发展变化概括为从冷战前的权力政治过渡到冷战后的权利政治。他指出,“国际政治的实质,始终是权力政治与权利政治的较量。权利,即合理合法的权力和利益,以国际法为依据;权力,则包括合理的权力与不合理的权力,以实力为特征。长时期来,权力政治与权利政治的较量,始终以权力政治为主导,这是不争的事实。冷战后,权力政治与权利政治的较量,在国际新环境下发生了重大变化:权利政治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是冷战后国际政治中产生的重大新现象。”梁守德指出: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中的权利与权力的较量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权与主权的关系问题,权利政治,说到底就是反对霸权、维护主权与人权、充实完善主权与人权,使两权完整的统一。人权与主权均属于合理合法的权利, 人权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主权则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在当今世界的权利政治中,主权同霸权的矛盾是国际政治中突出的主要矛盾。依据国际法准则的规定,主权利益以主权范围内为界限,只能维护和争取,不能用实力扩大,一旦扩大就是霸权;主权利益以相互尊重与对等为前提,一旦干预与侵犯,就是霸权;主权利益,以民族国家为重,只能输出意识形态,不能输出社会制度,一旦输出就是霸权。要维护国家主权原则,就必须反对霸权,反对推行强权政治的霸权主义,尤其是反对美国的新霸权主义[4]。可见,梁守德在此所说的“国际政治中的权利政治”是国际法语义上的人权与主权的合法政治,其中的“权利”不是法学意义上的“公民权利”,而是指普遍的人权与主权;而“权力”也不是国内法意义上的与“公民权利”对应的“国家权力”,而是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的“霸权”。
2005年,梁守德又在另一篇文章中进一步阐明了他的“权利政治”之概念。他指出: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如何界定, 权利总是它的直接目标。那么, 作为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新视角的权利是什么? 他认为,民族自决权、主权、球权, 既是人权的延伸,又是人权的让渡;既是保障人权的需要, 又是人权的扩大。当前在以人权、民族自决权、主权和球权为主要内容的权利中, 主权是第一位的, 球权开始上升为关键地位,而人权始终是前提。当然, 权利不是自发扩展的, 而总是在同强权的较量中取得的。权利的充实完善是一个不懈斗争的过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人为本的权利政治就是以人权为基础, 以主权为首位, 以球权为保障的人权、民族自决权、主权和球权互联互动及其同强权较量的政治。权利, 以法为准。权利既是法律制定的, 又由法律保护, 依法治球。权利政治就是依法治球, 这是国际社会长治久安、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权利包含的四权(人权、民族自决权、主权和球权)在今天的国际社会均有法可依, 因而必须同时注意发展。在现实国际政治中, 权力则包含两部分: 合理合法的权力和非法无理的权力, 如强权和霸权。权力政治的要害就是绝对主权, 倚重霸权, 实力决定一切。权利政治与权力政治相连的地方在于既用法也用力,两者的区别在于: 前者依法重力, 法先力后, 力随法动, 力法并用;后者则是依力借法, 力先法后, 法为力用, 力重法轻。如果说权力政治是现实主义的核心,那么 权利政治则是理想同现实的结合。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权利政治就是合理合法的力量政治[5]。在该篇文章中,梁守德所说的“权利政治”中的“权利”内容与他五年前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增加了民族自决权与球权。
2004年,秦亚青在《从权力政治走向权利政治》一文中,借用政治学上的权力与权利的概念,言说国际政治的“权利政治”与“权力政治”。秦亚青说的“权力”是指政治上的强制力量;而“权利”则更多地强调依法行使的权力和享有的利益。在秦亚青看来,一切政治活动围绕权力展开,一切国际关系都是权力关系,国际政治与权力政治成为同义词。然而,在当今世界,一个大国不经联合国授权的强权行为,无论理由如何,都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因为它虽然有这样做的权力,却没有这样做的权利。强权并非公理。因此,在秦亚青看来,国际政治的一条日趋明显的发展脉络就是从权力政治走向权利政治[6]。可以说,秦亚青所说的“权利政治”中的“权利”指的就是合法的权力与利益,而“权力”则是一种缺乏法理依据的“强权”。
2008年,夏安凌教授在《论国际政治中的权利政治》一文中,认同了梁守德的国际政治中的“权利”概念,认为权利应当被定义为“合理合法的权力和利益”。但是,对“权力”则做了进一步深化。他们总结说:“1948年至今,‘权力政治’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明显的弱化与泛化趋势。从最初作为‘控制力’的权力,发展到作为‘能力’的权力;由传统的单一的物质权力发展到‘硬权力’和‘软权力’的综合;由传统的军事政治权力发展为对于‘结构性权力’和‘联系性权力’的综合;由传统的国家综合权力发展为划分‘总体权力’和‘具体领域问题的权力’。”[7]
从以上学者站在国际政治语义的角度所谈论的“权利政治”概念与内涵看,虽并非完全一致,但他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皆认同“权利政治”之范式,并运用这一范式的武器批判国际政治中的强权政治与霸权政治。
三、法政治学语义的“权利政治”
笔者曾在2003年出版的《权利政治论》中较早接受了作为分析工具的“权利政治”范式,以“权利政治”之范式批判人类社会的权力政治、强权政治、专制政治、人治政治,而倡导一种保障人权与权利的宪法政治、法治政治、民主政治,并提出了“权利政治是近现代政治的本质”之命题,进而将“权利政治”的特征概括为四个方面:政治主体都是一定的利益主体,法律是权利政治关系调整的主要方式,权利本位文化是权利政治文化的应有内涵以及社会政治问题的法律化思维[8]26-44。
2004年刘江在《论“权力”政治向“权利”政治的转变》中解释了“权力”政治与“权利”政治的概念。刘江指出,所谓“权力”政治或“权利”政治,都是指国家或政府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实施对社会的管理时,是以“权力”为本位,还是以“权利”为本位:在“权力”政治的社会里,国家权力至高无上,社会秩序的建立是以公民对国家权力的绝对服从来实现的;在“权利”政治的社会里,公民权利至高无上,国家权力是有限制的,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需视权利对其的授予和其对权利所起的作用而定[9]4。
2005年胡水君在《法律的政治分析》“前言”中对“权利政治”做了解读。胡水君认为,权利政治是与政治专制主义相对的一种政治类型,权利政治主要按照“人权和公民权利—国家权力”这一二元对立的理论范式建立起来的。胡水君说:“权利政治以个人自由为价值目标,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并进而以市民社会制约政治国家为社会基础,以权力分立为政治原则,以法治为法律原则,其要义在于‘人权和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目的与手段关系:国家权力是实现人权和公民权利的政治手段,国家权力的存在和运行以保存和维护人权和公民权利为目的。”[10]前言1-22007年胡水君在《权利政治的流变》一文中再次对“权利政治”概念做了简明概括:“权利政治是以个人权利或个人自由为出发点,通过国家和市民社会相分离、权力分立来限制国家权力,通过‘法律之治’来保障人权和公民权的现代政治。”[11]
2007年黄叶微在《从权利政治观浅析洛克的自由主义思想》一文中认为:“权利政治观是以个体的自然权力为根据论证政治关系与政治秩序,以权力为基础界定权威与自由、社会公共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的政治思维方式。”[12]
2008年任剑涛在《权利政治的兴起》中,通过考察新中国以来的政治行为模式的变化,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政治行为模式是权力政治模式,而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变化,尤其是中国政治存在形态与政治认知方式的变化,则是从权力政治向权利政治的变迁,是“权利政治的兴起”[13]21。
2010年徐双敏在《从权力政治到权利政治: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演进轨迹》中对权力政治与权利政治做了界定。徐双敏认为,权力政治是指主要依靠暴力手段维持的国家统治,其特征是专政和强制;而权利政治则是指以实现公民权利为主要手段和目标的国家统治,以民主和法制为特征。权利政治以承认公民的主体性、尊重和实现公民的权利为前提,是经济现代化的产物,也符合现代化的发展方向[14]54。
以上学者从法政治学的角度观察“权利政治”的基本内涵,虽然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运用“权利政治”的范式,解构古代政治或威权政治,其对立面是“权力政治”。笔者与胡水君皆是把“权利政治”视为近代启蒙以来的一种政治发展模式,是与启蒙前的西方古代政治相对应的一种政治治理方式。笔者曾在《权利政治论》中指出,古代社会的政治,由于多属君主专制政治,家天下和一人统治即人治是其主要特征,所以权利主体总是少数人,权利也往往表现为有权阶级的特权。古代政治的生活原则是权力本位。近现代政治是民主与法治政治,它是在对古代权力政治理念和制度根本否定的前提下建构起来的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模式和理念思维方式。近现代政治是在理论思想与制度体制上彻底否定了专制权力的无限性、集权性、专断性和任意性背景下建构起来的新型的关键制度和政府体制,它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社会的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模型,实现了权利对权力的根本性否定,是对传统权力至上理念的永远埋葬[8]27-35。胡水君也指出,为了给一种与教权统治和君主专制针锋相对的新型统治或治理形式提供正当性论证,启蒙思想家建构了一套自然状态学说和社会契约理论,成为18世纪以来权利政治的重要理论渊源。这种权利政治的新类型自18世纪产生以来,一直是西方政治法律实践的主导模式,成为世界范围政治法律改革的主要导向,近三百多年来的现代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利政治和权利话语的扩展史[10]前言2。所以,这种从西方古代政治到近现代政治模式的观察与判析,都是以“权利政治”这一基本范式为分析视角的。
刘江、任剑涛、徐双敏等学者则基于新中国以来、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的发展历程而以“权利政治”范式分析中国自身的政治发展模式。刘江把“权力”政治向“权利”政治转变视为中国当下政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认为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是这一转变的经济前提,逐步形成良好的法治秩序是这一转变的根本途径,建设以契约精神为核心的权利文化是这一转变的精神条件[9]4。任剑涛考察新中国以来的政治行为模式的变化,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政治行为模式是权力政治模式,而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变化,尤其是中国政治存在形态与政治认知方式的变化,则是从权力政治向权利政治的变迁,是“权利政治的兴起”[13]21。徐双敏通过回顾与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得出的结论是武装斗争建立的政权最初形式只能是权力政治,从这种初期的权力政治过渡到权利政治需要一个发展历程,而这一历程是开始逐步实现[14]54。因此,上述学者同样以“权利政治”之范式解构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发展实践,而倡导一种以权利为本位的政治文明发展模式。
四、作为一种范式的“权利政治”
通过上述对“权利政治”在西方政治哲学、国际政治学以及法政治学语境下的语义及其内涵的阐明,人们就会发现,虽然都在运用同一个概念术语,但其学术使命与批判或被批判的对象几乎完全不同:西方政治哲学的“权利政治”是社群主义者所批判自由主义观的对象,而国际政治学的“权利政治”是批判现实国际政治主义的武器,中国国内的法政治学的“权利政治”则是批判古代传统政治或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治政治的武器。如果从具体的学术实践与历史实践的形态分析,那么,各自的“权利政治”对应于不同的面向:公益政治、霸权政治或强权政治、权力政治或专制政治、人治政治等等。然而,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所使用的分析工具即概念范式却是共同的,这就是“权利政治”。可见,“权利政治”作为一种分析问题的范式理论,获得了不同学术领域学者的共同承认。
“权利政治”作为一种以保障人的权利为标签的新时代范式的提出,解决了种种之理论知识性描述难题,正如“现代化”范式解决了对现代社会之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资本化、民主化、法治化等难以涵盖其全部特征之描述难题一样。范式理论的创始者托马斯•库恩说:“范式一经改变,世界本身随之改变。”[15]110“权利政治”作为一种理论范式之深刻意蕴即在于: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政治学、法学的研究应当集体性地、自觉地由“权力政治”范式转换为“权利政治”范式上来,只有且惟有如此,才能解释自国家产生以来围绕权力与权利这对根本矛盾范畴所带来的种种政治法律问题。根据库恩对“范式”的界定,能够成为“范式”的命题必须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了解决各种问题的开放性空间。”[15]10“权利政治”作为理论范式完全合乎库恩的“范式”命题。首先,“权利政治”范式无论是社群主义者在批判新自由主义者的“权利优越于善”的观点提出来的,还是国际政治学者用来批判现实国际政治主义的霸权政治或强权政治,以及中国法政治学者借此批判传统的人治或权力政治,总能够吸引着一批坚定的范式拥护者,使他们脱离传统的权力本位的政治范式,各个领域的学者以此作为反思与批判的武器,对古代传统的国家权力观与政治实践进行颠覆性的批判,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权利政治”的新时代范式。可以肯定地说,“权利政治”这一新范式一经提出并为学术共同体所接受,就使学者们对传统社会以及中国自身的政治法律现实问题揭示得更为深刻与彻底,而缺乏这样的范式,将对传统社会的政治实践以及凡是与权力相关的政治问题无法说清楚。黄文艺在考察了不同领域的“权利政治”术语之后,还是承认“权利政治是一个不可替代的重要范畴,它确实描述了一些重要的政治法律现象”[1]80。其次,“权利政治”范式具有一种开放性的无限空间,凡是以后的实践者一旦重新组成一个学术团体,并在“权利政治”范式下思考政治法律现象与现实问题,那么一切现代政治法律问题皆可归结为“权利政治”问题。“权利政治”范式理论能够引导学者们集体性地自觉参与到现代政治法律现实问题的思考上来,使他们带有主体性权利意识,在反思与批判“权力政治”的基础上关注人的权利与公民权利问题。所以,“权利政治”范式之最重要价值在于它所具有的向未来的开放性以及对由此开放出来的问题进行反思和批判。中国的现实是我们思考的出发点和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只有对中国现实问题进行思考,才能建构“权利本位”的政治文明,从而才可能为我们这个权利时代提供更多的思考,才能使个人有尊严地活着。范式的转变就会使研究者对其所研究的对象的看法改变了,正如库恩所说的,“在革命之后,科学家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中国法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也同样使研究者所面对的必将是一个崭新的权利世界。
参考文献:
[1]黄文艺.权利政治的语义分析[J].云南大学学报,2010,(3).
[2]俞可平.权力政治与公益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俞可平.政治与政治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31-32.
[4]梁守德.国际政治中的权利政治与中国国际政治学的建设[J].国际政治研究,2000,(4):1,3,6,8.
[5]梁守德.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的探索[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2):18-19.
[6]秦亚青.从权力政治走向权利政治[J].国际政治研究,2004,(5):1.
[7]夏安凌,封帅.论国际政治中的权利政治[J].教学与研究,2008,(7):34,37.
[8]范进学.权利政治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9]刘江.论“权力”政治向“权利”政治的转变[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4,(9).
[10]胡水君.法律的政治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1]胡水君.权利政治的流变——关于权利与国家理论的一个思想史考察[J].清华法学,2007,(3):29.
[12]黄叶微.从权利政治观浅析洛克的自由主义思想[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2007,(4):96.
[13]任剑涛.权利政治的兴起[J].民主与科学,2008,(4).
[14]徐双敏.从权力政治到权利政治: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演进轨迹[J].重庆社会科学,2010 ,(11).
[15]KUHN T S.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
Semantic Analysis and Its Paradigm of “Politics of Rights”
FAN Jin-xue
(KoGuan Law Schoo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China)
Key words: politics of rights;politics of public interest;politics of power
[责任编辑:张莲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