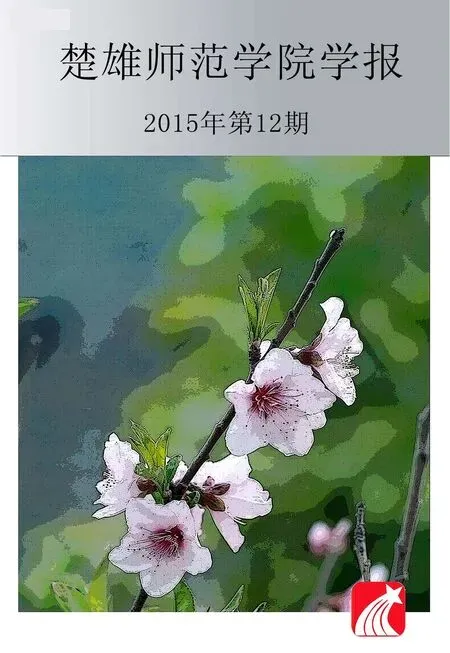苦难时期的心灵慰藉——从《一只绣花鞋》看“文革”期间民间文学的审美取向
布小继,李 钧
(红河学院人文学院,云南 蒙自661199)
“文化大革命”给我国带来了无法估算的物质损失,也使我国的文艺事业遭遇了一次空前的劫难。这一时期的中国内地文学(以下简称“文革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对于这一时期的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的探讨和研究是值得继续深入下去的。“文革文学”的成分比较复杂, “其主流无疑是被林彪、江青之流所利用或炮制的、在极“左”政治专制之下沦为奴婢地位而失去本性的‘样板戏’文学,它见于当时公开出版的书刊;其非主流则包括诸如手抄本小说、北岛、郭小川的诗作等保持一定独立性的地下文学。”“在一些当代文学教科书中,大致以此论为基调。这是相当偏颇的,至少是论者忽略了民间文学存在的事实,或者有意无意地把民间文学排斥在文学之外,没有看到民间文学在全部文学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与作用。”[1]民间文学显然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源头上来看,中国文学就是发端于民间文学的,《诗经》中的“风”就是各个国家流传于民间的诗歌谣曲汇集。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就简单地将“文革”期间的民间文学作为文学发展中的主流,从而贬低了一些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这虽然是有意识地要改变传统中存在的轻视民间文学的文学史观,但是,过于夸大民间文学的艺术价值、思想意义,也会使论断失去其科学性。
“文革”期间流传的手抄本多为民间口头创作,后经无数人传诵、加工,最终被整理记录下来的,是整个“文革文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应以独特的视角给予理解和探讨。本文以《一只绣花鞋》为例,就民间文学在“文革”期间的贡献作一些探析。
一、《一只绣花鞋》所表征的精神渴求
《一只绣花鞋》(又名《梅花党》)的作者张宝瑞是中国悬疑小说的“开山鼻祖”, “文革”期间手抄本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在“文革”期间流传的300 多部手抄本文学作品中有20 多部(种)出自张宝瑞之手。 《一只绣花鞋》是他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小说由《梅花党系列故事》、《绿色的尸体》、《武汉长江大桥的孕妇》、 《火葬场的秘密》等故事组成。讲述的是国民党政府在崩溃前夕,曾秘密成立梅花党,旨在打入共产党内部伺机而起,共产党特工龙飞与梅花党斗智斗勇,几经波折最终获得胜利的故事。
当时,《一只绣花鞋》故事的产生和繁衍,十几种手抄本的辗转流传,除故事本身引人入胜外,更与“文革”期间的林彪、 “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文坛的萧条、寂寞以及小说自身所带来的特殊价值有关。极“左”政治专制与极“左”文化专制使不少革命先辈与作家蒙受了不白之冤,各类歌颂社会与革命历史的优秀之作都无一例外地被冠以“毒草”的头衔,传统文化中的主体意向性思维对于客体认识的忽视,一经与政治狂热结合,便导致了“文革文学”严重偏离了现实主义的轨道,从而走向夜郎自大式的抒情主体极度膨胀的道路。 “文革”时期,文艺领域各方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打击,各类文艺组织及其活动被全面终止,许多权威性的刊物也被迫停刊,造成文艺界氛围低落、阴冷的局面。在一连串的批判运动后,新中国的文艺传统成了一片空白,文学创作也恰似一张白纸,没有任何生机和色彩。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精神生活的匮乏、心灵的空虚充斥着人生,个人生活变得无比乏味,反映到生产中就表现为消极怠工、无精打采。张宝瑞在谈及《一只绣花鞋》的诞生时提到:“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调动大家干活儿的积极性,特别是上夜班的时候大家都是爱犯困儿,于是,我就给大家讲故事……就这样,讲故事提起大家的精神头。我这一讲就是十年。由于大家都爱听故事,劳动的积极性也被带动起来了,所以我所在的生产班组几乎年年都是厂里的班组生产冠军,而我因为所在的班组生产上的业绩也‘平步青云’,还当了车间团总支副书记,也是每年的先进生产者。可见在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时代里,文学对人们产生的巨大影响。”[2](P6)这也就更好地反映出了我国人民在动乱岁月中特有的思维机制与创作表现机制。也可以说民间文学的产生正好迎合了特殊历史时期人们的精神渴求,而这一渴求也时时刻刻反映在作品当中。
“天上的流星偶尔拖着长长的尾巴,无声无息地从夜空坠落;迷人的月亮,拥抱着城市的大海,温柔,慈祥;夜风像个俏皮的姑娘,摇碎了天上的月光,摇碎了天上的繁星。在灯光和月光的映照下,大海撒出一把把闪光的碎银,亮得刺眼。几只海鸥仿佛并不困倦,追逐着海面的碎银,偶尔掀起的浪花微笑着嘲弄着它们的双翼……”[3](P1)《一只绣花鞋》开头部分的描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高尔基的《海燕》,它通过对暴风雨到来之前的大海景象的描绘和对海燕战斗英姿的刻画,深刻反映了1905 年俄国革命前急剧发展的革命形势,热情洋溢地歌颂了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先驱者们坚强无畏的战斗精神,预言沙皇的黑暗统治必将崩溃,号召广大劳动人们积极行动起来,迎接伟大的革命斗争。其中的“海燕”意象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两篇作品虽使用了不同的意象,但其手法和所隐喻的内涵却是一致的。在这里也可以看到:“文革”时期的文学正远离文学真实,一步步地走向衰落,正“无声无息地从夜空坠落”。一代知识分子在专制政治的高压之下,在那个失去理性的年代,虽身处困境、深受迫害,但仍然顽强地求生存,释放出生命的火光,闪射着正义与正气的锋芒,是“五四”以来知识分子抗争精神与现实战斗传统在特定时期内的恢复和张扬。文中关于“海鸥”的部分,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景物描写,必须和作家当时的处境以及“文革”的大背景联系起来,才能真正理解它的暗示性与针对性。
小说结尾表现出的是一种人们“不能忍受文化沙漠中长途跋涉的饥渴”的反抗意识的觉醒。比如对白薇觉醒的描述,将她比喻为一朵金色的梅花就是一个悖论。这是一个由“狼”到“人”的转变,是一种“狼性”与“人性”的抗争,一种不甘于被禁锢的反抗意识的表现。
在“文革”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三突出”、“三结合”样板式的规范化、原则化的限定之下,描写正面形象只能用诸如“高大英俊”、“英勇”、“勤恳”、“无私”等特定的政治语汇。在一个动辄“因言获罪”的年代里,爱情、亲情、友情都被“政治”牢牢桎梏,一切个人的需求都被打上了“资本主义”的标签,人们的不满与个人欲望的诉求间接地促进了口头文学创作的产生,“民间传奇”也因此得以广泛流传,这是寻求叙事安全的需要。而文本肌理深处对人性、个性的追求,对情感、欲望的表达,才是叙事者内心真正的诉求。
小说中白薇与柯山的一段爱情故事,表面上看显得有些突兀,不可思议,柯山并非什么重要人物,作为特务的白薇为什么会嫁给他?我们可以认为这是白薇为了更好地隐藏自己的身份,但更为重要的是,白薇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女人,对自由爱情、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是其最原始也是最真实的一种心理需求。在与柯山的相处过程中,在柯山无微不至的关怀中,白薇真切地体会到了这种幸福,她的幸福感是真实的,发自内心的。在看似平凡细小的生活本真状态的爱恋里,没有虚浮,没有争斗,平和安宁,使人忧愁皆忘。这种平和,和当时喧哗浮躁的时代气息形成了鲜明对照,恰恰代表了人们不甘禁锢的思想和对人性、个性、情感的渴求与反思。有人说,爱情是小说永恒的主题,实际上表现人性才是永恒的主题。作为“敌特分子”的白薇在这里,一切的“阴险”、“狡诈”、“凶狠”都与之无关,她就是一个“柔弱”的、内心充满幸福的平凡女子。这种美好、幸福的生活也是当时人们普遍向往的,它满足了人们渴求自由、渴求情感的心理,深深地滋润了人们枯竭、干涸的心灵。这是自由思想与专制政治的激烈碰撞,是对社会现实与生活本真的尖锐拷问,是对人性的深刻挖掘。虽然白薇最终还是离开了柯山,回归到自己的“特务”身份,这既是一种叙事需要,又是一种反思,人们不希望“她”就此一直待下去,不希望故事就此结束, “枯竭”、“空虚”的心灵需要更进一步的滋润。同时,这也是时代的必须,白薇作为台湾当局的一个接受过特别训练的特务,肩负的“责任”与“使命”使她不得不作出这样一个抉择。故事将她内心的矛盾充分展示出来,使这一人物血肉丰满,人性的主题也表现得更加完美。
再看小说中“白蔷”、 “白薇”、 “白蕾”和“黄妃”等特务活动的失败,尤其是王牌特务“3 号”以死亡收场,具有极强的暗示性与预见性,这体现出了该时期文艺的局限性。“文学从属于政治”是当时的风气,民间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冲破了这种局限,但不可避免地受到它的影响,对党的肯定与赞颂,所谓“邪不胜正”的思想始终贯穿于小说之中。但基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一表现也反映出了人们思想上的觉醒。
二、 “文革”民间文学:表现特殊时代人民群众的审美取向
抛开现当代所有流行的文学批评理论,让文学回归到其本真状态来看,“文革”时期的民间文学,在“性”、“爱”、“自由”等方面无不体现出特殊政治背景下人民群众的审美取向。
诸如《于飞三下南京》、 《许世友三进故宫》、《第十三张美人皮》、《梅花党》、《一张发黄的报纸》、 《神秘的教堂》、 《夜半歌声》等,其产生都得益于特殊的政治背景:“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4]由此可见,“文革”的核心内涵之一即是阶级斗争。这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政治运动,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大灾难,中国文学也因此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打击。疯狂的阶级斗争打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除却精神上的空虚与恐惧,物资上的匮乏外,作为人本性的“性”、 “爱”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酷的禁锢。“文革”前后的那段岁月,绝对是中国历史上“性禁锢”最严厉的时期。
“文革”期间,民间文学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了人们心灵的慰藉,使人们枯竭的灵魂得以滋润,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人们的审美取向。“文革”期间,及时、高效、普及的大众文艺以空前的规模和声势席卷全国,把文艺推到了“为政治服务的极端”。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虽然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桎梏,但同时也鲜明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与生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民间文学以其独特的创作方式和传播方式对“文革”期间的文学格局形成了必要的补充,一定程度上滋润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田,丰富着他们的审美天地。同样是在塑造英雄人物,但民间文学中的英雄人物不再是仅仅局限于“英武”、 “伟岸”、“机智”,也不再是“永远正确,不犯错误”,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感需求,会感情冲动、会犯错误的形象。比如龙飞、肖克等,人们给予了这些英雄人物更多的人文关怀,非对即错、非好即坏、非黑即白的“二元化”理论在这里已渐渐被消解,人们的审美取向也逐渐趋于多元。
实际上,以《一只绣花鞋》、《少女的心》等手抄本为代表的“文革”民间文学(地下文学)审美取向的悄然位移绝非是一时一地的产物,而是文学合乎逻辑的演化结果。
“文革”之前及“文革”前期的“文化专制主义”、“文化暴行”和“反启蒙”及所谓的“文学纯化”,都是“五四”以来文学一路“左”倾乃至“极化”的必然。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否定势必意味着中国文学在常规发展途径上自我封闭起来,对“古典文学”传统的否定又意味着要再另辟蹊径。但1950 年代以“新民歌运动”为代表的文学实践,证明了当代文学无法纯粹依靠“民间文学”来获得充足的营养补给,以实现内在驱动和自身的合理发展,在靠强力意志推行文学政策的行动受阻后,以更加激烈的方式否定文学传统、抹杀文学规律并试图重新建构文学版图的系列努力都只能是徒劳无功,贯彻执行上级意志的集体化创作,其投入与产出、效果远远无法对等,它所带来的后果却是极其严重的,即人为地导致了文学发展的断层和文化的荒漠化。
同时,以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所代表的,得到官方认可和力挺的作家作品无法担负起拯救文学衰落和荒芜下去的重任,在一段时期内反而成为了创作者的精神负担。随着时势的变化,文学政策和控制的松弛,年轻一代和有识之士的崛起,各种文化运动的“波浪效应”立即显现,即在控制严密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民间文学的发展越发趋于隐蔽形态,一旦这种严密性得到缓解,它们就会浮出地表,呈现为公开或半公开的状态。受到压抑的情感、诉求、愿望、理想就借助这些通俗易懂,为普通人喜闻乐见的作品得到传播,并迅速演变为一种文学现象。
鉴于民间文学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对正常生活状态下的人情、人性、人心进行呼唤和回应等特点,其就不可避免地与普通人的审美取向挂起钩来,减少阶级斗争及意识形态化,呼唤人间真情的回归,抛弃理念色彩浓烈的描述方式和非黑即白的创作逻辑,舍弃好大喜功的史诗性叙事以及单线条、粗纤维和疏放的形象处理方式,转而结合、适应民众的需要,从“红色”、“革命”、“理想”中摆脱出来,获得超越现状的契机——民众被无休止的运动与革命弄得疲惫不堪,民众的精神信仰从无条件的崇拜中、从各种革命幻象所堆砌的沙塔中被拯救出来,从集体无意识回复到对自身、个性的关注。显然,这种转向毫无疑问是小心翼翼的、彷徨四顾的,即便描写爱情,也无法即刻就显得从容和淡定,只有获得适宜的条件和环境,才会有一展身手的机会。换句话说, “文革”后期的民间文学作品本身具有了摆脱严密控制的可能,其文本内部张力逐步加大,是适应了社会情势发展的结果,也是对民众厌恶运动、斗争、革命,希望回复到正常生活轨道的回应,顺应了民众审美取向从特定时期的“高大上”向“平民化”和日常化的转变,又与之形成有效的互动,引领民众的审美取向,为当代文学进入新时期,形成第二次启蒙营造出了合适的氛围,充当了新时期文学春天即将到来的迎春花和报春鸟。
由此可见,民间文学在“文革”轰轰烈烈的主流文学之外,为人们开辟了另一番精神的天地,支撑着、滋润着也鼓舞着焦躁、空虚、绝望的人们。它与该时期人民群众的审美价值取向形成互动,是对文化枯竭环境中心灵与精神的一种重构。
[1]高有鹏. 关于“文革”时期的民间文学问题[J]. 河南大学学报,1999,(2).
[2]张宝瑞. 宝瑞真言[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
[3]张宝瑞. 一只绣花鞋[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五一六通知[N]. 人民日报,1966 -05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