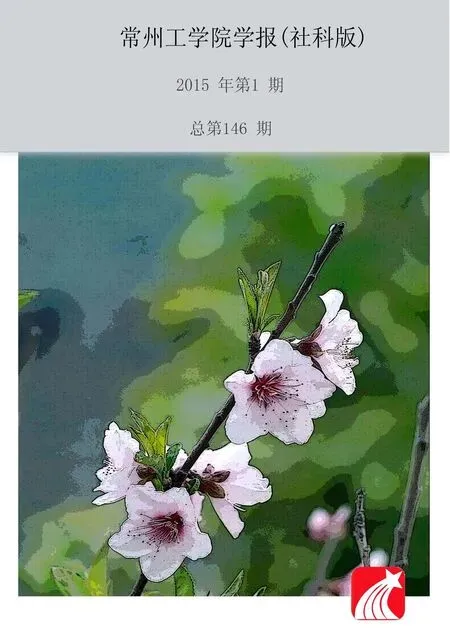论电视媒体价值取向与常州文化传播话语体系的建构
方忠平
(常州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2)
拥有2500多年历史文化积淀的常州,成就了令人瞩目的近现代常州文化奇观:从影响中国文坛的常州词派、常州画派到名闻遐迩的孟河医派;从历史人物季子的人格力量、齐梁艺术的洒脱到青果名家大师云集,常州文化传播伴随着运河文化的兴盛衰落进入了重构城市形象的数字媒体传播时代。数字新媒介的兴起和普及导致媒介的传播模式已经从单向传播向交互传播转变,从平面传播向立体化传播转变,这种转变使媒介文化与地域文化在阐释与被阐释的合作关系中建立了当代的文化景观,即当代社会以媒介化生存为特征,城市形象以及城市文化已经无法脱离媒介的塑造和重构,甚至,借助于传媒的电子特性的影响,城市文化很容易按照传媒图式被构造、表述和感知[1]。常州的文化传播自然不能游离于媒介传播的变革之外,在这场现实的非现实化的美学重构的文化历程中,传媒布局、媒体品格、传媒人才素养,乃至话语生态、受众面貌相互交织共同构筑复杂的文化传播体系。电视媒体的价值取向对于建构常州文化传播话语体系发挥着积极而又重大的作用。
一、传承与沟通:新媒体时代电视媒体的价值取向
电视媒介的传播与发展是人类工业化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产物,电视传播以真实还原世界为己任,创造了大众传播的媒介平台。对于大众来说,电视不仅给予了人们信息资源共享的权利,更从深层意义上影响到当代文明的构筑。与其他媒介不同,电视符号的解读并不需要专门的训练,因为电视符号由画面和声音构成,它们直接诉诸人的感官,只要是耳目健全的人,接受电视节目传播的信息内容可以说门槛最低。没有任何一种媒介,能像电视这样走进人们的家居空间,填充人们的休闲时光。在文化学者菲斯克看来,电视在人们的生活中充当了现代的吟咏诗人的角色。电视的吟咏功能其实质就是将抽象具体化,将意义影像化,使文化含义在屏幕上被表演出来,并使之适合更多的人参与,使之更平民化、通俗化和大众化。这一过程的实现必须伴随着趣味性和游戏性去实现。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当代电视更以其高分辨率和高清晰度给人们带来视觉震撼体验,从电视的技术手段看,电视提供的阅读符号不仅真实感是其他艺术门类所无法比拟的,电视造型的动态性、电视时空的即时性以及电视叙事的悬念性更是打破了新闻传播的传统定义。从电视的表现内容看,电视是以反映社会生活中人与事为主,无论是虚构类的电视剧、综艺节目,或是非虚构类的新闻、专题、纪录片节目,都离不开人的生活。因此当人和人的生活成为电视的吟咏对象时,电视的吟咏行为必定是在传递文化的整合以及社会共识的塑造。实际上,吟咏是一种故事的讲述行为,它与人类的求知欲望和目的行为紧密关联,不仅如此,吟咏还是一种语言游戏,在追求时间的流程和人物场次秩序的更迭中,吟咏被赋予了程序性。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休闲时间的增加,在人们的生活中,电视以这种文化吟咏特性与人们结成了无法剥离的审美关系。这种审美关系起始于画面和声音的蒙太奇组接,通过对细节直观的呈现,进而产生美感。电视的吟咏功能和美学特质从当代所谓的“后工业”社会的视角来看,电视媒介分明扮演了一个文化变革的角色,它推动了整个社会文化经历一场革命性变化:把握世界的方式——从以语言为中心转向以视觉为中心。电视似乎将社会的这种文化变革力量完全地凸显出来,并使世人认识到世界的图景都会在电视中逐一呈现。
电视图像化的电子媒介特性,可以说超越了所有媒介,电视不仅介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认识、感官体验,在某种程度上还建立了我们与外界的关系。人们对世界的把握,从以往的以文字为主导的方式改变为以直观的图像视觉方式为主导方式了。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指出:世界图景并非指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构想和把握为图像,该变化并非是中世纪的世界图景演变为现代的世界图景,毋宁说在根本上而言,世界本身变成了图像[2]。图像和视像的阅读和观赏离不开人们的视觉,毫无疑问,视觉是人的全面发展在感性上的先导因素。电子传媒为视觉成为主要的审美方式和文化模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与支撑。从审美观照的角度分析,电视给人们呈现的视觉图像,明显区别于传统艺术,使审美的含义和审美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变异和迁移。对于抽象和静态的以文字为代表的传媒符号阅读而采取的审美方式,中国古代美学将其概括为“澄怀味象”“心听”“神遇”的过程,其审美理想表现为:强调审美作为人类特有的精神活动,必须是怡情养性,净化心灵,超越世俗的功利色彩,实现主体感官愉悦到心灵自由的升华和超越。这种审美的超越性,表达了审美的至高境界,即探寻主体在审美中如何摆脱对象世界的有限性,以期在精神中获得最高的自由。电视传播媒介形式的出现,不仅造就了物质生产审美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人类生活图景,从审美实践上来说更是实现了客体性美学和主体性美学之争向主体间性美学的历史转向,其意义在于凸显了在当代文化消费背景上的体验式美学,这种体验式美学不仅有别于传统的静思默想的审美方式,更是受制于当代物质消费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牵制性和迷恋化的美学追求。这种体验式美学源自于流动的电视画面提供的零碎的形象以及它的诸多部分组接在一起所依赖的蒙太奇原则。电视作为现代工业的产物,其多种属性的包容性意味着:电视商品的使用价值、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统一,电视获得了其他媒介的文化传播优势,同时也更容易陷入消费逻辑的陷阱。
当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数字媒体的快速普及,使电视媒体不得不面对大众媒介的舆论格局颠覆性的变革和媒介话语环境的显著变化:话语平台从相对单一向多元化发展,互联网、网络论坛与微博等媒介形态与电视共享话语格局;话语主体从少数精英向多数公众延伸,当技术不再成为传播屏障时,多数公众都能够参与到由少数精英操控的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的过程中来;话语空间从相对封闭向更为开放转变,开放自由的PC网络和随时随地的移动网络通过声、画、信息、表情互动、即时刷新使得大众传播从单向走入了双向传播时代;话语内容从严肃向娱乐漫延,以大众消费欲望置换宏大庄严的叙事主题推动娱乐至死的盛景出现。事实上,网络新媒体的崛起已经造成了传统电视媒体话语优势的淡化。在我国社会转型价值观影响下,价值标准多元化、新旧价值观的矛盾以及消极价值观的影响,直接造成了电视媒介为应对价值标准的区别、价值选择的多元化、价值追求的适用性和价值实现的多途径局面。电视媒体在被动地进行话语形式改革中不自觉地充当了社会消费和娱乐的先锋,运用有限的媒体资源纠缠于生活的琐事和无意义的细节,将商品推销悄然编织进电视媒体的叙事流程,进而导致大量有独立判断能力的受众离去。然而新媒体时代,信息海量和信息传播的迅捷直接导致的信息碎片化和情绪表达失控问题,使人们有可能直接放弃理解全文和语境的动机,进而产生误解和偏见。在这样一个媒介融合的发展进程中,电视媒介必须积极探索与受众的互动、与新媒体的联动,在话语方式上寻求更具开放性的突破而重拾话语权威显得尤其迫切。传播学研究表明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主要功能表现为监督社会、联系社会、传承社会文化和提供娱乐。这其中“联系”意指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事件加以选择、评价和解释,将复杂的世界有序化并将事件意义化,使大众得以了解其重要性。电视媒体的价值取向则在于文化的传承与社会规范的传递,以强化社会整合、沟通共同经验并确保社会价值的联系。电视之所以能够实现“联系”功能,这与电视的媒介传播优势密不可分。
二、议程巧设:电视媒介构筑常州文化传播的个性特色
常州文化传播是常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是常州的历史积淀和当代传媒视角的认知、解读和融合。常州文化传播话语体系是针对常州城市形象、城市性格、城市实力乃至城市意志具象在较为广泛的区域舞台乃至更大范围的综合展现,所形成的常州文化和文明的重要表达系统。常州文化不仅体现了本地域的民情风貌,反映了本地域人们的生存状态,更重要的是,长期形成的历史遗存、文化形态、社会习俗、生产生活方式直接影响了本地域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习惯、社会心理、审美追求等,决定着本地域人们精神和生活的一切规范。大众心目中对一个地域的形象的认知与接受往往来自媒介,而同时媒介自身强大的特质功能也在极大地影响着地域文化的形成。伴随着媒介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个体对于群体的依附也从以往的紧密型变得更加疏离,个人对于世界的理解也变得大相径庭甚至形成偏见和对抗。因此寻求对话、沟通与建构自然已经成为地域文化传播的一种迫切需求!
就电视媒体而言,由于覆盖面更广、受众更多、影响力大、感染力强的特点,与其他媒介相比,电视媒介价值取向往往通过其节目形态的引领和暗示作用构筑地域文化传播的个性和特色。
在常州电视媒体的节目形态中,非虚构类节目自始至终占据了话语传播的重心地位,从地域文化出发,架构话语沟通平台,设置议程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不可回避的是,随着互联网的日益发达,当代自媒体的兴盛,公众的自发性、自由性、参与性直接导致传播的无序,并试图打破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大众传播影响舆论的方式。传统的电视话语方式,以价值评判单向性和传播的线性表达,容易造成媒介意见与公众意见的关联裂隙,电视媒体重构话语体系,只能从受众需求出发,寻求话语创新。常州本地的电视民生新闻或许可以借力微博等平台和新媒体的互动方式,创建受众与受众之间话语沟通的平台,让受众参与到新闻生产的过程中。这一方式对传统媒介话语的传播扩散以及被认同接受,有着较为积极的作用。就非虚构类的节目来说,事件真相的追逐,地域文化现象的深度解读,特别是信息爆炸时代真伪难辨的信息,更需要对信息进行深度阐释,这就要求传统媒体必须具有理性地分辨梳理信息,主动设置议题的能力。常州电视媒体的专题类节目如政法、文化、经济等题材并不只是将社会中发生的事件信息原封不动地传递给受众,而是可以人为地介入,通过巧妙的议题设置,引起公众的注意与思考,形成受众对媒介话语的深刻记忆,甚至影响受众个人态度的形成与改变。电视媒介话语能否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某种程度上要看新闻报道的议题设置是否紧贴受众的社会体验和主观判断,常州文化的历史积淀使广大受众具备一定的思考判断能力,如能突破常规思维,在议题的选择和设置上多作思考,话语力度、传播效果应会更佳。在常州地域文化的报道和传播过程中,将时效性、突发性、未知性结合起来,既能客观反映历史文化积淀,更能够使受众对该地域或者模糊或者清晰的主观印象,通过经验、记忆、媒介、传播以及环境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形成良好的传播效果。这种主观印象或认知往往是由新市民、城市,以及城市内部的组织、管理、教育、制度等动态行为组成,其复杂的文化系统的外在表现构成了非虚构类电视节目的形象传达的潜意识内涵。议程设置原理是大众传播的基本规律,电视栏目中的非虚构类节目的议程设置早已有之,当代电视传播的议程设置的意义更在于其与当代的文化消费背景有关。当代消费的多元化已经形成了消费者的个性差异,所以电视栏目必须充分考虑到各类目标受众的心理和需求,这种个性化的需求趋势强调节目的独特性、非标准化、多样化、分散化,深层原因即在于此。
虚构类节目,如以电视剧为代表的节目形态在文化传播中,巧设议程更能够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利用城市景观和地域文化特色,塑造城市形象,使城市文化传播具象化。当代虚构类电视节目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节目形式和表现手法的创新建立在较为深沉的主题立意上。《爸爸去哪儿》叙事以亲子为主题,《花样爷爷》以人物角色的变化为视角,这些节目选取地域中有标志性的景观或建筑作为拍摄外景地,较好地传播了地域文化的特色和气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近年来电视剧《青果巷》的制作与传播是常州文化传播的重要尝试,将城市形象植入电视剧中,电视剧运用这种创作方式既表现城市文化风貌,同时还打造城市新的文化名片。常州历史悠久,传统的制造业城市要将文化产业引入自己的产业布局中,常州有着独特的优势,常州电视媒体应该可以成为本地影视文化产业的传播平台。
常州文化传播话语体系建构和话语能力的提高,离不开话语环境建设、受众培养、传媒布局、范式转型、队伍建构、地方经济能力的提高等诸多策略。就电视媒体在常州文化传播话语体系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来说,寻求战略主动才会使媒体自身适应数字传播态势的发展。在具体的电视媒体运作中,常州电视媒体,在坚持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意识形态功能的前提下,要以内容生产为核心来影响社会,无论是贴近社区百姓的电视新闻,各种各样的专题、纪实节目,还是虚构类艺术性强的电视剧都不同程度地对当代社会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乃至心理、心态、语言及习俗产生着不可忽略的影响。人们把电视看作是当前世界最具时代价值的影像,乃至视觉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标志并不为过。强调电视媒介的话语战略,只要坚持媒体的原创性,结合电视媒体的传播特点,坚守电视媒体的价值取向,就不会跟风和机械复制,从而有效地推动常州文化的建设和传播,在构筑常州文化传播的大平台中发挥引领和支点的作用。
[1] 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M].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97.
[2] 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M]//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