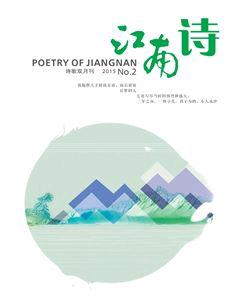冬夜读诗(外十三首)
◎韩文戈 Han Wenge
冬夜读诗(外十三首)
◎韩文戈 Han Wenge
黄昏里,我看到他们,约翰或者胡安
沿着欧洲抑或美洲的大河逆行
温驯的、野蛮的河水,逆行成一条条支流
他们来到渡口,一百年前的黑色渡船,晚霞
连绵雨季中的木板桥
农场上空的月亮,草原云朵里的鹰隼
他们在岸边写下诗句:关于地球与谷物的重量,自我
的重量
如今,约翰或者胡安早已死去
世界却在我的眼里随落日而幽暗
钟楼上的巨钟还在匀速行走
有时我想,努力有什么用?诗又有什么用
甚至还要写到永恒
而更深的夜里,我会翻开大唐
或者南北宋
那时,雪在我的窗外寂然飞落
黑色的树枝呈现白色
布衣诗人尾随他们驮着书籍的驴子,踩碎落叶
沿山溪而行,战乱在身后逼近
他们不得不深山访友,与鹤为伴
有一年,杜甫来到幕府的井边
一边感慨梧桐叶的寒意,一边想着十年的流亡
中天月色犹如飘渺的家书
他说鸟儿只得暂栖一枝。而秋风吹过宋代的原野
柳永的眼里,天幕正从四方垂下
长安古道上马行迟迟,少年好友已零落无几
此时恰是深夜
我正与一万公里之外或一千年前的诗人聊天
他们活着时,没人能想到
会有一个姓韩的人在遥远的雪中
倾听他们的咳嗽,心跳,像听我自己的
在我们各自活着时,一个个小日子琐碎又具体
充满悲欢,特别像上帝发放的年终奖
没人看得到,但没谁不充盈
开花的地方
我坐在一万年前开花的地方
今天,那里又开了一朵花。
一万年前跑过去的松鼠,已化成了石头
安静地等待松子落下。
我的周围,漫山摇晃的黄栌树,山间翻涌的风
停息在峰巅上的云朵
我抖动着身上的尘土,它们缓慢落下
一万年也是这样,缓慢落下
尘土托举着人世
一万年托举着那朵尘世的花。
种 子
爸爸走了以后,整个人世
我已如孤儿,过去的旧日子也一个挨着一个走远了
当我回到老宅子,收拾剩余的东西
看到在厢房,父母用旧报纸和大小葫芦
包裹、盛放的种子
那是芸豆,烟草,谷子和高粱
看起来,它们被藏了很多年
想当初,他们一定像护佑自己的孩子
珍藏这些子实
在他们眼里,种子不亚于另一种血脉
薪火传承,大地一派生机
我曾把这样一个情景写进过我的诗:
在遥远的春天,幼小的我被放进
爸爸那副担子的前框
而后框里,他装满了种子、农家肥
以及给我预备的水壶、零食
妈妈跟在爸爸的身后,一只母山羊
跟在妈妈的后边,它的奶汁喂养着我
这就是当年我们家的写照
直到我变老,直到我们那代人一同变老
太阳向西移去,黄昏渐渐升起
不绝的种子依旧深藏人世
牛粪上的花
我走在荒凉的山野
看到一棵孤零零的苹果树
正在四月的微风里开花
那些年,当它还是株幼苗
我就遇到过它
它和我差不多一般大
在无人光顾的山谷
我也曾无意看到过一棵甜瓜
它顺着敞开的山地,密集的草丛
递送枝蔓与触须
那棵苹果树、那棵甜瓜秧
都是从牛马的排泄物里长出的植物
牛马粪便里的种子
经由咀嚼,反刍,轮回,重新发芽
它们与深谭里的莲籽一样
从黑暗重新跑在阳光下
我想起,我还曾在久远的黄昏
看到过一个人
他出生在马槽和预言里
他的另一些名字都与拯救有关
我所读到的诗
我所读到的绝大部分的诗
无论它是用泥巴与草捏成,还是用石头筑造
都不过在俢一条通往三段论的路
它们终结于某个结论:形而上的高蹈
不同的,是那些路的宽窄,曲直
是穿越的地界和季节,这使我厌倦
我想写出与此不同的诗,它没有豹尾,没有洞见
就像我们所处的原初世界
植物都没有目的,自生自灭。动物只有本能
但没有哲学。河流只是跟着海拔在下降
它翻山越岭,澄澈或浑浊
我也一样,充满偶然,打发游戏的时光
仅只是宇宙中一个细微的事件,此外,我还写诗
发 光
我们发光,是因为万物把我们照亮
比如生下一百天,陌生的养父母就收留了我
给我内心储备了足够的能量
自此,一生,我都会在贵人中间与时光为伴
一些人老了,一些事远离了我
另一些人、事又来到我面前
他们发光,我们发光,万物在身边歌唱
遥远的星星呵护着我,像死去多年的亲人
它们垂下了天鹅绒的翅膀
山中小路
我正走在多年前走过的山中小路上
它领着我,翻越着往事的山谷
此刻我看不到另外的人,也看不到一只鸟
只有密林深里的鸟叫声,像往昔的回忆
这些隐秘的鸟鸣,仿佛多年前的人们
在山中交谈,那敞开的山谷包容着我的前世
在我之前,谁能说清有多少人像我一样
也走过这条路,多少鸟曾在这片密林里出没
避 风
山中突然起了风,我走进山阴处的松树林
我、树林、山脉都在风中摇晃
在我不远的地方,有一棵树一动不动
它的下边,灌木丛也一动不动,树上的松鼠一动不动
整个树林都在摇晃,我也在摇晃
唯独那棵松树不动,树下的杂草,树上的松果都不动
事物总有意外,人总有幸存:
当时间从所有人的头颅撤走,总有人不死
山下避风的人看不到山中的我,也看不到我避风的树林
我们都在摇晃,但总有一棵树却纹丝不动
大风过处,所有事物都在顺风弯腰,我也是
但那棵树却挺立着,像黑暗笼罩时,总有人会在体内
点起一盏灯
给 你
感谢天地生我,容我,宠我,最后又收回我
让我闻一遭树木的香味,中药的苦味
听吧,溪谷在簌簌地响着,季节在无声地更替
让我看到了光照在女子的脸上
看到林中空地,野花静美地开放。
树下的暗影里,羊在吃草
十二月的雪也会落在枯枝上。
让我结识了那么多好人、坏人和亲人
好人得到了我的祝福,坏人得到了我的谅解
亲人受到了我的伤害,却给予我刻骨的爱。
让我在人群里与更多的人擦肩而过吧
这样我才得以轻松。
我还暂时拥有了一个古老的姓氏,一张床
一个远处的故乡。
经过漫长的时日
我认识了自己,然后又把自己忘掉。
那么多小兽围在我身边跑动
那么多庄稼围在小兽的身边被雨淋湿
那么多河水围在庄稼的四周,在草根下流淌
作为万物之一,我成长,并忧伤着老去
听吧,听最后的灰烬,它的流亡以及回声。
整个下午在林中独坐,俯瞰山下的水脉,乃进入时间的断层
一头白象从林子左边绕过,
给我驮来经卷。
我不仅是一个姓名,更是一个雨浸的地址。
两只凤凰在黄昏落下,
给我衔来火的口信。
我不仅是一片河谷,更是一粒劫后余生的草籽。
当我经过……
我经常自恋地写下:当我经过……
当我经过,空气分开了一小会,马上又复合。
地下的水没有改变流向,黑或许更黑。
身边的树安静生长,楼里的灯光照出了人影。
当我经过,就像我没有经过
没有什么发生变化,世界波澜不惊。
风慢慢移动
风慢慢移动,把向阳的一面移进阴影
把河流从山前移动到从前,把一个孩子移动到暮年
把所见和喧嚣移进无和空
把人世慢慢移动,慢慢移到树下的黄昏
风继续慢慢移动,把灰烬移进初现的星星
把双手握住的羽毛移动给凤凰
把土里的秘密移进阳光,把我像一只钟移回往事
把地球的另一面,咬牙移动到河边的清晨
马 灯
风小了,可以把门廊的马灯灯芯调低些
这样,干草、牲口棚、沉睡的马匹便暗下来
像前天以前的某一天
重新把面纱还给世间诸物
周围的寂静和心跳会更凸显出来,证明没有什么在死去
当风大起来以后,一定要把树上的马灯调到最亮
让光束穿透风,犹如大起来的雪片压弯枝条
借着光亮,有人在风中的村庄走动
他踢翻碎瓦片,大风踢翻石头,它说:沙子,纸,名字
他能够看到每一个失踪了的人
日常朴素的事物
春天地气上升,乡亲们早早擦亮了农具
刨开积攒一冬的农家肥,选种、修路
牲畜的食槽里,也添上了精饲料
有时夜里还要加一次黑豆,或棉籽饼
过几天就要开犁了,男人会在阳光下摆正犁铧
让生铁铸造的犁尖划开泥土
种子被紧跟其后的人轻轻藏进垄沟
就这样,稍微打量,一犁下去不偏不倚
我一直纳闷,在辽阔的土地上开犁
从没见过有谁还要去丈量土地
但邻居们从不为此红脸
地桩边界早就在庄稼人心里
这就像那些祖传的道理,无须谁教
也会沉淀在心头,仿佛与生俱来
说真的,我从没弄清怎么分辨自家的地块
这也难怪,每家都有老辈子人埋在土里
他们的骨头成了灰,混合着
一年四季的尘埃,也会把田畴连在一起
天堂的雨淋湿了天下草根,小兽在大地上跑来跑去
夏天的草,冬天的雪
都知道今年长在谁家,明年落在谁的田里
他们不用跟着水跑,也知道渠里的水
流多大时辰,就能浇透禾苗
一块块不同姓氏的泥土连成了大地
不同姓氏的命连成了人世
平常的日子里,他们各自分得都很清楚
但当某些大事来临,比如洪水或蝗灾,比如战乱
他们又不分你我,血脉相连
可现在,当我谈论这些
仿佛是在谈论上个世纪的黄昏,遥远,不确定
尽管我仍能在日常朴素的事物上
看到一点点神圣的踪迹
韩文戈,1964年生,现居石家庄。1982年发表第一首诗,1990年出版诗集《吉祥的村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诗集《渐渐远去的夏天》(九州出版社)。近20年来写作了大量诗歌,偶有少量诗作面世。曾获《青年文学》杂志、《诗选刊》杂志、《新诗》杂志年度诗人(作家)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