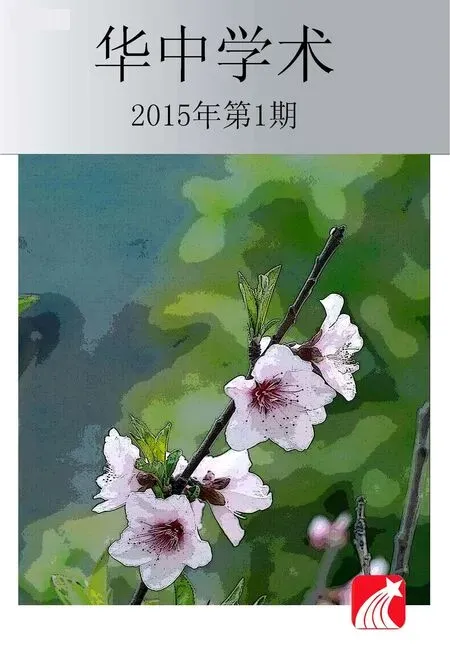“历史是永无休止的争论”——关于九叶诗派研究几个问题的探讨
张岩泉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大部分具有历史因素的批评术语都是追溯式的:济慈并未自称为浪漫主义诗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使用浪漫主义这一批评术语。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理解往昔文化的一种尝试。”[1]把这段话移用到九叶诗派研究上面十分恰切。
1981年7月,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九叶集》。它还有一个副标题“四十年代九人诗选”,选编了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和穆旦九人20世纪40年代的代表诗作共144首[2]。在随后的新书推介和作品评论中,人们有意无意地将《九叶集》视为一部新诗流派选集(甚至是新中国公开出版的第一部新诗流派选集),把辛笛、穆旦等九人看作一个20世纪40年代形成和产生影响,具有现代主义性质的新诗派别,由此出现了“九叶诗派”“九叶诗人”等说法,在新诗研究界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界流传开来。不过,从那时至今,也一直并存着各种质疑乃至反对的声音,涉及九叶诗派历史存在的客观依据、九叶诗派概念称谓的合理范围、九叶诗派的总体性质与内部差异、九叶诗派的成员结构等一系列问题。当然,就像既有的以确认其“有”为前提的九叶诗派研究无意也无法压抑质疑、反对的声音,这些力证其“无”的批评意见的浮现同样并不妨碍人们在一个“约定俗成”的学术语境中继续使用九叶诗派的概念,开展九叶诗派及一切与此相关的研究。
作为文学史、新诗史现象的九叶诗派,确实是在时过境迁之后才获得命名的,具有历史追认的色彩。本文自然是主张九叶诗派的“有派”,但是,为了进一步确立研究立场,划定阐释边界,非常有必要对质询与驳难先行清理,对上述疑问作出解释;而且,本文乐于承认,正是包括质疑与反对在内的严肃认真的学术探讨,共同支撑了九叶诗派的研究成就,也一起促成着九叶诗派研究走向稳健、开阔、深入与坚实。
一、九叶诗派的概念名称
这里牵涉一组问题需要辨析和解答:其一,在20世纪40年代是否出现过一种现代主义风格的诗歌创作,或涌现出一波现代主义诗歌潮流?其二,从这一波诗潮中是否形成了一个现代主义的诗歌流派?其三,对这一诗歌流派,该怎样认识和如何命名?其四,“九叶诗派”的概念是否适当可行?
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承认,在20世纪40年代,从沦陷区到大后方,从北方城市平津到东南都市沪宁,从校园杂志到诗歌专刊,包括具有西南联大背景的师生诗人冯至、卞之琳、穆旦等,以《诗创造》《中国新诗》为主要阵地的上海诗人辛笛、陈敬容等,以及具有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吴兴华、叶汝琏等,还有来自左翼阵营的欧外鸥、胡明树等,此时都出现了面向现代主义的转型与变化,某种程度上在现代主义诗风方面形成了同盟关系与对话关系。对此,研究者近期已经奉献了一批史论兼备的扎实成果[3]。
从人数上说,主张20世纪40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潮中形成了流派的意见占了上风,自然,学术研究依据的是详实的证据与严密的逻辑而非人多势众。少数人坚持不承认流派的存在,也不在正面意义上使用“九叶诗派”或其他替代性名称。这里又分两种情形:研究者的学术结论与当事人的现身说法。张同道在“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时,从未使用“九叶诗派”这一称谓表述南北诗人的聚合,而是将其置于“西南联大诗人群”和“上海诗人群”中分别论析[4]。王毅则从命名的滞后、两个诗人群创作的差异等方面入手,力辨两部分诗人未能形成以“统一性”为前提的诗歌流派[5]。作为王毅导师的陆耀东先生在序中对此作了支持性的发挥,且增加了他们当年未组团结社和在同一刊物共同发表作品过少的质疑[6]。近来,邓招华一方面重新质疑“九叶诗派”的存在,同时又在学院文化背景中阐释西南联大诗人群的特色与贡献[7]。其实,中外文学史上文学流派的形成、形态与命名的由来五花八门,并不强求一律,只要满足了基本条件就可以获得认可。盛唐的边塞诗派和20世纪20年代以鲁迅为先驱的乡土小说流派,就既没有社团组织,也未发表理论宣言,但并不妨碍后人将当时的一些诗人作家归为群体,视为流派。至于流派内部的差异是客观存在,不影响整体面貌的认定,如文学研究会中的王以仁向往郁达夫式的感伤的浪漫主义,创造社的郑伯奇则倾心于文学研究会提倡的现实主义,但我们从总体上认为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分属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流派并无大碍。邓招华的辨析号称“力图从最基本的史料和历史文本入手”,却暴露了不少遗漏错讹[8],质疑也就大打折扣了。其实,他们每每论及西南联大诗人群的现代主义创作,是否也间接地承认当时确实已经形成了一个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呢?叫什么倒在其次。
郑敏在2004年的一次访谈中明确否认“九叶诗派”的存在,她说:“没有什么‘九叶派’,就是因为出了一本《九叶集》,就叫我们‘九叶派’了。当时我们互相几乎都不认识。我们都不同系,不同年级。当时有的倒通过信,但是没有见过面。”[9]郑敏的理由包括:九叶诗派的说法来自《九叶集》的出版(前面已经说明了流派追认的例证与可行),成员间除了通信联系外,彼此互不相识,以此为据来佐证流派不存在的主张。这里需要作两点辨证,一是“九叶诗派”(因为如果要用“九叶诗派”这一专有概念,势必将上海诗人与西南联大诗人包括在内)的成员并非全部出身西南联大,因此并不全部存在同学不同系之类问题,这可能是访谈时回答问题的仓猝所致;而且,成员间的联络不畅也不构成否认流派存在的充足理由。比如,七月诗派的一些成员就只在刊物和丛书中“会聚”,他们中有的人直到第一次文代会或更晚才见面相识。如果对郑敏有关九叶诗派或九叶诗人的言论作一番“考古”,那么可以发现,本次访谈之前她是认可诗派存在,并且也“乐享”诗派存在的光环对自己的正面影响的。她对“诗友”唐祈的作品不仅有惺惺相惜的珍爱与不无溢美的评价[10],唐祈的不幸逝世还触发了她的“唇亡齿寒”之感,创作了名篇《诗人与死》组诗,她在其他诗文中也或直接或间接地肯定过九叶诗派的存在。郑敏作为“九叶”中的长寿者,我们固然要尊重当事人的说辞,但同时也应坚持以事实为依据的分辨。
在承认九叶诗派历史存在的研究者中,在称谓上却分歧颇大。也许是为了避免“九叶”予人过于坐实的数字联想,又或者是意图在某种特定意义上重建历史现场感,人们相继以“新现代派”“四十年代现代诗派”“中国新诗派”等命名他们。蓝棣之先以“四十年代的‘现代诗’派”概念具体分析其创作,后以“九叶派”名义编选他们的作品。“40年代现代诗派”之名承接30年代现代诗派而来,特别注重后来居上的超越性,“新现代诗派”的说法接近于此。洪子诚、刘登翰在当代诗史的撰著中,通过追溯前史,接受了“中国新诗”派的说法。解志熙借用唐湜术语,认为将其称为40年代“现代主义诗潮的‘新生代’”也许最为合适。
后来,《九叶集》入选199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图书大厦联合评选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作家出版社2000年重版诗选时加写了一段按语:
《九叶集》是辛笛(王馨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曹辛之)、郑敏、唐祈、袁可嘉、穆旦(查良铮)等九位诗人的合集。这九位诗人的创作在四十年代的“国统区”诗坛因其较为相近的融合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现代诗歌的语言风格、较为相似的沉静而严肃的诗艺追求、较为一致的反“国统”政治的进步立场、较为集中的诗歌阵地(《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等诗刊物)而被视为现代诗歌史上一个相对成熟的诗歌流派。但在本书出版之前,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原因,这九位诗人的作品一直未得共同结集出书。[11]
也算是代表了一种多数的意见了。既然“九叶诗派”概念流传的时间长,接受的人群多,那么为什么不可以以此来指称那一波现代主义诗潮,概括那一个由上海诗人群、西南联大诗人群联手形成的诗歌流派呢?
二、九叶诗派的流派性质
从文学精神、创作方法尤其是作品本身体现出来的艺术特征角度,分析进而判断文学流派的基本性质,虽然艰难却十分必要。关于九叶诗派的总体面貌是倾向现代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或者九叶诗派中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是彼此融汇还是互相冲突,已有的研究既出现过多种论断,也经历了明显变化。
《诗创造》时期,辛笛、杭约赫等自觉意识到他们是在革命现实主义大众化诗歌之旁(非“之外”“之上”)探求一条诗歌发展新路,也即要容纳现代主义诗歌思想与艺术,用现代主义思想与艺术来改造现实主义诗歌,从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诗歌走向现代主义诗歌,当时的论争与批评也从侧面证明了他们诗歌探索的现代主义性质。《中国新诗》阶段,这一“标新立异”——既是对现实主义诗歌主流的立异,也是对20世纪30年代现代诗派的标新——越发引人瞩目,也招致了更猛烈的抨击。因此,从40年代诗坛的反应和诗派的努力来看,应是十分明确地趋向现代主义。
然而,《九叶集》出版引发的评论热点却不无复杂,耐人寻味。大致说来,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中期,人们包括九叶诗派自己主要是在现实主义诗学范畴中言说,无论立场是褒扬还是贬斥;80年代后期以来,对九叶诗派现代主义的性质认定渐成共识。这一辗转流变,体现的不仅是对一个特定历史对象认识程度的变化,潜藏其间的还有更为重要的时代精神和文学风气的迁移。
对现实主义文学回归的强劲呼唤,使现实主义文学重新掌控8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文坛,现实主义几乎成为“政治正确”的徽章[12]。因此,人们更愿意也更习惯以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来解释当时的文学现象,评论者与当事人都是如此;如果涉及现代主义,则要么是小心翼翼地在剥除精神内核之余谈到对现代诗艺的吸收,要么则对其进行指斥,再或者予以模糊化处理。公刘的《〈九叶集〉的启示》是当时影响较大的关于九叶诗派的评论,他的总体判断是:“在艺术上,作为一个整体考察,他们还应该说是基本上是倾心于现实主义的。”也许他的判断受到了《九叶集》的限制,这一选本现实关怀性作品的比例超出了流派的平均数值,但更可能是捍卫现实主义文学理想所致。公刘是典型的文学内容与形式二分论者,他明确表示“我不怎么喜欢穆旦的诗”,原因是“他的诗太冷”,“过多的内省,过多的理性,消耗了他的诗思”[13]。而强化知性、冷峻抒情,不仅是穆旦的个人风格,也是九叶诗派极力学习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基本趋向。孙光萱、吴欢章所说“从《九叶集》中可以全面认识我国新诗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在四十年代的深化与发展”[14]。木令耆认为九叶诗派当年“过着革命的生活”[15]则在表达政治上的“好意”之时,导致了双重的扭曲与误解:既扭曲和误解了现实主义文学,又扭曲和误解了九叶诗派的现代主义努力。九叶派诗人当时也多作现实主义的回忆与阐说:辛笛1982年说“不论是《诗创造》或《中国新诗》都是在现实主义道路上前进的”[16],唐祈1984年甚至说九叶诗派和七月诗派“共同的倾向是忠诚于时代,忠诚于党和人民,倾向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17],政治保护就做得过了火,简直是把现实主义作为回归诗坛的护身符了[18]。然而,等到他写《唐祈诗选·后记》时则毫不迟疑地说:“生活在40年代那个历史的严峻时期,我必须学会以一个现代人的意识来思考、感受和抒发,把上海那些丑恶、复杂、冷酷、恐怖……放进现代主义的冷峻中。”[19]可见诗人对自己40年代的艺术追求并非懵懂无知,而是出于非关诗学的考量。郑敏曾详细转述唐祈的创作回顾:“从诗的艺术上讲,诗人说他有过青年的抒情阶段,又有过成年的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或者按诗人自己理解就是他的现代主义阶段。后者,他说应当归于40年代英美现代主义大师如奥登、艾略特和法国象征派及奥地利现代主义诗人里尔克对他的启发”;“唐祈多次向他的诗友们说,单纯的模仿现实的狭义现实主义创造观不可能表现出现实的真实性和丰富复杂的内涵,只有以现代主义现实主义为基调,揉进象征主义,才能表现现实的深度”[20]。对比一下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与唐祈的《时间与旗》,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与唐祈的《严肃的时辰》,其影响效应一目了然。袁可嘉的《九叶集·序》与艾青的新诗史论也都是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融合的角度为九叶诗派的流派性质定位的。
如果说九叶诗派中的上海诗人群经过了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迁移,那么,西南联大诗人群则经历了从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换,二者是“逆向接近”,相遇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或“现代主义现实主义”途中。王佐良当年介绍穆旦时说,“每一个有为的中国作家多少总是一个左派”[21],而四十多年后杜运燮回忆正是奥登的“左派”身份让他感觉亲近[22]。这里“左派”的意味最具体的体现便是在孜孜矻矻于诗歌艺术之时对国族灾难与民众疾苦的感同身受,在作现代主义沉思之时不忘向现实突进向时代进言,卞之琳创作《慰劳信集》、冯至创作《十四行集》便是典范。因此,说他们是现代派,但却是20世纪40年代现代主义诗潮的“新生代”,是既俯仰宇宙、凝然沉思又脚踏大地、大声疾呼的现代主义诗派,是慧眼独具的研究者所说的“五四以来某些现代派诗歌在走向现代生活的突进中合理而健康的发展”[23]。
三、九叶诗派的成员结构
九叶诗派的个人写作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于40年代中后期开始“逆向转化”,在1947年到1948年间,完成了从部分集结到南北汇合的过程,标志着流派的正式形成,而流派被命名或得到文学史追认却在1981年《九叶集》出版之后。种种缘由,为梳理九叶诗派的成员结构带来了始料未及的一些困难。当年,他们没有组织社团,公开打出流派旗帜;缺少公认的创作领袖、代表诗人和理论代言人。唐湜执笔《中国新诗》创刊号的《我们呼唤·代序》对现实的感怀远多于对团体艺术追求的标举,不宜作为标准的“流派宣言”看待;袁可嘉在“新诗现代化”总题下写作的系列论文也主要着眼于对当时形成的新诗风的经验总结,以及关于个人诗学趣味的理论说明,并不必然承担催生流派或为流派“鸣锣开道”的职责。此外,流派形成和活动时间的短暂,诗人们的创作个性还在磨合调整,《诗创造》《中国新诗》作者群的纷繁复杂,《九叶集》成书的周折等[24],也使对流派成员的指认更加不易。
当事人之一唐湜对此曾作过一个介于明晰与模糊之间有点“滑头”的说明,他说:“‘九叶’的‘九’并不是什么‘阳九之数’,而是具体的九个人;可话得说回来,当年环绕着《诗创造》,尤其是流派色彩较浓的《中国新诗》的诗人并不只是九个人,年纪大些的前辈诗人就有冯至、卞之琳、方敬、徐迟、金克木几位,年轻一些的也有莫洛、方宇晨、李瑛、杨禾、羊翚几位。特别是方宇晨,他应该是流派风格最浓的第十叶,1948年左右就英译了一本《中国现代诗选》在伦敦出版。”[25]将冯至、卞之琳列入,除了可以为当年不免稚嫩的“九叶”“以壮行色”之外,实在难以从这些师长辈诗人身上发现“诗的新生代”的特质。因此,这是一个既要坚持“九叶”的数字确定性又希图摆脱困扰的补充说明,却是不能自圆其说更不能服众的。辛笛之女王圣思编选了两部很有价值的资料集,其中之一是:《九叶之树常青——“九叶诗人”作品选》。但在只收九叶诗派作品的第一辑外,“考虑到在《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上发表诗歌的不止他们九人,本书第二辑收入另一些诗人的作品,基本按发表的年月排列。这些诗歌入选的标准是:仅以发表在这两份诗刊上的诗歌为限,并以我们认为与‘九叶诗人’诗风有某种接近的诗歌为限。目的在于展现促成‘九叶诗人’流派风格的那一片园地”[26]。这样一来,展示“园地”生态环境的目的或许可以部分达到,但也很可能因此将当年的某种艰难性与复杂性遮蔽了。因为正是与臧克家一派诗友的分歧与争论导致《诗创造》的内部裂变,将臧克家、沈明、林宏等诗人视为“九叶诗人”的外围诗人,对他们也绝非抬举。后出的《“九叶诗人”评论资料选》便纠偏扶正,所有入选材料均不出九人范围,也许这仍不能服人,但起码提供了明晰的边界。游友基、蒋登科等人都在梳理九叶诗派的成员结构时,提出核心成员与外围诗人的概念,将一些诗人列入“外围诗人”予以简要论述;虽然分析时前瞻后顾、小心谨慎,但在目前研究条件下,要做到周延细密怕是很不容易的。
关于这一问题仍然可以探讨下去,并不断提出新的成员谱系,但倘若参考一般文学流派对“共性”的强调,考虑九叶诗派形成过程中的人事因素,本文认为,将“九叶”视为一个概数(至于这一概数的确定人选则暂时将它悬置起来),在讨论诗派时以九人为核心是合理可行的。
卡西尔说:“‘历史’一词在双重意义上被使用着。一方面它意味着过去的事实、事件、行为举止,而在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我们对这些事件的重组与认识。”[27]历史已然发生又不可折返的双重特性使其成为人类社会最奇诡的现象之一,而“历史”“真相”也许就是世界上最歧义缤纷、遭受误解的词语之一了。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九叶诗派综论”【CCNU12HO100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美]彼得·福克纳:《现代主义》,符礼军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89年,第2页。
[2]参见郑敏:《辛之与〈九叶集〉》,载《艺术之子曹辛之——曹辛之(杭约赫)纪念文集》,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年。《九叶集》的出版,九叶诗友多有回忆。
[3]参见解志熙:《摩登与现代——中国现代主义的实存分析》中“暴风雨中的行吟:抗战及40年代新诗潮”叙论部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张松建:《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40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相关章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谢冕等:《百年中国新诗史略——〈中国新诗总系〉导言集》吴晓东执笔的“战争年代的诗艺历程——40年代卷·导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4]参见张同道:《探险的风旗——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
[5]参见王毅:《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1925—1949》,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6]陆耀东:《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1925—1949·序》,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按:陆耀东先生作为优秀的新诗研究者和笔者导师黄曼君先生的同乡兼好友,曾是笔者硕士学位论文评阅人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他在答辩会上和其他私人场合,多次表达过上述立场;但他也从未要求笔者改变思路,而是认为不妨在求同存异中各自继续研究,这是让笔者始终感佩在心的。
[7]邓招华:《“九叶诗派”质疑》,《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09年第6辑;《论西南联大诗人群的学院文化背景》,《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8]其一,不知江天漠、胡双城、林棘丝、杭约赫均为曹辛之笔名,只计算了杭约赫而遗漏了前者;其二,未将“外几首”之“外”统计在内,造成数字失实;其三,唐湜的《华盖·古砚教授》为两首诗,被算作一首;其四,忽略诗论、诗评、译文,其实这些与流派的关系和创作一样重要,即使要力证其“无”,也不该有意无视这些史料。
[9]郑敏、李润霞:《诗与哲学的起点——郑敏访谈》,《新诗评论》2005年第1辑。
[10]郑敏:《唐祈诗选·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
[11]辛迪等著:《九叶集·按语》,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第1页。
[12]此时虽有朦胧诗从地下走向公开,但引起的是激烈的争辩,“归来诗歌”代表了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回归与恢复;在小说领域,“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此起彼伏,风骚各领,基本特质也是现实主义,而“反思小说”中的荒诞变形技巧和意识流手法一时招致了许多非议。这一方面固然是文学思潮演变的惯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坚持现实主义具有某种政治的保护作用。
[13]公刘:《〈九叶集〉的启示》,《花溪》1984年第6~8期。
[14]孙光萱、吴欢章:《〈九叶集〉的思想和艺术》,《上海文学》1982年第7期。
[15]木令耆:《〈八叶集〉序》,《上海文学》1985年第6期。
[16]辛笛:《试谈四十年代上海新诗风貌》,《诗探索》1982年第3辑。
[17]唐祈:《论中国新诗的发展及其传统》,《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
[18]参见唐湜:《随感:关于诗歌的一些问题》,《文学评论》1989年第6期。论文中,唐湜也描述过当时的这一情形:“在国内外当时发表的五六十篇长长短短的评论中,谈论最多的则是诗的政治性的凸出、深化与尖锐、锋利。一时间,我们竟由先前被咒为‘唯美派’一变而为进步战士了!只有少数评论家才谈论到我们九人的艺术个性与意象、语言运用的现代跳跃方法。在当时,先必须‘在政治上站稳’,才能谈到诗艺。”
[19]唐祈:《唐祈诗选·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
[20]郑敏:《唐祈诗选·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
[21]王佐良:《一个中国新诗人》,王圣思编:《“九叶诗人”评论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09页。
[22]杜运燮:《我和英国诗》,《外国文学》1987年第5期。
[23]孙克恒:《试论新诗的传统及其发展》,《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
[24]参见蒋登科:《九叶诗派的合璧艺术》,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1页。按:不过笔者对唐湜先生的回忆尚有疑惑,理由如下:据多人回忆,对《九叶集》的编选出版,曹辛之、袁可嘉最为热心,也出力颇多。而曹辛之当年编辑《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时尚“舍近求远”,让唐湜从杭州来上海帮忙,此时又怎么会将他遗漏呢?唐湜还谈到过《〈九叶集〉·序》定稿是参与了他的意见的。以上分析仅供参考。
[25]唐湜:《九叶在闪光》,《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4期。
[26]王圣思:《九叶之树常青——“九叶诗人”作品选·前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27][德]思内特·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李小兵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