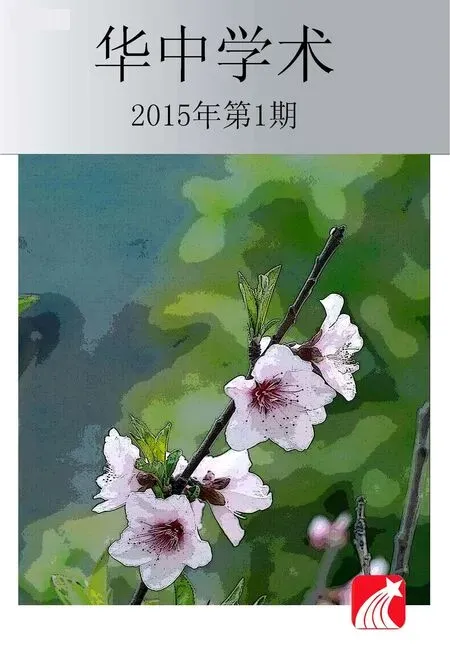关系名词的语义特征和界定标准
杨 红
(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56)
关系名词的语义特征和界定标准
杨红
(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56)
本文考察关系名词的语义特征,指出关系名词的语义特征包括多项性、依存性和推导性。这三个语义特征是辨别、界定关系名词的关键。关系名词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关系项,根据关系项的不同可以分为指示项和参照项,其中指示项是关系名词进行推导的核心因素。文章在语义特征分析的基础上,遵循意义与形式相结合的原则,设定三个鉴别框架,为确认关系名词提供界定标准。
关系名词指示项关系项语义特征界定标准
一、引言
关系名词是表示人或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名词。学界对关系名词一直缺乏统一的、明确的界定,谈到名词分类时,也不把关系名词作为单独的一类。如朱德熙将名词和数量的搭配分为可数名词、不可数名词、集合名词、抽象名词和专有名词[1];王珏对名词做了专题性的研究,将集合名词从语义角度细分为六小类[2]。集合名词中包含着一部分关系名词,如“夫妻、父子”等,但是表示相互关系的“同学、朋友”等名词却另作他类。因此要研究关系名词,首先要明白关系名词有什么样的语义特征?有没有具体的鉴别方式?这些问题都可以为关系名词的界定提供参考标准,即如何将关系名词与其他名词区分开来。我们认为,界定关系名词应遵循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本文先从语义方面分析关系名词的语义特征,然后从形式上提炼关系名词的鉴别标准,以期丰富汉语名词的语义语法认识。
二、关系名词的语义特征
根据我们的观察分析,典型的关系名词具有区别于其他名词的三个基本语义特征:多项性、依存性和推导性。
(一)多项性
由于关系名词是表示人或事物、现象之间关系的名词,因此,关系名词在语义上必然涉及两项及两项以上的人或事物、现象,这就是关系名词的多项性,也是关系名词区别于其他名词的一个基本语义特征。我们把关系名词所涉及的人或事物、现象称为关系项。关系名词一般涉及两个关系项,有时涉及三个或更多关系项。例如:
(1)他是小李的师傅。
(2)他在小王的后面。
(3)他是小李和小王的儿子。
(4)他在小李和小王的中间。
(5)他被小李、小王和小张围在中间。
上述例子中的“师傅、后面、儿子、中间”都是关系名词,“他、小李、小王、小张”都是关系项。其中“师傅、后面”涉及两个关系项,“儿子”涉及三个关系项,“中间”在例(4)中涉及三个关系项,在例(5)中涉及四个关系项。
关系名词涉及多少个关系项,是由关系名词的语义决定的。大多数关系名词只涉及两个关系项,如“师傅”“后面”,师傅与徒弟相对,后面与前面相对。虽然一个师傅可以有多个徒弟,但多个徒弟也只是一个关系项。少数关系名词涉及三个关系项,如 “儿子”,儿子与父亲、母亲相关。极少数关系名词可能涉及三个以上的关系项,如“中间”可以与前、后、左、右等相关。涉及两个关系项的关系名词就是双项关系名词,涉及三个关系项的就是三项关系名词。其余依此类推。
根据关系项的不同性质,我们将关系项再分为两类,一类是指示项,一类是参照项。指示项就是关系词语指向的人或事物。如上述例句中的“他”都是指示项。如例(1)、(2)可以变换为“小李的师傅是他”“小王的后面是他”。可见“他”是关系词语“师傅”等指示的对象。参照项就是与指示项构成特定关系的关系项。如上述例句中其余的关系项“小李、小王、小张”都是参照项。其中指示项在句子中一般必须出现,参照项在一定的语境中可以不出现。例如上述例句中的指示项“他”一般必须出现,而参照项“小李、小王、小张”都可以不出现。如:
(6)他是师傅(媒人、儿子等)。
(7)他在后面(中间、左边等)。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指示项是关系词语指示的对象,指示项如果不出现,就会造成关系词语的指示对象不明确,影响交际。而参照项只是指示项的参照点,参照项如果不出现,虽然有可能造成参照点不明确,但并不会影响交际。这是因为从认知的角度来看,指示项是前景信息,参照项是背景信息。就像拍照片一样,背景图像可以模糊化,甚至隐去,前景图像则必须清晰地得到凸显。例如只说“他是师傅”,就意味着他是某人的师傅,至于这个某人是谁,可能并不重要,不是说话人要凸显的信息,因此可以隐去。换个角度来说,正因为关系名词在语义上具有多项性,如果句子中只出现指示项,没有出现参照项,我们仍然会推知有一个省略或隐含的参照项。
(二)依存性
关系名词的依存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系名词所关涉的对象(所指)[3]之间相互依存,没有一方,就没有另一方。例如丈夫依存于妻子,师傅依存于徒弟。没有妻子,就不成为丈夫,没有徒弟,也就不成为师傅。反之亦然。二是关系名词本身(能指)具有依存性,一个词语依存于另一个词语。例如“丈夫”这个词和“妻子”这个词相互依存,没有“丈夫”这个词,就没有“妻子”这个词。反之亦然。
大多数关系名词都具有这种双重依存性。具有双重依存性的关系词语,往往可以凝固为粘合式联合结构表示特定的关系(简称粘合式关系词)[4]。如“丈夫”和“妻子”构成“夫妻”关系,“师傅”和“徒弟”构成“师徒”关系,“原因”和“结果”构成“因果”关系等。当然也有少数例外。如“手段”和“目的”是也是具有双重依存性的,但不能凝固为粘合式并列结构。
有一些关系名词只是所指具有依存性,能指不具有依存性。有的关系名词依存的参照项,不太明确或不太固定。例如“敌人”,肯定要有一个参照项,但是这个参照项没有固定的词语来表示。虽然有时“敌”似乎以“我”为参照项,如“敌进我退”。但是“敌”的参照项并不限于“我”,任何人都可能有敌人,任何人都可以作为“敌人”的参照项,“敌人”这个词没有固定的对应词语表示参照项。又如“客户”的参照项可以是厂家、商家、银行等,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固定的词语与之对应。又如“侄子”可以和很多亲属名词对应,“叔叔、伯伯、婶子、伯母、姑姑”等,甚至朋友、同事的儿子也可以叫“侄子”,这时,从“a是b的侄子”就很难推知b是a的什么人了。
这类没有所指依存性的关系名词还可以分为两个小类:
一类是对称性关系名词。对称性关系名词的指示项和参照项是对等的、可逆的,两个关系项之间互为参照项,也可以同为指示项。其逻辑语义特征为“如果a与b是R关系,那么b与a也是R关系”,用逻辑公式表示就是“aRb→bRa”。也可以表示为“如果a是b的R,那么b是a的R”[5]。如“朋友”“同学”“对手”“对岸”等。例如:如果“张三和李四是朋友”,那么张三和李四就互为“朋友”;但这种对称性关系名词往往会产生歧义。如“张三和李四是朋友”,既可以表示“张三和李四”互为朋友,也可以表示“张三和李四”都是另外某人的朋友,这时“张三”与“李四”之间不一定互为朋友。
这种对称性关系名词与“夫妻”类粘合式关系名词既有相同点,也有明显区别。共同点在于:两者都可以说“a和b是R(关系)”。如:“张三和李四是朋友(关系)”“张三和李四是夫妻(关系)”。不同点在于:可以说“张三是李四的朋友”,而不能说,“张三是李四的夫妻”。此外,如前所述,“张三和李四是朋友”有歧义,既可以表示两人互为朋友,也可以表示两人同为另外某人的朋友;而“张三和李四是夫妻”则没有歧义,只能表示两人互为夫妻。
另一类是非对称性关系。这种非对称性关系名词只能指指示项,不能包括参照项。如“客户”之类只能指指示项,不能包括参照项。如可以说“张三是李四的客户”,“客户”只指“张三”。虽然也可以说“张三和李四是客户”,但这时只能表示“张三和李四”都是另外某人的客户,而不能表示他们互为客户。
此外,还有些名词只具有能指的依存性,不具有所指的依存性。例如“中医、西医”“客车、货车”,这些词语本身也是相互依存的。例如没有“西医”这个词,就没有“中医”这个词,“中医”这个词就是为了区别于“西医”才产生的。反之亦然。但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事物本身并没有相互依存关系。中医这一事物历来就有,只不过在没有引入西医之前,不叫“中医”。这类只有能指的依存性,没有所指的依存性的名词,就不算关系名词,因为它们不是表示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而是表示事物的属性的。
由此可见,所指的依存性是关系名词的一个基本语义特征,能指的依存性则不是。没有能指的依存性,只有所指的依存性,还是关系名词;没有所指依存性,只有能指依存性,就不是关系名词。但是下文我们将会看到,能指的依存性对关系名词的界定也有一定的影响。
(三)推导性
由于关系名词表示人或事物、现象之间的关系,具有依存性,因此往往可以进行语义推导,从关系项的一方可以推导出关系项的另一方。
具有双重依存性的关系名词,由于不仅关系名词的关系项之间具有依存性,关系名词本身也具有依存性,因此可以从一个关系名词推导出另一个相依存的关系名词及其指示项。如:“师傅、徒弟”具有双重依存性,可以从“a是b的师傅”推导出“b是a的徒弟”。其他如“丈夫、妻子”“前面、后面”等都可依此类推。
有些关系名词的参照项不止一项,也可以推导出其中一个可能项,得出一个选言结论。例如:“从a是b的儿子”,可以推导出“b是a的父亲或者母亲”。反过来,从“a是b的父亲”可以推导出“b是a的儿子或者女儿”。
粘合式关系名词具有对称性,可以进行对称性推导,即可以将两个关系项易位。例如从“a和b是夫妻”,可以推导出“b和a是夫妻”。
不具有双重依赖性的关系名词,其中对称性关系名词可以进行对称性推导。例如从“a是b的同学”可以推导出“b是a的同学”。而非对称性的关系名词则难以进行确定的推导。例如“a是b的客户”“a在b、c的中间”都难以推导,因为与“客户”“中间”相对的参照项不确定。例如“中间”的参照项可以有很多可能:“上、下,前、后,左、右,东、西”等。
总之,具有双重依存性的关系名词或者对称性关系名词,都可以进行关系推理,不具有双重依存性的非对称关系名词,则难以进行关系推理。
三、关系名词的鉴别框架
所谓关系名词的界定标准就是指根据什么标准来鉴别哪些词属于关系名词,哪些词不属于关系名词。我们认为,关系名词的界定标准应该遵循意义与形式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应该依据关系名词的语义特征,根据关系名词的构成要素来界定;另一方面,也要尽可能找到一些形式标准,确定一些鉴别框架来加以界定。
根据前文对关系名词的语义特征的分析,关系名词涉及三个构成要素:一是表示某种特定关系的关系名词本身,二是关系名词的指示对象即指示项,三是与指示项构成特定关系的参照项。我们将关系名词的这三个构成要素构成的典型句式作为鉴别关系名词的基本框架。
(一)框架一:如果a是b的R1,那么b是a的R2
在框架一中,R1与R2有相互依存关系,因此可以从R1推出R2。例如:
如果张三是李四的丈夫,那么李四是张三的妻子。
如果张三是李四的师傅,那么李四是张三的徒弟。
这一框架是根据关系名词的推导性建构的。如果a和b都是指人的词语,凡是能够进入这个框架中R1或者R2位置的名词,都属于关系名词。即使有些名词在一般情况下不是表示关系的,一旦进入这一框架,就能表示某种特定关系。例如,“医生”和“病人”单独使用时并不表示特定的人际关系,“医生”是“掌握医药知识、以治病为业的人” (《现代汉语词典》),表示一种职业,与“工人、农民、干部”等类似;“病人”是“生病的人;受治疗的人”(《现代汉语词典》),表示具有某种性状的人,与“好人、健康人”相对。但进入这一框架后,二者就构成了特定的人际关系: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和接受者,即医患关系。不过,“医生”和“病人”之所以能够进入这一框架,表示特定的人际关系,还是因为它们的意义中包含着人际关系的因素:“以治病为业的人”实际上是给别人(病人)治病的人,“受治疗的人”实际上也是接受别人(医生)治疗的人。
如前所述,有些缺乏能指的依存性的非对称性关系名词,有时难以进行一对一的推导,但是,只要能根据某个表示关系的词或者短语推出这个词,仍然可以断定为关系名词。例如:从“他是我的客户”很难推出我是他的什么人,但是反过来从“我是他的经纪人”或者“我是卖东西给他的人”,可以推出“他是我的客户”。这时名词“经纪人”和“客户”都可以断定为关系名词,短语“卖东西给他的人”当然不算关系名词,而是表示人际关系的名词短语。这是因为“客户”这类词的所指是有依存性的,没有与之交易的人(参照项),就不成为客户,只是这个参照项没有明确的固定的词来表示,即“客户”这个词(能指)没有依存性,没有固定的对应词语。
前面说到,这个框架中的a和b必须都是指人的词语,如果a或者b不是指人的词语,就不能适用这个框架。例如:
如果这是我的书包,那么我是这的主人。
表面看来,上例中的“这”是a,“我”是b,“书包”是R1,“主人”是R2。但是,由于“这”不是指人的,而是指物的(书包),其中“书包”并不表示a和b之间的关系。a和b确实有某种关系:领属关系,但这种领属关系并不是由“书包”这个词表示的,而是由“我的书包”这种领属结构表示的,而这种表示领属关系的偏正结构,中心语是可以省略的,因此,去掉“书包”,推导仍可成立。而当a和b都是指人时,R1和R2都是表示a和b之间的人际关系,而且R2是根据R1推导出来的,如果没有R1,就推不出R2,因此R1不能去掉。例如:
如果这是我的,那么我是这的主人。
*如果张三是李四的,那么李四是张三的妻子。
框架一中的a与b之所以必须是指人的,这是因为只有a与b都是指人时,才能保证a与b构成相互依存的人际关系,如果a或者b是指物的,那么a与b之间就可能构成一般领属关系、类属关系、整体部分关系、事物—性状关系等,而不是相互依存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与领属关系等是有很大差别的。当“a的b”这种偏正结构表示人际关系时,中心语b是不能省略的,如果是表示一般领属关系、类属关系或者事物—性状关系等时,中心语b是可以省略的。例如:
*这是张三的父亲。→ 这是张三的。
*他是我们公司的客户。→ 他是我们公司的。
这是张三的书包。→ 这是张三的。
这是张三的公司。→ 这是张三的。
在“我们公司的客户”中,“我们公司”与“客户”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主客关系,而在“公司的职工”中,“公司”与“职工”是领属关系。
又如:“他是你的什么人?”意思就是“他跟你是什么关系?”而“这是你的什么东西?”却不表示“这跟你是什么关系?”也就是说“你的什么人”中的“什么人”是表示关系的,而回答这里的“什么人”这一问题的名词,如“父亲”等,就是关系名词。而“你的什么东西”中的“什么东西”则不是表示关系的,回答这里的“什么东西”这一问题的名词,如“书包”等,也不是关系名词。
(二)框架二:如果a是b的R,那么 b是a的R
这一框架也是根据关系名词的推导性建构的,能够进入这一框架中R的位置的名词,就是关系名词。例如:
如果张三是李四的朋友,那么李四是张三的朋友。
如果张三是李四的敌人,那么李四是张三的敌人。
这一框架实际上可以看成框架一的特殊变体,当框架一中的R1与R2相同时,就构成框架二。所以关于这一框架的问题不必多说了。
(三)框架三:a与b之间是R关系
在框架三中,“R关系”是表示关系项a与关系项b之间的特定关系的关系词,R可以是名词、动词、短语或缩略语。能够进入R位置的名词,就是关系名词。例如:
张三和李四之间是夫妻关系。
他和我之间是师生关系。
能够进入框架二的关系名词,大多数也能进入框架三,但是也有少数能进入框架二的不能进入框架三。例如“敌人、老伴”:
如果张三是李四的老伴,那么,李四是张三的老伴。
如果张三是李四的敌人,那么,李四是张三的敌人。
?张三和李四之间是老伴关系。
?张三和李四之间是敌人关系。
能进入框架三的,有些不能进入框架二。如“夫妻、婆媳”等粘合式关系名词一般都不能进入框架二,但可以进入框架三。根据我们对词典和语料的考察分析,凡是关系名词,都能进入上述三个框架之一;凡是不能进入上述三个框架的,就不是关系名词,至少是不太典型的关系名词。
四、小结
本文对关系名词的语义特征进行了分析,得出关系名词最典型的语义特征是多项性、依存性和推导性。其中依存性分为所指依存性和能指依存性,如果两者同时具备,是双重依存,可以进行关系名词的推导。还有些名词只具有能指的依存性,不具有所指的依存性,不能进行关系名词的推导,如“中医”和“西医”,就不能看作关系名词。根据关系名词的三个语义特征提炼出三个鉴别框架,凡是能够进入其中之一,就可以看作关系名词。如果一个框架都不能进入则不是关系名词。还有一种特殊的现象是有的关系名词需要进入特定的框架,如“军民”“医患”,进入“NN关系”框架中,才可算是关系名词,脱离这个框架则不能算关系名词。
*本文系2015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关系名词的语义特征与界定标准”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朱德熙:《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1~42页。
[2] 王珏:《现代汉语名词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4~205页。
[3] [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4~46页。
[4] “师傅”“老师”之类的词语都有不同的意义,一种意义是表示人际关系的,另一种意义是表示职业身份或某种泛称的。前一种意义属于关系词语,后一种意义不是关系词语,同“工人”“农民”“教师”或“先生”“小姐”“同志”之类的词语类似。表示职业身份时,没有徒弟、学生的人也可以是师傅、老师。如“工人师傅”“中学老师”,这种现象属于词义的泛化现象。
[5] 吴振国:《现代汉语中的粘合式联合结构》,《语言研究》2004第1期,第24~29页。
[6] 胡习之:《关系词浅说》,《语言与逻辑学习》1989年第6期,第40~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