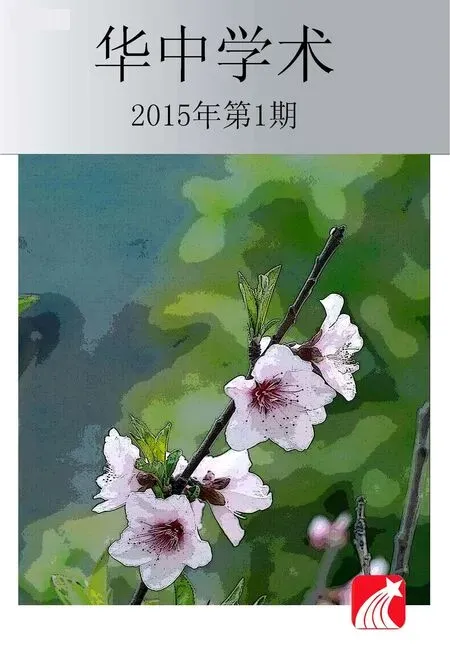论韩愈《南山诗》与李贺《昌谷诗》的“感知”表现
陈沛淇
(静宜大学,台湾台中,43301)
一、问题发想与研究背景说明
在文学史上,“中唐”这个概念的发源,可追溯到宋代严羽和刘克庄。严羽将唐代诗歌区分为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和晚唐体。又有刘克庄在《中兴五七言绝句序》写道:“昔人有言,唐文三变,诗亦然。故有盛唐、中唐、晚唐之体。”刘克庄的分类较笼统,但严羽明确地指出“大历体”和“元和体”,意为中唐诗歌群的确存在某些“类特征”,而可以再区分出大历和元和二体。此后,关于唐代诗歌分期的讨论不断。明代高棅综合诸家对唐诗的分体观念,在《唐诗品汇·总序》有更为缜密的说明。高棅并不将“元和诗”归为中唐,他看到这时期诗歌的种种变相,皆与盛唐诗给人的印象渐行渐远;因此他倾向将元和之后的诗歌,归类为“晚唐”[1]。这个分类到了徐师曾《文体明辨》中,又被推翻了。徐氏将元和诗歌再次纳入中唐,并对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做了明确的界说,自此“四唐说”形成定论。
从高棅的分类可察知,他对于盛唐诗有其定见与向往;大历、元和之后的诗风,因远离了盛唐诗气象,而被定位为“变”。元代袁桷于《书汤西楼诗后》曰:“诗至于中唐,变之始也。”[2]清代叶燮《百家唐诗·序》亦云:“吾尝上下百代,至唐贞元、元和之间,窃以为古今文运诗运,至此时为一大关键也。”[3]凡此都是诸家察觉到中唐诗不同于往昔诗歌的例子。明清二代在议论中唐、晚唐诗和盛唐诗的差别时,也跟唐、宋诗的优劣之争相关;因为中晚唐诗之工巧、俚俗、以文为诗等特质,启发了宋代诗歌的发展。这些议论都有其洞见,然而中唐诗应仍有独特之处可供发掘。
诗歌发展至中唐时,的确有了重大转折。从根源来说,这转变是一种“质变”,而不只是诗歌主题与题材的世俗化、修辞工艺化、语言赋化或口语化等表现的变迁。在寻思如何跳脱明、清的讨论框架,以新视角讨论中唐诗歌的质变现象时,我们注意到苏珊·朗格(Susanne K.Langer,1895—1982)对诗歌语言的质性辨析。朗格在区分诗歌语言与非诗歌语言的本质差异时提到,一首诗在创生之际,同时也产生了某些限定。诗歌不如绘画、舞蹈或戏剧,可直接借由“形象”展现,诗歌的表现媒介主要是语言,诗人借由语言塑造了诸多“意象”,通过这些意象的排列组合,才得以构成一首动人的诗。因此,诗歌的意象及其排列,不但决定了读者能看见什么、什么可以被感知,此意象组合还决定了读者心理活动的方式,其中包括了感觉和思考的顺序[4]。借由这样的思考路径,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唐诗歌的转折之所以能被察觉——就诗歌的构成本质而言——也就是因为读者看见的、感觉到的,乃至于阅读时的感觉或思考方式及顺序等发生了变化使然;这其中,“意象表现”显然是最大标的物[5]。
葛晓音在《中唐文学的变迁》中,归纳了中唐诗歌的四大艺术特征,分别是“深入内在感觉以表现印象”“艺术想象的避虚走实”“诗体的铺张和赋化”“用口语、俗语入诗的白话化倾向”[6],而前二项特征,又以韩、孟为首的尚奇诗派表现得最为明显。川合康三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归纳了对唐世描写终南山之作品群的观察,发现中唐后的终南山书写,有“去超然绝俗化”且“具体知觉化”的特征。韩愈的《南山诗》,便是显著代表。造成这种差异的分野,可能与诗人逐渐脱离集体共识的文学趣味,转而专注于以个体性的知觉来作诗的态度转折有关[7]。由此可知,以“感觉造诗”是中唐后的诗歌所表现出的共相之一。
在中唐诗歌的转折中,诗人览物所引发的感知、思维、观览过程中人与景物的主客关系之变化,令人倍感兴趣。盛唐诗中那种恢弘辽阔的视野,产生自诗人览观宇宙、吞吐万物的“超然视觉”;这种目光习于从全体去宏观局部。古来一直被誉为盛唐气象代表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王湾《次北固山下》)二句,就是这种超然视觉及思维的表现。与此不同的,中唐诗歌的意象所表现出的视觉,则愈有固着、流连于局部与具体之物的趋势;这种观物的目光有细微化、深刻化、化虚为实的特征。因此,这就导出了一种研究的可能性,即从诗歌意象、譬喻及其组合方式所表现出的感知,再审视中唐诗歌的特质。
本文使用的“感知”一词,与“感官知觉”的意涵相通,而与“身体感”的观念接轨。“身体感”一词,源出于日本医学史学者栗山茂久的研究;他认为在判读古代的医学经典时,除了了解古人思想外,还要尽量抛去现代人的认知,尽量从感官层面做“还原”,了解古人的身体感,以及借由此身体感所做出的联想与医学判断[8]。“身体感”与“感官”“情感”不是同一层面之物。情感与心理层面的活动关系较为密切,而感官则是指人之“五感”(眼、耳、鼻、舌、身)接受到外部刺激后,产生的感觉。依照余舜德的界定,身体是一个多重感官、复杂情感和身体经验综合作用的“场”;身体感研究是为了以身体作为经验的主体,重新思考日常生活中的感知项目,是如何借由身体感的反应与联想,进而对人们的认知产生影响[9]。本文研究诗歌的感知表现,意在于回归身体感的层面,审视诗歌意象的多重感官召唤和情感的渲染,并观察“身体经验”对此感知做出了何种联想或判断。从诗歌意象的感知表现进行研究,是向中唐诗的解释传统提出一种补充的可能性,并提供不同的阅读视野。
本文选择以韩愈《南山诗》、李贺《昌谷诗》作为讨论对象,有两点理由:第一,韩愈与李贺同属于中唐时崇尚“奇语”的诗人。若欲观察中唐诗的感知取向,尚奇派诗作是很好的取样对象。当诗人有意识地创造“奇语”时,这些语汇经常都与细密的感官知觉相关,有时甚至比诗中的兴寄之意,来得更为显目。孟郊《苦寒吟》即为一例:
天寒色青苍,北风叫枯桑。厚冰无裂文,短日有冷光。敲石不得火,壮阴夺正阳。苦调竟何言,冻吟成此章。[10]
全诗为了记述贫穷寒冷之苦,而做“刻苦”之言,它没有太多言外之意,诗的意义被“划定”在那些富涵身体感的意象中——青苍色的天空,因为极度寒冷和北风不停号叫,虽晴朗却透着冷峻的感觉;没有裂纹的完整厚冰,固然是视觉上的描述,但厚冰的坚实无缝,同时也引发了触觉上的冰冷和无可穿透的窒闷感。冷峻的天空、坚实的厚冰等看似直描的文字,实际上都譬喻了诗人的身体感知。就诗人的感觉而言,这些被选择且编织的素材,多少都带有譬喻性质[11]。诗人欲表达的,便是贫穷寒冷带给人的具体又深层复杂的感受。寒冷是人共同的感官经验,但同时也是诉诸个别体验的;从抒情言志的角度看,《苦寒吟》是在抒发贫寒的慨叹;但从身体的角度来解读,却能从诗文意象中多重感官、情感的叠合,读出一种倾诉生存处境的身体语言。
第二,韩愈与李贺虽同为主张诗歌尚奇的诗人,亦皆不乏感官知觉取向的诗作;但他们的感知表现恰好是二种不同的类型。宇文所安曾就“自然秩序之表现”的视角,解读《南山诗》和《昌谷诗》;他注意到,前者表现出建筑般的严谨结构,而后者则零碎而着迷于细节。换言之,《南山诗》将自然视为可掌握的整体,而通过结构的构筑,以期一一把握细节;而《昌谷诗》则仿佛迷失在自然景观的诸多细节中,“整体”像个遥不可及的梦。因此以这二首诗互为对照,可观察出一组中唐诗面对自然的不同态度[12]。就诗歌意象的研究而言,《南山诗》的结构严谨和《昌谷诗》的零碎,此两种不同样态也就说明了韩愈和李贺是用不同的态度在表现身体感。
只以《南山诗》和《昌谷诗》作为取样,或稍嫌不足;然二诗同为篇幅较长的作品,内容则为诗人在自然中的体物书写。又,二诗的结构与词汇,皆大量涉及感官的譬喻与联想;因此试并列讨论之,谨作为研究中唐诗歌之感知表现的引玉之砖。
二、《南山诗》的感知表现
钱仲联将《南山诗》系为唐宪宗元和初年所作,时值韩愈三十九岁时,自江陵法曹召为国子博士[13]。前人在评论此诗时,习惯与杜甫《北征》一并比较;从而产生《南山诗》与《北征》孰优孰劣的辩论。诸家评论可分为二类:一类认为《南山诗》不如《北征》;另一类则以为此二诗各有各的体制与优点,不可并列比较。在反对《南山诗》的评论中,曾著《韩昌黎集辑注》的蒋之翘,其说法颇有代表性:
《南山》之不及《北征》,岂仅仅不表里风、雅乎?其所言工巧,《南山》竟何如也?连用“或”字五十余,既恐为赋若文者,亦无此法。极其铺张山形峻险,叠叠数百言,岂不能一两语道尽?试问之,《北征》有此曼冗否?翘断不能以阿私所好。[14]
蒋氏的批评主要有三:一是《南山诗》没有兴寄义,而《北征》则有可直追《诗》之风、雅的比兴寄托义;二是《南山诗》虽属五言古诗,但看起来更接近长赋或有韵散文,这种明显的“以文为诗”现象,破坏了诗歌该有的简练之美;三是韩愈用了数百字形容山势宏伟险峻,但这件事似乎用一两句诗也能概括,不知为何冗言至此。从蒋氏的批评里,我们可以看到某种熟悉的诗歌共识:诗的内容必须有言志抒情、比兴寄托的成分,而诗歌的形式应保有体裁与音韵和谐、用字精炼等美的标准。《南山诗》刚好在各方面都打破了这种审美观。
韩愈在文学创作上是力求创新与突破的大家,蒋之翘所着眼批评的点,恰好都曾是韩愈的“实验项目”,这其中包括以赋入诗、作新奇险怪之语等。终南山多变的样貌,不能以三两语概括之,那是因为诗人想表现的不是概约的或印象的山,而是被具体把握住大小细节的山。就此而言,程学恂的评论比较能理解韩愈的立意:
读《南山诗》,当如观《清明上河图》,须以静心闲眼,逐一审谛之,方识其尽物类之妙。又如食五侯鲭,须逐一咀嚼之,方知其极百味之变。昔人云赋家之心,包罗天地者,于《南山诗》亦然。[15]
令人玩味的是,程学恂这段文字提到了视觉和味觉。他指出读《南山诗》时,目光应一一凝视诗文所形构的物态;又应慢慢地品读,才知道诗文里包藏了各种奇妙的变化和感觉。我们认为,这里已经看得到“感知阅读”的端倪,而这也是读《南山诗》的适当途径之一。《南山诗》所刻意抛去的那些诗歌标准(比兴寄托、和谐美),不应成为被诟病的原因;相反的,它完成了什么样的新艺术,方为值得探究之处。
程学恂言“赋家之心,包罗天地”者,乃出自《西京杂记》所载司马相如谈作赋之法,其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也。”[16]司马相如这段话有两个重点,其一是“赋之迹”为细致而繁多的,且能按照一定的秩序(经纬、宫商)组织而成。其二是赋之所以能表现出物之细致与多样,乃得自于赋家能览观宇宙万物。在这里,能看到一种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赋家借由览观而掌握整体,继而在其体察的秩序下,表现一一之品类。又,赋家这种观物与组织能力,只能得之于心而无法言传,俨然是“难以言状”。借由程学恂的引言,将司马相如语放到《南山诗》中,我们可以对韩愈的“赋家之心”有较聚焦的观察。这首诗的确展现了终南山整体与山之局部的结构性关系,也极尽所能地囊括了山的姿态;那么韩愈览观终南山时,他的观物立场、态度是什么?他凝视着山的时候,“得之于内”的又是什么?
这些问题带领我们回到诗歌作品上,并产生分析《南山诗》结构与意象性质的好奇。就文章结构作观察,《南山诗》的组织方式是十分严密的;可以看出,韩愈排列景物、以组织总摄终南山万象的企图。以下分两点叙述《南山诗》的结构特征:
(一)从整体掌握局部
《南山诗》的结构有强烈的“定位”终南山的意图,这种结构安排与表现,又与两种观物的方式相关。首先是“如地图般的全览视角”。韩愈虽有提到这是登高后看到的景象;但他有些视野是想象的,如“东西两际海”“西南雄太白,突起莫间簉。藩都配德运,分宅占丁戊。逍遥越坤位,诋讦陷乾窦”[17],这是借由想象的空间安排,将终南山定位在一个明确的位置。他登高所见的是山的走势、形态与整体环境;登高所不能见的,就以想象来补足。其次是“如画家般的黏着目光”。韩愈的目光来回流转于终南山的整体环境和样态上,仿佛像个画家站在欲描绘的对象前,时而量比,时而深思,务求以最精准的色彩和线条呈现所观之物。
(二)试图从时间把握终南山的连续性存在样态
《南山诗》在空间结构的安排外,还有时间结构。时间结构的安排与掌握终南山样态的变化相关。比较显目的有三处:
其一是从四季更迭,动态地描述终南山景致的变化;如“春阳潜沮洳,濯濯吐深秀。岩峦虽嵂崒,软弱类含酎”“夏炎百木盛,荫郁增埋覆。神灵日歊歔,云气争结构”“秋霜喜刻轹,磔卓立癯瘦。参差相迭重,刚耿陵宇宙”“冬行虽幽墨,冰雪工琢镂。新曦照危峨,亿丈恒高袤”等。
其二是回溯想象中的远古,以神话解释山势之开合样态。此处见于“巨灵与夸蛾,远贾期必售。还疑造物意,固护蓄精佑。力虽能排斡,雷电怯呵诟”等句。巨灵、夸蛾都是神话人物,以力大能移山开河见称。韩愈见眼前的山岭交叉横错,又仿佛曾有坼裂的迹象,他追想起终南山的形成和变动。当然这个追想只能停留在想象的层面,因此巨灵与夸蛾为了炫耀神力,曾想分裂山脉而又被雷电吓阻的虚构情境,便应运而生。这里特意营构出想象的过去,用意还是为了把握并解释奇特的地表样貌。
其三是韩愈借由自己的回忆与经验,描述终南山的多变样态。诗中提到三次登终南山的经验。按照实际的时间顺序,第一回是贞元十九年冬,韩愈遭贬放,出长安,从蓝田县入山;当时他经历了暴风雪和危险路况。第二回是因为时间不充分,加上山路难行,他中途就折返了;但因而有机会参访“炭谷湫祠”[18]。第三回他趁天气晴朗入山,总算是攀登到高处,得以一览终南山的样貌。
借由空间与时间的布局去掌握并描写地景并不是太特别的事,但《南山诗》开头就有这样的一段话:
团辞试提挈,挂一念万漏。欲休谅不能,粗叙所经觏。
这意思是韩愈原本就打算逞其才、穷其辞,将眼前景细细记录下来;因而全诗言志抒情的成分很少,反而体物、写物的成分很高。当诗人一心一意只想刻画眼前景或某个特定对象时,他全副的感官、思维、经验与记忆便投入与对象物的交流当中,他的文字便像是当下各种感知活动的描述、纪录与譬喻。因此《南山诗》的时空布局可视作韩愈为自己那纷纷的感知所搭盖的“屋宇”,在其结构下,细琐纷杂的感知就能毫无顾忌地全盘托出。
因此,我们就读到了诗文中那些滔滔不绝的、关于山景的譬喻。这些譬喻由于目的都在于尽情表现诗人所感知的终南山,故句句都是实指;且其譬喻性质颇有生活化、具体事物化的倾向。如“天空浮修眉”,是以画眉譬喻浓淡不一、从云霭间浮现的远山;“海浴褰鹏噣”是以张开的鸟嘴譬喻山立于水域中的样貌。画眉、鸟嘴都是日常可见、令人熟悉的物事,“难以把握”的终南山正在被诗人一点一点地“可把握化”。这部分,在诗中连用五十一个“或”字处,表现得更为明显。
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或妥若弭伏,或竦若惊雊;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辐辏;或翩若船游,或决若马骤;或背若相恶,或向若相佑;或乱若抽笋,或嵲若炷灸;或错若绘画,或缭若篆籀;或罗若星离,或蓊若云逗;或浮若波涛,或碎若锄耨。
有些研究已指出,南山诗的譬喻有日常化、世俗化的倾向,本文欲进一步说明这些譬喻的感官知觉性质。在作为喻依的数个词中,“相从”“相斗”“弭伏”“惊雊”“相恶”“相佑”,这些都属于人或其他动物的身体姿态,读者很容易就能从过往感知经验而把握山的形态。另外,“瓦解”“辐辏”“船游”“马骤”“抽笋”“炷灸”“绘画”“篆籀”“星离”“云逗”“波涛”“锄耨”等,虽种类不一,但都属于透过视觉经验所能把握的具体事物。以“或翩若船游”为例,“船游”的譬喻,诉诸人们对行舟的视觉经验和与此相关的复合感觉,比如船行的微曲水痕带来的延续感、柔和感或轻快感。因此“船游”就用来譬喻山势联翩、舒缓连绵的样子。韩愈在这里是以具体的感知及其所能引发的综合感知经验与联想,指涉终南山实景。
后段连用“或”字的情形亦然:
这段出现了更多属于生活文化层面的喻依,但作者欲取的仍是这些事物所能带来的综合感知印象。如“贲育伦”是以勇士奋发行动的样子取譬,“帝王尊”是以君王临朝,上下行礼如仪、亲疏有序的样子取譬;勇士奋起和君王临朝,都不是纯取其动作或形态而已,这当中蕴含的动能、身体的姿态、礼仪加诸身体的约束感等,也包含在取譬的用意之内。唯有把这些动态的、可诉诸感官知觉的因素纳入,这些譬喻才能达到令人“感同身受”的效用。其余如“食案”“坟墓”“婚媾”“峨冠”“舞袖”“战阵”“搜狩”“行而不辍”“遗而不收”“斜而不倚”“弛而不彀”等的情形皆类同。比较不同的是“龟坼兆”“分繇”“若剥”“若姤”等,这几项比较像是单纯的以视觉形象取譬。
由此可知,韩愈笔下的终南山除了是“人文的”山景之外,还是“感知的”山景。山的起伏开合、四季变化、云气和光影的流动,无一不勾起诗人的知觉,从而寻思相对应的譬喻。这些用以譬喻的素材,一致呈现出将感知具体化、具象化和入世化的特质,而给人留下紧紧抓住存在感受与对象物的印象。在《南山诗》中,诗人面对着自然,没有洒脱放逸的心情,却情不自禁地想要以词语、以全副的感受与文化认知去把捉,这与盛唐诗普遍表现出来的面对自然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异。
三、《昌谷诗》的感知表现
李贺《昌谷诗》作年难以确定,钱仲联认为大致是在元和八年所作[19]。姚文燮《昌谷集注》亦云:“此归昌谷山居即事而作也。”[20]一般来说,这首诗可视为李贺辞去奉礼郎一职,自长安归乡后所作。原诗标题下,附有“五月二十七日作”等字,可知作诗时正值夏季。
不同于《南山诗》的严密结构性,《昌谷诗》显得零碎而片段。吴正子在《昌古诗》诗题下作解曰:
本传言长吉旦出乘马,奚奴背古锦囊自随,遇有所作,投入囊中,其未成者夜归足成之。今观之此篇可验。盖其触景遇物,随所得句,比次成章,妍蚩杂陈,斑斓满目;此所谓天吴紫凤颠倒在短褐者也。[21]
观其言,像是对李贺的做法感到不以为然;但吴正子的观察有些有意思的地方。他在批评的同时,想象着李贺骑瘦马、小仆背着旧囊跟随的情景。这诗人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有成篇的,也有不成篇的;那些不成篇的美丽句子,就等回家后再补缀成篇。所谓“触景遇物,随所得句”就像以诗句为眼前情景写生、速描一样。为了讽刺《昌谷诗》的斑斓零碎,吴正子想到以“天吴紫凤颠倒在短褐”来形容。
众所周知,天吴紫凤语出自杜甫的长诗《北征》,原句为“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意指诗人在战乱中回家探视,发现妻儿都穿着拼补的“百衲衣”;原本不知绣在何处的吴神与紫凤花纹,如今被裁下又歪斜扭曲地缝在破衣服上。吴正子的用意,是借凌乱缝缀的意象批评《昌谷诗》的随兴与杂陈。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吴正子的确想起了《北征》。杜甫在这首长诗中,用了数十句诗描述他出凤翔北行后,在邠州郊外所见的景色[22]。就这部分而言,他也是“触景遇物,随所得句”;然而《北征》的写景之所以不至于零碎,是因为整首诗忧国忧民、自叹平生的兴寄之意十分明显。旅行中的杜甫一度沉浸在自然景色里,可是纠结的烦思很快地又将他从“桃源”带回现实。是以《北征》的写景与《昌谷诗》的写景有其相似处,但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有兴寄的主轴,后者则几近漫无目的。吴正子感到不满之处,恐怕也包括这一点:比兴寄托、抒情言志的作诗传统,在《昌谷诗》中只剩下意图不连缀的体物与写物。
《昌谷诗》写的是李贺家乡风景,在这片熟悉的山水中,李贺是个漫游者。虽说与《南山诗》比较起来,看似没有主轴、完整结构可言;但平心而论,《昌谷诗》还是有自己的结构。这个结构是随着诗人的漫游而开展的,因而与现场、当下的整体情境、诗人的视野之关系特别紧密,而刻意布局的成分便大大降低。有些诗文的意涵,甚至必须从这“随感知而漫衍的布局”的体会,才能得到较充分的解释。
以此段为例:
高眠展玉容,烧桂祀天几。雾衣夜披拂,眠坛梦真粹。待驾栖鸾老,故宫椒壁圮。鸿珑数铃响,羁臣发凉思。阴藤束朱键,龙帐着魈魅。碧锦帖花柽,香衾事残贵。歌尘蠹木在,舞彩长云似。珍壤割绣段,里俗祖风义。邻凶不相杵,疫病无邪祀。鲐皮识仁惠,总角知腼耻。县省司刑官,户乏诟租吏。[23]
这一段写祭拜神女、访福昌宫和赞扬乡民的勤勉纯朴。乍看之下,这三件事之间似乎无甚联系,只是作者随意写下;但细读之下,令人又觉不然。李贺在昌谷郊外山道间游逛,来到了神女庙;他焚香祭祀后,那惯常的奇思幻想又活跃起来。从诗文来看,他也许在庙里休憩了一会儿,伴着倦意和暮色,恍惚间仿佛感觉到神女降临。神女相对于人,是更为长久不朽的存在;诗人既然感受到神女的飘渺气息,作为触发点,他随即对人世的变幻无常唏嘘起来。这是一个“李贺模式”,在他的诗集中经常可见神/人、常/变的设问和思考。在别处的诗章中,李贺或许让读者清楚地看到,他在诗歌中书写这些辩证思维的意图;但在这里,李贺比平常更加地“跟着感知”走,又让感知牵引着诗句,诗人连说明的笔墨都省去了。
因此,李贺对着荒凉的宫殿沉思起来。他沉思的方式,是凝视和静静感受。从陈旧的器物、颓圮的墙、屋檐的铃响、被藤蔓缠住的锁、等不到主人入寝的床帐,到尘埃厚积的梁柱和帷幔。他也许是真的目睹,也许只是想象;总之他用一连串的“物”指涉无常带来的怅惘。在这诉诸视觉的诸意象中,各种感官知觉也随着活跃起来;而李贺却只用“羁臣发凉思”形容自己此刻的感受。“凉思”是个带有身体感的词汇。荒废的故宫破败且阴森,于是李贺想起了鬼魅——那绣着龙纹的帷帐内,恐怕早已住着非人之物。这是第二个“李贺模式”,他对人世无常的感觉就是冷或某种死亡的预感,又往往因此而衍生出对神怪魍魉的幻想。诗作的视野和作者的感知是互相牵引、互相譬喻的,问题不在于李贺是不是真的“看见”,而在于他只要感知到就如同见到;因此诗歌中的实际意象也好、虚构意象也好,都是感知的相关物。具体表达出感知内容,对李贺来说,可能是他最在意的事之一。
诗人没有在对福昌宫的慨叹中沉浸太久,他的笔锋随着视线流转,突然写下了“珍壤割绣段,里俗祖风义”二句,以下就谈起了昌谷人如何民风纯朴、安居乐业。从福昌宫里久无人用的锦绣,到宫外的锦绣良田,此二者有微妙的联系:人造的华丽在宫殿里腐朽,自然的绮丽却在乡民的耕耘下,进化为让人欣喜的生活常景。诗人虽未明言,但这俨然是他对存在之茫然感、不确定感的回答:只有素朴踏实的生活,才能带来安定和救赎。昌谷是李贺的故乡;的确,只有故乡才有这种强大的召唤力量,让心思飘渺的诗人再次看见生活的美好,自神鬼世界重返人间。
从祭神女、访福昌宫到乡民生活的描写,这中间的联系,先是感知的,而后才是意义的。川合康三指出,李贺“不把事物作为概念,而是作为‘感觉’来把握,从而以感觉再构成‘物’”[24]。这是非常精微的观察。在《昌谷诗》中,散漫零碎的结构首先意味着诗人放弃了以“意义”或“概念”主导诗歌的写作;再者,这种结构零碎、片段式的写作,比起其他诗歌文体,更能明显地表现诗人的内在感受。从这二点来看,就不难理解《昌谷诗》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文体表现出来。
除了整体结构有“随感知漫衍的”倾向之外,《昌谷诗》还有两点感知取向的特征:
其一是全诗几乎是由带有视觉意象的诗句拼组而成。李贺和韩愈一样,诗歌有赋化的迹象。唐代诗歌的赋化是个普遍现象,就题材内容而言,是可见到大量的咏物写景之作;就形式而言,是如古赋般长篇幅或讲究章法之张力与对比的作品屡见不鲜。李贺也常被认为是善赋的诗家;但一般对于“赋”的认知,不全然适合用来解释李贺诗中的赋化现象。所谓“赋”,除了是指善于铺陈、巧构形似、利用章法达到戏剧性的张力外,还包括能串起全篇的“理”或叙事目的。而李贺诗在铺陈、状物这方面独具风格,但在“理”这部分比较薄弱——或如宋人刘辰翁所说,李贺之所长正在“理外”[25];我们把这位南宋批评家的话理解为:李贺擅长以感觉为“理”,并据此创造新词、构造诗篇。从这个角度来看《昌谷诗》的赋化,也可以解释为何全诗几乎都在描写景物,而又为何这些描写景物的诗句,看似没有强烈的意义联系。
其二是《昌谷诗》亦可见以感官知觉把握事物,重新造词的现象。如“遥峦相压叠,颓绿愁堕地”“草发垂恨鬓,光露泣幽泪”等句皆属此类。“遥峦相压叠”以“压”的感觉名状重山,但这还属普通;较特殊的是“颓绿愁堕地”。这个诗句以颓倾下坠感形容山野中植被繁茂盛大的样子,又因为诗人兴起颓倾下坠感,故“愁”字也随之而生,这是以感觉造词,又以感觉衍生感觉性词汇的例子之一。又,“草发垂恨鬓”是先掌握如发丝般的细草垂散的感觉,于是与“垂散”相呼应的低落情绪,比如“恨”“泣”也就连带地产生了感觉的联想。“露珠”之所以能成“泪”,不只是修辞上的譬喻手法而已,它是以诗人的身体感为基础而衍生的譬喻。
钱锺书曾用另一种方式,解释李贺这种奇特的譬喻手法:
……而其比喻之法,尚有曲折。夫二物相似,故以此喻彼;然彼此相似,只在一端,非为全体。苟全体相似,则物数虽二,物类则一;既属同根,无须比拟。长吉乃往往以一端相似,推而及之于初不相似之他端。……《秦王饮酒》云:“羲和敲日玻璃声。”日比玻璃,皆光明故;而来长吉笔端,则日似玻璃光,亦必具玻璃声矣。[26]
所谓“以一端相似”推而变成“不相似之他端”,指的就是李贺以具体之物名状感觉,又追随着感觉,延伸譬喻之物的属性。如“羲和敲日玻璃声”句,先是以“敲日”名状羲和驱车驾日的样子;这意象一开始是视觉的,但执鞭驱车有扬鞭的声音,诗人的想象便随着听觉移转,倘若被鞭策的不是马而是如玻璃般的太阳,肯定发出的是“玻璃声”。原本这句诗想形容的是时间飞逝这件事,但最后表现出来的却是极抽象却又需诉诸具体感官的譬喻。《昌谷诗》中“霜禽竦烟翅”“簧掉短笛吹”等句,皆属此类。一物先勾起诗人的感知,而后与此感知内容能连类相应的譬喻、此譬喻之属性所延伸的联想便油然而生。所造之譬喻看起来愈新奇、愈能细密贴合当下的感觉,就能为诗人所采用。此为李贺以感官知觉造词最大的特色。
四、两种不同的叙述主体
延承前文对《南山诗》与《昌谷诗》之感知表现的分析,最后讨论此二诗之叙述主体的观物立场与态度。这里的叙述主体,指的是诗歌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在诗文中那个能行动、感受与思维的主体我。此叙述主体不必然等同于创作主体,但却是在阅读诗歌时,读者最能真切体会到的“说话者”。
《南山诗》与《昌谷诗》迥异的结构表现,代表两种观看山水的态度;前者是积极主动的剖析与掌握,“以理观景,刻画形象”[27];后者则是随意任性,让诗歌意象服膺于兴起或偶遇。韩愈并非每首写山水景物的诗,都如同《南山诗》般深刻描画、恣意逞才;但韩愈与李贺同为中唐尚奇诗派的佼佼者,这个诗派所特有的去陈推新、重视感官知觉的刻画等特征,在此二诗中表现无遗。而《南山诗》与《昌谷诗》南辕北辙的结构形式,正好足以说明韩愈与李贺的“感知书写”策略不同。《南山诗》的“建筑式结构”,是为了安排布置变化多端的终南山景,并且确实地以相应的感官知觉去把握;而《昌谷诗》的“漫游式结构”,则给人一种随意记录当下风景、感官知觉、心理与词语的多方互涉的写作取向。
《南山诗》的视角是灵活的,诗人时而从至高处宏观或鸟瞰,时而贴近山的纹理作巨细靡遗的观察;他的目光甚且穿越时空,从回忆乃至往溯到想象的远古。韩愈的视角灵活多变,但综观全诗却可发现,终南山自始至终充塞着视野;诗人的目光黏着在山的本体与周围环境上,诗中的譬喻多是为了将感知具体化、具现化而使用。这让人联想到《西游记》中脱不出佛陀“五指山”的齐天大圣,《南山诗》的视野也脱不出终南山。一种局限了文本视野的“画框”隐隐存在。在框内,诗人尽情地裁造修辞以名状终南山;超出框外的事,则几乎不谈。
此处不宜贸然地说,这种主体为景物所囿的构图,是中晚唐诗的共相之一;但《南山诗》的确有这种征候。然而,唯有诗文的末尾几句是例外。韩愈描绘完终南山后,他走出了框外,像个画家般站在自己的作品前——同时也是站立于虚实杂糅的山之整体前——发出叹语:是谁造出了终南山?造化能造山,而他则以摹写山的歌诗作为礼赞。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抛却虚无、拥抱存在现实,十分积极入世的态度。若以韩愈的排佛思维和中唐诗歌的世俗化走向作为参照背景,《南山诗》的结构与譬喻特质,也能得到互为呼应的解释。
宇文所安曾形容,《昌谷诗》中的诗人,仿佛被山林田野的细节所“吞噬”[28]。因为诗句没有强烈的意义连贯,所以每一句诗所刻画的情景,都像是可以独立的小图景。散漫的整体,仿佛可以独立的局部,既给人秩序失控制感,又让人感到叙述主体乐于耽溺在每个零碎的片段。然而很有意思的是,同《南山诗》有其“画框”一般,在《昌谷诗》里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局限。昌谷的田园景致,从青田到山涧、神庙宫殿到乡里民家,从白昼到月夜,诗人都未曾让自己“超然物外”。山水景物构成了一个绮丽而让人眷恋的世界,诗人甚至打算将主体隐蔽或藏匿于山水之中。
在全篇的漫游记述之后,诗末的“刺促成纪人,好学鸱夷子”二句是隐逸之意,但李贺的隐逸和王维的隐逸显然大不相同:后者是一种主体的升华与旷达,前者却更像是主体的隐蔽与某种秩序的放弃。《昌谷诗》表现出既否定秩序又拥抱现世的态度,这种看似矛盾的心态,在诗人的身体感中却取得了一种审美的平衡——在景物细节与感知的互证中,他找到了存在感;而“奇语”则再次将这种审美价值与存在感,绮丽地具体化。这种对秩序的消极否定、借由感官知觉和语言落实存在感的特征,若与李贺不顺遂的际遇和中唐之后的政治乱象作为参照,我们也能从中察觉一些关联性。
五、结论
中唐诗歌的文变现象,自古以来,就为评论家所关注。文变与世变显然有不容否认的关系,但要如何理解这层关系、如何解释文变的本质与现象,这个课题至今仍值得讨论。本文从感知取向转变之进路,研究中唐诗的“转折”现象;虽仅以韩愈和李贺的两首诗作为讨论对象,但由于《南山诗》和《昌谷诗》在感知取向的写作上,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故通过分析后,也能局部说明诗歌感知表现型态的异变。
可以肯定的是,诗歌意象的感知具体化与入世生活化是这两首诗的共同特征;而《南山诗》建构理路以掌握景物,与《昌谷诗》否定秩序、专注细节以更深入的体物,这一组看似对立的态度,实际上是并存于中唐诗歌中,且与盛唐诗的普遍特征大相径庭。无论如何,建构理路以观物也好,否定秩序以深入体物也好,具象的感知和具体的山水景物,都是这两首诗所刻意表现之事。这也正好反映出了中唐诗歌的创作心理之一:在具象中寄托存在的矛盾与辩证,身体感知、现世与物成了诗人注目的核心。
注释:
[1](明)高棅《唐诗品汇·总叙》云:“大历贞元中,则有韦苏州之雅淡,刘随州之闲旷,钱郎之清赡,皇甫之冲秀,秦公绪之山林,李从一之台阁,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际,则有柳愚溪之超然复古,韩昌黎之博大其词,张王乐府得其故实,元白序事务在分明,与夫李贺、卢仝之鬼怪,孟郊、贾岛之饥寒,此晚唐之变也。”参见(明)高棅:《唐诗品汇》,《四库全书珍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页。
[2](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四部丛刊》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缩印元刊本,第678~679页。
[3](清)叶燮:《已畦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别集类244,济南:齐鲁书社,1977年,第81~82页。
[4]参见[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1年。朗格的主张是:艺术形式乃情感概念的表现。情感概念是一抽象物,它自艺术家的生活、经验、情绪和心理中抽离出来,以一种“概念”的形式被把握,然后安置入艺术作品中。关于诗歌形式与情感概念的部分,本文并不采取与朗格相同的观点;因为中国古典诗的创作逻辑,从根本处还是与西方不同。
[5]为了避免将“作者创作的身体感”与“读者阅读的身体感”混淆,此处先言明,本文讨论的是“诗歌意象的身体感”,因此主要是从作品表现与读者阅读的角度进行诠释。
[6]葛晓音:《中唐文学的变迁(一)》,《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第4期,第36~39页。
[7]参见[日]川合康三:《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8][日]栗山茂久:《身体的语言——从中西文化看身体之谜》,台北:究竟出版社,2001年。
[9]参见余舜德:《从田野经验到身体感的研究》,余舜德编:《体物入微》,台北:(台湾)清华大学,2010年,第1~43页。
[10](唐)孟郊著,韩泉欣校注:《孟郊诗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11]参见[美]雷可夫(George Lakoff)、约翰逊(Mark Johnson):《我们赖以生存的譬喻》,周世箴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6年。
[12][美]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陈引弛、陈磊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7~57页。
[13]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35~436页。
[14]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60页。
[15]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62页。
[16](汉)刘歆:《西京杂记》,台北:三民书局,1995年,第77页。
[17](唐)韩愈:《南山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32~435页。下文引《南山诗》处亦同,不再赘注。
[18]参见《南山诗》中“因缘窥其湫”句。
[19]钱仲联:《李贺年谱会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54页。
[20](唐)李贺著,(明)曾益等注:《李贺诗注》,台北:世界书局,1963年,第457页。
[21](宋)吴正子笺注,(宋)刘辰翁评点:《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钦定四库全书》,集部二别集类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29页。
[22]《北征》中随写眼前景的部分:“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前登寒山重,屡得饮马窟。邠郊入地底,泾水中荡润。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见(唐)杜甫著,(清)钱谦益注:《钱注杜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57~59页。
[23]引自(唐)李贺著,叶葱奇注释:《李贺诗集》,台北:里仁书局,1982年,第227~229页。以下《昌谷诗》文出处同此,不再赘注。
[24]川合康三:“以这种感觉性的词或感觉性联想来代替事物的名称,意味着李贺并不把事物作为概念,而是作为‘感觉’来把握,从而以感觉再构成‘物’。”参见[日]川合康三:《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17页。
[25]刘辰翁《评李长吉诗》曰:“诗之难读如此,而作者常呕心何也?樊川反复称道,形容非不极至,独惜理不及《骚》;不知贺所长,正在理外。”引自(南宋)刘辰翁:《须溪集》,《四库全书珍本》四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据《钦定四库全书》本影印,1973年,第53页。
[26]钱锺书:《谈艺录》,台北:书林出版公司,1988年,第51页。
[27]颜昆阳:《从南山诗谈韩愈山水诗的风格》,《学粹》第17卷第1期,1975年,第18~22页。
[28]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