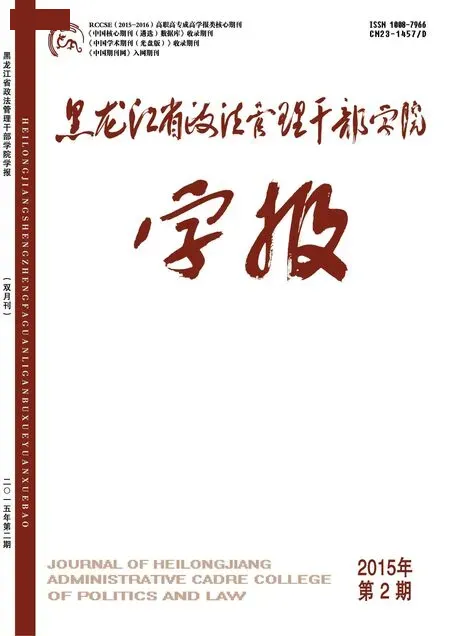家庭自治权的运行模式及其制度保障
李奇才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江苏苏州 215006)
家庭自治权的运行模式及其制度保障
李奇才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江苏苏州 215006)
家庭这一社会基本单元所应该享有的家庭自治权在当代中国大陆受到国家公权力和社会力量的过多干预。和台湾地区相比,家庭自治权在中国大陆的存在状态被破坏得较为严重,保护措施相对不足。特别是在社会城镇化迅速发展的今天,更多的传统熟人社会转变成了陌生的聚居社区,家庭作为社会组成的基本单元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更加凸出。因此需要加深对家庭自治权的运行模式和制度保障的探索,从而为新社会背景下家庭自治权的保护提供理论指导。
家庭自治权;运行模式;法律保障
一、家庭自治权的内涵及其存在意义
(一)家庭自治权的内涵
1.家庭概述
对于“家庭”的定义,从来都是有众多不同的理解。在古代,古希腊人对“家庭”一词的理解是“靠近炉火之处”。这表明一个家庭就是由一群宣布有着同样的圣火,并祭祀共同祖先的人所组成的。罗马人认为,“家庭”是一个由拉丁词派生而来的词,大概是指生活在同一屋顶下的全体奴隶和仆人,后来指在主人统治之下的妻子、儿女及仆人[1]。到了近代,学者对家庭一词的理解更是各有不同。一些心理学家强调家庭是人与人之间的生理结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家庭的形成主要是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必然结果,因此在他们看来,“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2]。社会学家孙本文的认为“所谓家庭,是指夫妇子女等亲属所结合之团体。故家庭成立的条件有三,第一,亲属的结合;第二,包括两代或两代以上之亲属;第三,有比较永久的共同生活”[3]。可以看出,“家庭”一词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时代,都会有不同的定义,很难有同一的界定。但是综合来看,认为可以采一些学者的观点,家庭是以婚姻、血缘关系为主要纽带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
家庭通常是具有不同身份的多个人的集合,是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的存在主要依靠两种关系:横向的婚姻关系和纵向的血缘关系。首先,家庭这一组织形式需要以婚姻为基础而建立,其表现在男女两性的结合,从而构成姻亲关系的存在。其次,家庭是一个社会群体,是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统一体,家庭在婚姻关系的基础上依靠代际的繁衍形成的血亲关系得到衍生和扩大。因此,可以说家庭是自然的产物,自然的血亲关系和世代关系是维系家庭的重要纽带。家庭这一社会组织形式仍然是人类身份关系的延续,通过浓烈的人类情感维系其持续性和稳定性,是尚未被契约融化的领域,所以家庭区别于其他因为社会需要而建立的普通的社会组织。从社会角度看,家庭的存在是需要一定的规范和准则的,可以说,家庭是一种社会制度。家庭制度是由一系列制度组成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其中包括婚姻制度、生育制度等。每一种制度都表现了它对家庭存在的一定功能[4]。
2.家庭自治
家庭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和一种制度存在,必然有其社会功能和责任。那么,家庭在发挥其社会功能、完成其承担的社会责任时,就会表现出对一定范围内家庭事项的治理模式,这一治理模式既可能表现为家庭自治,也可能表现为外在权力的干预。比如在生育和抚养上,家庭是最为普遍的承担监护职责的组织。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就谈道:“当今世界上,我们到处可以看见男女们互相结合成夫妇,生出孩子来,共同把孩子抚育成人。这一套活动我们称之为生育制度。”[5]可以说家庭是人类至今为止抚育未成年人的最普遍也是最有效的社会组织形式。
家庭自治作为一种家庭管理家庭事务的治理模式,其存在基础在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离及个人意思自治。在西方,家庭历来被传统的家庭法视为“私人的城堡”,其存在的核心基础是“家庭自治”,家庭成员对家庭生活范围内的诸多事项享有的自我治理的家庭自主权被当作“自然权利”对待,并受到法律制度的切实保障,使其免受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的侵犯和干预。家庭生活之所以被认为属于私人领域,与家庭的伦理属性以及家庭成员之间血缘的关系密切相关。
家庭自治的理论基础是个人意思自治,个人意思自治在现代社会中被众多国家的民事法律制度所确认,其具有正当性的伦理基础在于“自己决定权”。家庭是由个体组成的,家庭自治是个人自治的自然延伸。
3.家庭自治权
从传统社会的家族看,家庭自治权的内涵十分丰富,主要包括神权和父权,父权又包括夫权、族权和绅权。但是传统社会的家庭自治权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几乎被洗涤的干干净净,其存在空间被公权力占据,现实情况是家庭自治权出于极端弱势和受压制地位,未能得到法律制度的保障,并且缺乏实际的权利运行制度。在现代社会看来,家庭自治权自然应当有其全新的内涵,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家庭私生活的自治权。这些家庭私生活的自主权可以根据日常家庭事务具体化为众多细小的权利形态:监护权、扶养权、继承权、姓名权、隐私权、名誉权、身体健康权、婚姻自由权、同居权、贞操权、生育权、亲权、人身自由、住所决定权(或迁徙自由权)、财产权(非经营性财产)及其他家庭私生活权利。家庭享有的这种对日常家庭范围内的事务的自我治理权应当受到法律制度的保障。
现有法律制度对家庭私领域的事务干涉太多,这就有可能侵犯家庭自治的权利从而侵犯个人的“自己决定权”。因此在法律赋予家庭以自治权的基础上呼吁对家庭自治权的保护及相关家庭自治权运行制度的建立。
(二)家庭自治权的存在意义
家庭自治权存在首先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论语》中有“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6]。这启发我们:法律制度不是万能的,并不是法律制度的触角伸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才会发挥最大的效用、实现最好的社会效果。因此探讨对家庭自治权的保护可以加深我们对法律制度局限性的认识,并深化私权自治的观念。在传统社会中,社会和法律都承认家长或族长的权力,家族被认为是政治、法律之基本单位,以家长或族长为家族的核心而对国家负责。到了现代社会,家庭自治权仍是作为社会最基本组成单元的家庭得以良好存在的基础和灵魂,也是在逻辑上充分发挥家庭这一社会单元活力的必然要求。
家庭自治权的保护存在必要的现实意义。分析传统家庭自治权的内涵和回顾反思近代家庭自治制度发展历史,对完善现代社会家庭管理制度和减少国家公权力对家庭的干预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从而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家庭社会的稳定。法律制度应当重视对家庭自治权的保护,公权力的介入也更应有所保留,这样才能在家庭隐私性事务的处理和公益、家庭自治和法律干预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并最终很好的改变我国家庭自治权遭破坏的现状,以期能进一步有助于对国家管理成本过高和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的解决。
二、台湾家庭会议制度考察
早期台湾地区的家庭自治权也遭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但是台湾社会较早的认识到了这些,让国家公权力积极退出家庭私领域,并建立了保障家庭自治权的相关制度。台湾地区家庭自治权的良好实行主要体现在了当地的亲属会议制度上,亲属会议制度是台湾地区民法中独特的法律制度,其秉承了“法不入家门”的传统。亲属会议权限广泛,对于监护、继承、抚养及亲权等事务行使决定权,并排除公权力的干预,从而比较充分地保证了家庭自治权的实现。
“亲属会议是以亲属为成员所组成的会议,主要以保护亲属利益为目的,同时也是决定或处理有关亲属特定事项的机构。”[7]这主要体现在了台湾地区民法和诉讼法当中几十个条款的规定。这种亲属团体逐渐发展成了社会基本单位,其以亲属成员彼此之间的婚姻、血缘为枢纽,发挥着感情和经济等方面的社会功能,现已成为一种比较理想的家庭自治模式。
亲属会议制度较好地体现了家庭自治观念,其强调家庭内部事务是家庭的隐私,应由家庭内部自行解决;国家则应尊重家庭内部事务的决定,原则上不得介入家庭内部事务。其在台湾地区的存在有着良好的法律基础:台湾地区的民法同样继承了“法不入家门”的传统,不以法律干预家庭纠纷,法院也不主动介入和解决家庭内部纠纷,而赋予亲属会议对于监护、遗产继承、遗嘱、抚养和亲权等事务行使决定权。同时台湾的亲属会议制度具有鲜明的特色:一是亲属会议会员亲属化,台湾亲属会议的会员仅限于亲属,以未成年人、受监护人或继承人的亲属为限,即非亲属不得干预亲属范围内的事务,不得参与亲属会议,在主体上为实现家庭自治奠定了基础。二是亲属会议权限广泛化,与国外的相关立法例相比,台湾亲属会议权限广泛,并作为亲属利益或者处理亲属死亡后特定事项的重要机构而存在,其不仅是监护的监督机关,而且还拥有纠正亲权的滥用、决定抚养方法、选定遗产管理人、认定口授遗嘱的真伪、选定遗嘱执行人、改选遗嘱执行人等权力。三是亲属会议程序民主化,亲属会议并非常设机关,由召集人召集,亲属会议权限的启动因召集人的召集而开始,在遇到特定事项发生时,可随时召集。召集人对亲属会议的会员以书面或口头方式于开会前的相当时间发通知,说明开会的日期、地点及议题,以保证亲属会议程序的民主和公正。同时法律对决议的方式、决议通过的条件、表达异议的途径都有明确规定。四是亲属会议决议自治化,在台湾亲属会议决议形成的过程中,秉承意识自治原则,有出席亲属会议的会员多数决定其决议的内容,各会员只有一个表决权,会议主席亦是如此。亲属会议一旦形成,即当然自始有效,决议事项所涉及的当事人应该自觉遵守[8]。
三、家庭自治权的运行模式与制度保障
(一)家庭自治权的运行模式
家庭自治的正当性不仅仅在于其理论基础,同时也体现在家庭事务的现实处理难度上。家庭是一个以情感和伦理为基础建立的特殊社会组织,因此现代国家的法律规则不适用家庭纠纷的处理,传统的“清官难断家务事”在现代同样存在,这也使得国家法律应当对家庭事务和纠纷的处理在原则上保持回避的态度。但是家庭自治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需要一定的制度模式,根据台湾亲属会议制度的存在现状看,家庭会议制度在充分发挥家庭自治治理模式功能上是比较理想的制度。
家庭自治制度的主体即家庭权利行使的主体,从家庭事务的现实运行状况看,家庭自治权的主体当然包括家长,因为家长在家庭事务的处理中起主导作用,其决定着家庭事务的处理方式。那么家庭自治的主体是否还包括除家长之外的家庭成员呢?针对这个问题,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显然是不同的,在传统社会,家庭成员的地位和人格是严重不平等的,家长和其他家庭成员之间是拥有和被拥有的财产附庸关系,其他家庭成员只是对家长意志的遵守,这决定了传统社会的家庭自治仅仅是家长自治,即传统社会的家庭自治权的主体只是封建家长而不包括其他家庭成员。但是,在现代社会,亲属作为家长的财产附庸的观念已逐渐被新的思想理念所代替,现代法律规定人人平等,享有同等的人格尊严和法律赋予的权利,没有传统社会的尊卑贵贱,人人在法律的世界里原则上都是平等的。因此,现代社会的家庭自治不再是传统的家长的专制性的个人自治,家庭自治的权利主体不仅包括家长,还包括其他具有相应民事权利的家庭成员。
家庭自治制度的对象是家庭范围内的家庭事务和家庭纠纷。家庭自治权的运行就表现在了对一定范围内的家庭事务和家庭纠纷的排除外在组织和个体干预的独自处理权限上。这些家庭事务的范围非常广泛,通常包括家庭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婚姻事务、抚养和赡养事务、家庭教育事务、迁徙、收养、继承、经营、生育等方面的事务,当然还包括由这些家庭事务所引发的各种纠纷。家庭自治的事务只是关乎家庭生活方式、家庭生活计划等内容,但涉及家庭成员的法律权利则不属于家庭自治的范围。
但是,家庭自治的权限在现代法律框架下不是绝对的。因为任何组织和团体都不可能享有绝对的自治权利,家庭这一基本而又特殊的社会组织也不例外。那么家庭自治权的界限究竟何在呢?一般认为,家庭自治权针对家庭范围内的事项发挥自治权限止于公共利益,即以公共利益为界限。如果某一家庭事务不涉及公共利益,则可能完全属于家庭自治权处理权限的范围,家庭成员的决定应当被法律认定为合法行为,应当受到法律制度的保护。众多家庭事务是公民私生活的一部分,公民的私生活属于公民的隐私权范畴,是典型的私权利,公民在行使私权利时也应当享有独立性和自主性。在不涉及公共利益的私人生活空间内,家庭有权拒绝外在组织或个人的干预和介入以维护家庭这一基本单元的独立价值,家庭自治意味着家庭成员可以对自己的家庭私生活依据自己的价值偏好和评价标准做出选择,只要其行为没有损坏他人或社会的利益和权利。这也从反面表明家庭自治权的发挥作用在必要时候仍需外在公权力的干预,但必须是在家庭的私行为危及公共利益或者造成社会危害的情况下。
(二)家庭自治权的法律制度保障
当前大陆的家庭自治权存在状况,和大学自治、基层组织自治相比,在学术上探讨较少,家庭自治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家庭自治权在当下存在较为严重的运行困难的问题,因此,需要加强家庭自治权在法律制度上的保障。
首先,家庭自治权缺乏切实可行的运行制度。这使得家庭自治权没有发挥作用的平台,结果是家庭自治权的实施不够充分,并且未能得到外在制度的保障。在台湾民法中明确规定了专门负责家庭自治权利实施的亲属会议制度,亲属会议被认为是以亲属所组成的会议,为保护亲属利益为目的,议决或处理有关亲属特定事项的机构[9]。其权限涉及监护、遗产管理人的监督、扶养、亲权、遗嘱认定等众多事项。该亲属会议可以就相关家庭领域内的事项形成相关决议,并且决议的形成按照意思自治原则,由出席亲属会议的成员多数决定。亲属会议的每个成员都只有一个同等效力表决权。亲属会议召开必须有三人以上出席,决议的通过必须过半数以上的会员同意,否则只能重新召集会议。因此可以考虑在大陆现有民事法律制度中规定诸如台湾地区亲属会议这样的特色制度,从而为家庭自治权的实际运行奠定制度基础。
其次,根据近代历史的发展状况看,国家公权力过多地加入到家庭私领域中,严重挤压了家庭自治权利发挥作用的空间。比如公权力对家庭私领域内的教育、迁徙、收养、继承、生育等事项存在较多的干预,以至于导致了众多严重的社会后果,如家庭对公权力的极端抵制和社会管理成本过高而效率低下等。所以需要国家公权力退出家庭自治权发挥作用的范围,切实保障家庭自治在解决家庭私领域内事项和纠纷的权利。比如在家庭的迁徙自由上,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二元结构严重影响着人民的迁徙自由权利和教育权利的享有,因此废除二元户口结构对保障家庭迁徙自由权利和受教育权利具有重要意义。还有国家的计划生育制度也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自由,因此公权力对生育自由的过多干预在现实中也导致了众多家庭诸如躲避等消极抵抗。那么,就需要国家公权力从一些家庭事项的私领域中退出,以保障家庭自治权的切实有效运行。
四、结语
细致观察大陆当下家庭自治权的存在和保护状况,以及社会城镇化发展以来家庭自治权呈现出来的新型存在形态,可以清楚看到在公权力盛行的今天家庭自治权作为私权的存在空间和在真实家庭中的尴尬处境。在挖掘这种状况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及缺陷不足之处的基础之上,以比较法的眼光从同样的角度审视台湾地区和西方家庭自治权在社会中运行的状况,审慎地提出家庭会议制度在民事法律制度中的构建和国家公权力在家庭私领域中后退的建议和设想,以期家庭自治权的良好运行并充分发挥家庭这一社会基本单位的活力和社会积极作用。
[1][法]菲斯泰尔·德古朗士.古代城市——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及制度研究[M].吴晓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0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2.
[3]孙本文.社会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4]邓伟志,徐榕.家庭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0-27.
[5]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侧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03.
[6]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12.
[7]何丽新.述评台湾亲属会议制度下的家庭自治[J].台湾研究,2008,(1).
[8]陈棋炎.从民法上亲属会议及家庭纠纷的解决途径[J].台大法学论丛,1985,(1-2).
[9]林菊枝.亲属法新论[M].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6:397.
[责任编辑:刘 庆]
DF7
A
1008-7966(2015)02-0053-03
2014-11-28
江苏省2014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实践创新计划项目(SJLX_0550)
李奇才(1989-),男,湖北十堰人,2013级法律硕士,主要从事民诉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