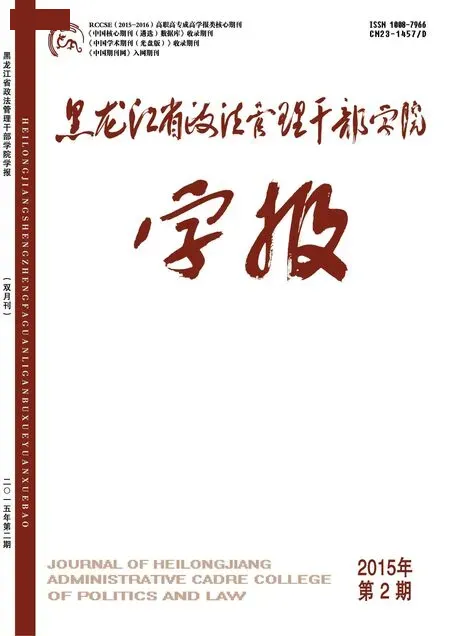论合同形式的发展路径
刘 庆,贾一曦
(1.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哈尔滨150080;2.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哈尔滨150090)
论合同形式的发展路径
刘 庆1,贾一曦2
(1.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哈尔滨150080;2.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哈尔滨150090)
合同的形式,是缔约人明确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表达方式,也是缔约双方对达成协议之合意的表现方法。合同的形式对合同效力产生影响,法定形式的要件通常会决定着合同效力的走向。研究合同形式要件的发展历史,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厘清合同发展的走向、趋势,另一方面,可以帮助立法者平衡合同形式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后果。
合同形式;适用范围;合同效力
合同形式作为合同内容的载体,从古至今一直未离开法学者的关注,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合同形式的关注程度不同而已。合同,是双方或多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最初表现为一种社会习惯,后来逐步被法律所认可,上升为法律的形式,但现代合同法通常认为,“意思自治”是合同的灵魂所在。而合同的形式则作为合意的外在表现,在某些情况下会直接影响合同的效力,因此一直被法学者所关注。
一、合同形式的发展史
纵观合同形式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合同形式的发展路径:从合同法定形式的过度关注到意思自由的泛滥,再到合同法定形式的重生。
(一)合同形式的过度法定化时期
在古代合同法领域中,因为经济的落后,彼此之间的信任程度极低,对文字掌握的程度极弱以及对神灵的敬畏等因素的存在,导致法律要求经济主体之间订立合同时,必须采用特定的法定方式,这些方式的表现多样化,各个国家均有不同,但相同的是,一旦疏于合同的法定形式,则合同必定无效。对合同形式的刻意追求,使人们往往忽略了合同本身内容的健全,而将关注点局限于订立合同本身的过程中,所以,法律对合同形式的过度追求,并不利于合同本身的发展,一方面阻碍了立法者的视野,无法关注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内容;二是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对合同形式的刻意、呆板的追求将阻碍合同订立的数量,影响经济效率的提高。
法兰克王国时期(公元5-9世纪),交付标的物要用一定的语言。象征性的动作配合。违反法定的程序则合同无效,订立土地转让合同。在证人面前。双方当事人要用语言公开表示转让的意思。由于土地不可直接交付。出卖人把象征土地的草皮、护手甲、长矛等代替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合同方告成立。有的民族用身体某部位接触或用舌头舔标的物用以表示交换顺利完成[1]。而早期罗马法对合同形式要求最为完备,曾对合同行为规定了烦琐的套语和行为程式①如依照市民法订立保证契约,“允诺保证”(sponsio)的固定表达语言为:“允诺否?”“允诺”。。在曼兮帕蓄(mancipatio)中,获得某种财产的基本条件是受让人需要得到被转让的物品,并要以特定的方式发表意见。所有这些都须在转让人、独立的主持公平的公证人和五位见证人在场的情况下作出[2]。
而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形式的法定要件,最早有据可查起始于西周时期,当时的借贷合同称作傅别,买卖合同称作质剂,均将合同内容写于木片或竹片上,一分为二,分别为如依照市民法订立保证契约,“允诺保证”(sponsio)的固定表达语言为:“允诺否?”“允诺”。双方持有,合则见全文。其中的质剂还有长短之要求,最长不过二尺,最短不少于六寸,牛马、奴隶买卖用长券,兵器、珍宝买卖用短券。而赠与合同成为书契。通常,均要求订立时需要见证人在场。
可见,合同法发展的早期,立法者对合同形式过度关注,使得合同形式直接决定了合同效力的走向,并成为合同产生预期法律效果的直接根据,正如《学说汇纂》所述,“仪式不但和允约本身有同样的重要性,仪式甚至比允约重要”。当然,这种立法的表述和要求,在那个经济欠发达,诚信制度尚未建立的早期人类社会中,将会促使人们逐步形成对允诺的尊重和遵守,对早期社会中的信用观念的建立和经济的稳定是大有裨益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信用制度的建立,立法者的关注必将会有所改变,从对合同形式的过度关注转向对合同内容及合同法律关系的建立和规制上,以追求合同实质上的公平和正义。
(二)合同形式自由主义的泛化时期
而到了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经济类型的种类化和成型化,使得经济发展要求合同形式必须便捷化,摆脱僵硬、刻板的形式要求的束缚,资本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资产阶级思想上树立起了“自由”的观念,体现在合同领域中,要求合同的形式也要自由化。合同自由原则的建立,意味着要在立法上体现对自由的尊重和渴望,因此,合同的形式变得不是那么刻板和统一,合同法上更加关注的是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法国民法典》第1101条规定:“合同为一种合意,依此合意,一人或数人对于其他一人或数人负担给付、作为或不作为的债务。”可见,法国民法典明确了契约“仅得依当事人相互同意”而成立,从根本上摒弃了罗马契约法中重形式轻意思的观念,确立了以非要式行为为原则,以要式行为为例外的合同形式制度[3]。
合同自由原则的建立,合同形式简易化和合同内容的随意化,使得大量的合同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只要是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合同的形式和权利义务的约定便具有法律拘束力,这是合同自由原则的积极面,但不受任何限制的契约自由,可能被滥用。尤其是在订立合同时,双方主体经济实力的差异,或是合同境况的不同,可能会使强势一方迫使弱势一方订立不公平的合同,若仅仅因“合同自由”而确定合同的成立生效,势必要产生合同不公之现象,这将损害合同正义之原则。因此,毫无限制的合同自由将会产生更大的不自由。
(三)合同形式的有序化
正是基于合同正义与合同自由原则的对撞,迫使立法者必须正视合同自由的适用范围,于是合同形式的法定化便得以复兴。但这相对于合同早期的“合同形式法定化”是截然不同的,在近现代,各国均通过立法,一方面表明对合同自由的尊重,一方面要防止合同自由的滥用,既确立了不要式合同,又规定了少量的要式合同。
例如,英国合同法在传统上,将合同形式分为三类,即盖印合同、简单合同和记录合同。但现代社会里,当事人通常可以在合同生效前签署封印,有的甚至不用封印,只需在合同盖好的盖印处签字,即被认为具有签字盖章的效力。盖印合同原则上只要交付受让人即具有法律效力,尽管受益人可能并不知道合同的内容[4]。简单合同包括书面合同、口头合同和默示合同。简单合同的特点在于,只有对价的支持合同才生效。对于法律直接要求的书面形式,不可欠缺,否则直接影响合同的效力,而对于口头形式的合同,有时候一会也会要求只有提供书面证据时,方可提起诉讼。而记录合同,是通过法院判决、具结和其他强制措施,以确定当事人之间具有债权债务关系而产生的合同。严格讲,这并不属于合同范畴,而是司法判决强加给当事人的各种义务。
而我国1999年《合同法》第10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现行立法相较于其前身《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而言,对合同形式的改变可以说是颠覆性的。这三部合同法遵循的是合同形式的法定主义,强调只有即时清结的合同才可以成立口头形式,可以说现代立法改变了过去传统的束缚,强调市场经济下合同自由的理念,建立起了“从重形式到重内容,从重文义到重意思,从单一的书面形式要求到多种类的合同形式”[5]。
法律对多种合同形式的认可,一方面体现了合同形式自由的要求,一方面也体现了国家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干预和保障。但我们认为,合同法毕竟是私法,国家只有为了公共利益的考量,才可以公权力的方式介入私权利领域进行必要而适当的管理,否则就涉及公权力的滥用。因此,在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的对撞下,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对撞下,现代合同法需要建立“以不要式合同为主、以要式合同为辅”的合同形式模式。
二、影响合同形式的要素
(一)合同形式的多样化
合同形式最早表现为书面形式,即将合同内容一般刻制在木片或竹板上,之后纸张的出现,形成了最为基本的书面合同,再之后允许出现口头和默示形式的合同,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合同形式更为多样化,形成了扩张的趋势,出现了传真形式、电子邮件、电子商务合同等多种形式。多种合同形式的出现,为现代合同订立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方式,但也给合同内容的认定带来了不便,因此,对不同形式的合同有必要进行适当的规制。
如我国《合同法》第16条规定:“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该条即是我国合同法对电子邮件合同的基本规制,一方面表明了立法对合同形式种类扩张的容忍或接受,一方面通过立法规制避免交易中的矛盾纠纷,使诉讼举证有据可查。
(二)影响合同形式的基本要素
总体来说,合同形式按照是否具备一定的形式要件,分为要式合同和不要式合同。作为要式合同而言,其产生依据要么是法律直接规定的,如我国的融资租赁合同、建设工程合同、超过六个月的租赁合同等均要求采用书面形式;要么是当事人特殊约定的,对合同形式有着特殊的追求。通常情况下,影响合同法定形式的要素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主体要素
合同的主体在进行合同订立时,是处于同一法律维度之下的,法律地位平等。自然人、法人、其他社会团体都可以成为合同的主体,但当国家机关成为买卖合同的主体时,为了保证行政职能的正确行使,以及维护国家利益的需求,我国立法机构制定了《政府采购法》,其第44条对政府采购合同的形式作出了特别规定,即“政府采购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因此,国家机关的主体特殊性,决定了其从事民事活动时,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的合同。
2.标的价格
早在1566年,法国《穆兰法令》(OrdonnancedeMoulinsde 1566)第54条就作出了“超过100英镑的合同禁止以口头证据证明合同的存在”的规定。法国民法典保留了这一传统。英国1677年《防止欺诈和伪证法》第17条规定:“标的金额达到或者超过10英镑的货物买卖合同需采用书面形式。”
书面合同具有较强的证明能力,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一旦发生争议,合同书可以作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于双方当事人订立的标的额较大的合同,通常我们建议当事人采用书面形式。虽然我国法律并没有对具体达到多少数额而要求签订书面形式,但我们采用了较为抽象的立法方式,如《招标投标法》第57条规定“招标投标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拍卖法》第52条规定“拍卖成交后,拍卖人和买受人应当签订确认书”。这两部法律涉及的招标投标和拍卖的标的物价款都较高,对当事人有着较大的影响,因此要求采用书面形式,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在中国,不动产一直都是直接影响当事人生存或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不动产交易活动中,法律要求采用书面形式。如不动产抵押、不动产买卖合同等。需要说明的是,《物权法》并没有规定不动产买卖需要订立书面形式,只是规定在过户时必须采用登记方式,而登记时需要提供双方的买卖合同,间接地对不动产买卖合同的形式进行了书面的规制。
3.合同性质
合同按照双方承担的权利义务是否对等,分为单务合同和双务合同。单务合同具有权利义务的不对等性,因此,这类合同的履行主要依靠当事人的信用为支撑基础,典型的单务合同包括赠与合同和担保合同。合同形式的强制性要求通常针对单务合同而言的,立法者的目的是要通过强制性书面形式甚至公证的形式,时刻警示无偿一方履行其作出的允诺。如我国《担保法》、《物权法》都对担保性质的合同,如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定金合同作出书面形式的要求。而对于赠与合同,法律并无强制性规定,仍为不要式合同,但对于采用了公证形式的赠与合同,则具有不可任意撤销的效力。在德国,对于赠与合同则规定需要公证方产生效力。在英国,若想赠与的允诺获得法律的执行,契据(修改后的“盖印”合同)仍然是首选的方式。因此,合同性质从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合同形式的类型。
4.合同履行时间
根据合同的履行时间的长短,可以分为即时清结合同和非即时清结合同,即时清结合同是合同订立、生效和履行完毕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这类合同以信誉为支撑基础,一般较少发生纠纷,为了合同订立的便捷、经济效率的提高,通常对即时清结合同采用不要式的立法方式;而对于非即时清结合同,通常由于合同生效时间和履行时间存在间隔或者履行期限较长或者履行分为多次,时间的持久性特点可能对当事人的合同意思表示产生模糊之后果,信用基础会有发生动摇的可能,若采用口头方式,容易造成权利义务关系不明,产生法律纠纷,建议采用要式合同,即书面形式的合同,便于明确相关的权利义务关系,减少不必要的合同风险。最为常见的保险合同,便是基于履行时间的长远而均采用书面形式。当然,履行时间的长短,并不能作为直接决定合同法定形式的关键性理由,但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对“租赁合同”采取了相同的立法方式。即,对于达到一定租赁期的租赁合同,法律要求当事人需要订立书面形式的合同,否则视为不定期租赁。不定期租赁意味着,当事人虽然没有采用书面形式,但并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只是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即双方当事人可以随时行使单方解除权,而无须承担违约责任。如我国《合同法》第251条规定:“租赁期限六个月以上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的,视为不定期租赁。”
5.公共秩序
大陆法系的公共秩序,在英美法系中相当于公共政策。公共秩序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往往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基于国家政策的需要,如公众健康、安全、道德以及一般的社会福利都会包含其中,如消费合同和劳动合同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均要求采用书面形式,对于集体用工合同还需要经过劳动部门的鉴证。但我们认为,各个秩序虽然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但概念的外延不应该过大,应该严格限制在国家和公共利益的范围中,否则会涉嫌公权力借助于“公共秩序”或“公共利益”的影响,而过分干预合同形式的制定,导致之私权利的适用受损,妨碍合同自由原则的贯彻。
总之,影响合同形式的因素很多,从总体上看,合同形式主要以不要式合同为主,虽然基于合同交易的安全考量,存在一定种类的要式合同,但合同形式的发展趋势还是遵循了“纯粹的形式主义——合同形式的自由化——形式主义的复兴”这一发展方向。但笔者认为,政府的有限思维不可能为市场经济下越来越多的交易形式进行逐一立法,立法者需要做的是通过规定出行为的规则,让人们在这种秩序下做出具体情势下的各自决策,以私法为基础构建的市场经济才会得以持续发展。如《联合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第11条仍明确规定:“销售合同无须以书面订立或书面证明,在形式方面也不受任何其他条件的限制。”《欧州合同法原则》第101条第二款规定:“合同无须最终形成书面的形式,或以书面的形式证明,或是符合其他的形式要件。合同可采用任何方式加以证明,包括证人。”
因此,笔者认为立法对合同形式施以过多的强制均是不适当的。而我国,由于历史原因,政府对私权的干预不是过少而是过多,从促进交易发展,保护当事人的利益的角度考虑,我们均应对我国的合同法定形式及其强制进行检讨[6]。
三、形式要件欠缺的后果及治愈理论
(一)合同形式要件欠缺的后果
要式合同,是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的合同。前者称为法定之要式合同,后者称为约定之要式合同。广义的“要式”所表现的形式包括书面形式,也包括登记、审批、公证、鉴证等形式。若要欠缺合同的法定形式,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我们认为,欠缺合同的法定形式,意味着合同的订立方式不符合国家意志的基本评价,往往认定合同是尚未生效的,即使双方当事人已经履行了合同的义务。那么,法律保护调节的目标是事实上已经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还是合同的外在形式要件呢?目前,这个问题已经通过立法的方式给予了肯定的答案,即合同法调整的是业已存在的合同法律关系,即使存在形式要件的瑕疵也可适度容忍,但法律的容忍是需要限度的,如果尚未建立起实质的债权债务关系,则欠缺形式要件,将不能导致合同的成立。《合同法》第36条规定和第37条规定便是明证。这种立法表明,合同立法注重的是合同实质关系的调控。
对于登记、审批要件的欠缺,会产生何种效力呢?这要区分不同立法情况,我国法律对于合同“登记”的目的有两种,第一种是为了便于有关机关的管理,这是一种行政管理上的需求,即登记的目的是备案,不登记并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和效力。如公安部要求房屋租赁合同应向房屋所在地的派出所进行登记备案。第二种登记时具有效力性的登记,即不登记将直接导致合同不能生效的后果。如《专利法》第10条第三款规定:“转让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登记,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予以公告。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转让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对于欠缺形式要件会产生何种效力后果,《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9条规定:“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对于强制性效力性规定的区分方法,王利明教授提出三分法:第一,法律、法规规定违反该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的,为当然的效力性规定。第二,法律、法规虽然没有规定:违反其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但违反该规定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这也属于效力性规定。第三,法律、法规没有规定:违反其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虽然违反该规定,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并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是损害当事人利益的,属于取缔性规定(管理性规定)。
(二)合同形式要件欠缺的治愈理论
对于我国《合同法》在采用了要式合同的规定后,又规定了合同形式要件的治愈理论,即即使合同欠缺形式要件,但只要当事人完成合同义务或者完成合同部分义务,那么合同形式的欠缺并不会影响和成立,其治愈的法律基础何在?对此我们可以考察德国比较发达的治愈研究理论。
一是方式目的完成说。该说认为,要式仅为满足一定目的之工具,当该目的已通过其他方法达成,或已失其意义时,则方式的要求可被放弃。换言之,当合同已经通过履行实现了合同目的,那么合同要式所追求的警示及证明等目的已经达成,因而要式的强行性规定便不再成为必要。拉伦茨(Larenz)认为,“在治愈规定之情形,法律将保护因法律行为承担义务的当事人免遭操之过急之害视为形式要件的主要目的。如果当事人嗣后履行了他的义务,那么这个目的也就告成了。法律允许形式瑕疵在事后得到补正”[7]。
二是信赖保护说。该说认为,即使合同形式要件欠缺,但由于当事人基于对合同的合理信赖而履行了合同义务,那么,为了维护当事人间的信赖利益,需要对已经形成的合同法律关系予以保护,此时,形式要件的欠缺便不再成为合同不成立的理由了。笔者认为,信赖保护说将更能体现现代合同法的进步理念,合同目的说的功能在于表现合同形式的警示功能,但相对于当事人间的信赖基础,这种警示功能就显得渺小而卑微了。正如拉伦次所说,“治愈的基础普遍在于保护对合同有效性的信赖,并禁止事后的矛盾行为破坏这样的信赖”[8],因此,信赖保护说应成为合同形式要件治愈理论的奠基石。
我国《合同法》对于合同形式欠缺的治愈理论体现在第36条和第37条的立法规定上。第36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第37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综上所述,合同形式的发展经历了从形式刻板到形式放任自由,再到有效规制的发展历程,一方面表明合同形式的发展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现代合同法形式的发展态势是以服务于合同内容为根本目的的。随着合同种类的多样化、复杂化,合同的形式也会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立法在做必要规制时要避免公权力过度干涉私权利的情况出现,尊重私法自治、合同自由的立法原则。
[1]谭亚光.合同形式及其法律效力的演变[J].法制天地,2006,(7).
[2]江平,米健.罗马法基础[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237.
[3]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6-17.
[4]何宝玉.英国合同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78.
[5]谢晓尧,宋婕,陈斯.新合同法要求[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9:76.
[6]张红.合同形式的法律评价[J].贵州大学学报,2004,(6).
[7][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M].王晓晔,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563-564.
[8]W·Lorenz,Das Problem derAufrechterhaltung formnichtigerSchuldvertr?ge,1957,S.381f.f
[责任编辑:李洪杰]
DF525
A
1008-7966(2015)02-0062-04
2014-11-22
刘庆(1976-),女,河北吴桥人,副教授,从事民商法学研究;贾一曦(1985-),女,河北武安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半岛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