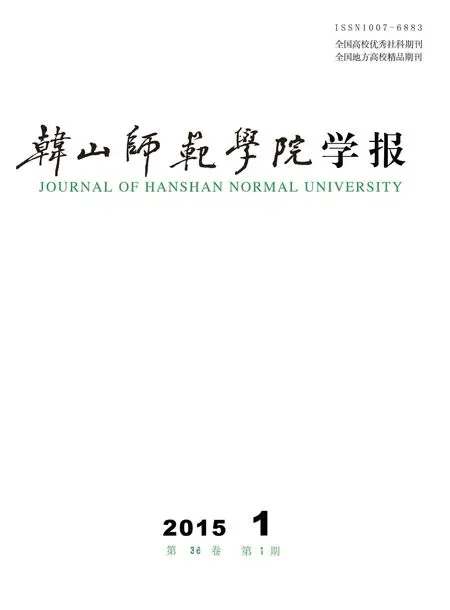艾约瑟史学思想与对西方史学的绍介
舒习龙,陈舒玉
(韩山师范学院历史系,广东潮州 521041)
艾约瑟史学思想与对西方史学的绍介
舒习龙,陈舒玉
(韩山师范学院历史系,广东潮州521041)
“欧洲中心论”成为艾约瑟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以此为视角和立论的出发点,发表他对中西史学的观点和见解,对西方古典史学和近代史学的独特性和价值引以为豪。艾约瑟是从思想史自身的脉络来体察唐宋之际思想史上的巨大变革的,其“唐宋思想变革论”的提出,主要得益于道教、佛教和儒教的融合,儒生借取道教、佛教的“哲学观想”,从而赋予儒家哲学形上学的色彩,这种思想与中古儒家思想相异其趣,体现了较强的思想史范式转换的特色。艾约瑟对西方古典史学怀有浓厚的兴趣,抱有温情的敬意,认为研究西方史学应从古典史学开始,古典史学是西方史学的源头,故他对古希腊、古罗马著名史家皆有论述和评析。艾约瑟的史学素养不仅仅表现在对古希腊罗马古典史学的介绍,同时也表现在他对西方史学最新成果的分析和阐释,为沟通中西史学的交流和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
艾约瑟;“欧洲中心论”;“唐宋思想变革论”;西方史学输入
约瑟夫·埃德金斯(Joseph Edkins,1823~1905年),中文名艾约瑟,字迪瑾,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汉学家。作为出名的“中国通”汉学家,他对中国历史、宗教、文化、语言等抱有浓厚的兴趣,同时他又从宣传西方文化和服务于传教策略的角度,将西方的古典史学和近代史学、西方的科学技术、地理知识等传播到中国,在沟通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影响。本文拟着重对艾约瑟的史学观点、史学见解以及他在引进西方古典史学和近代史学中的作用做细致的梳理,希望对推进艾约瑟史学研究有所裨益。
一、艾约瑟的史学思想
艾约瑟深受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观点的影响,故而他提出了“中学西源”的观点。1870年,艾约瑟在《教会新报》上发表文章,他把《书经》、《礼记》等儒家经典与《圣经·创世记》有关上古的记载相比较,发现书中所载天文、水利、国政、民情、风俗、盲语、农事、工作等等,俱可彼此互证,从而得出中西学虽异而源实同的结论[1]。在《论〈列子·汤问篇〉意多出于波斯印度》一文中,他又说:《列子·汤问篇》中一些故事“为寓言无疑”,“其说皆出于幻想凿空而为”。而“波斯、印度之风俗多喜作此恍惚悠谬、不可究诘之谈,而巫术、医卜之徒从而传之于四方。西域为最近,则先传于西域,继而渐及于中国,《列子》之言要即引其绪余”[2]。在《论黄帝》一文中,他则指出:“中土各国皆有吉凶相应之星,占之以测国中后日所有吉凶之事。而此事实先见于巴比伦古书。即如五行,亦波斯古书所载。以此观之,则《素问》地球悬于空中云云,先时自必从巴比伦渐推渐广,得入中国。阅《旧约·但以利》第二章所设之官,分巫觋、太史、博士,与中土分立公孤、六宫相似,可知中国古时与西国风俗本自相通,而从西方以至中国为无疑义,明也。”[3]在《分野之说始周宣王时考》一文中,他言道:分野、占星之说虽于中国古书中屡有所见,但“非华所自造”,“而《洪范》五行之说亦自西方来”,故分野、占星之说,“其来由滥觞于波斯”[4]。
艾约瑟等人提出“中学西源”说,其意图在于通过对中西文化同出一源的阐释来减轻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敌对情绪,为基督教的在华传播扫除障碍。传教士论证中学西源的惯常手法是将早期儒家经典与《圣经》中的记载相较,以证明中国文化实传自西方。艾约瑟鼓吹“中学西源”,其意在于以儒家文化附合基督教文化,试图以中西文化同源来说服儒生放弃对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敌视,但是中学西源说表现出的西方中心主义确是艾约瑟历史观的真实写照。
西方中心主义在18世纪中后期西欧思想家那里,已经以欧洲的文明、进步与东方的落后、停滞、没有发展而表现出来。19世纪,西方社会更把这种思想加以发挥,认为西方白人是人类的优等公民与代表,世界精神的体现者,东方各国没有发展,处在世界历史之外,并且成为白人的负担[5]。18世纪的思想家以人类的普遍理性和进步的观念来衡量世界诸种文明的优劣,他们认为西方文明代表着人类理性和进步发展的方向。19世纪的西方思想家则将人类理性和进步观念加以普遍化、绝对化,从而掩盖了欧洲以外的世界,导致其他文明从属于西方文明,处于“世界历史”之外了。正如西方史家所说:“欧洲的主子在所有大陆上都接受了弱小种族的效忠,认为这种效忠是事物神性的一部分——是‘适者生存’的必然结果。在印度,他们被恭敬地称为大人,在中东被称为先生,在非洲被称为老爷,在拉丁美洲被称为恩主。”[6]19世纪西方中心观的特点可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把特殊的东西说成是普遍的东西,再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欧洲中心论”成为艾约瑟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以此为视角和立论的出发点,发表他对中西史学的观点和见解,对西方古典史学和近代史学的独特性和价值引以为豪。比如关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艾约瑟一方面认为,欧洲人早在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时代就已普遍使用纸和墨水,并且很可能通过贸易途径把它们带到中国;但另一方面他又声称不能认为纸和墨水是从西方输入中国的,这种自相矛盾的观点实际上与他的“欧洲中心论”的观点有着天然的耦合关系。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提出以下观点:“中国人发明了纸,并从印度和罗马帝国获得一些启发,这帮助他们制造出了各种纸张。”[7]这样的立论是与历史的真实不符合的,说明他在观察中西历史文化时,所采用的视角是常以欧洲文化优越论来审视其他文化。
艾约瑟对中国的历史和宗教也进行过较深入、全面的考察和研究,在梳理华北秘密宗教的基础上,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唐宋变革论”的史学思想。晚出的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主要是从“历史分期”的角度提出的。他说:“由于过去的历史家大多以朝代区划时代,所以唐宋和元明清等都成为通用语,但从学术上来说这样的区划法有更改的必要。不过,为了便于讨论,在这里暂且按照普通的历史区划法,使用唐宋时代一词,尝试综合说明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情形。”[8]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主要是受到欧洲人的传统分期法的影响而提出的观点。而艾约瑟的“唐宋变革论”主要是从思想史自身的脉络以及印刷工具的革命角度来立论的,尽管其思想还不够成熟、系统,但其思想的主旨已经初具雏形。早在1886年,艾约瑟就在《教务杂志》上发表了《华北的秘密教派》一文,该文主要考察晚清流行于山东地区的秘密宗教流派,提出了“教派”的重要概念。该文在梳理华北教派的过程中,以敏锐的眼光注意到“第十世纪”思想的重大变化,他指出:“第十世纪是中国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期,它对以后的两个世纪造成了重要影响。彼时著名道士陈抟的出现以及他和宋太祖的过从给儒生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当然也是他们十分需要的。这些儒生本来致力于诗歌创作和佛学,可是这时候开始转向哲学的观想。道教和儒教开始走向融合,近代中国思想受到这种融合以及佛教哲学的极大影响。”①转引自陈怀宇:《英国汉学家艾约瑟的“唐宋思想变革”说》,《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4期,第91页。“唐宋思想变革论”的提出,主要得益于道教、佛教和儒教的融合,儒生借取道教、佛教的“哲学观想”,从而赋予儒家哲学形上学的色彩,这种思想与中古儒家思想相异其趣,体现了较强的思想史范式转换的特色,故艾约瑟认为“第十世纪是中国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期,它对以后的两个世纪造成了重要影响”,这种认识是具有卓识的。所以,我们认为,艾约瑟是从思想史自身的脉络来体察唐宋之际思想史上的巨大变革的,他的贡献也正在于此。
除此之外,艾约瑟还是进化论思想和考古学理论知识的积极输入者。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是和“西方的冲击”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被当作应对“西方的冲击”的法宝。它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内核在当时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契合了人们忧国救亡、寻求变革的社会心理。艾约瑟的《西学述略》也介绍过一些拉马克和达尔文的有关自然界进化和人猿同祖的观点。艾约瑟及《申报》、《万国公报》等也介绍过达尔文的学说[9]。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从地质学开始。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是从西方传入的,始于19世纪下半叶。当时中西接触日趋频繁,西方传教士来华人数逐年增多,同时也有部分中国学人走出国门,正是他们把考古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早期以传达西方的最新考古消息为主,随后考古学理论知识也逐渐输入。1886年,艾约瑟的《西学述略》第6卷《史学》,如“释古文以识古史”、“泰西诸国推埃及最古”、“巴比伦古迹”等内容,均与考古学有一定关联。他说考古学家在埃及“即于既倒塌之土石堆中搜取有文字之瓦砾石块”,识其文字而知埃及“精于文学,勤于贸易,以及古帝王之实事”[10]55。
二、艾约瑟对西方史学的输入
艾约瑟对西方古典史学怀有浓厚的兴趣,抱有温情的敬意,认为研究西方史学应从古典史学开始,古典史学是西方史学的源头,故从墨海书馆开始即有志于引进和介绍古希腊、古罗马著名史家和史学。本此目的,他较早向中国史家和学人介绍了希罗多德及其撰著的《历史》。可以说艾约瑟的《黑陆独都传》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西方史学和史家的窗口。在该文中,艾约瑟介绍了希罗多德的生平见识、修史始末、史料来源、《历史》编纂的宗旨和思想、《历史》的内容和特色等。他指出希罗多德是“希腊作史之祖也”,“小亚细亚哈里加拿苏人,生于耶稣前四百八十四年。……幼时喜诵和马所作之诗。……所作之史,凡九卷,皆记波人与希人战事,至希人自亚西亚海滨凯旋,而此书终矣,事止于耶稣前四百五十六年,后屡加删改始成。”“作史既成,宣诵于阿伦比亚希(奥林匹亚)之文士咸会,辄魁其曹。会众称贺,声情激越,士居提代闻之,悲不自胜,其感人如此。”[11]从中可见,艾约瑟对希罗多德的生平和修史情况做了初步的钩录。艾约瑟认为,希罗多德著史十分重视实地考察、亲身践履搜访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性:“作此史时居于以大利之土里依,先是出游四方,周知列邦山川险要、风土人情,名城废垒、古庙丛祠,靡不遍览,远至黑海、阿拉尔海。……足迹所至,手笔甚勤,凡有记载,委曲详尽,实事求是,古来作史者,此为第一。”[11]因为实地考察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故使得《历史》成为古典史学“求真”的信史,“于其所目睹者,言之详且确也,至今有至埃及、希腊、亚西亚诸国者,考之尤信。”[11]对于希罗多德史学的特色,艾约瑟也有非常精当的评论:“黑陆独都喜谈奇异,见闻广,多学识。”[11]“闻见博洽,富有学识”,这是对希罗多德史学的高度赞誉。对于希罗多德的叙事手法和技巧,艾约瑟也做了鲜明的描绘与揭示:“若其用笔,喜仿古法,水到渠成,自在流出,绝无斧凿痕迹。希腊腊顶(拉丁)载籍极博,惟此书不务艰深,达意而止,谐谑间作,天真烂漫,如婴儿语,故人多喜读之”[11]。历史表述务在简约和达意,希罗多德舍拉丁文的“艰深”,而采取古法“简约”的表现手法,反映了他在历史编纂方面的高超技巧。艾约瑟在介绍和评价希罗多德史学的特色和成就的同时,也非常客观和中允地评价希罗多德史学的不足,“喜书敬鬼神之事,较他史尤多。”又说:“第过信人言耳。……希国故事,彼仅据一家言,未遑他引。”[11]应该说,艾约瑟的评价是比较中肯和到位的。
艾约瑟对于修昔底德及其史学的梳理和评论,同样十分精彩和到位。在《士居提代传》中,艾约瑟精心地梳理了修昔底德的生平行实,将修昔底德的史学放在古希腊广阔的时代背景下加以考察,据此总结《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生平行实和主要内容:“士居提代者,雅典国人,希腊作史名家也。生于耶稣前471年。当雅典国与士巴达国征战二十七年之始,年已四十矣。书此战事以成史记。在外二十年,客士巴达境内。四百有三年,归于雅典后,国人杀之于德拉基。其作史也,出于耳闻目见,恒坐德拉基大树下,成是书凡八卷。前七卷中,载卿士议政,将帅誓师之辞。第八卷无之。有疑其文劣,非出一人者,或云其女续成之。首卷论两国战争为希腊一大事。”[12]“惟时都君为武弁,亲历行间,凡所见闻,皆极真确”,“其史乃即当时希腊境内诸城称兵互相攻击,竭虑殚精,以详考其间战争诸事而作也”。艾约瑟对修昔底德史学特点的评论颇有卓识,见解独到,他说:“其旨以兵刑得失为国家治乱之原。其可贵而垂远在此。……又道理明通,俾人人知所观感。如论雅典疾疫事,雅典以兵船攻破西西里之叙拉古事是也。史家文笔往往好以己意出奇,士居提代亦然。字字遒炼,力破余地,为希腊群籍中难读之书,日久且莫识其文所在。近泰西诸国翻译此书者颇多。”[12]修昔底德被誉为西方史学“政治史之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被称为西方政治军事史的典范之作,开创了西方政治叙事史的传统。正因为修昔底德秉承政治和战争是历史叙述的中心,所以他的史学体现了鲜明的政治叙事史的特点。艾约瑟评价修昔底德史学,“其旨以兵刑得失为国家治乱之原”,非常准确地概括了修昔底德史学的特色。
对于古希腊、古罗马其他著名史家,艾约瑟也有初步的勾勒和介绍。他认为,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三位史家是“古希腊三大史家”,开创了信史时代,将他们比作中国的司马迁和班固。他认为色诺芬:“赛挪芬所纪,记当巴西王薨,其世子之第名古烈者,外募希腊万人为兵,入巴西国与兄争立嗣,兄弟相约,皆挺身亲出博战,古烈遂为其兄所杀,希腊人亦皆自退归,而时赛挪芬实为之帅,故所著之师,即名之曰万军,言旋实录”。①艾约瑟:《希腊著述经史诸士》,《欧洲史略》。转引自赵少峰:《“西学启蒙丛书”中的西方史学及学界回应》,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第29页。对于“伯路大孤”(普鲁塔克)所著《希腊罗马名人传》,艾约瑟也有较高的评价:“择取希腊与罗马伟人之彼此才德伯仲功业相侔者,如或皆长于治国或皆善于治军,皆两两相较,分为立传,考定优劣,以示后人。”[10]55
艾约瑟对西方古典史学的引进和介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正如张广智先生所言:“从接受史学的角度而言,一位西方史家,一部西方名著,一种西方史学流派,一股西方史学思潮等,它何时传入中国,通过何种途径输入的,输入后又产生了怎样的回响,这种回响是微弱的还是强烈的,等等,都应当引起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家的关注,都应当从输入的接受环境与读者的“期待视野”中找到解释。……倘舍去了对西方史学输入史的研究,那么对于西方史学史的研究,它终究是一种缺憾。”[13]我们认为,梳理艾约瑟输入西方古典史学的路径和反响,是深化中西史学互动交融非常重要的一环。
艾约瑟的史学素养不仅仅表现在对古希腊罗马古典史学的介绍,同时也表现在他对西方史学最新成果的分析和阐释。《英文诸史》一目对西方近代以来的重要历史著作和史学家的介绍十分精彩:“凡以英文著史之人,计其间之杰出者甚多。如英人休摩②休摩,即指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年4月26日~1776年8月25日)是苏格兰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被视为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西方哲学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所著《英格兰史》在西方史学界颇负盛名。所著英史,则叙载清真兼之雅正。基本③“基本”即18世纪西方富有盛名的史学家“爱德华·吉本”,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至今仍是西方史学的经典,该书在当时成为英格兰历史学界的基础著作长达60至70年。所著后罗马史则器度雍容,亦复华丽。近又有马高来④马高来,即指马考莱、麦考莱(Macaulay,Thomas Babington,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所著《英国史》着重记述自1685年詹姆斯二世即位至1702年威廉三世逝世17年间的历史。者,其所著之后英史,则字句警炼,几于突逾前人矣。”[10]55艾约瑟在近代英文史家中首推休谟,是非常具有远见卓识的。休谟的《英格兰史》主要梳理和解读英国社会从“野蛮社会”演变发展到1688年“自由社会”的故事。休谟写作《英格兰史》的直接目标是为了消除“党派仇恨”,主要目的是“教育现代英国人公平和真正温和讨论党派政治。”休谟通过对英国历史发展的描述与评析,揭示出社会的正义规则与政治权威在自由社会形成过程中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辩证发展关系。该著在休谟生前即出版了七版,成为英国及北美殖民地史教学领域的标准教科书,在休谟辞世以后,仍然持续产生了半个多世纪的影响。在美国史家中,艾约瑟也有所点评:“班哥罗夫著有《美史》,摩德利著有《和兰开国记》,皆能详明通博,不愧作家。兹考摩、班二公所著之史,概于民主之国三复其政治焉。”[10]艾约瑟对欧美著名史家的选择,是经过精心的考虑的,目的是使中国读者能够通过阅读,尽快地熟悉欧美史学的发展趋势。文廷式似乎阅读过艾约瑟对近代西方史学的介绍,因为他介绍的思路与口吻与艾氏一脉相承,他写到:“今计凡以英文著史之人,其间杰出者甚多。如英人休摩所著《英史》,叙载雅正,兼擅三长。基本所著《后罗马史》,雍容彩丽。近又有马高来者,其所著之《英史》,字句警炼,几掩前人。他若班哥罗甫,著《美史》;摩德利,著《荷兰开国记》,皆能详明博赡,毋忝作家。史之体,以国政为纲领,礼乐、征伐、法令、政刑悉详载而靡遗。英史尤首重教会。国中大政,无事不与教会相关,故叙述不容简略。”[14]
1877年10月的《格致汇编》上刊有艾约瑟所撰《英国新史略论》一文,该文较为客观地梳理了英国浪漫主义史学家弗娄得(又译夫鲁德)的《英国新史》①弗娄得(James Anthony Froude,1818~1894),系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卡莱尔的弟子,卡莱尔去世后成为他遗稿的唯一管理人。所谓《英国新史》是指其以20年时间完成的12卷本《英国史》,该书前两卷出版于1856年,随后1858、1860、1863、1866、1870年每年出版两卷。古奇批评夫鲁德史学的特色是“持论不公”、“个人好恶十分强烈”。参见古奇著、耿淡如译:《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第538-548页。,给予较高的赞誉:“英国夙尚史学,撰史之家不少,今名之最著者惟一人,厥名弗娄得。其书现已撰成八卷,当其第七、八卷初版时甫到书肆,一日之间人购之殆尽,几同于洛阳纸贵矣。”[15]《英国新史》出版后,社会反响非常好,成为在英国非常时髦和流行的历史著作。艾约瑟认为该书可以与“正书信史”的“中国之《春秋左氏传》”相提并论,他评价道:“今弗娄得所撰之史考据精详,所以人人皆喜阅之。”鲜明地指出该书的特点在于“考据精详”。艾约瑟评论道:“史家之要,在于纲领清楚,脉络分明”,不可以“专详于君相,不详于庶民”;“固不可专详于军旅战阵之事,不详于风土民情,亦不可专详论律法、征伐、民数、贸易及教门之事”,而应当“一切周详全备”。[15]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艾约瑟特别强调史著结构的“纲领清楚,脉络分明”是对史学家撰写史著的根本要求,史学家撰史结构严谨、脉络分明对于史著的价值非常重要;同时,艾约瑟认为,过去的历史偏重于政治史、战争史,西方民史观念兴起后,历史开始向普遍史、综合史方向发展,历史表述的内容更加丰富和周详。应该说,上述见解符合西方现代史学的主流,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在表达方式上,艾约瑟主张历史应当作为戏剧来写,这是深受其师卡莱尔的史学观点的影响的,他认为(撰写历史)要“善于刻画形容,论人如现在目前,论事如身历其境;纪战阵之事,人读之如亲在行间睹其锋镝交冲之势;纪国家之事,读之如身历朝省。操建白议论之权者,方称能事”[15]。他认为:“故撰史须胸襟高朗、广见博闻之人,则其落笔必雄奇超妙,而要其大体则不于真且正,斯乃可谓良史之才。”而“今弗娄得所撰能细心体察,凡古人之隐微无不洞烛,且能知人所未知,言前人所未敢言”。他以亨利八世为例,将其视为人民的代表,认为亨利八世的议会法序言代表了英国受教育平民的意见:“英国上代之君内有言行难测者数位,就中惟恒里第八尤甚,撰史之人议论纷纭,咸谓其起于私心,而弗娄得独谓恒里第八之行系为公政。”[15]虽然艾约瑟关于作者和该书的讨论还非常肤浅,对亨利八世的所谓新评价也未必正确,且包含着对英国海外殖民统治政策的辩护之言,但该篇文字确乎是介绍西方文明史学比较早的文章。
三、结 语
艾约瑟的史学思想和对西方史学的输入正处于晚清“西史东渐”的重要时期,作为传教士,他将史学输入和史学思想服务于“学术传教”的策略。其史学思想、史学评论散见于他所译介的西方史学中,其史学思想不够系统和完整,但却真实地体现了传教士西方文化优越论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旨趣,具有鲜明的“传教士史学”的特色。其输入的西方史学以西欧古典史学为主,但也兼及对欧美近代史学的介绍,他对西方史学的介绍侧重于史家和史著本身,对西方史学演变发展的脉络、西方史学的特点和价值的分析则稍显不够,这与他作为中西文化、史学沟通的“中介者”身份有密切的关联,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一种“新史学”,而是作为一座“桥梁”,沟通中西史学的交流和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确是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转型产生了重要作用。
[1]艾约瑟.稽古集解[J].教会新报,1870(106-111).
[2]艾约瑟.论《列子·汤问篇》意多出于波斯印度[C]//万国公报:第27册.影印合订本.台北:台湾华文书局,1968:11921-11922.
[3]艾约瑟.论黄帝[C]//万国公报:第28册.影印合订本.台北:台湾华文书局,1968:11975-11976.
[4]艾约瑟.分野之说始周宣王时考[C]//万国公报:第30册.影印合订本.台北:台湾华文书局,1968:12131.
[5]陈立柱.西方中心主义的初步反省[J].史学理论研究,2005(2):54.
[6]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M].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565-566.
[7]EDKINS J.Paper—a Chinese Invention[J].China Review, 1899~1900,24(6):269-270.
[8]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G]//刘俊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北京:中华书局,1992:10.
[9]鲁军.进化论在中国近代的传播及其哲学影响[C]//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研究论文集.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3:82.
[10]艾约瑟.国富无常[M]//艾约瑟.西学述略.上海:总税务司,1886.
[11]艾约瑟.黑陆独都传[J].六合丛谈,1858,2(2).
[12]艾约瑟.士居提代传[J].六合丛谈,1857,1(12).
[13]张广智.关于西方古典史学入华史的学术通信[J].史学理论研究,1998(1):149.
[14]文廷式.文廷式集:上[M].汪叔子,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245.
[15]艾约瑟.英国新史略论[J].格致汇编,1877(10).
责任编辑黄部兵
Joseph Edkins’Historiography Thought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SHU Xi-long,CHEN Shu-yu
(Department of History,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Chaozhou,Guangdong,521041)
Eurocentris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Edkins’s conception of history.He regarded this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view and argument,published his views and opinions o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ography.He was proud of uniqueness and value of western classical history and modern history.Edkins ob⁃served the Great changes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n historical thought,which differed from medieval Confucianism,reflecting strong characteristics of ideological history paradigm.Edkins had a deep interest in western historiography,believing that studying western historiography should begin from classical history.So he had studies and comments on the ancient Greek,Roman historians.Edkins’s historiography’s literacy not only found expressions in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classical history,but also in th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test results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mmunication and the ex⁃chang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ography.
Joseph Edkins;Eurocentrism;transformation theory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ought;introduction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K09
A
1007-6883(2015)01-0037-06
2014-05-26
2014年韩山师范学院教授启动项目(项目编号:QD20140324)。
舒习龙(1968-),男,安徽巢湖人,韩山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