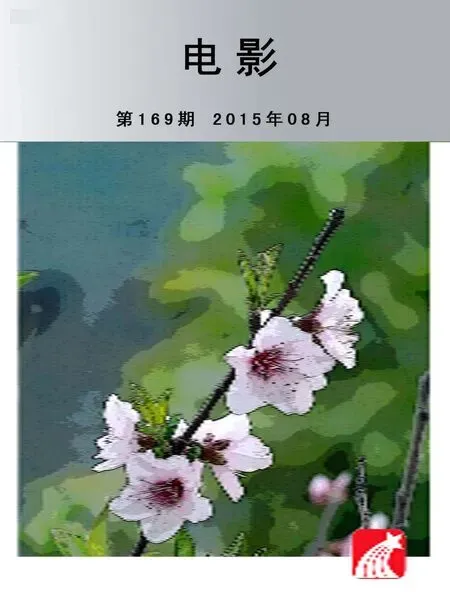侯孝贤背对观众拍武侠
文/张云 图片提供/光合映画
侯孝贤背对观众拍武侠
文/张云图片提供/光合映画
16年前,侯孝贤就开始构思《刺客聂隐娘》。
最初的构想,只是个小成本电影,使用二战战地记者那种手持摄影机,一次只能拍30秒,还得重新上发条。“让摄影师直接找到演员身上的闪光点,30秒之后再来,每次都是新的。这样可以把成本降低,质感也会非常粗,打破了目前的数字摄影造成的画面太细。”
可到了实际操作,相当注重影片“底色”的侯孝贤,仅仅为还原聂隐娘的生长背景和时代样貌,就陆陆续续做了8年准备。这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剧本越写越复杂;选景地从大陆多地延伸到日本,再到台湾搭景,加上还原当时服装所费,制作成本越来越高。
最终,《刺客聂隐娘》变成了一部大制作武侠片。在全球范围内的版权售卖,使它能够成为侯孝贤在内地公映的第一部电影。
作为电影界公认的大师,侯孝贤罕少拍武侠,这让《刺客聂隐娘》从开拍就备受瞩目。但人们最终会发现,侯孝贤还是那个侯孝贤。虽然演员着了唐装,说着文言,侯孝贤依旧还是使用擅长的长镜头,场景切换仍“任性”地不在乎是否衔接无间。
与传统意义的武侠片不同,侯孝贤承继的是《卧虎藏龙》美学、武术、文化内涵俱佳的路数;在武林世界构建中,他沿袭的是推重写实和文学底蕴的《倭寇的踪迹》和《一代宗师》特质。
“中国的主流电影是什么?武侠片,是外国没有办法取代的。”2007年,侯孝贤在香港浸会大学做演讲时这么说。如今,他探索起这种独特类型片,做一个只有中国才可能达到的武侠片规格界定和复原。

聂隐娘和玉娇龙很相似。玉娇龙见识了真正的江湖之残酷后绝望自杀,聂隐娘则最终无法杀人。
金庸的“侠”大气滂沱:“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而在侯孝贤看来,侠,并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行侠仗义”。身而为人的“侠”心理犹疑更有感染力,包括“侠”对于“行侠”缘由的深层次思考,及至深思后做出的行为抉择。
武侠片是侯孝贤心心念念要拍的电影,“还没拍电影时就想了”。打小爱读武侠小说的侯孝贤,到小学六年级,已经几乎看遍所有能找到的武侠书。高中时,侯孝贤不停念叨一句:“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明显颠倒本来语序的宣告,道出了侯孝贤对“侠”的理解:
“该片不少空镜头,大部分都是湖光山色,人在景中走,颇为写意。金马影展执行长闻天祥给侯孝贤发简讯问:“你拍的是你吗?一个人没有同类。”侯孝贤回应:“你往前走,随着自己的成长,越看越深,最后就是一个人。”
“侠其实很累的,因为他要判断,该不该打抱不平。你不能被骗了,否则不是要亏欠一辈子吗?帮助人的尺度也非常难拿捏,有些人是不能帮的,你越帮他越惨,就是扶不起的阿斗。侠客是为救难、救急,为正义,但人毕竟都是人,有时候可能会出差错。
还有个现实面的问题,就是侠再怎么厉害,还是要吃饭的,对人情世故要练达到一个程度。当侠客是很辛苦的,假如骨头又很硬的话,那更辛苦了,不能偷、不能抢。做临时劳力吗?把武术当做生活的用具?”
类似的观念在很多影片中都有展现,却没能获得观众的广泛认可。比如《剑雨》的武林高手也要自己找房子住;有的人甚至发愁于一日三餐,连豆皮都吃不起。


侯孝贤执导每部电影的动力就是人物,这也是他的电影最终呈现出来的根本。在他看来,即便一名刺客,“最后还是人”。这也是他想改编唐传奇《聂隐娘》的原因。唐朝以前的武侠小说,刺客、侠客的世界观单一、没有思想,宛如李白形容的“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到唐代传奇,主角的选择就出现思想斗争了。
1732字的《聂隐娘》被改编成电影后,展现了一名刺客的“醒觉”历程。她有过两次踟蹰:十岁女孩被训练的13年(原文是5年)中,聂隐娘动过一次恻隐之心,看见对方跟小孩玩耍,没忍心下手,放弃执行任务;师傅让聂隐娘取表兄首级,还教导她“杀一独夫可救千百人,则千百人可以杀之”,但聂隐娘终究没有下手,师傅只能叹息“汝剑术已成,却不能斩绝人伦之亲,可惜了……”
聂隐娘的价值观是在瓦解中重建,也就是侯孝贤所偏爱的她人性的苏醒:“每当主角试图逃脱传统习惯规范时也就关涉侠义。她执行任务时动了恻隐之心,对于刺客这件事怀疑动摇了,所以武功在一夕间瓦解。她脑袋还隐藏了一个匕首──是道姑把它放在那里,好让她随时拔出来,但一夕间都不管用了。这和传统武侠小说完全不同。”
有影评人发现,聂隐娘与玉娇龙很相似:“都有一个从他认到自认的过程。有一个另怀打算的师傅,为此将她们训诫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从而完成‘他认’。在与世界/江湖接触的过程中,完成了自认改变了原有的轨迹——玉娇龙见识了真正的江湖之残酷最终绝望自杀,聂隐娘则是最终无法杀人。”
没有什么傲人和了不得的动作设计,尤其是刺客,他根本不能曝光太多,基本上能一刀解决的就解决了。
或许是因为侯孝贤是个被认为有江湖气的导演,所以才长久之中始终不放弃拍武侠的梦想。在法国人为他拍摄的纪录片《侯孝贤画传》里,他说自己推崇“雄性”,因为现在的男人越来越中性,他更怀念人与人之间像狗在撕咬的世界。
华罗庚对梁羽生说: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这个为世人推崇的理念不适用于侯孝贤的武侠电影,侯孝贤也不打算在武侠片中展现神乎其技的武功绝学。“轻功这些东西都可以做,但是要有物理现象,要借力。”他不认可胡金铨的电影里,刀变飞剑的路数,更不允许很有看点的“飞来飞去”出现在《刺客聂隐娘》。甚至,连原小说中聂隐娘可以变作小蚊虫的内容,就因为太不现实,弃之不用。
甚至黑帮片,侯孝贤都承认是假的:“我当时拍《南国再见,南国》,里面那些主角都是穿得很拽啦、很嚣张的样子啊,其实根本就是瞎编。”
这样说,是有底气的。大家都知道侯导年轻时曾为“黑社会”的经历:“我上学的时候经常打架,高中就一直是‘留校察看’的状态也毕不了业,所以也没法考大学。那个时候我们在那边城隍庙一带活动,那里有个铁器店,我们就拿很多武器跟人家火并。最严重一次,我是把士官俱乐部的大门给砸了,还有一次我跟两个兄弟背着砍刀在大街上找仇家,后来被警察发现,我们被迫逃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后来就成了《风柜来的人》的拍摄地。”
甚至,他还亲身经历了一场黑帮遭遇战——在黑夜中看到了双方冷兵器交战而打出的火花:“有人肯定要问,我们这种火并会不会死人?完全不会,受伤都是轻伤,毕竟大家都是中小学生的样子啦,反倒是那种伏击战可能会要命。”

01-兵库县姬路市书写山圆教寺摩尼殿也是汤姆·克鲁斯《最后的武士》日本取景地

02-周韵进入侯孝贤剧组,是个意外。当时,周韵和姜文准备请侯孝贤演戏,没想反被侯孝贤抢了先。侯孝贤评价周韵,演技和舒淇平分秋色。

03-侠其实很累的,因为他要判断,该不该打抱不平。侠客是为救难、救急,为正义,但人毕竟都是人,有时候可能会出差错。
侯孝贤研究过日本的武士电影,比较中日武打动作的不同:日本片到现在还保留武士刀、道场训练场所,打法基本没有花招的,力道很实;中国的“少林”、“武当”只是听说,其实没有,到现在更是几乎断绝。同时,日本武士重视对决,中国武术则表演性质较强。
“在动作部分,侯导没有去追求什么傲人的和了不得的动作表现,他更多的是要讲人的能力,所以动作部分是我们感觉最困难的,我们的武指(董玮)常常为此头疼,因为过火了侯导不喜欢,火候不到又完全没有视觉表现力。”担任《刺客聂隐娘》摄影的李屏宾称,片中一切动作戏为剧情服务,绝不会“为了打而打”。
侯孝贤进一步解释这个理念:“尤其是刺客,他根本不能曝光太久,基本上是能一刀解决就解决了。所以我设计的打斗基本上都是这样,很干脆。每次打斗要有你自己的一个想法,比如,聂隐娘和田季安两人有过一段情,她要让他认出她来,她才下手,没想到田季安拼命打,半天也没认出来。后来他才回想起来,就讲起以前的事。我更看重这些细节的安排,会产生一种戏剧性。”
台词都是文言文。还有很多空镜头,大都是湖光三色,人在景中走。
第6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面对首批观影观众时,《刺客聂隐娘》得到两极评价,但有一点共识,那就是电影画面的唯美。为武侠的发生设置幽远浪漫的意境,于细枝末节赋予情致古韵,是侯孝贤导演的《刺客聂隐娘》。
徐浩峰曾经评点中国的武侠片说:“武侠片的不衰,不是补充现实生活的细节,而是补充古典文化典故”。早期的武侠片大师张彻、胡金铨,虽然身在台湾,可熟读明史,他们的片子有一种共性:不管故事有多荒谬,片头总要先念白一段史书。《刺客聂隐娘》的台词也都是古文。念对白成了影片拍摄过程中的挑战,张震说:“台词跟剧本一样很难读,要花很多功夫。我们看唐人小说,三页纸我都读不完。”
侯孝贤以往执导电影很少如此,他更倾向于让演员在自然情境下随性发挥。侯孝贤对此的解释是:为了增强历史感。“文言文,其实它就是一个字一个意思,商朝的时候,要记录,要刻下来。但我们看到的这个其实不是文言文,但接近,不是白话,所以比较难。以前人的讲话,比较简洁。里面的师父讲的就是当时的口语了。”唐传奇中聂隐娘骑的驴子,其实是纸做的——道家能指挥纸人纸马打仗,侯孝贤据此在影片中做出“纸人杀人”的桥段。更多的,他也把自己对传统文化的思考渗入影片。比如,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和道家是互补的,聂隐娘师父教导的“杀一独夫可救千百人,千百人可以杀之”,就源于孟子提出的相似概念。研究壁画等艺术品遗留。最后展现在片中的,不过是冰山一角。
唐朝,在侯孝贤眼里是个恢弘气派的国际都市。“那时候很开放。一夫可以多妾,女子也很开放。长安以前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城市,外国人最多的城市,你看我们有敲鼓的声音,陈鼓三千击把所有人叫醒,打三千下。木鼓五百,五百击之后,‘里’跟‘里’之间就要隔起来了,你这个‘里’里面可以活动,活动多晚没人理你,但是你不能流动,不能到别的‘里’……”
在对整个故事大背景唐代的构建,侯孝贤花了一年时间,翻阅各种史书典籍——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笔记小说,研究藩镇制度与节度使制度的书……包括
唐传奇中,聂隐娘是被道姑带走的,道教在唐朝基本算是国教,所以侯孝贤认为,聂隐娘其实是被朝廷训练成刺客,用来对付政敌或者叛乱者,侯孝贤认同《聂隐娘》蕴涵的道家思想。片中他采用了一些道教的“神秘主义”,也就是法术。侯孝贤看吕洞宾的书,发现很多神奇故事,比如用笔在墙上画一只猴子,猴子可以跳下来表演杂技,表演结束后又回到墙上。而

他到湖北的武当山、神农架、恩施等地取景,在台湾搭起木建筑,还跑到日本专门拍摄遣唐使的段落。侯孝贤想展现“一部流动的、光影中的唐诗”,正如影片被称道的多个大景深下的空镜头,幽远灵动,颇具中国传统的写意风致。
唐朝的丝制品很发达,为原样呈现,剧组去了苏杭,还从韩国、印度购买手工丝制品,影片中的衣服和纱帐都是精挑细选的上品。拍摄丝织品在光线反射下的美感,侯孝贤借鉴《海上花》积累的经验:“光很低,而且要用烛光,你不能打太强的光,要配合那个烛光。”
侯孝贤拍摄武侠片的处理思路和工作手法,带有鲜明个人印记。但无论有心还是无意,侯孝贤对于武侠的别样理解,必将掀起讨论的波澜。精益求精的考据求实,也会带给中国武侠片发展新的启发。
2015年5月,第6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的新闻发布会上,侯孝贤谈到接下来的拍片计划时说,如果能找得到投资的话,他会继续拍武侠片。这值得期待。

侯孝贤在片场

内蒙片场

银杏谷拍摄现场

经典的卯榫结构

田季安父亲戴立忍饰(后左一)

小隐娘(聂窈) 定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