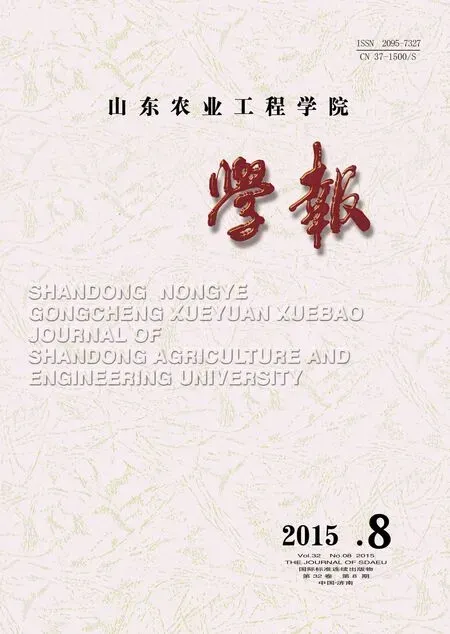论共罚的事后行为的概念及其成立要件
李玉洁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论共罚的事后行为的概念及其成立要件
李玉洁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以“共罚的事后行为”概念取代“不可罚的事后行为”概念有其深层次意义。“不罚”忽视了后行为对法益的第二次侵害,“共罚”则对后行为进行了否定性评价。成立共罚的事后行为需要具备的成立条件包括没有侵害新的法益、后行为该当构成要件、违法且有责、该违法性已被事前的状态犯所评价完毕。
共罚的事后行为;不可罚的事后行为;成立要件
0.引言
行为人实施盗窃犯罪行为既遂后,又持有、处分、毁坏该财产的,一般对持有、处分、毁坏该财产的行为不予处罚。行为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死犯罪行为既遂之后,为了毁灭现场证据又肢解被害人尸体,虽然该当了侮辱尸体罪,但对行为人侮辱尸体的事后行为不予以处罚。此即所谓的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即行为人实施某些犯罪行为(即前行为)达到既遂之后,又实施依据一般社会经验而伴随的危害行为(即事后行为),对事后行为,一般不会按照犯罪处理。
照此是否对于所有的事后行为都一概不罚?如果行为人实施盗窃行为时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后行为人在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之时实施了毁坏该财物的行为,对于盗窃行为由于存在责任阻却事由不可罚,但对于毁坏财物的行为是否也不可罚呢?“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和“共罚的事后行为”的概念是否可以通用呢?哪些事后行为需要单独定罪,哪些事后行为又为前行为构成要件所包括评价?这就需要我们对事后行为的概念进行取舍,对事后行为的成立要件进行深入分析。刑法理论界虽然经常使用“不可罚的事后行为”的概念,但对该概念和“共罚的事后行为”的概念经常互用,且对其含义未有统一明确的解释,对事后行为相关问题也未展开深入的讨论和研究,笔者认为明了事后行为的概念和构成要件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1.概念的取舍:“共罚的事后行为”抑或“不可罚的事后行为”
我国刑法理论认为,实施某些犯罪既遂之后,又实施依据一般社会经验通常会伴随的危害行为的,后行为视为不可罚的事后行为。[1]这可谓“不可罚论”。不可罚论通常是指行为人实施某一行为后,继而实施另一独立的不同的犯罪行为,基于事前行为(主行为)与事后行为(辅行为)之间的关联关系,对其实施的事后行为,不再单独予以定罪处罚。[3]例如强奸行为人实施强奸过程中对妇女实施的强制猥亵的伴随行为,也是不可罚的行为。在实施盗窃行为(第一行为)后,盗窃犯人又将该财物毁弃(第二行为)。盗窃犯人仅仅对于第一行为成立盗窃罪,第二行为属于不可罚的事后行为,不作为处罚的对象。正如有学者所言:“在状态犯的场合,利用该犯罪行为的结果的行为,如果孤立地看,符合其他犯罪的构成要件,具有可罚性,但由于被综合评价在该状态犯中,故没有必要另认定为其他犯罪。”[3]换言之,在状态犯的理论里,提前预设了犯罪完成后违法状态还在继续存在的情况,那么行为人依然处于该状态下所实施的新的行为即使符合别的构成要件,也只能由前面的犯罪进行包括性评价,只以盗窃罪处罚。
然而不可罚论存在以下问题:其一,在无法证明第一行为该当于盗窃罪构成要件时,就无法处罚第一行为,但是在无法证明不存在第一行为时,即使能够证明第二行为该当了毁坏财物罪构成要件,也不能处罚第二行为,未免产生处罚上的漏洞而有失妥当;(2)如果该当于盗窃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存在违法性阻却事由或者责任阻却事由,不能处罚第一行为,但是该当于毁坏财物罪构成要件的第二行为如果没有阻却事由也不处罚却不合理。如当盗窃犯实施盗窃行为时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但是在实施毁坏财物行为时行为人存在责任能力的场合,不追究第二行为的责任恐怕难言妥当。(3)如果超过了第一行为的刑事追诉时效,行为人毁弃盗窃物的行为,如果按照“事后不可罚”论得出行为人无罪的结论,未免有失偏颇。由此可见,采用不可罚的事后行为的概念会出现司法实务中一系列涉及事后行为的相关问题无法解决。如果用“共罚的事后行为”概念替代“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则可以有效地解决上述难题。例如上述第一种情况,按照“不可罚的事后行为”的观点来看,在无法证明第一行为该当盗窃罪构成要件时,就不能处罚第一行为,即便证明第二行为符合毁坏财物罪的构成要件,也不能处罚第二行为。但依“共罚的事后行为”的观点来看,虽然不能按照盗窃罪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是,依然能够就毁坏财物的行为继续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同理,按照“共罚的事后行为”观点,上述第二种、第三种情况都可以得出合理的结论。上述第二种情况,如果符合盗窃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存在违法性阻却事由或者责任阻却事由,该行为就不能成为处罚的对象,但是符合毁坏财物罪的构成要件的第二行为如果没有阻却事由则可以单独处罚。上述第三种情况,如果超过了第一行为的刑事追诉时效,行为人又毁弃盗窃物的行为,对事后行为要“共罚”,而非“不罚”,毁弃财物行为的诉讼时效独立计算,如此会更加合理,也不会存在处罚的漏洞问题。
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中往“不罚”和“共罚”二者概念互用,实际上,二者含义不同。“不罚”忽视了后行为对法益的第二次侵害,“共罚”则对后行为进行了否定性评价,考虑了事后行为对法益的两次侵害,同时也更有利于解决司法实务问题。
2.共罚的事后行为成立要件
事后行为是否可罚,目前尚无明确的判断标准和精细化的成立要件,究竟哪些事后行为可以单独定罪,哪些事后行为又为前行为构成要件所包括评价,这就需要对共罚的事后行为成立要件加以分析。笔者认为,成立共罚的事后行为需要具备以下成立条件。
2.1 没有侵害新的法益
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判断,要从实质上判断是否存在值得科处刑罚的法益侵害。违法性的判断,是以法益侵害或威胁为中心考虑。如果状态犯又伴随有新的法益侵害,与前行为所侵害的法益不同,就不是前行为所能包括评价。反之,如果法益侵害的状态继续存在,如盗窃犯人毁坏所盗物品,对同一对象同一法益进行二次侵害,刑法法规既然已经对前行为进行了处罚,对该法益已然提供了保护,那就没有必要对后行为再施以重复的保护。行为人盗窃信用卡后使用所盗的信用卡,其盗窃行为只侵害了公私财产权,而后的使用行为则造成对金融管理秩序的侵害,侵害了新的法益。
如日本学者认为伴有对新的法益侵害的状态犯的构成要件所评价不了的可罚行为,不是共罚的事后行为。[4]有日本判例认为,向供应店出示骗取的供应票证骗取大米的场合,是新的侵害法益的行为,所以,另外成立诈骗罪;向银行职员出示骗取来的支票骗取金钱的场合,是新的侵害法益的行为,所以,另外成立诈骗罪。[5]
2.2 没有扩大法益损害
状态犯没有伴随新的法益侵害,与前行为所侵害的法益相同,但却扩大了法益侵害,对于后行为是否可以处罚,是否属于共罚的事后行为呢?例如,行为人出于报复社会动机,盗窃了国家珍贵文物,并将该珍贵文物烧毁,显然,后行为对法益进行了二次侵害,造成了珍贵文物不可逆的毁损结果,扩大了法益侵害,已经难以包括在前行为的评价中。行为人伪造假币后又使用所伪造的假币,其使用假币的行为虽侵犯的是同一法益,但却扩大了法益侵害,应“从重处罚”,同样不属于共罚的事后行为。所以,扩大了法益侵害程度的行为也同样不属于共罚的事后行为。
2.3 后行为该当构成要件、违法且有责
如果后行为不成立犯罪,则没有必要讨论处罚事后行为的问题,只有在事后行为该当构成要件、违法且有责的前提下,才有上述问题讨论的必要。
2.4 该违法性已被事前的状态犯所评价完毕
如日本学者前田雅英指出事后行为虽然满足构成要件,但由于前行为所触犯的罪名已经对行为的法益侵害事实进行了包括的、一体性评价,故没有必要对事后行为再进行处罚[6]。在日本2003年4月23日作出的大法庭判决认为,所谓不可罚的事后行为,是指类似于盗窃犯人损坏盗窃物的行为,如果将两种行为分开来观察,虽也可以认为后一行为成立其他罪,但是由于损坏行为已经被完全包括在对原本的犯罪行为所进行的违法评价中,就不能再成立其他犯罪的。本案的先行行为是土地担保行为,仅仅成立侵害土地经济价值的犯罪,相对的,本案的后行为是将土地所有权(土地所具有的全部价值,包括土地的经济价值)出让给第三人的行为,由于后行行为无法完全地被包含在对先行行为的违法评价中,所以不属于不可罚的事后行为。[7]由此可见,在后行为所导致的法益侵害超出了先行行为所导致的法益侵害时,后行为就不能被包括在先行行为的违法评价之中了。
[1]周光权.《刑法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53.
[2]陈兴良.《刑法总论精释》[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703.
[3]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368.
[4]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38.
[5]大谷实.最判昭23、4、7刑集2、4、298[M].《刑法讲义总论》(第2版),2007: 438.
[6]大谷实.最决昭38、5、17刑集17、4、336[M].《刑法讲义总论》(第2版),2007: 439.
[7]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第五版)[M].东京大学出版会,2011.
the concept and essential elements of the subsequent conduct of co-penalty
Li Yu-jie
(Nanjing ForestPolice College Jiangsu Nanjing 210023)
Replacing the concept of“subsequent conduct of co-penalty”of"subsequent conduct of non-punishment"concept has its deep meaning. Non-penalty ignores the second violation of the legal interests of subsequent conduct while co-penalty makes a negative evaluation of subsequent conduct.Establishing the subsequent conduct of co-penalty requires the essential elements including no new legal interests,subsequent conduct should be essential elements,the perpetrator is illegal and responsible and the illegality has been committed by a state evaluation is completed beforehand.
Subsequent conduct of co-penalty;Subsequent conduct of non-penalty;Essential elements
D90-052
A
2095-7327(2015)-08-0124-02
李玉洁(1982—),女,河南南阳人,就职于南京森林警察学院,讲师,东南大学反腐败法治研究中心基地研究人员,东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行事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