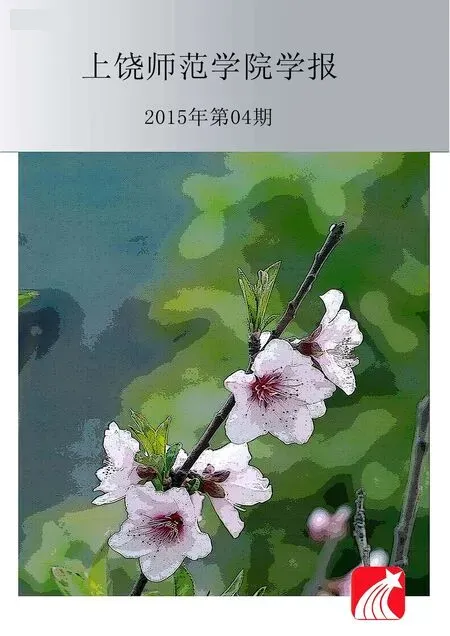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研究综述
杨 安
(华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1)
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研究综述
杨 安
(华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1)
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是当代技术哲学争论的一个焦点,也是当代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使技术更多地渗透到生活世界的每个角落,影响制约着生活世界,而意识形态的诸形式构成技术发展的社会精神环境,制约着对技术及其社会功能的理解,这就使得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具有特别的意义。
技术; 意识形态; 关系
技术的最早论述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人们对技术的认识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不断深入,技术的去形而上学化使得技术可能取代传统生活样式。而自从特拉西引入意识形态概念以来,围绕意识形态的研究就没有停止过。几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科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做了开拓性的研究,决定着后人的研究方向及评价。
一、技术问题研究
技术构成了现代人生存的整体性的背景环境,成为人的全部生活的内在制约机制或基本存在方式。现代技术给予了人类无穷的馈赠和美好的享受,也促使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和研究技术,本文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对技术的内涵和马克思视域中的技术思想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
人类的发展与技术同源。人类社会形态的嬗变,也促使着技术的内涵发生转变。陈凡通过“文本”的具体历史语境,揭示了技术概念的历史过程:从以“艺术”为中心的技术概念,过渡到以“应用科学”为中心的技术概念,再发展到以“工程研究”为核心的技术概念体系。[1]通过对比一般的技术概念和现代的技术概念,吴跃平认为,技术可界定为出于仪式化生活的需要,对于器物进行赋形赋义的方法;而现代技术确立了世界与自然环境同质化的趋势,以自己座架(Cestell)的力量绑架了文明,让文明世界的一切为它的运行服务。[2]刘爱文揭示了技术的朴素整体论、构成系统论、新批判理论和生成总体论的演变历程,认为技术存在着自在状态、自为状态和自在自为状态的转变,技术的本质是一种实践性的知识体系。[3]而在王凤珍看来,技术的本质是“实现人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充分自由”,它的实现以人的本质实现为前提。与人的发展三阶段相一致,技术的发展经历了古代经验型技术、近代实体型技术、现代知识型技术三个阶段。[4]对技术内涵发展的讨论只是涉及到技术理论的一个方面,但它影响着技术理论其他方面的研究,涉及到技术的本质及其实现。
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始终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关注人的存在和发展。马克思视域中的技术思想是其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相关讨论主要集中在马克思技术实践思想、马克思技术人学思想。
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发展出一套技术实践思想,但马克思实践哲学本身已经包含了建构马克思主义技术实践思想的可能性。田鹏颖认为马克思有个主体“实践”的元概念。这个实践包括人与人(社会)的关系,调整这种关系的技术手段——社会技术蛰伏着社会哲学本体论的深刻隐喻。[5]马克思的技术批判强调要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社会生活,理解世界,揭示了技术“脱离”生活世界的虚假性,把技术理解为一种关乎人类本质的活动,技术问题必须在现实的活动中得到解决。[6]马克思超越传统实践哲学的实质是在于他在物质的生产关系和世界的历史视域中展现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看到它的本质是直接与人的本质,与人所处的特定社会的历史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7]吴书林从技术作为实践活动的一种样式、作为生产的核心概念和作为社会形态的指示器三个方面来论述马克思的技术本质观。[8]管晓刚认为马克思捕捉到了技术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革命性力量和决定性作用,并把技术引入自己的实践哲学,赋予技术以本体论、认识论、生活论、价值论等多视角哲学意蕴。[9]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技术实践思想把技术视为实践的一种样式,赋予技术多重内涵,认为它在人的社会关系中产生作用。
马克思技术观是其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活动具有两种可能的性质——属人的和异化的。宫敬才认为,马克思发现和揭示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过程中的内在矛盾——“自然必然性王国”的“退缩”与“扩大”同时并存,这一过程及其结果具有有限性甚或局限性。[10]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技术发展史,马克思的人学思想旨在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避免异化为目的,最终提出关于技术应用的科学方式,实现人和技术的融合。[11]马克思在世界历史的语境中将现代技术批判置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之中,为我们积极面对和解决当代技术问题指明了现实的可能性方向。[1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超越人本主义技术批判之处在于把人的抽象本质理解为一种类的外在活动,批判的对象是生产活动,而非生产活动中的技术,不把异化的根源简单归结为技术;马克思所指明的克服异化的道路,即废除私有制,是实践性、革命性的。[13]马克思的技术人学思想把正确地使用技术当做是人类解放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对技术与人的关系做了恰当的解释。
有的学者从生态学、历史逻辑等角度理解马克思的技术思想。何炼成认为技术是人创造出来的用在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之间的传导或中介,它时刻影响着人和自然的关系的变革,技术是人与自然内在统一的中介。[14]从历史发生学看来,马克思的技术内涵变化多样:意会技术(观念形态、信息形态的技术);实体技术(意会技术的物化);具体技术物。王华英阐述了马克思技术思想的几对矛盾:文本解读与哲学(前后期哲学)推演的技术思想的矛盾;预成的与生成的技术思想的矛盾;前后期哲学思想推演的技术矛盾。[15]
传统的研究倾向于对技术进行静态的分析,但其实并不存在于应用情景之外的所谓技术本身,目前国内学者已开始将技术作为一种过程进行研究,将技术以动态的形式加以呈现。这有助于全面动态地考量各种技术观,探索其所隐含的价值取向,澄清技术研究中的价值冲突。对马克思技术实践思想和技术人学思想进行研究,以往被忽略的主体性原则重新得到了重视,研究视角从认识论领域扩展到实践论、人学等领域,但目前对马克思技术思想和人学思想的理解存在较大争论,制约了学界的进一步研究。
二、意识形态问题研究
意识形态是个现实性很强而又敏感的理论课题,在当代世界的各种理论文献中以及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被广泛使用。综观当代世界意识形态领域,与意识形态概念刚刚提出之时相比,其内涵已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我国学者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演进、意识形态建设、马克思视域中的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深入的研究。
申小翠认为,“意识形态”起源于培根的“假象说”,经历了托拉西的“观念科学”、马克思的“虚假意识”与“观念上层建筑”、列宁的“科学的意识形态”、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等四个发展阶段。[16]赵静对此说予以了补充,认为意识形态概念发展到今天形成了两种思潮,一是马克思所建立的意识形态学说,它正日益广泛地成为社会上各种弱势群体反抗强势群体的支配和压迫、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武器;二是一些西方学者举起“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旗帜,宣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失败。[17]魏崇辉则认为意识形态概念缘起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去蔽。对意识形态的剖析可有以下理路:其一是以培根、特拉西、黑格尔等为代表的局限于认识论意义上的研究理路,强调理性的作用;其二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立足于经验事实的研究理路,从现象背后的利益出发寻找原因。[18]郑海侠认为自德·特拉西首次提出意识形态概念以来,其含义己经发生了五次重大转变,即非科学性转变、科学性转变、实存性转变、非价值性转变、泛文化性转变。[19]学者张九海借鉴蒙德·盖茨的“描述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否定性的意识形态”和“肯定意义的意识形态”概念,从肯定、否定、中性三个研究视角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20]邓伯军反思了历史上意识形态问题的哲学主题,认为意识形态从观念学到符号学的历史演变中,存在着本体论转向、认识论转向、生存论转向、符号学转向的现象。[21]学者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作历史的划分,表明意识形态在理论上是发展的,缺陷在于鲜有学者分析不同阶段或不同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
在意识形态认同与建设的研究方面,余源培认为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与认同建构必须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的关系;改善民生、努力实现社会公正和增强党的信任构成了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有效途径。[22]邓彦提出,在当代文化多元化背景下必须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机制,他分析了分层整合、规范整合、强制整合等不同方式。[23]面对微博等新媒体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影响,宣云凤倡议要加大网络审查力度,建立健全有效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网络文化“红军”队伍建设,转变不良思想导向。[24]针对新媒体的特点,余源培提出要依靠全体人民,重视对社会心理的分析与研究,提高网民的能力和素质。[25]王翠芳阐述了意识形态建设的改革和创新问题:加强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研究,努力提高意识形态建设的科学性;强化理论创新,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着眼解决问题,强固意识形态建设的政策支撑;坚持以人为本,提高意识形态的受众性;立足客观实际,突出意识形态建设的层次性;创新工作机制,构筑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平台。[26]学者大多从实践操作和理论层面对意识形态认同和建构进行立论,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合理性依据和操作层面的可行性依据论述不多。
马克思在不同的文本中对意识形态做过不同的论述,但没有写过专门研究意识形态的书籍,也没有对意识形态做系统全面的论述,这为后人理解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留下了充足的空间。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作不同层次上的区分和使用,是学界研究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焦点之一。
周民锋指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有三种用法:Ideologie、Bewuβtseinsformen和IdeologischenFormen。对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的正式表述中,马克思采用后两种用法,即意识形态之全体和意识形态之部分。前者指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人类意识的各种形态,后者仅指以思想体系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意识形态。[27]马克思最初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语境中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他赋予其否定性维度;在随后对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的阐述中,赋予其现象学维度;在分析个人的历史行动时,又赋予其历史性维度。[28]国外有学者梳理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的三种内涵,分别是论战—揭露的意识形态、解释—功能性的意识形态以及批判—哲学的意识形态。[29]国内学者也有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分为三层含义:作为唯心史观的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和作为掩盖物质利益和真实动机的意识形态。[30]与此类似,有的学者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分为作为意识形态的虚假意识;作为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体系;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体系。[31]
胡大平强调,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既属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又同时不属于这两者,它是在这两者之间进行联系的中介。作为一种历史地形成的思维图式,意识形态不再是思维本身,而是构成调节思维与存在之间关系的一种具有惰性的“实体”。[32]徐彦伟、张志丹两位学者都从否定和中性二维角度探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否定意义上的是虚假的意识形态,中性意义上的是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33]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更凸显否定的虚假的涵义,而中性的肯定涵义在马克思著作中显得更为模糊。在意识形态的属性方面,赵敦华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概括出认识属性、语言属性、社会结构属性和阶级属性的四重描述,可以被视作意识形态概念的“家族相似”意义上的描述性定义。[34]
作为现代意识形态理论的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对“意识形态”的涵义、特征作出了规定,分析了它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其与经济基础的关系等,他们主要是从否定的意义上来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歪曲的意识,并且主要从意识形态与社会矛盾的关联来证明这种歪曲性质。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发生了变化,逐步被用作中性的概念。
对一个概念或范畴下定义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但任何定义都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仅仅从定义来理解某一个概念的本质,也往往会因为各种原因发生分歧。对于变革时代的意识形态而言,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三、科技与意识形态关系理论研究
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是当代技术哲学争论的一个焦点,也是当代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使技术更多地渗透到生活世界的每个角落,影响制约着生活世界,而意识形态的诸形式则构成技术发展的社会精神环境,制约着对技术及其社会功能的理解。这就使得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具有特别的意义。
法兰克福学派较早研究了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霍克海默首先提出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这一论点;韦伯提出同科学技术相联系的“合理化”过程是以一种积极的、进步的形象出现的,指明行为导向的世界观的世俗化和非神化;而马尔库塞则强调,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和统治(合理性和压迫)在发达工业社会形态下融合。通过对科技功能的历史分析,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具有生产力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功能。[35]围绕着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内部又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其一以阿尔都塞为代表,认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互相对立,从此论证科学技术的合理性与进步性;其二以哈贝马斯为代表,通过论证科学技术就是意识形态,指出科学技术的社会政治效应完全是负面的、消极的。研究表明,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成员缺少对科技功能的历史分析,认为科学技术从来就是意识形态。
认为科技与意识形态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是国内研究的主流观点,其他的主张包括:科技具有意识形态性,技术是中立的,技术是意识形态等。
郑永廷与阳海音赞同科技与意识形态是对立统一的观点。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与价值辩证关系的基础上,他们认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既不能等同也不能对立。在本质属性、功能属性、社会属性上,在反映、服务的对象上,在社会生活中所担当的任务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都是不同的,不能把它们等同起来。[36]科学技术影响着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但科学技术本质上只是生产力的一个要素,它与意识形态之间有着鲜明的区别。[37]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具有决定作用;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发展具有反作用。由于意识形态的多义性、多功能性以及意识形态与社会科学的特殊复杂关系,使得在哲学上思考社会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有了很大的难度。田鹏颖和陈凡区分了三种情况:一是从意识形态与社会科学具有同一性而言,意识形态可能成为社会技术的一个观念、理论来源;二是从意识形态与社会科学具有差异性而言,意识形态又比较强烈地反映了社会主体的主观倾向性和工具理性特点,因而又具有一定的社会技术功能;三是从逻辑上思考,社会技术的理论形态与意识形态可能也有一致性。[38]因此,我们难以把社会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界定清楚。
刘英杰明确指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技具有了意识形态的特点,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种科学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科技不再具有价值中立性,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围绕着技术原则进行了重构,也就参与了意识形态的构造。[39]科技从两种意义和层面成为意识形态:一种是指纯技术的东西或技术的外在应用,这是一种显性层面的狭义的强功能分析;另一种是指技术的本质或技术本身的内在以及构造,这是一种隐性层面的广义的弱功能分析。[40]只有从第一层面深入到第二层面,对科技意识形态功能的理解才能更全面和更深刻。
金瑶梅认为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科学技术在现实的社会中究竟起什么作用,这主要是人选择的结果,即主要取决于人们在什么样的价值观念支配下对其进行使用。科学技术有一个从可能变为现实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受人的选择决定的。[41]科学技术产生消极作用或正面效应,都是人造成的。莫茜面对科学技术地位的上升和功能变化的情况下,做了更为普遍的客观分析。近代以来的理性启蒙运动和实践方面的成功,已使科学精神及技术实践意识在工业化国家社会中发展成为具有普遍性的精神意识,科学技术也因之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获得了文化话语权,逐渐演变成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一种基本导向。当科学技术的文化话语霸权地位形成之时,它进而转变为意识形态也就势所必然。[42]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制度中,科技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表现和性质是不一样的。技术如何成为意识形态,以及技术成为意识形态之后,技术和意识形态应该怎么继续发展,都是学界应该厘清的重要问题。撇开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撇开了社会因素的制约,抽象地谈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关系,抽象地来谈论科学技术的社会政治效应,是不可能真正清楚地认识技术与意识形态的效应问题的。
科技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及其实质,揭露了当代工业社会的发展的复杂状况。挖掘科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既是完善传统唯物史观关于意识形态观点的需要,也是全面科学地认识科学技术自身的客观要求。法兰克福学派把科学技术的异化分析置于文化危机的背景下,并在人的生存层面揭示出异化的文化力量对人的主体性的操纵和消解,将科技发展与公众舆论、民主政治相结合,这一思想对于解决当代中国的科技异化问题具有较大的启示性。[43]科技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复杂性也挑战着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认识,现代意识形态是通过技术与科学的有效性发挥自己的作用的,这与传统的意识形态起作用的方式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叙述形式也应该随之而发生相应的变化。[44]
把科技与意识形态直接等同,对它们进行批判,视科学技术为“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最终只能在“科技是物化、统治的工具”与“科技是一种解放力量”两个相反的命题之间徘徊,既不能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科技异化现象,也不可能找到消除这些异化的有效途径。[45]科技异化是工业社会突出的异化现象,对之进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由此引申的社会批判也是合理的;然而将对科技异化的批判转变为对科技本身的否定,并归结为意识形态的批判,就走向了社会批判初衷的反面,“意识形态不是出自人类形成初期面对原始自然界的思考,确切地说,人类必须配置一定的生产方式才能使自然界服从自身目的,因此,意识形态就是在确定的生产方式的坐标内产生的”[46](P232)。
[1] 陈凡,陈玉林.技术概念与技术文化的建构[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8,(3):39-45.
[2] 吴跃平.“技术的一般涵义”与“技术的现代涵义”[J].人文杂志,2012,(2):1-6.
[3] 刘爱文.技术的哲学根基及其历史演变[J].江西社会科学,2012,(10):43-46.
[4] 王凤珍,杨延坤.从人的发展看技术本质的实现[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8):51-56.
[5] 田鹏颖.从马克思的“两种实践”统一观看社会技术的本体论隐喻——兼论从康德的“实践智慧”到马克思的“社会关系”[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1):156-159.
[6] 谢永康.技术批判与马克思——一种实践哲学视野下的重新思考[J].江海学刊,2004,(5):34-40.
[7] 韩志伟.生产与技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嬗变[J].学术研究,2005,(11):48-52,147.
[8] 吴书林.马克思技术本质观的实践哲学解读[J].学术研究,2011,(6):8-12,24,159.
[9] 管晓刚.试论马克思技术之思的哲学意蕴[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1,(4):63-67.
[10] 宫敬才.马克思劳动人道主义视野中的科学技术观[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07-115.
[11] 范君.马克思人学思想视阈下的技术应用[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94-96.
[12] 郝继松,韩志伟.马克思现代技术批判的历史维度[J].学术研究,2014,(8):7-11.
[13] 邓联合.人本主义技术批判的困境与超越——马克思《1844年手稿》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之比较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1):54-58.
[14] 何炼成,庄静怡.马克思技术思想与当代科技创新关系刍议——基于生态视角的马克思技术观[J].理论学刊,2011,(5):4-8,127.
[15] 王华英.历史发生学视域下的马克思技术思想[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2):59-65.
[16] 申小翠.“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流变[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4):35-41.
[17] 赵静.浅析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J].社会科学家,2007,(S2):5-6,10.
[18] 魏崇辉.意识形态的流变:概念、理论与透析理路[J].求索,2011,(12):123-125,262.
[19] 郑海侠.论“意识形态”概念流变过程中的五次重大转变[J].教学与研究,2014,(9):104-111.
[20] 张九海.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历史与当代审读[J].学术界,2005,(3):93-99.
[21] 邓伯军.意识形态:一种哲学层面的分析[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6):66-70,83,85.
[22] 孔德永.当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有效途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6):91-99.
[23] 钟添生,邓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机制[J].江西社会科学,2006,(10):144-147.
[24] 宣云凤,林慧.微博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影响及对策[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10):96-101.
[25] 余源培.新媒体与意识形态建设[J].河北学刊,2013,(1):128-132.
[26] 王翠芳.意识形态建设的改进与实践创新[J].学海,2006,(6):107-111.
[27] 周民锋.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两个来源及其两重含义[J].学术研究,2008,(6):36-41.
[28] 吴荣荃,黄少华.意识形态概念的多重维度与唯物史观的形成[J].兰州大学学报,2002,(1):78-84.
[29] 乔治·马尔库什,孙建茵.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1):139-150.
[30] 胡辉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6):14-21.
[31] 王晓升.“意识形态”概念辨析[J].哲学动态,2010,(3):5-12.
[32] 胡大平.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范畴[J].教学与研究,2009,(11):17-22.
[33] 徐彦伟.否定与中性: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文本考察[J].求索,2009,(7):114-116.
[34] 赵敦华.“意识形态”概念的多重描述定义——再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J].社会科学战线,2014,(7):1-11.
[35] 戈士国.统治与操控的合理化机制——“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文本学解读[J].哲学研究,2012,(5):93-98.
[36] 郑永廷.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互动共进[J].高校理论战线,2012,(9):9-16.
[37] 阳海音.马克思论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J].黑龙江史志,2009,(10):13-14.
[38] 田鹏颖,陈凡.社会技术哲学引论:从社会科学到社会技术[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3.
[39] 刘英杰.论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构造[J].社会科学战线,2010,(5):239-241.
[40] 刘英杰.科学技术在何种层面和意义上成为意识形态[J].学习与探索,2009,(3):44-46.
[41] 金瑶梅.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吗?——两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不同回答[J].社会科学家,2012,(5):7-10.
[42] 莫茜.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J].广西社会科学,2003,(10):34-36.
[43] 阳海音.论哈贝马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价值和限度[J].社会主义研究,2007,(5):92-94.
[44] 俞吾金.从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到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3):14-17.
[45] 陈旭玲,刘京.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意蕴[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10):89-93.
[46] 罗伯特·C尤林.理解文化——从人类学和社会理论视角[M].何国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邱忠善]
A Re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Ideology
YANG An
(School of Marxism,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1, 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tific technology and ideology has been the focus of debates of contemporary technological philosophy and it’s also an important issue of contemporary theory of ide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makes technology penetrate more into every corner of life world, affecting and restraining the life world while various forms of ideology constitute the social spiritual environment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restrict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echnology and its social function. This mak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ideology have special significance.
technology; ideology; relationship
2015-03-16
华南理工大学“百步梯”项目(KB31815008)
杨安(1989-),男,江西吉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辩证唯物主义与创新理论研究。E-mail:184526970@qq.com
B089
A
1004-2237(2015)04-0068-06
10.3969/j.issn.1004-2237.2015.04.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