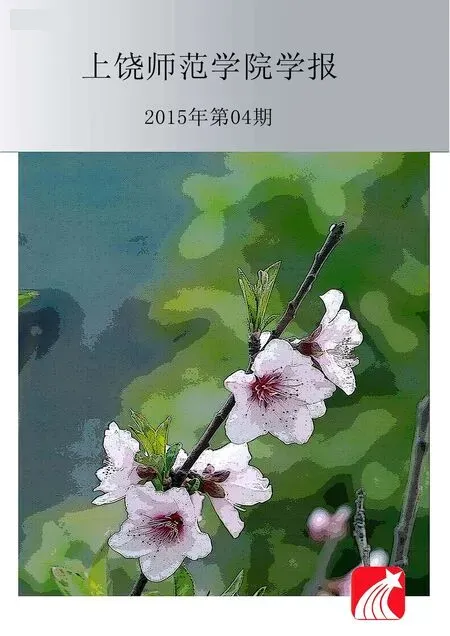明中期商人新论
——以商人传记中盐商与木商异同为切入点
张 世 敏
(上饶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江西 上饶 334001)
明中期商人新论
——以商人传记中盐商与木商异同为切入点
张 世 敏
(上饶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江西 上饶 334001)
以明中期的商人传记作为文献基础,以盐商与木商形象的异同分析作为切入点,可以对明代商人研究领域的一些观点进行反思。明中期传记中的盐商与木商70%以上属徽籍,记的作者绝大多数是徽籍文人与江浙文人,这说明在沿江这一空间范围内,“无徽不成镇”说具有一定的可靠性。传记中的盐商与木商都少有义行,说明“以义为利”并非明代所有行业商人的普遍特征。盐商与士人关系密切,木商不重视与士人交往,缘于盐业由官府垄断,与士人交往会带来更可观的利润。商人基于求利的需要,其经营的行业是否由官府垄断,决定了商人与士人之间的亲疏程度。
盐商; 木商; 徽州; 商人传记
商业的发展与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使明中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已被学界普遍接受。相关领域学者在论及明代商人时,基于历史文献提出了独到的观点,诸如基于第一大商帮而提出的“无徽不成镇”之说,“以义为利”、重士向学是明代商人的重要特征等。本文以笔者在明中期文集中搜集到的160篇商人传记作为研究的文献起点*具体篇目见笔者《明中期文人别集中商人传记文献研究》附录二《明中期文集中商人传记目录》,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以商人传记中的盐商与木商形象异同进行比较研究作为切入点,对上述学界差不多达成共识的观点进行反思,认为当今学界对于明代商人的认识,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存在可以进一步商榷之处。
一、“无徽不成镇”的可靠性求证
明清徽商在盐业、木业、典当业等行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几个行业又以盛产富商而闻名,因此,明清以来,“沿江区域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谚”[1](P39)。在徽商研究领域学者的论著中,不少都会提到“无徽不成镇”一说,且前面多未加“沿江区域”这一限定。那么,“无徽不成镇”是否真实客观地述说了徽商在当时的重要性呢?
明清之时,富商大贾多出自盐业、典当业、木业等行业,在这些行业中,徽商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徽州与江浙一带。以盐商为例,当时盐商经营盐业大多需要前往食盐主要集散地淮扬,淮扬盐商中,以徽商为翘楚。万历《扬州府志》载,在扬州经营的盐商,“新都最,关以西、山右次之”[2](P6)。这类记载反映,从明代中期开始,淮扬的盐商中,徽商的风头最盛,山陕稍居其后。明清木商中,徽商地位同样很高。《歙事闲谭》载:“徽多木商,贩自川广,集于江宁之上河,资本非巨万不可。”[3](P603-604)这些文字说明徽州木商遍布了南方从四川、湖广到江南之地,而且资本雄厚。雍正《浙江通志》更是说:“当杉利盛时,岁不下十万,以故户鲜逋赋,然必仰给于徽人之拼本盈,而吴下之行货勿滞也。”[4](P181)徽州木商的资本力量大到足以影响浙江一带木材市场的行情。浙江在编撰地方志时,没有为徽商夸饰的必要,因而其中的描述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张海鹏在《徽商研究》一书中论道:“木材贸易作为徽州商帮的四大支柱行业之一,发展最早,而衰落最迟,由此可知它在徽州商帮中的地位和作用何等重要。”[5](P257)至于典当商人,当时民间则有“无徽不典”之说。
以上文献证明,徽商在盐业、典当业、木业中确实占据了重要地位,但其影响力主要限定在江浙之内。那么,明代中期的商人传记能够印证上述观点吗?笔者搜集到的160篇商人传记,其中可以确定传主经营行业的传记,共有23篇的传主或传主之夫是盐商,而盐商传主绝大多数为徽籍,资本雄厚的盐商传主几乎都是徽籍。23篇盐商传记,分别是茅坤《黄烈妇传》、汪道昆《沈文桢传》《朱介夫传》《许长公传》《程长公传》《潘汀州传》《松山翁传》《吴汝拙传》《海阳长者程惟清传》《吴伯举传》《世叔十一府君传》《再从叔十六府君传》、李梦阳《贞义公传》、沈炼《金处士传》、王世贞《许长公传》、归有光《归氏二孝子传》、宋仪望《仲玉翁传》、方弘静《吴季君传》、耿定向《儒贾传》、吴子玉《程次公传》《程贤孝母传》《韦庵记》、郑若庸《味菜记》。这23篇盐商传记中,只有5篇的传主不是徽籍,分别是《沈文桢传》《松山翁传》《贞义公传》《归氏二孝子传》《仲玉翁传》,传主为徽籍的18篇,比例高达78.3%。
木商传主绝大多数亦为徽籍。160篇商人传记传主为木商的共7篇,分别是金瑶《纪祁门李征君代偿事》《百滩汪翁传》《东泉金传士传》、汪道昆《沈文桢传》、毛伯温《贾尚德传》、吴子玉《存六公传》《吴枢传》。7位传主有5位是徽籍商人,惟《贾尚德传》的传主为陕西籍,《沈文桢传》传主为浙江四明人。木商传主中,徽籍商人比例高达71.4%。
以上数据表明,商人传记中传主为盐商与木商的徽商,比例高达80%左右,与当时其他文献对于徽商的描述可相互印证,“无徽不成镇”之谚,具有较大的合理性。如果再考虑到明中期的160篇商人传记,传主可以确定为徽籍的占99篇,比例高达61.9%,若将不能确定传主籍贯的传记考虑在内,比例还要更高。笔者所见,明中期共有50位商人传记作家①,其中徽州5人,江浙地区30人,两地作家占全国的比例为70%。也就是说,明中期商人传记的传主大多数都是徽籍商人,为徽籍商人作传的绝大多数是徽籍文人或江浙地区的文人。因此,若以商人传记作为衡量商人知名度的标准,徽州商人的影响力主要限于徽州与江浙地区,这与前文中所提到的“沿江区域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谚”合若符契。
总而言之,“无徽不成镇”说具有一定的可靠性,但必须限定在“沿江区域”这个范围内,若为了夸饰徽商的影响力,运用“无徽不成镇”这一谚语时,有意地忽略了“沿江区域”这一空间范围的限定,难免会产生偏见或误差。
二、义商特征的普遍性追问
学界在论及中国古代商人时,往往将商人与儒家联系起来,将其称为儒商,受儒商概念的影响,今天的大多数学者往往将“义”作为古代商人的一大特征。例如,张海鹏在《徽商研究》一书中认为,由于受儒家思想的支配,徽商表现出了“以义为利”[4](P388)的特征。无可否认,这类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考之古代文献,可知地方志中的商人传记,包括盐商与木商传记,往往列于“孝友”与“义行”之中,与学界的观点是相合的。
明代文集商人传记中,丝帛商人、典当商人、以及经营行业不明的商人,很多都有义举。尤其是典当商人,到明代已把施行义举提高到经营理念的高度。金瑶《吴畏轩传》中的传主吴玠,将施行义举与“市义”联系了起来。不过,在肯定一些行业的商人多有义举的前提下,我们也要看到,明代文集商人传记中,传主中的盐商与木商绝少有义举。以下将以文集中的商人传记作为文献依据,分别论盐商与木商少有义举的特征。
(一)盐商豪侈而少有义举
中国古代的商人由于受到儒教、佛教、道教的影响,以及政治权力的逼迫与引导,到明代时,商人群体中多有善行与义举之人。明代文集商人传记中的盐商,也有因宗教信仰而施行义举者,如李梦阳《贞义公传》中的传主李忠:
任侠有气人也,即小时而好解推衣食,衣食人。于是闾里人皆多处士公。处士公顾愈谨治生,日厚富有赀。郡中人用赀无问识不识,皆与次,于是郡中人亦无不多处士公。处士公载盐过闾里,与闾里门斗盐。及载菜,即又与闾里
①见笔者博士论文《明中期文人别集中商人传记文献研究》附录一《明中期商人传记作者小传》。
菜。卒岁散盐、菜数十车,于是闾里率岁不复购盐、菜,而俗谓善人为佛,处士又治佛,号曰佛王忠。[6](P1262)
李忠散菜、盐数十车给乡邻,以至乡邻不再需要购买盐与菜,可以肯定与“处士治佛”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与《贞义公传》相仿的还有归有光所撰《归氏二孝子传》,该传传主有高义之行。明中期的23篇盐商传记,除了这2篇之外,其他盐商并无值得称道的义行,甚至有些盐商自认为只要没有不义之行,就是值得向后人夸赞的了。金通在教育后代时如是说:“吾与汝母平生未尝行一不义,以累若等,若等有不肖者,必毋曰我父母之遗殃也。”[7](P43)即使有义行,其层次也都比较低,具体表现为:盐商一般只对和自己有亲缘关系的人,才会施以义举。在对与自己无亲缘关系的人施以义举时,往往带有直接的功利目的。
大多数盐商只对有亲缘关系之人施以义举,表现出亲亲之义,徽州盐商靠家族抱团经营而获得成功,正是以这种亲亲之义为基础的。王世贞与汪道昆都为盐商许铗作有传记,根据这两篇传记的记载,许铗对与自己无亲缘关系的人,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义举,但对自己的兄弟却谦让且迁就,其季父之子“金既得志,遂诬长公尝侵季赀。长公不辨,益割橐而授之。人或谓长公衷也,而奈何授之橐而自居辟。长公第谢曰:‘金辟我衷,幸诸君知之,而吾又何恡也。且不忍倍吾季,’则长公橐日损。”[8](P363)根据传记可知,盐商通常施行的义举,与亲情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许长公传》《程长公传》等传记中俱有类似记载。
盐商还会为了获取政治权力而施行义举。如歙县盐商潘惟和,汪道昆在其传中记述道:“境内数苦兵,编户去籍者半,仅筑一城以守,县治且颓。公自歙鸠工,橐出三百金为之改作,且移书诸子:‘若等输’。”[9](P740)潘惟和的义行是出资修城,与一般赈济穷困之人有很大的差别。盐商通过施行义举而获取政治权力的主要目的是让商业经营更加地顺利,对此,盐商程豪说得特别清楚:“大启木分榆社,与里中父老朝夕讲宴。邻有斗,直取片言解释,不复烦有司。立义仓义塾,缮梁除道,日费橐中装不惜。”他完全是为了“贾且什倍”[10](P396)这个目的服务的。显然,盐商通过施行义举,进而接近士大夫与权力中心,只是为了使得商业经营有更好的发展。
盐商是商人中财力最为雄厚的一个群体,他们拥有雄厚的财力,却吝于施以义举,其最典型的群体特征就是肥于奉己,豪侈以自恣。盐商豪侈生活最为典型的就是多买婢妾。朱介夫“尝贾妾武林,不数月而生子,家人欲弗举”[9](P613);宋仲玉“入蜀十余年,乃更多买妾婢,为终焉计”[11](P389);吴汝拙“居淮阳,内一姬,下车而容有蹙,既知良家之自出,不欲列诸宠人,辄蕃车载归,无问采矣”[9](P789)。盐商广纳妾婢,最能够反映他们肥以自奉的特征。吴汝拙在纳妾时,因知其为良家,不欲列诸宠人,载归而不问采礼,他这个举动被传记的作者作为义行书入传中,以此可知盐商之义确非高义。
鉴于盐商豪侈以自奉,且少有义举,故明清时期社会对于盐商的评价普遍不高。清人朱轼曰:“凡商贾贸易,贱买贵卖,无过盐斤。”[12](P727)很显然,少有义行,肥于奉己的盐商,难以得到文人的认同。
(二)木商同样少有义举
明代中期木商与盐商一样,也少有义行。7篇木商传记中,其中有6篇虽记录了木商有孝顺父母、兄友弟恭之行,却没有木商赈济不相识之人的记载。唯有《纪祁门李征君代偿事》中有勉强可算义行之事的记录:
李子曰:“家君(李征君)兄弟五人,而家君长,性孝友,疏财崇义,尤好振人之急。少年客句容,有社友洪姓者驾木过河下,称欠榷木价,恳家君为贷谭主人五十金以去。及偿期,主人索之急。家君躬造其木所,始知洪为人驾木。洪无木,得前金逐手快意费尽,锱铢不能偿。家君不得已,懋迁已有代之偿。家君原不满百金,既偿而句容之业遂废,因而抵家。访洪家,徒四壁立,室人大小皆归怨,而乡里多为家君持不平。内有雠洪者,谓家君:“洪犹有基并舍,若鸣于官,尚可偿原贷无缺。”家君自念曰:“始以旧识代之贷,既不能偿,代之偿。若复鸣于官,坏其家室,使无居,不以德贾雠乎,非算也。古人有言:‘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人牛。蹊者固无情,而夺者则又甚矣。’宁人负我,无我负人。”[13](P534)
从该传记载的木商仅有的义行来看,李征君替洪姓社友贷五十金,是因为上当受骗所致,非纯为义也;偿期已到,洪姓社友不能偿所贷之钱,李征君代偿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今天的担保贷款,贷款人不能偿还债务时,担保人有偿还债务的连带责任,两者之间的道理是一样的。故代偿非因义之故也;代偿之后,李征君不愿鸣于官,有出于不愿使洪姓社友居无定所之义,但同时也有不愿“以德贾雠”的想法。因此,李征君代人偿债,可以称为义行,但与其他行业的商人主动施以义行相比,要逊色一些。
明代中期的商人传记中,传主为木商的只有7篇,以这7篇传记中的传主来代表明代中期木商群体,基本上还是符合抽样原则的。从这7篇传记可以看出,明代中期商人传记中的木商大多是信奉“商职利”的商人,他们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不太重视与士大夫的结交,也很少有义行可书。虽然木商在明代没有盐商的名声那么坏,但没有高士化的商人,就连一般的义行也是少之又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集中的商人传记,大多数都是收取润笔费之后而撰写的,难免会有谀墓之嫌。只要传主有义行,作者都会用力夸饰传主义行。在笔者所搜集到的160篇商人传记中,丝帛商人、典当商人与其他行业的商人传记,大多数传记中都记述了传主的义行。在典当商人传记中,典当商人的渝行甚至被比做“薛公市义”[13](P595)。有谀墓之嫌的商人传记所述传主的义行,不一定都是可信的;相反,传记中若没有义行,则可据以认定传主确无义行。明代文集中盐商传记与木商传记中的传主普遍少有义行,说明明代这两个行业的商人生平之中确少义行可书。由此可以引发两个方面的思考:第一,明代文集盐商传记与木商传记80%左右的传主是徽商,这两个行业的传主几乎都少有义行,因此,“以义为利”是否是徽商的普遍特征,理应受到质疑;第二,商人传记中的典当商人、丝帛商人与其他行业的商人大多有义行,盐商与木商少有义行,不同行业的商人在施行义举之间反差巨大,其原因值得深思。
三、商人重士向学的差异性分析
士商关系是商人人际关系中很重要的关系,从整体上来说,明代商人与士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了。不过,具体到不同行业,士人与商人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很大的区别。通过对明代中期文集中的160篇商人传记进行考察,可知明中期与士人关系最为密切的商人是盐商,木商则与士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疏远。
(一)重学喜与士大夫交的盐商
张海鹏在论及徽州盐商时如是说:“徽商在两淮之能执诸盐商之牛耳,还因为占有文化优势。微商是一支以‘儒贾’为特征的商帮,他们虽是商人,但不少人又是文人,具有程度不同的文化知识和儒家的道德修养。”[4](P167)张海鹏所论的是徽州盐商,但也可以反映出其他地区盐商与士人之间的关系,只不过相对其他地区来说,徽州地区盐商重学、喜与士大夫交表现得更加典型。
徽州休宁盐商朱介夫“年十四,贯武林籍,补郡诸生……介夫故受《易》东越,乃得交东越士大夫,由是以好客特闻。诸士大夫毕至,即布衣来谒,一切周事之。甚者望介夫深,不啻外府”[9](P612-613)。歙县盐商许铗“叔喜客,长公独务为俭,佐客资。居常恂恂,即旅次,读书不辍”[9](P635)。歙县盐商程长公“幼受儒术,矢将奋武,绳之学射,逾年业已当室。母太恭人嫠也,仲五年而孤。长公计守穷庐,兆页仰且不给,宁去而贾,以纾家步”[9](P694)。歙县潘恒和“初,公父处士命伯以儒,仲以贾。仲无禄早世,公不释业,代贾真州。家世用陶公,独与时逐,或用盐盬,或用木童布,或用质剂,周游江淮吴越,务协地宜……虽托于贾人,而儒术益治,诸学士过真州者辄屏刀布相与挟策论文”[9](P739)。徽州程惟清“父息子四,叔则惟清。叔尝为儒受经矣。父命之曰:“洁尔!伯也、仲也贾,无如叔也才。而不遑儒,而其左右二昆,力贾以糊余口”[9](P800-801)。歙县吴伯举“少入成均,一再试不利,退而深念曰:‘古之有道者非征辟不行,乃今蓬首跣足以干有司,耻也。’遂释博士业,出藏书遍读之,自《三坟》以及百家,独观大指,或当意,援笔数千言”[9](P808)。休宁金通“少博综《坟》《典》,习为儒,弱冠丧父,遂弃去”[7](P43)。歙县吴光升“在兄弟中最少而早慧,游太学亦有名,至乡试则亦弗偶”[14](P237)。歙县程豪贾于麻城,“有郭令者,尝游王文成门,谈良知学。子德悦而师之,为巍冠褒衣,趋绳视准,阛阓少年咸相目笑,子德益自喜。闻有从之游者,子德持麈高谈,与相往复,弥日不较。阛阓少年复相诟曰:‘贾而欲赢,而迂言废事,吾见其垂橐归耳。’”[10](P395)休宁程元善“以简重自居,言无阿挠,极意学经书,屡试于有司不售”[15](P644)。徽州地区以外的盐商亦重学,如宋仪望先祖仲玉公“早从中隐公受诗,已乃弃去”[11](P389)。
以上所列传记中的文字,足以说明无论是徽州地区,还是其他地区的盐商,都有重学的倾向,其文化水平相对其他行业的商人来说要高。
(二)不重视与士人交往的木商
盐商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程度,并与士大夫有交往,才能更好地获利。木业在经营过程中,砍伐、长途贩运需要大量的人力。两个行业一为知识密集,一为劳动力密集。因此,明代中期的木商相对“儒贾”盐商来说,呈现出文化程度不高,不注重与士人交往的特征。明中期文集中7篇木商传记的传主,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纪祁门李征君代偿事》中,传主之子为祁门县学诸生,但从传中却不能看出传主有入学经历。[13](P534)《东泉金处士传》中的传主金处士初为木商,后为典当商人,是一位崇信“商职利”[13](P588)、无入学经历的商人。《贾尚德传》传主贾怀,“少年时事商贩”[16](P321),传记亦不载其中年或晚年有读书之事。《存六公传》与《吴枢传》中的传主亦是如此。唯有《百淮汪翁传》之传主汪庆,有过一段很短的入学经历,该传载汪庆:“少有至性,家贫,入小学仅九阅月,余时事樵采给二亲爨燎。晚伴诸兄顾斋封君宿。宿则质以小学所闻,故虽不日就小学,而所得于小学与诸幼等。年弱冠从商。”[13](P574)这段文字说明了汪庆入小学仅九个月就因家贫而辍学,即使是辍学之后,跟着哥哥完成了小学阶段的学业,也仅粗通小学而已,对于经学、史学、诸子百家等当不通晓,故金瑶对他的评价是“翁为人厚重而颖慧,虽未学而行谊默与儒合”。并在该传传末论道:“不日在小学,而能记姓名,与达者通书问”,“未讲道与义,而行事多与道义合。”[13](P576)金瑶对汪庆的评价,确证了汪庆只是粗通文字,对于经史之义理全然不知。
与木商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相对应的是,木商们不太重视与士大夫们交往,这与盐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7篇木商传记中,能够发现木商与士大夫有交往的记录并不多。《纪祁门李征君代偿事》仅记李征君为洪姓社友代偿五十金之事,不及其他。《百滩汪翁传》传主汪庆“子北,国子生。孙某,国子生。孙曾辈,大半易世业从士。北兄圻与予三男诸生应南为儿女姻,又予家去翁家仅十里,而遥闻翁迹为详”[13](P576)。虽然后代已完成了从商到儒的转型,但该传没有记载汪庆与士大夫交往之事。《东泉金处士传》传主为金瑶之侄,传主没有记录有传主与士大夫交往的事迹。《贾尚德传》传主贾怀“生子四,长曰祯,生从贵,任吏目;次曰顺,子宗周,俱为太学生;次曰颜,□(原文缺字)府典膳、引礼、舍人,生子二”[16](P321)。贾怀之子孙,多学儒而有职官者,但《贾尚德传》中并无记录贾怀与士大夫交往的蛛丝马迹。
《存六公传》与《吴枢公传》两篇传记,与以上四篇传记稍有不同,其中记录传主与士大夫的结交,《存六公传》曰:
盖读金陵梁舍人文,而知存六公功达之质行云。当其丐乳以乳同产子聪,则与郄鉴、元德秀何异也。聪长游学庭,公资助之。应试上金陵,则与俱。以好文喜士闻于里中。[15](P740)
此处所载存六公助兄弟之子游学庭,并陪同至金陵应试之事,当不可与商人与士大夫之间一般的结交活动等而论之。传载存六公“以好文喜士闻于里中”,但未述传主与士人交往细节。《吴枢公传》载传主吴枢“与余御史之尊人蓝田公善”,然蓝田公也是“货木驵侩”,吴枢与蓝田公之间,完全是商业上的合作关系。
明代盐商喜与士大夫交往,而木商与士大夫交往不多,两者之间存在差异的根源在于盐业自古与官府关系密切。《明史·食货志·盐法》载:“煮海之利,历代皆官领之。太祖之初,即立盐法,置局设官,令商人贩鬻,二十取一,以资军饷。”[17](P1931)在官府垄断的行业中经营,学习诗文,与士大夫形成亲密关系,对于经营来说至关重要。如盐商程惟清,其父让他弃儒帮助兄弟经营盐业时说道:“伯也、仲也贾,无如叔也才。而不遑儒,而其左右二昆,力贾以糊余口。”[9](P800-801)可见有一定的学识,对于经营盐业来说,很有帮助。另《儒贾传》的传主程豪经营盐业,在训其子姓曰:“吾家世受什一,不事儒。自吾一染指而士庶亲悦,贾且什倍,由是观之,儒何负于贾哉!”[10](P396)程豪之言,说明业儒能够让士庶,尤其是士人亲悦,进而可以收十倍之利。相反,木业在当时并未由官府垄断,明中期的7篇木商传记的传主,只有1位有过入学经历,与士大夫之间也未能亲密来往,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富有资财的大商人。通过明代盐商和木商与士大夫之间的不同关系,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的规律,当经营官府垄断的行业时,适当地提高文化修养,注重与士大夫之间的交往,对于商业经营来说是完全必要的;反之,经营的行业未被官府垄断,商人与士大夫之间便难以形成亲密的关系。
四、结语
总而言之,以明中期的商人传记作为文献基础,以盐商与木商形象的异同分析作为切入点,可以对明代商人研究领域中“无徽不成镇”说,义商、重士向学是否是商人的普遍特征等问题进行反思。从籍贯来看,明中期传记中的盐商与木商80%都属徽籍,数据证明,明清关于盐商与木商的文献记载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无徽不成镇”之说具有一定的可靠性,但必须限定在“沿江区域”这一空间范围之内。从义行来看,传记中的盐商与木商都少有义行,与同为传记中的典当商人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差别。两个重要行业的商人,都少有义行,说明明代商人是否如学界说,具有“以义为利”的义商特征,是值得商榷的。从与士大夫关系来看,盐商与士大夫关系密切,木商不重视与士大夫交往,原因在于盐业由官府垄断,拉近与士大夫的关系能带来更可观的利润;木业未被官府完全垄断,又是劳动力密集行业,故木商不会汲汲于与士人交往。商人基于求利的需要,其经营的行业是否由官府垄断,决定了商人与士人之间的亲疏程度。
[1] 许承尧.民国歙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2] 廖道南.万历扬州府志[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3] 许承尧.歙事闲谭(下册)[M].合肥:黄山书社,2001.
[4] 张海鹏,王廷元.明清徽商资料选编[M].合肥:黄山书社,1985.
[5] 张海鹏.徽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6] 李梦阳.空同集[M].四库全书本[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 沈炼.青霞集[M].四库全书本[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M].四库全书本[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9] 汪道昆.太函集[M].合肥:黄山书社,2004.
[10] 耿定向.耿定向先生别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Z].济南:齐鲁书社,1996.
[11] 宋仪望.华阳馆别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Z].济南:齐鲁书社,1996.
[12] 魏源.皇朝经世文编[M].魏源全集本[Z].长沙:岳麓书社,2004.
[13] 金瑶.太函集[M].金栗斋先生别集[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4] 方弘静.素园存稿[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Z].济南:齐鲁书社,1996.
[15] 吴子玉.大鄣山人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Z].济南:齐鲁书社,1996.
[16] 毛伯温.毛襄懋先生别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Z].济南:齐鲁书社,1996.
[17]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责任编辑 邱忠善]
A New Study on the Businessmen of the Mid-Ming Period——from the angle of compar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alttraders and wood traders recorded in the businessman biographies
ZHANG Shi-mi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hangrao Normal University, Shangrao Jiangxi 334001, China)
Based on the businessman biographies of the Mid-ming period, and taking the analysis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salt traders and wood traders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his article introspects some ideas in the studies of the businessmen of Ming Dynasty.80% above of the salt traders and wood traders of the native place is Huizhou, and the majority of the biographic authors are literati from Huizhou and Jiangzhe, which indicates that “No Hui Native, No Town” sounds reliable along the coast. According to the biographies, there were few acts of righteousness, which means “to take righteousness as benefit” was not a general character for all the businessmen of Ming Dynasty. Salt traders had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scholars, while wood traders seldom associated themselves with scholars. The reason is that salt trading was monopoliz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association with scholars would bring about great benefits. Thus, the degree of familiarity between businessmen and scholars was actually determined by the businessman’s need for benefit and by whether their trades were monopolized by the government.
salt traders; wood traders; Huizhou; businessman biographies
2015-05-07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ZGW1416)
张世敏(1982-),男,湖南邵东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明清文学思想史文献研究。E-mail:zsmwzy@163.com
I207
A
1004-2237(2015)04-0074-06
10.3969/j.issn.1004-2237.2015.04.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