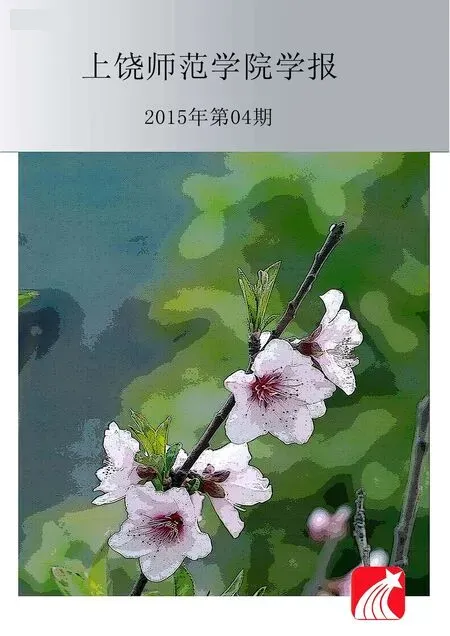赵尊岳词作艺术审美观探论
汪素琴,胡建次
(1.浙江海洋学院 东海科技学院,浙江 舟山 316000;2.南昌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赵尊岳词作艺术审美观探论
汪素琴1,胡建次2
(1.浙江海洋学院 东海科技学院,浙江 舟山 316000;2.南昌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赵尊岳词作艺术审美观主要包括对“神味”“风度”“重、拙、大”等审美范畴的阐释。其中,“神味”是其词作审美境界的最高理想,“风度”是其词作审美风格的独特显现,“重、拙、大”是其词作艺术品格的重要尺度。上述几个范畴相互联系、相互映照,共同铺陈出较为完整的词作审美观念体系,在传统词学史上显示出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赵尊岳; 词作审美观; 神味; 风度; 重、拙、大
赵尊岳(1898-1965),字叔雍,号珍重阁主人、高梧轩主人,现代词学名家,江苏武进(常州)人。出身名门,自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从清末词学名家况周颐学词,传衍况氏词学。抗战中曾依附汪伪政府,抗战胜利后沦为阶下囚,服刑三年出狱,家庭变故接踵而至,穷迫潦倒,遂于1950年移家香港执鞭谋生,1958年应新加坡大学之聘主讲国学,往来于港、新两地,1965年病殁于新加坡。
赵尊岳的词作艺术审美观是在创作观的基础上展开的,不但是其词学思想的核心,同时也是其理论批评中最具创新意义的部分,其内容主要包括对“神味”“风度”“重、拙、大”等审美范畴的阐释。赵尊岳一方面较为详尽地论述了这几个范畴与命题的理论内涵,另一方面对它们的涵养方法及词学地位进行了阐述,构建出较为完整的词作艺术审美观念体系,在我国传统词学理论批评史上显示出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一、“神味”:词作审美境界的最高理想
“神味”说是赵尊岳词作艺术审美观的核心,亦被其视为词作审美境界的最高理想。他在《填词丛话》开篇中提出:“作词首贵神味,次始言理脉。神味足则胡帝胡天,均为名制。唯神来之笔,往往又出之有意无意之间,或较力求神味者,益高一筹。此中消息,最难诠释。”[1](P161)赵尊岳认为追求“神味”是词之创作的首要任务,但凡神味充足之词定是名作。与此同时,他又指出:“作词之神味云者,盖谓通体所融注,所以率此理脉字句而又超于理脉字句之外者。若以王阮亭所谓神韵释之,但主风韵,则尚失之俳浅,非吾所谓神味也。”[1](P161)赵尊岳将“神味”视为创作主体与环境相交融的产物,它通过理脉字句呈现在读者面前,却又有着理脉字句所不能传达的意趣美韵,其内涵比王士礻真所倡“神韵”更为丰富。
王士礻真《池北偶谈》言:“汾阳孔文谷云:‘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薛西原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言:‘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莲’,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神韵二字,予向论诗,首为学人拈出,不知先见于此。”[2](P351)“神韵”说主于“韵”,着眼于词作艺术形式方面,强调的是情与景、心与境相互交融所产生的平淡清远的审美境界,指向一种远离市井世俗的平静闲淡的寂寥之美。而“神味”说则不同,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指出:“填词先求凝重。凝重中有神韵,去成就不远矣。所谓神韵,即事外远致也。”[3](P4409)如果说“神韵”讲求的是“事外远致”,偏重于外在形式美的话,那么“神味”则有词意凝重的一面,是一个内外并举的审美范畴,它将“神”与“味”融合在一起,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对词作审美特性提出了独特要求,具有全面性与融合性、主体性与内蕴性。
“神”是指由一种难以穷尽的底蕴所流露出来的神妙无方的境致,由词之含嗜深远的立意所决定。赵尊岳对词之意涵十分重视,曾说:“词之为道,在于意内言外,因之格调固不可不严,而含嗜尤贵深远。”[1](P182)他认为词的外在形式固然重要,但言之不尽的内在底蕴却能决定一首词优劣与否。与常州派标举“意内言外”以作为词的创作宗旨不同,赵尊岳引“意内言外”只是为了指出词有一种言外之意蕴的特质,并无太多功利性。相对于“神”,“味”更多地指向词之外在形式,体现为一种“绵邈不尽”的韵味:“词属意内言外之音,亦当有事外之远致。意内言外,则所言为非伪;事外有远致,则情绪绵邈不尽,足耐寻味。”[4](P229)理想之词其味当醇厚、深长,有无穷之余味。赵尊岳在《填词丛话》中多次讲到词味,认为其最易从词情、词笔中流露出来。所谓“情语宜有含蓄,有含蓄始可令人回味无穷”[1](P168),指的是词味深藏于含蓄之情与真情之中。所谓“深入者其词味厚,耐人寻思”[1](P186),指的是当用曲笔、入笔以传词味。可见,“神味”是词之“含嗜深远”的内在深意与“绵邈不尽”的外在韵味相融合所显现出来的一种审美境界,它体现了词作独特的审美特征,是词作艺术的最高审美理想。
既然“神味”如此重要,那么如何才能获得“神味”呢?赵尊岳提出了以“性灵学问”陶钅容“神味”的观点。他说:“神可自致而不可强求。欲求致力于神味,但当就常日之灵性学问为陶钅容。”[1](P161)赵尊岳虽然十分重视词之用字、音律等问题,但认为获得“神味”的关键在于“常日性灵”的培养。他将“性灵”与“天分”“襟抱”并举,认为它只可涵养不能强学,这与有蹊径可循的“学力”“笔力”是截然不同的。“学力”深厚仅可得“精金美玉”之词,而“涵养与学力”兼备则可得“神味天生”之作。其实,明代的公安派、李贽及清代的袁枚在论诗文时均标举“性灵”,况周颐《蕙风词话》中也多有提及。然而,在“性灵”与“学力”哪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上,赵尊岳与况周颐的观点存有差异。虽然二人均将读书视为学词之门径,但况氏较为注重书中的知识、方法,认为“性灵天分”固然重要,但会随着词人年岁的增长渐渐逝去,因此,他更提倡多读书以培养“学力”,认为“学力”才是人们作词的终极保障。而赵氏于读词之时更为注重词人的性情襟抱,认为只要能对此加以体会并涵泳玩索,久而久之就能使读者受到启发陶钅容。显然,赵尊岳将“神味”的涵养之道与“词心”的涵养之道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然而与此同时,赵尊岳对“神可自致不可强求”的特征亦深有体会,认为在创作过程中,要想更好地使灵感之“神”降临,就需要有合适的创作环境。可以说,创作过程中的任一要素对“神味”的涵养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有词心流利、词境浑成、词笔纯熟、词情荡漾才能获得“神味”之词。
赵尊岳的“神味”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它是赵氏词学审美理论的核心,把握“神味”说的美学内涵对深入理解“风度”“重、拙、大”等命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以“神味”说为出发点,赵尊岳进一步阐释了“风度”说、“重、拙、大”说,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初具系统的审美理论体系。这三个审美范畴相辅相成,有“神味”的词定是符合“重、拙、大”要求之词,也定是有好“风度”之词。赵尊岳的这种理想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审美取向,他喜短调多于长调,并十分赞赏唐人小令,认为它们不但格高而且韵足正缘于此。其次,透过“神味”说的论述,赵尊岳将词作艺术创作理论与审美理论有机结合了起来,构建出以学问涵养词心、酝酿词境,用词笔抒写作品的创作原则。况周颐《蕙风词话》虽对词心、词境、词笔亦有论述,然而他并未将三者串联起来。相对而言,赵尊岳的理论更富有现代气息。其三,“神味”说内外并举,从“含嗜深远”与“绵邈不尽”两方面对词之审美特质提出要求,试图将词之内在特质与外在美韵融合在一起,不但打破了长期以来词学史上“雅正”与“婉约”对立的状态,而且从根本上抬高了词体的地位,体现了中和的词作审美理想。其四,赵尊岳将“神味”视为词作艺术最高的审美境界,不但丰富了“境界”理论的内涵,同时也开拓了常州派的“境界”观。自周济指出常州派的学词门径乃“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之后,常州词家们便视“浑成”为词之最高境界。赵尊岳对“浑成”提出了另一种思索,认为它并非词之极致:“造语则第一义当求浑成。或以其浅而加深之,求深于意而不求深于文字为第二义。再进为三四义:愈进则意愈浓,情愈厚。若并此三四义,融之为一语,而别立新意以纵之,则益见精胜,为精金矣。”[4](P217)造语自然、理脉顺畅、一气呵成之词固然浑成,但欲求深入,则须注重词意的宛转曲折,先立一意,转入一层,再别立一意,更转进一层,如此层层深入,才能酝酿出深沉邈远、余韵无穷的“神味”。 赵尊岳标举“神味”,追求超越理脉字句之外的绵邈不尽之致,于浑成之外别立准的,可视为常州派论词观点的延伸、拓展与深化。
二、“风度”:词作审美风格的独特显现
“风度”是赵尊岳词学理论中的另一重要审美范畴,亦被其视为词作审美风格的独特显现,其“风度”说是在“神味”说的基础上展开的。“风度原贵在神味之间,而不必尽见于文字”[4](P232),有“神味”之词必有好“风度”。如果说“神味”是词之最高审美理想,那么“风度”则是词必备的审美特质,它于词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药“空”“实”之病。“风度与词,如影随形,盖不可须臾离者。”[1](P174)
“风度”在古代多用来形容人的仪容气度,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内在品格的审美显现。晁补之曾赞扬晏几道词“不蹈袭人语,风度闲雅,自是一家。如‘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乃知此人必不生于三家村中者”[3](P1153),其用“风度闲雅”来评论词的艺术风貌,可谓词学领域中较早对“风度”引起关注之人。此外,况周颐于《蕙风词话》中亦有两处论及“风度”,但并未将“风度”作为一个特定概念予以重视。赵尊岳吸收了“魏晋风度”的理论精华,将“风度”命题引入到词学理论中,对其内涵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说:“词最尚风度,摇曳而不失之佻荡。字面音节求其摇曳,骨干立意,则以重拙大为归。”[1](P166)认为“风度”同“神味”一样,是一个内外并举的审美范畴,指作品在体格上由内而外流露出的审美风格,“摇曳雍容”与“不失佻荡”是其美学特征。其中,“摇曳雍容”是就词之字面音节而言的,而“不失佻荡”则是就词之骨干立意而言的。赵尊岳论词重“风度”,要求词不仅外在形式应空灵疏秀、气韵流动,同时内在骨干应不流于纤弱轻佻之弊,要符合“重、拙、大”之旨。他批评清初人词作失之纤靡正缘于此。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赵尊岳要求每个词人都追求同一种“风度”。相反,他将“风度”视为一个动态性的范畴,认为不同词风可呈现各异“风度”,其云:“词语苍润,各有风度。”[1](P167)“调之谐涩,亦各有风度。”[1](P167)在此基础上,赵尊岳进一步提出了“风度”有优劣之别的观点。他将“风度”比作词之“体态”,“体态”虽人皆有之,而其美丑程度却不尽相同,其曰:“词中风度,大抵以骞举、沈刻、清雄为工,而婉约次之。”[1](P168)认为具有阳刚之气的“风度”比具有阴柔之气的“风度”更值得称道。不难发现,赵尊岳是将“风度”视为同“风格”类似的概念而予以阐说的。
“风度”是词作必备的审美特质,但“最不易求致”。赵尊岳从“词心”与“词笔”两方面对“风度”的涵养之道提出了见解。首先,他认为“词心”的涵养对“风度”的获得至关重要。其云:“欲求学得风度,不如学致词心,二者固均不易求。学风度当取古人名作之风度绝胜者,吟诵不辍,久之词语都忘,而风度犹在,似读者已化身词境之中。”[1](P171)赵尊岳反对死读书,赞赏读书之时融入自己的体会与思考,并教导初学作词者当取古人风度绝胜的名作,吟诵不辍,反复咀嚼其中韵味,以至与词境浑融一体,从而感受词之绝妙风度。他又说:“学词本不能就词以求词。词为天下之至文,而至文固不限于词。风雅骚诵,两京遗制,衍而为诗、为文,多有至文。”[4](P232)各种文体触类旁通,多读词以外的其它优秀作品,学其睿智之言,感其智慧之思,对于作词同样大有裨益。只有将“词内求词”与“词外求词”相结合,才更容易创作出有“风度”之词。其次,赵尊岳十分重视“词笔”的锤炼对于涵养“风度”的重要性,认为“清空之笔”“疏秀之思”是获得“风度”的重要途径。他在论及长调易患“质实”时曾言:“质实之作,虽珠玉并陈,不过如五都之肆,瑰丽错落。故必参以清空之笔,疏秀之思,方足引人穷其胜概,此则非济以风度不可。”[1](P169)“质实”之词虽然眩人耳目,但缺少灵气,若能在其中注入“清空之笔”“疏秀之思”,那么词的整体风貌便会有一番新的气象。在此,赵尊岳并非否定“质实”之词的审美价值,而是在为好用质实之语的词人提供创作途径。秦观有《满庭芳》一词:“晓色云开,春随人意,骤雨才过还晴。古台芳榭,飞燕蹴红英。舞困榆钱自落,秋千外、绿水桥平。东风里,朱门映柳,低按小秦筝。”赵尊岳在谈及“质实语可同见风度”这一观点时曾分析此词道:“一映、一低按、一小字,已经驱使质实为疏秀,大见其风度矣。”[1](P171)由于秦观在“东风”“朱门”“垂柳”“秦筝”等意象中使用了两个动词和一个形容词,于是原本沉寂静态的画面便顿时活化起来,仿佛春日美景佳人就在眼前,从而使词作收到情貌俱佳的效果。可见“清空之笔”“疏秀之思”对于涵养“风度”的重要性。
此外,赵尊岳在“风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气度”说。两者虽极其相似,却具有微妙的区别。其中,“气度”比“风度”更不易获得,它是后者的美学升华。“风度之外,别有气度,此中消息至微,不可不察。风度指体态,气度指神情,其最胜者无论语之苍润,气度必雍容和缓……故有风度之词,尚易获见;有气度之词,尤复罕观,知讲求气度之益难也。”[1](P167)但凡符合“摇曳雍容”标准的词均是“风度”翩翩之词,然而要使一首词有“气度”却并非易事。所谓“珠光剑气,不足抗其明;红英翠锦,不足方其艳;玉堂金马,不足夺其贵;清歌妙舞,不足称其俊”[1](P167),可见,“气度”同“神味”一样,是赵氏词作艺术的最高审美理想。赵尊岳将体制、品格、风度、气度、炼字琢句、起承转合等视为人们在作词过程中必须注意的六个要素。如果将作词比譬为建造一个园林,那么“体制”就是指设计图纸,“品格”指建筑材料,“风度”指整体风貌,“气度”指舒适度及享受度,而“炼字琢句、起承转合”则是最后的验收。除“气度”以外,其它几个要素都是词作所必备的。“气度”是“气”与“度”的有机融合。所谓“度”,即“风度”;所谓“气”,乃作者之元气、气运在作品中的独特彰显。其中,“气”乃“度”之源。有“气度”之词,不但形式上“摇曳雍容”,内容上“不失佻荡”,而且能让读者见出词人的生命力、创造力与精神风貌。《填词丛话》中共有三处论及“气度”,均集中在“风度”论之后。可见,赵氏引入“气度”这一范畴更多的是想表明“风度”并非他所追求的最高审美境界——“风度”之上别有境界,“气度”只是其审美理论中的一个过渡性范畴。
赵尊岳常将“风度”与“浑成”“冲淡”等审美范畴对举,并将后两者视为比“风度”更为难得的审美境界。他说:“词中警句,初则力求风度,继乃进于浑成,终则使淡而能深,由无情而有情,始为上乘。”[4](P219)“浑成”是一种不见勾勒之迹的情景浑融之境,“冲淡”是一种似淡实腴、自然天趣的美妙境界。虽然它们并非赵氏心目中审美价值最高的风格,与“神味”相比仍有缺失,然而赵氏十分推崇这两种境界,其在《<珠玉词>选评》中大量地使用了这两个命题。如果说赵尊岳对“浑成”的推崇与其对常州派的继承有关的话,那么他对“冲淡”的追寻则更多的是源于内心对“真”、对“情”的体认。虽然“浑成”与“冲淡”一主阳、一主阴,属于两个不同方向的范畴,然而赵尊岳却同时将它们视为价值极高的审美风格,其融通的审美观念在此可见一斑。
三、“重、拙、大”:词作艺术品格的重要尺度
赵尊岳的“重、拙、大”说是在吸收和继承况周颐之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涉及词格、用笔、立意诸多方面,既包含了对词之基本审美品格的态度,又包含了对词之用笔的主张,同“神味”“风度”等审美范畴有着甚为紧密的联系。
“重、拙、大”说最早由端木采提出,后传于王鹏运,至况周颐而发扬光大。况氏《蕙风词话》对“重、拙、大”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其论“重”云:“重者,沉着之谓。在气格,不在字句。”[3](P4447)“重”是气格的沉着。又云:“沉着者,厚之发见乎外者也。”[3](P4447)“情真理足,笔力能包举之。纯任自然,不假锤炼,则沉着二字之诠释也。”[3](P4409)“沉着”是词之内在深挚的情思作用于外在强劲笔力的结果,它并非呈现于个别词句之中,而是整首词所显现出来的气格与境界。可见,“重”是沉挚的感情和深刻的思想体现出的气格,笔力遒健是其重要特征,情思深厚是其根本特征。其论“拙”云:“问哀感顽艳,‘顽’字云何诠?释曰:‘拙不可及,融重与大于拙之中,郁勃久之,有不得已者出乎其中,而不自知,乃至不可解,其殆庶几乎。犹有一言蔽之,若赤子之笑然,看似至易,而实至难者也。’”[3](P4527)刘永济解释道:“况君诠释‘顽’字,归本于赤子之笑、蹄,实则一真字耳。……然而情之发,本于自然,不容矫饰,但使一往而深,自然痴绝,故又曰‘至易’。”[5](P84)可见,“拙”一方面指无可感化、执着不悔的真情,另一方面指不琢不率的自然之性。其论“大”云:“不俗之道,第一不纤。”[3](P4408)所谓“纤”,是指因注重勾勒而失于机巧所形成的尖细、纤靡之弊。可见,“大”与纤滞、轻巧、靡弱相对,是大气、恢宏、壮阔之意。
赵尊岳是最早对况周颐“重、拙、大”说进行阐释的人,也是继况氏之后对“重、拙、大”说论述较多的词论家。可以说,至赵尊岳,“重、拙、大”理论才得以系统完善。他在《蕙风词话·跋》中云:“其论词格曰:宜重、拙、大,举《花间》之宏丽,北宋之清疏,南宋之醇至,要于三者有合焉。轻者重之反,巧者拙之反,纤者大之反,当知所戒矣。”[6](P452)释“重、拙、大”为词的品格,以为其师欲集宏丽、清疏、醇至三种词格于一体,大概近于况周颐所谓“浓穆”风格。而后,赵尊岳在《填词丛话》中对“重、拙、大”亦多有论述。总体而言,赵尊岳对“重”“拙”“大”意涵的理解基本上继承况周颐,但其对“重、拙、大”的理论地位,“重、拙、大”与用字、用笔的关系,“重、拙、大”与“厚”的关系等问题都有新的认识。
“重、拙、大”在赵尊岳的词学审美理论中具有显著的地位。虽然赵氏仅在《蕙风词话·跋》中对“重、拙、大”的意涵进行过论述,但其所有词学审美理论的论说均不忘以“重、拙、大”为旨归。可以说,“重、拙、大”说是赵氏审美理论的基础。如在论述“神味”时,他指出若以王士礻真所谓“神韵”来解释“神味”,“但主风韵,则尚失之俳浅”,以为有“神味”之词当“含嗜深远”,具有沉着、凝重之气,而沉着、凝重正是“重”“大”的最基本特点。又如,在论述“风度”时,他指出:“字面音节求其摇曳,骨干立意,则以重拙大为归。”[1](P166)认为“重、拙、大”是词之骨干立意最基本的评价尺度,只有兼具外在形式的“摇曳”与内在立意的“重、拙、大”之词才是有“风度”之作。在此,他直接将“重、拙、大”视为“风度”的基础。赵尊岳将“骨干立意”视为词的立足点,指出:“词中辟一新境界,立一新意义,甚至用一新字面,无论为侧艳、豪雄、婉秀、激越,要当先在骨干上着力,而不在字面上吹求。”[1](P179)赵尊岳对“骨干立意”如此之重视以致他几乎每次谈到字语的摇曳时,都提醒初学者要注意“重、拙、大”之旨。
虽然“重、拙、大”是针对词之品格提出来的,然而赵尊岳深刻地认识到它并非仅仅关乎词格,同时也关乎词之用字用笔。他指出:“无论写景言情,用笔均当重大。重大又恐易失之拙,则当以至情说至理,出诸慧心以避拙。”[1](P174)“用字先求精当,再及于情味,而归结于重大。”[7](P81)认为重大之笔不但是作词的最基本笔法,同时也是用字的最高准则,但凡作词者都须学会用重大之笔、重大之字。然而,“重大之语,重大之字,重大之意义,极不易入词”[7](P76)。因此,如何掌握它们的用法,成了一门及其重要的功课。赵尊岳在《填词丛话》中为学词者提供了一些具体的门径,提倡初学者先学吴文英:“用字研炼,首推梦窗。梦窗有真情真意,以驱策此若干研炼之字面。又全篇气机生动,使实字不致质滞,此大笔力也,何易语此。”[7](P75)吴文英词是用字炼字的典范,赵尊岳之所以有这种认识并非完全因袭常州派论点,而与其自身学词经历大有关联。他在《珍重阁词集自序》中提到自己刚学词时“欲进于南唐五代”,到后来才发现这并非明智之举,终以“病未能至”而告结。正因为其在学词之道上走过岔路,故而他对学词方法的体会也更为深刻。
此外,“重、拙、大”与“厚”有紧密的联系。在词学批评史上,“厚”之一语最早见于张炎《词源》中,其在评价周邦彦词时指出:“美成负一代词名,所作之词,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词句,而于音谱,且间有未谐,可见其难矣。”[3](P255)虽然张炎此说的重点并不在于“厚”,但这毕竟是“厚”范畴在词论史上的第一次正式显现。到了晚清,越来越多的词论家开始关注到“厚”这一范畴,他们不但对“厚”的内涵进行了总结性论说,而且结合当下词坛的创作实践对“厚”的审美表现也作出新的阐说,如刘熙载“寄厚于轻”、谭献“柔厚之旨”、陈廷焯“温厚以为体”和况周颐“填词以厚为要旨”等论点都是这一时期词学理论结出的硕果。赵尊岳“朴厚”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发展而来的。“词贵朴厚,初非徒以秃笔为藏锋也。朴则直,厚则重,情斯深,味斯永。再济之以婉约之风度,自益见其情致。彼徒矜小慧,漫言清空,以致轻坠词格之清初一流人,何尝能悟及此点。”[4](P214)所谓“朴”即质实朴素,用白描的笔法表现纯朴至真之情;所谓“厚”即笔重、情深,用暗转、曲折的笔法表现沉郁至深之情。“朴”与“厚”的结合,不但是两种迥然不同的笔法相互融合的过程,同样也是词情、词味被最为酣畅地表达出来的过程。晏殊《清平乐》云:“金风细细。叶叶梧桐坠。绿酒初尝人易醉。一枕小窗浓睡。 紫薇朱槿花残。斜阳却照阑干。双燕欲归时节,银屏昨夜微寒。”赵尊岳评曰:“少饮已易醉矣,醉且浓睡,此‘浓’字点出深愁,运字之细,不见斧斤,直开二百年后吴梦窗之蹊径。以后阙重描前阙……但重描则可,过于勾勒则伤朴。词伤于朴,便不浑厚。”[8](P15)“厚”是积于内而发于外的一种情感传达,以“朴”达“厚”,为“朴”而注意“厚”之用法,可见,在赵尊岳眼中,“朴”与“厚”是不可分离的。它与赵氏对“重、拙、大”的追求及对“轻、巧、纤”的反对的整个词学理论主张是相为一致的。
四、结语
归结来看,赵尊岳将“神味”视为词作审美境界的最高理想,由“含嗜深远”的内在深意与“绵邈不尽”的外在韵味相融合而成,内外并举,使这一范畴呈现出融合性、主体性与内蕴性,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神韵”说,另一方面也打破了常州派长期以来以“浑成”为准的格局。同时,他又将“风度”视为词作审美风格的独特显现,“风度”由内而外呈现出“不失佻荡”与“摇曳雍容”的美学特征,不但是“神味”产生的前提,亦是词作必备的审美特质。赵尊岳还将“重、拙、大”视为词作艺术品格的重要尺度,是“神味”与“风度”产生的共同基础。总之,虽然赵尊岳是通过词话的形式来阐发其词作艺术审美观念的,但其审美观具有较为完整的体系,呈现出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特征,在我国传统词学理论批评史上显示出重要的价值与独特的意义。
[1] 赵尊岳.填词丛话[A].词学(第三辑)[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2] 王士礻真.池北偶谈[M].文益人(校点).济南:齐鲁书社,2007.
[3] 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 赵尊岳.填词丛话[A].词学(第五辑)[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5] 刘永济.词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6] 孙克强.蕙风词话 广蕙风词话[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7] 赵尊岳.填词丛话[A].词学(第四辑)[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8] 赵尊岳.珠玉词选评[A].词学(第七辑)[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 邱忠善]
On the Aesthetic View of ZHAO Zun-yue’s Ci-writing
WANG Su-qin1, HU Jian-ci2
(1.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 Zhoushan Zhejiang 316000, China;2. School of Humanities,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31, China)
The aesthetic view of ZHAO Zun-yue’s Ci writing mainly includ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such aesthetic categories as “divinity ”, “grace” and “heavy, clumsy, and big”. “Divinity” is the highest ideal of ZHAO’s Ci-writing’s aesthetic state, “grace” is a peculiar manifestation of ZHAO’s aesthetic style, and “heavy, clumsy, and big” is an important yardstick of his Ci-writing’s artistic character. The above categories, which are related with each other, and reflected by each other, come together to make a complete system of Ci-writing aesthetic view, which has its important value and meaning in the traditional history of Ci study.
ZHAO Zun-yue; aesthetic view of Ci-writing; “divinity ”; “grace” ; “heavy, clumsy, and big”
2015-06-0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ZW006);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3WX06)
汪素琴(1988-),女,浙江乐清人,助教,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词学。E-mail:jchu@ncu.edu.cn
I207.23
A
1004-2237(2015)04-0080-06
10.3969/j.issn.1004-2237.2015.04.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