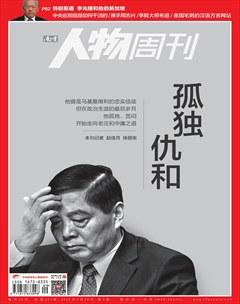水面下的人
邹金灿
知道徐永昌这个人,是在2014年6月。那时本刊的华东站站长陈磊联系上编辑同事白伟志,说有这么一个历史类的题材,适合我去做。这个题材就是徐永昌。刚听到徐永昌这个名字时,我还误以为是徐世昌,一查之下发现不是,而且发现两人的名字虽是一字之差,但行事风格却谬以千里。
陈磊接触到这个题材,也是因为知道李玺林推动兴建徐永昌纪念馆受阻这件事。李先生的事已经在徐永昌封面报道中提及,他与徐永昌一样,都是出身于山西大同,由于对徐这位乡先贤有极深的感情,他近年试图推动大同市建一个徐永昌纪念馆。刚开始时,他接触了大同原市长耿彦波,耿对此事也很上心,但由于后来调离了大同,建纪念馆这件事也停滞了下来。李玺林为此东奔西走,但完全没有进展。我在上海采访了李先生,交谈中发现,他言辞间常为耿彦波调走而痛惜不已。当时给我的感慨就是,“人走茶凉”这4个字,实在说得再精当不过了。
无论如何,对于徐永昌这样一位国军陆军一级上将来说,在其成长地没有一个纪念馆,是说不过去的。
之后,我从广州飞去大同,重访将军故里。出发那天,大雨滂沱,航班延误。由于广州飞大同的航班一天只有一班,如果当天飞不了,就意味着只能改日出发。在机场里等得焦躁的时候,随手上网查阅资料,无意中看到了徐永昌的毛笔字,写得古朴遒劲,中正雅重的气息扑面而来,瞬间静下心去。等了一个小时后,飞机顺利起飞。
历史类题材的稿子向来不好写,而徐永昌这个选题更不好写。最大的限制便是资料短缺。本来国人普遍对这位将军所知不多,我也不例外。国共内战后,徐永昌追随蒋介石到了台湾。而受制于两岸的特殊关系,台湾方面的很多资料无法一一获得,于是只能在手头所得的各种资料中,按图索骥,不断扩充,才慢慢得以充实。其实资料是看不完的,直到稿子写出来后,依然觉得还有很多書需要寓目。
这是一个矛盾:为了选题的写作,不得不多看相关的书,而看得越多,则发现需要看的书更多,这时候提笔,诸多顾忌就如影随形。历史题材吃力不讨好之处,就在这里。
读了5个月的资料,我开始动笔。通篇稿子都在试图解决这两个问题:徐永昌是谁?他有什么遗泽赠予今人?徐身历晚清民国两个时期,见证了满清垮台、北伐、抗战、内战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他为孙岳、阎锡山、蒋介石三人奔走,都竭智穷力,又保持了自我的独立。在蒋麾下时,主要从事幕后工作,事功并不浮在水面上,可谓是个“水面下的人”。好在历史并不总是书写那些水面上的人物,否则一部二十四史只写帝王本纪就可以了,世家、列传可以都不要了——事实上,列传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本纪。
凝视徐永昌那手古朴厚重的毛笔字时,联想到徐的心志和行事风格,我脑海中突然闪过了一句话:这是一位士君子。后来,“士人与将军”这5个字成了主文的标题。士之所以成其为士,其要在修身。《大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徐永昌留给今人的遗泽也在这里,值得书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严格说起来,徐永昌依然属于“水面上的人”,因为他是军令部部长,抗战胜利后又代表中国政府赴日受降,可谓万众瞩目。然而缔造抗战胜利的,还有大量的无名英雄,这些真正的“水面下的人”,同样值得后人纪念。

徐永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