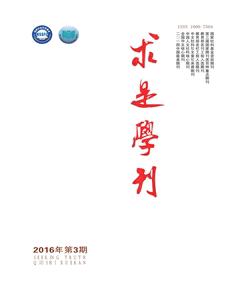教学论的生命之维
摘 要 “实践转向”的教学论研究陷入理论与实践的“伪通约”、传统与现代的“伪衔接”和文本与现场的“伪表述”的两难境地中,根源在于没有真正理解教学论的生长点是什么。教学论是历史性的思想,是实践性的历史,建构“历史·实践”的中国教学论体系,需要建立在通晓历史思维和成就基础上的理论研究,介入现实生活和事实基点上的实践探索,展示学术个性和情怀基准上的品性塑造。
关键词 教学论 生命之维 实践转向 史论建构
著名教育家张楚庭教授在2012年提出“‘理论联系实际着重的是当下,是实用,是功利”[1],“我们更缺的是理论,是哲学,是那种登高望远的志趣”[1],意在阐明理论研究虽然要联系实际情境,但又不能为其所拘囿,理论品质和实践情怀各有其质。反观时下,中国教学论研究的“实践风”在悄然兴起,对“教学理论脱离教学实践”的批判之声不绝于耳。在这种似乎“合情合理”的“扬弃”与“重建”的大势所趋之下,教学论研究的未来路向不但未能愈辨愈明,反而充满着不少潜在的“忧患”,究其根源就在于我们未能真正明确:教学论的生长点或者说生命之源到底是什么?
一、溯因:教学论研究的两难之境
1.理论与实践的“伪通约”
“实践转向”的教学论研究倡导教学理论来源于教学实践,教学理论研究必须从教学实践中寻找问题并以解决实际困难为己任,教学理论研究是解决教学实践危机的工具和手段。但是,真实的研究现状却并非如此。大多数教学理论研究虽然也打着“实证研究”的旗号,但并没有将探索解决教学实践问题的有效策略作为核心目标,要么用旧理论剖析新实际,要么用新实际反驳旧理论,更有甚者,理论对实际的阐释不是“蜻蜓点水”,就是“牵强附会”。理论研究的对象是实践问题,但它却不是“真研究”,于是,“穿新鞋,走老路”现象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本是教学这一事理的两个方面,二者之间既密切通约,又存在距离,即使力倡“实践转向”的教学论研究也需要正视和把握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张力。
2.传统与现代的“伪衔接”
教学论研究在法理上一贯主张要探寻教学经历的历史踪迹、释解教学事件的历史意义,总结教学演变的历史规律以及吸取教学思想的历史精华,在继承传统优秀教学思想上规划教学发展的图景和推动教学变革的进程。但是,真实的研究现状却也并非如此。目前,教学论界鲜有对中国漫长的教学发展史做一番历史性的、系统性的和探究性的深度研究,而是比较关注某一时段、某一人物或某一事件所负载教学主题、内容和意义的探讨,缺乏整体观念的系统思维。这主要体现在对中国教学论史的研究方面,成果稀少,影响乏力。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鸿沟”和“隔阂”造成中国教学论缺乏本土意识和历史根基。
3.文本与现场的“伪表述”
理论教学论与实践教学论的分野不仅仅是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这两种不同研究方法的表征,而且也是教学理论对教学实践改造乏力的体现。教学论的理论性研究和实践性研究本是教学论研究的两个维度,彼此观照和沟通,是教学论研究的双重属性。所以,教学论研究应该将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加以紧密结合,将历史眼光和时代视角进行合理聚焦,使教学论的文本分析与现场调研成为同一事理的统一体。但是,真实的研究现状却依然并非如此。教学论的“理论性研究”被误解成专注于书斋文献的“理论教学论”而饱受责难,并将其界定为“理论的再研究”,如此,那些致力于传统教学思想的理论研究也就极易被认为是皓首穷经式的“书斋研究”而被“贬至末流”,以致众多理论研究者不敢轻易“接近”,即使“闯入”也必要冠之以“实证”之名。从而,文本的理论表述与现场的实践表述混为一谈,失去了各自独特的话语体系。
二、探寻:教学论发展的生命之源
有论者认为,“教学论真正的生长点在于对教学实践的热衷和关注,在于研究者能否真正地走向教学生活”[2]。这是一种明显的“实践转向”的教学论研究观,把课堂教学生活当成是“真正意义”上的教学论来源,尽管它并不否认教学理论性研究的重要性,但是却把侧重于教学论史研究的传统教学论研究的落脚点定位在现实的教学理论与实践上,这就陷入了纯粹的实践误区中。需要明确的是:传统教学论研究并不侧重于教学论史的研究,而是注重以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为宗旨的教学活动研究,“传统教学论的研究更多的是教学论史的研究”[2]这种观点过于狭隘;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美好的“距离”,正因教学拥有这种“理想的理论”和“危机的实践”二者间的张力,才使教学本身不断地以审视自我和调整结构来促使内部要素的优化配置,换言之,教学理论研究需要一定的超越性;“教学生活”的意蕴不仅包括“教学课堂生活”的场域与主题,也包括“教学精神生活”的质量与境界,教学论研究者所走向的教学生活应是一种“具有提升人的生命价值和创造人的精神生命意义”[3]的教学研究场域。
教学论研究者所选择的教学生活样式决定了教学论生长点的定位。“实践转向”、“理论转向”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综合转向”是教学论发展的三个主导方向,具体而言,“实践转向”的教学论研究注重探讨教学现象和解决教学问题,“理论转向”的教学论研究注重归纳教学思想和揭示教学规律,“理论与实践的综合转向”的教学论研究注重借鉴教学经验和规划教学图景。这三个研究方向均不可偏废,因为教学论研究者选择不同的研究目的促成了教学论存在形态和发展路径的多样化和丰富性。教学论研究的根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以教学历史文献为主的史论建构,一个是以教学现实生活为主的问题解决。
教学论发展的生命之源在于历史的回眸和现实的审视,即在梳理教学历史文献基础上的思想提炼和在考察教学现实生活基础上的问题解决。没有理论的“历史”参照,实践的“现实”构建就失去了牢固的土壤,教学论必定会失去本土的话语形式;没有实践的“现实”构建,理论的“历史”参照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教学论必定会失去新鲜的生命活力。教学论研究不可顾此失彼,那种主张“高校应将教学论学习者学位论文的选题规定为必须要基于中小学教学实践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研究”[4]的谬误观点需要我们客观、审慎地加以分辨和修正。教学论发展需要“包容性研究”,既注重史论体系的建构,又注重实践问题的解决;教学论研究者既要“走下去”,又要“上得来”,把“实证研究”和“历史研究”同样作为教学论研究的重要范式,从教学实践和教学历史中寻求教学论发展的生长点。
三、建构:教学论体系的特色之性
1.建立在通晓历史思维和成就基础上的理论研究
“历史的探究,并不是要我们在过去事件中找到今日所需要的答案,而是我们从过去因变的研究,学习到找寻今日答案的方法……要想对现在有深切的认识,就不能不研究历史。”[5]教学论研究的“实践转向”过于重视对当下教学实践的客观关照,忽略对历史教学思想的深度提炼,导致以历史形态延续的教学思想只能停留在文本话语上,而无法或者很少真正融入到实践情境中。教学论是历史性的思想,意在阐明真正的教学论能够清晰地展现历史发展的脉络,从本体论上为教学论的法理存在寻找历史的辩护缘由;教学论也是实践性的历史,意在阐明真正的教学论能够合理地解决教学实践的疑难,从生成论上为教学论的持续发展凝聚现实的多元能量。中国教学论需要更加关注教学论史的整体建构,而不是一味热衷于琐碎的、片段的、肤浅的“个案研究”,虽然教学论是作为一个名称的“舶来品”被引入中国,但是教学论在中国并非是既无“名”又无“实”。中国拥有辉煌的教学史,主要体现在:教学历史漫长、教学名家辈出、教学著作丰硕、教学思想深邃、教学视角多元以及教学影响广泛等,但今日的中国教学论史专著却屈指可数。教学论研究中大量充斥着国外术语,本土色彩暗淡。中国教学论的理论研究必须建立在通晓历史思维和成就的基础之上,一要提炼本土教学思想精华,增强教学理论的时空渗透力;二要遵循本土教学演变规律,增强教学理论的特色呈现力;三要建构本土教学发展图景,增强教学理论的未来创造力。
2.建立在介入现实生活和事实基点上的实践探索
教学论的“实践转向”本意是要扭转教学论研究“重理论、轻实践”的不良倾向,尤其是大量毫无建构效益的教学理论的繁衍既不能促进学科建设,又不能指导教学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还可能遮蔽教学论研究的真实性状而导致教学论研究者个人意识的迷乱。然而,这种“实践转向”的教学论研究却在批判现实的同时不自觉地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重实践、轻理论”。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论者将实践情境中的教学事件描述得绘声绘色,教学问题也定位得毫无偏差,可是在剖析教学事件和解决教学问题的理论诠释上却词不达意、泛泛而谈,原因就在于这些论者根本就没有彻底理解“实践转向”的本真含义,从而忽视理论知识的学习和盲目进入研究现场,理论的空乏致使其对实践的考察和释解缺乏独特的视角和深层的追问。因此,中国教学论的实践探索需要建立在介入现实生活和事实的基点上,但前提是必须要有充分的理论准备,而不是“带着虚空的头脑进入真实的实践情境中盲目地窥视”。一般而言,教学论的“实践转向”有三种方式:一是“目光上的转向”,将研究目光从抽象的理论世界转向生动的实践世界,通过直观教学的日常生活来实现教学论研究的“实践观照”;二是“理论上的转向”,将教学理论的研究立场不再一味定位于“理论促生理论”,而是更要通过解决实践问题来拓展教学论研究的“实践意蕴”;三是“目标上的转向”,将实践探索的目标瞄准在建构理论和改善实践这二者间的双重互动上,使它们共生共荣,共同提升教学论的实践效能。
3.建立在展示学术个性和情怀基准上的品性塑造
我们主张教学论采用“包容性研究”,意在提倡教学论研究者不必拘泥于“常态”,刻意附会时下的“实践呼声”而去做不能充分发挥个人学术优势的“实践性研究”,即善于理论建构的还是专注于教学理论的知识创生,善于实践探索的还是专注于教学问题的策略规划。何况,二者并非完全独立,而是在不同程度上可以相互通约。中国教学论的发展既需要各种风格的教学理论互相争鸣和繁荣共存,也需要各种理念的教学实践互相借鉴和持续变革。为此,中国教学论研究者需要培养丰富多彩的学术个性和兼容并包的学术情怀,以自身学术素养的综合提升来促进中国教学论的品性塑造。毋容置疑,时下中国教学论严重缺乏厚实的本土理论根基,建立在国外教学理论基础上的中国教学论只能算是一种“移植体”,而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体”。有论者认为中国缺乏能够诠释自己教学实践的教学理论,我国教学论研究者没有深入我国的教学实践生成本土的教学理论,而作为教学论研究者又有进行教学理论研究和指导教学实践的职业责任,所以只能用国外的教学理论来诠释中国的教学实践[4]。中外文化思维方式不同,教学思想的呈现载体也自然不同,理解差异在所难免,但据此就断言“中国缺乏能够诠释自己教学实践的教学理论”是不符合事实的。这其实是一些论者在批判“用国外教学理论诠释中国教学实践”的同时,自己也不自觉地用国外的理论思维审视起中国的教学事实。中国教学论拥有自己独特的教学思想基础。因此,中国教学论研究者需要做到两个基本点:一是加强教学理论的科学性,使其成为逻辑严密的组织系统;二是提升教学实践的时效性,使其成为坚实稳固的理论根基。
“理论就是对实践的反驳,理论就是对于实践的超越。”[6]把教学论的生长点仅仅局限于课堂教学生活的实践上是不全面的,况且实践只有在理论光芒的普照下才能生根发芽、枝繁叶茂。一种真正有意义的教学论总是在穿越历史时空、追溯历史踪迹的同时,关照着现实世界和畅想着未来图景。中国教学论的特色建设既需要清晰的教学发展脉络、多元的教学研究风格、本土的教学实践意识,更需要高屋建瓴的教学哲学理论。系统的史论建构和时效的实践探索均是中国特色教学论发展的生命之源。
参考文献
[1] 张楚庭.十问“理论联系实际”[J].大学教育科学,2012(4).
[2] 王鉴.课堂研究概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3] 徐继存.教学生活的精神意蕴[J].课程·教材·教法,2012(3).
[4] 安富海.教学论研究者为什么“走不下去”——兼论“国外教学理论诠释中国教学实践”现象[J].课程·教材·教法,2012(7).
[5] 陈东原.中国教育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6] [德]伽达默尔.赞美理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作者:包兵兵(1985-),男,河南漯河人,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硕士。]
【责任编辑 孙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