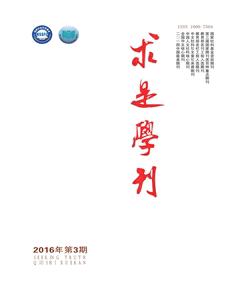学校教育中家长教育权边缘化之原因探析
摘 要 家长教育权是指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权利,其实现对未成年人全面发展作用重大。然而长期以来,在“学校本位”的教育格局中,家长教育权被边缘化。我国传统文化模式是导致其边缘化的根本原因,“天地君亲师”是传统文化模式下的产物,此产物在教育领域中“蚕食”了家长教育权。
关键词 家长教育权 边缘化 传统文化模式 “天地君亲师”
家长教育权是指家长基于其身份关系而享有的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等一切教育中对子女进行教育的权利,其实现对未成年人全面发展作用重大。然而长期以来,在教育实践中,家长教育权不被国家、社会和学校重视,甚至不被家长自己重视,权利受到限制甚至家长主动或被动放弃教育权。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逐渐重视家庭、学校、社区三方合作,也不乏家长教育权边缘化的原因的探讨[1],这对促进家长教育权的实现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迄今为止,家长教育权仍然处于边缘化状态[2]。这不利于家庭、学校与社会齐心协力培养人,严重影响了未成年人的全面发展。笔者认为,已有的原因分析中深层次的探讨较欠缺,削弱了理论与实践的反思与推进力度,文化哲学不失为一个较为有力的视角,本文拟从此视角对之进行探析。
一、家长教育权边缘化现象及教育困境
家长教育权边缘化主要表现在实践层面的家长难以参与学校教育和家长自己弃权以及法律层面的教育权缺乏保障。
1.“学校本位”的教育格局
学校始终是一个享有教育特权的地方,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对于学生而言,教育的权威是学校、教师。在学校,教师似乎总是对的,而学生好像只有听从、服从的义务。对于家长而言,学校、教师也是权威。家长必须“配合”学校而不是和学校“合作”来对孩子进行教育,充分体现了家长在学校和教师面前的被动性、服从性。在学校的教育管理中,家长难以参与,即使参与也只是一个形式:一般都是学生出现问题时或者开家长会时偶发性、临时性地参与,没有长期地形成制度进行;都是家长配合学校的需要而进行参与,使学校能更好地按自己的意愿教育管理学生,而家长的意愿没有表达的机会,即使有表达机会,提出建议,也不会有决策层次的权利。
2.家长教育权缺乏法律保障
我国法律对家长教育权至今缺乏明确的规定。首先,就家庭层面而言,我国家长的教育权与其说是权利,不如说是义务,并没有明确其中的权利内涵。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其未成年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受教育提供必要条件”,“应当配合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对其未成年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进行教育”。《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第一款也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监护是对被监护人的财产权利、人身权利等其他权利的保护职责。因此,对监护人来说,它实质上是一种义务。而国外许多国家的宪法都把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既规定为基本权利也规定为义务。如意大利宪法(1947)第30条规定:“父母的义务与权利为抚养、教导、教育子女(包括非婚生子女在内)”。日本民法第820条中规定,“行使亲权者,享有对子女监护、教育的权利和义务”[1]。我国这种单方面义务性的规定是法律对家长教育权保障的不力。其次,在家庭学校社会合作层面,没有明确规定赋予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管理的权利,相关政策法规也只强调家庭要配合学校、学校要指导家庭教育[2]。而欧美一些国家的家校合作,不仅有完善的制度,而且有具体明确的法律政策保障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管理的权利,如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多国都以法律政策等手段加以推广执行[3]。
3.家长弃权
因长期固化的“学校中心”“师道尊严”“教师中心”,加上家长教育权法律保障不力,家长意识不到自己的教育权利,认为教育孩子是学校的事情,自己可以不管;或即使意识到自己有教育权利但因能力有限却运用不了自己的权利;或有意识有能力但迫于学校教育管理的权威而不能很好地实施自己的权利,最终被迫弃权和出让权利。所以,现实中,家长有意无意地、主动或被动地弃权情况比比皆是。
家长教育权长期边缘化,致使教育出现多重困境:整个社会对家庭教育不重视,对家长教育更不重视,家长因长期的教育实践缺乏、专业培训和教育缺乏而导致教育素养难以提高;学校教育独木难支,弊端重重,学校教育虽然在集体教育和才能培养等方面有其优势,但与之相伴随的劣势也很明显,典型表现是在知识能力、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上,难以兼顾后两个维度,特别是在未成年人的个性和品德人格培养方面明显不及家庭教育,等等,最终严重影响未成年人的全面发展。
二、我国传统文化模式及其弊端
文化模式是特定民族或特定时代人们普遍认同的,由内在的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价值取向、习俗、伦理规范等构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或者说是基本的生存方式或样法[4]。文化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文化哲学的核心范畴。文化模式不同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它不以外显的、自觉的方式为社会的运行和人们的行为提供规范和框架,而以内在的、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制约和规范着每一个体的行为,赋予人的行为以根据和意义。虽然其作用表现不像政治经济制度那样直接和强烈,却更持久和稳定,它是人生存的深层维度。
众所周知,传统农业文明的文化模式是自然主义、经验主义的文化模式。在中国,它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制度为骨架,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维持了几千年。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小农经济是依据自然节律自发进行的重复性实践活动。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家族又扩展到国家,形成宗法制社会。在宗法制社会,重礼治而轻法治,人们并没有建立起自由、平等、开放、自觉的社会交往,没有独立的人格。儒释道在不同层面都主张“天人合一”,这是一种反分化的直觉的整体主义,天地万物都与人相应存在。因此,在上述因素综合作用下,我国的传统文化强调“重道轻器、经世重教、崇古重老、德政相摄、重整体倡协同”[5]。这种文化模式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典型地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气质与性格,使中国文化挺立于世。然而,这一文化模式也存在明显的弊端:第一,个体缺乏主体意识,重整体轻个体;第二,思维方式上缺乏理性意识,重视直觉与经验而缺乏科学思维与分析思维;第三,人际关系上强调伦理意识缺乏社会意识,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仅仅归结为一种内在的伦理关系,而未同时将其视为外部的现实的社会关系。
中国农业社会几千年形成和锤炼的这种传统文化模式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成为无法抹掉的集体无意识。即使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工业文明的现代文化模式给中国人的心灵带来了强烈的文化危机意识并引起人们深刻的反思,但是,这种传统文化模式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异常强大。
三、“天地君亲师”:传统文化模式的产物
“天地君亲师”是中国传统社会崇奉和祭祀的对象,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中许多伦理道德取得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依据。它们就像柱石一样,支撑起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大厦;它们深入人心,被奉为天经地义的信条,比任何法令经典都更有效果。在这里,“师”与“天地君亲”并列齐观,“师”的地位不可谓不高。
追溯历史,可以发现,“天地君亲师”的观念早在战国时期便已现雏形,《荀子·礼记》指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6]缘于中国传统社会特殊的政治背景,“天地君亲师”观念受到统治者理所当然的青睐与利用。至清朝雍正皇帝,还发布上谕:“至圣先师孔子,道冠古今,德参天地;树百王之模范,立万世之宗师;其为功于天下者至矣……”“五伦为百行之本,天地君亲师人所宜重。而天地君亲之义,又赖师教以明。自古师道,无过于孔子,诚首出之圣也……王公虽同属尊称,朕意以为王爵较尊。孔子五世应否封王之处,着询问诸大臣具奏。”诸大臣遵旨议定孔子父亲叔梁纥以上五代“并封为王爵”,并议定了具体封号。[7]在此,将“师”的意义与作用做了新的诠释“天地君亲之义,又赖师教以明”,这为其与“天地君亲”并列齐观,进一步提供了理论和合法性依据。
因此不难看出,教师的权威不仅来源于本身对知识的垄断性占有,更来源于国家赋予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正是传统文化模式的产物。特别是随着社会工业化以来制度化教育形式——学校教育的优势凸显,学校与教师的地位进一步得以强化。而且在我国,当今社会学校教育的强势地位在升学率的竞争中更为突出,这更使得家庭、家长的教育功能进一步弱化,以至萎缩成为学校和教师的附庸,处于从属的地位。
四、家长教育权边缘化:传统文化模式下“天地君亲师”的“蚕食”
在“天地君亲师”这一传统文化模式的影响下,教育系统呈现出明显的特点:第一,系统里各因素差序分明,以学校教师为本位、为中心,家庭、家长是附庸。第二,人伦关系超越客观的现实关系,伦理道德——“师道尊严”是这个王国的行为准则。除了伦理,没有别的规则和“契约”。第三,系统的封闭性。首先,整个系统是封闭的,缺乏对外沟通的意识,导致其保守、守旧。其次,学校教育这个子系统也是封闭的,被文化围墙锁定的学校教育俨然一个小小王国,它有着其以自我为中心的领域主义和评判标准,在“地位超群”的情况下,他们很有优越感,这必将导致夜郎自大和井底之蛙的心态。家庭则成了其圈外之物,彼此之间泾渭分明,尊卑有别,难以往来。
所以,教育活动中,作为受教育者的学生的主体地位丧失便顺理成章了,作为另一个重要的教育者——家长的主体地位的丧失更是自然,因为它不仅地位“低人一等”,而且学校教育根本就不视其存在于系统之中。实际上,对于学生来说,学校与家长都是教育的主体,它们之间本是平等、开放与对话的合作关系,但是,“师道尊严”下,在学校和家庭之间、教师和家长之间伦理关系超越现实的社会关系,现实的社会问题被遮蔽,“师道尊严”几乎成了所有关系的全部。于是,长期以来,家校合作的客观实际要成为一个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几乎没有可能,家庭教育的独立性价值和家长教育权的忽视与遗忘便成为自然而然的事。众所周知的是,在教育领域,学生的主体地位是直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才开始关注和思考的。那么,家长的主体地位和家长的教育权开始受到关注当然就更晚,这还只是近些年来,人们才恍然想起的事情。人们才似乎开始认真思考:对于孩子的教育而言,家长也是有教育权利的,学校应该和家长一起共同教育未成年人;教育的主体不只是学校,还有家庭、家长。
参考文献
[1] [日]久下荣志郎等.现代教育行政学[M].李兆田,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2] 金东海,蔺海沣.我国中小学家校合作困境与对策探讨[J].教学与管理,2012(34).
[3] 黄河清.家校合作导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 衣俊卿.文化哲学的主题及中国文化哲学的定位[J].求是学刊,1999(1).
[5] 刘卓红,黄小东.改革与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转换[J].岭南学刊,1994(4).
[6]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6.
[7] 文庆等.钦定国子监志:卷一[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
[作者:吴小叶(1974-),女,湖南新化人,贵州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副教授,硕士。]
【责任编辑 郭振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