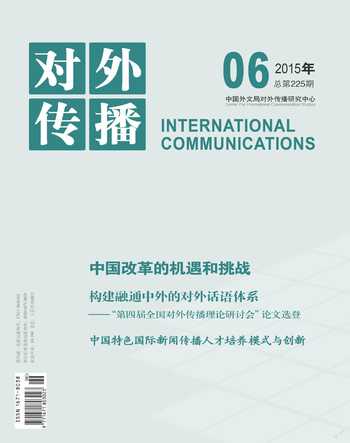国际话语体系中的“中国例外论”
侯自强
一、“中国例外论”产生的背景
对“中国例外论”的讨论要在客观中立的基础上展开,即“例外”并不带有价值判断。但凡讨论“例外”的事物,必须承认存在另一个与之对应的概念——“常规”或“普适”(普世),“中国例外论”亦是如此。一般而言,“中国例外论”有“国内发展模式”和“对外战略”两个分析视角,本文重点讨论“中国例外论”中的对外战略问题。
(一)古代中国的“普世”
与当下“中国例外论”观点相反,古代中国的发展历程更多体现了“中国普世”的特点。中华文明相对于周边文明起步较早,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拥有周边国家难以企及的优势。这种优势很自然地反映在古代东亚地区形成的“华夷体系”中,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坚定地认为“华夷体系放之四海之内皆准”,同时也希望将此论断不断传承下去。正如北宋时期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根据澳大利亚学者张锋的观点,此时期中华帝国对外关系的普世论以华夏中心主义、仁厚和平主义及等级包容主义为主要特征。
(二)近现代以来中国的“例外”
十九世纪中叶以降,中国从一个“老大帝国”逐渐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普世”的基础不复存在。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影响既包含对中国的破坏,也包含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从国内发展来说,中国知识分子讨论的焦点大多围绕“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否符合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一般规律”这一问题,例如“体用之争”“问题与主义之争”及“姓资姓社之争”等等。中国人历次救亡革新的尝试往往也都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从对外关系来说,“中国例外论”更能引起国际社会的争论。经历了半殖民地化的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但是曾经的辉煌让中国人大都认为中国应该重建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地位。
张锋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中,中国对外战略所体现的,可能更多是一种以“革命”为导向的“例外”。由于中国比其他国家更能了解霸权对中小国家的危害,在这一时期,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并提倡“独立自主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原则。这些原则加上“非功利性”的对外援助,让新中国在一段时间内一度占据国际政治的道德制高点。不过,由于受到“世界革命”思想的影响,中国对一些国家国内革命的态度使中国的外交原则与外交实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错位。
改革开放让中国仅用了30多年的时间,近乎完成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一两百年才走完的现代化道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国际社会的担心再次出现:“崛起的中国”是否会重复欧美国家和日本崛起的老路,即“修昔底德陷阱”:崛起国只有通过武力的方式才能取代原有霸权国的地位。在这样的情境下,中国需要一种新型的外交战略与实践。这种战略和实践需要超越霸权转移的理论,构建适合中国和平发展的“特殊”道路。这就是对外战略中的“中国例外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与理论意义。
二、崛起后的霸權与和平发展——“美国的例外”与“中国的例外”?
当谈及“中国的例外”时,不得不提及“美国的例外”,因为正是由于有了“美国的例外”与“普世”之争论,才引发了当下是否存在新型大国崛起的问题。
(一)从“美国例外”走向“美国普世”——美国崛起后的霸权之路
正如钱穆先生所言,从现实中发现问题,在历史中寻找答案。对于历史的考察有助于我们还原“美国例外论”的轮廓。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周琪研究员认为,“美国例外论”是美国外交关系的根源,美国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所有做得好的方面都可以追溯到这一理想主义的根源,所有坏的方面都可以追溯到其假仁假义的态度中所隐含的自高自大和伪善。声明自己在世界上的独特地位可能是美国最古老的政治传统之一。美国建国后在对外关系上始终坚持一种“特殊”的使命,即利用美国“榜样”的力量改造世界。
美西战争后,工业实力增长和领土扩张让美国逐渐认识到获得世界主导权的重要性。这种认识与原有的使命感结合在一起,逐渐成为美国走向世界霸权的动力之一。两次世界大战让美国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构建了以联合国等国际机制为代表的战后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从经济大国成长为一个全方位的大国,这一成长历程也促使“美国例外”的观念迅速向全球扩展。美国的“例外”开始逐渐转变为美国的“普世”。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这让美国的“普世”成为美国人的“骄傲”,更成为政治家们对外推行霸权的重要理据。
(二)“中国例外”——和平与发展之路
仔细推敲美国的“例外”与中国的“例外”,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黄仁伟研究员曾这样概括:美国“例外”的成立条件是空间边疆的扩展可以不断地释放东部积累的矛盾,而这一模式的扩展导致美国在崛起后走向霸权的道路。相反,中国的“例外”利用的是制度的边疆不断释放空间推动社会进步。不过,中国“例外”所释放的制度边疆带来的影响是否是一成不变的呢?改革开放让中国政府和人民体验到了财富带来的好处。然而,正如“金钱不是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一样,我们也不能将“致富”作为一个国家的唯一目标。习近平主席在论述“中国梦”时进行了修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蒙受了外国侵略和内部战乱的百年苦难,深知和平的宝贵,最需要在和平环境中进行国家建设,以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无论从客观上还是主观上看,美国“例外”的成立在中国都没有适用的空间。
客观上看,美国的崛起过程基本是一种“体系外崛起”,美国建国后长期奉行的“孤立主义”原则促使其超脱欧洲国家纷繁复杂的政治与军事冲突,为自己的崛起争取足够的时间与空间。反观中国的发展环境,由于中国已经处于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处于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之内,因此中国在这一全球体系内采取美国式的崛起方式将面临巨大的困难。从主观上看,如同我国领导人曾多次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促进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同时呼吁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始终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中国发展壮大,带给世界的是更多机遇而不是什么威胁。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
三、当前国际话语体系中“中国例外论”的讨论
从目前的国际话语体系来看,针对“中国例外论”的态度,根据立场与价值观念的不同,往往存在比较大的分野。但归根结底无非是两个问题:1.“应然”——从当前国际社会的反馈来看,中国公开的“和平发展”的战略是否被接受为“中国例外”?2.“实然”——从当前的外交实践看,“中国例外”能否用于解释中国的国家行为?
(一)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是否被接受为一种例外?
目前,作为“中国例外论”的重要当事方,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的领导人都不认为中国与美国的冲突是必然的。这从政治上确保了两个大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共识。2011年1月19日,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发表了联合声明:“中美关系既重要又复杂。中美已成为不同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发展积极合作关系的典范。……美方重申,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中方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两国领导人支持通过合作努力建设二十一世纪更加稳定、和平、繁荣的亚太地区。” 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会晤中概括了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原则:“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2013年3月11日,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马斯·多尼伦在阐述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的亚洲政策时,提出“美国欢迎一个和平崛起的、繁荣的中国,美国不希望中美关系被定位为竞争和冲突”。这被认为是美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国提出的这一理念。根据金灿荣教授的分析,这表明“新型大国关系”已经成为美国对华关系中的一个官方概念。
从学者的角度看,中国学者大多对“中国例外论”中的新型的大国崛起问题持乐观态度。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胡鞍钢教授的《2020年的中国:一个新型超级大国》。他相信中国的强国梦想与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崛起存在区别。中国不是一个谋取霸权、主宰世界的超级大国,而是一个主张平等、合作、共治的超级大国;不是一个自我主义、唯我独尊的超级大国,而是主张互利共赢、利益共享的超級大国;不是一个奉行单边主义、排他主义的超级大国,而是一个奉行多边主义、包容主义的超级大国。如何处理与美国霸权的关系是“中国例外论”中关于新型大国论述的重点和难点。对此,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认为:“当今的局势并非要求抛弃美国的价值,而是应该将可实现的目标和绝对的目标加以区分。美中关系并不应被理解为一场零和博弈,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之崛起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战略性失败。”
不仅是美国,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于“中国例外论”也逐渐接受。已故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曾表示:“美中关系不同于冷战期间的美苏关系,……美中关系中,合作与竞争并存……随着中国的崛起,必须让中国的邻国及整个世界都明白他的崛起是友好的,不会威胁世界,只会增进世界福祉,并将着力避免破坏和冲突,让邻国和世界放心是中国的责任,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当然,对于中美两国是否存在根本性的冲突,一些学者也提出了不同解释。虽然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因为不久前抛出“中国崩溃”观点而饱受争议,但是作为美国时下比较有影响力的学者,他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具有一定代表性:“尽管中美两国的政府极力营造一个双方合作的氛围,但是这些合作却无法掩盖中美两国竞争的实质。……这种合作被中美两国相互竞争的两种不同的世界观所遏止:美国希望推广自由秩序,而中国则对此很反感。”
(二)中国的行为是否可以用“中国例外”来解释?
一般而言,中国和平崛起“例外”的根源被认为更多来自传统的儒家文化。正如张锋所言:“一方面它被当做西方国际关系史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又被作为当代中国对外政策和平性的佐证。当代言论多称颂古代中国的和平性与防御性,儒家文化则被认为是这种和平性的主要根基。”然而,部分学者对此持不同观点。同样是从文化因素出发,文化现实主义的代表江忆恩认为:“儒家和平主义仅具有象征意义且不具备可操作性,中国拥有(却经常被忽视)一种可操作的现实政治的战略文化。”“这种战略文化并不同于无政府体系下的自助行为,而是一种强政治的战略文化。”中国传统的军事文献将其解释为:“处理安全威胁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战争手段。”因此,王元刚通过检验中国宋朝和明朝的对外战略认为:“传统儒家文化并不限制中国对外武力的使用。相反,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也使用现实政治的各种手段。中国实际上是根据相对实力的消长决定到底是采取扩张还是防御型的战略。”据此,所谓的“中国例外论”在回答中国崛起的国家行为时被过分夸大了其解释力。
造成上述争议往往与分析视角有关。从宏观上看,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国家行为与所宣传的“和平发展”并无本质矛盾,但是一些学者往往不会从口号或表面文章中进行探寻,相反,他们能从更加具体的政策或行为中挖掘中国崛起的动机。很多学者或政治家通过考察中国具体的行为认定:中国当前的国际定位存在一定的复杂性,这导致了其言行上的一些不一致。例如,沈大伟表示:“中国的国际身份存在多元性的特点,因此她在国际舞台上是一个复杂的国家。……中国的国际身份上没有最后确定,并引起一定的争议。”“当前中国还没有能力影响全球事务。真正的超级大国具备左右事态发展并输出影响力的能力。相反,中国始终强调韬光养晦,在一些涉外文件的谈判中字斟句酌并经常剔除那些自己不赞同的条款”。
方法论的选择往往会引起观点的偏差。欧美学者大多能通过对历史细致考察验证自己的观点。但是,正如威廉·卡拉汉指出,不同学者对于同一段历史材料往往会做出不同的结论。先用实证的方法解释历史,再用后实证的方法对历史材料进行实践分析后才能理解身份认同、安全(文明和军事)的相互影响,只有做到这些才能去质疑儒家的和平主义、现实主义权力政治和新东方论的观点。
尽管“中国例外论”强调大国崛起与体系内原有霸权国不必然导致冲突,但是对于政策是否具备可操作性或是具有较强解释力存在一定争议。简言之,“中国例外论”在“应然”角度上是乐观的,但是从“实然”角度则需要进一步论证。从国际冲突的理论出发也许可以给“实然”问题予以新的解答视角:即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冲突可以无需用“中国例外”的观点来解释。根据卡尔·多伊奇的观点,国际冲突分为1.拼到底/共存;2.根本性/偶然性。其中,根本性冲突不一定非拼到底,偶然性冲突不一定是共存的。例如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的冲突是根本性冲突,但是双方却不得不实现共存。这种分析方法是否也同样适用于当下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状态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最后,所谓的“例外”不过是一种认知的结果,而并非是一个事实,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活动本身才是问题的焦点。如同外交学院卢静教授所言:“中国例外论可能是一个伪命题,‘例外思想反映出一种与外部世界的距离感。”我们可能需要改变对“中国例外与否”这一命题的态度,而并非纠缠于“例外”本身的含义。
(因版面所限,本文略去了作者所加注释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