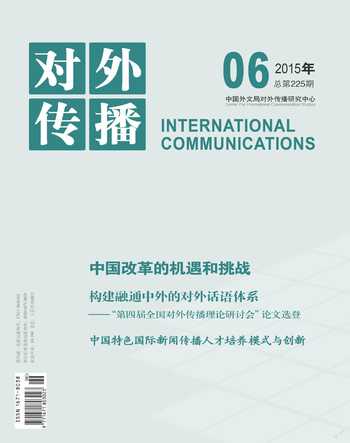透过内外舆论场的比较研究看中国
程云杰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及国内信息流传播速度与广度的增大,海外媒体关于中国新闻的报道正在从以时政、经济新闻为主的格局,转向报道更多的社会文化新闻,国内民众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海外议题设置。人们看到越来越多类似大妈广场舞、羊年说羊、Duang这样非常接地气的中国新闻正在进入海外主流媒体和新闻网站的视野。
这些外媒报道其实就像一面镜子,从不同角度照出了中国社会的世间百态,如果点开来阅读读者的评论,就更能够看到中外视角的差异,这些差异为我们预判对外传播效果和审视国内现实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借鉴。
镜鉴中国现实
值得探讨的最近一则报道案例是黑龙江庆安火车站暴力袭警案。中央电视台播出视频表明45岁男子徐纯合用电棍袭警,警察对其开枪并将其击毙后,英文网站Shanghaiist.com对此新闻进行了转载,并引起了外国读者的跟帖。评论中不少人除斥责徐在警察面前摔孩子和袭警外,还提出这样的行为在任何国家任何法律环境下都应该受到严惩。但是值得思考的是,他们也提出了以下的疑问:为什么当事警察在与徐对抗期间,他没有得到警力支援?为什么周围的乘客能够完全忽略这场发生在身边的冲突,继续置若罔闻地买票行走?为什么在对抗中没有人去保护孩子?为什么警察没有尽早将徐制服?这些隐含在评论中的提问其实很具有启发性,会让我们发现自己的“视觉盲点”,看出平常不一定会注意到的问题,比如说警察是否在处置突发事件中树立了权威?当前的警民关系应该如何来描绘?
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警察的权威应该是不容挑战的,在危急关头,他应该得到公众的支持,如果警察的权威性遭到挑衅,警察执法就得不到公众的支持,那“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依法治国”的原则在落实中不是会大打折扣吗?若干年前,有婴儿被汽车撞伤数十人路过而不管的消息被曝光后,有一位即将来华的外国朋友向笔者感叹,中国的经济发展那么快,人心却那么冷,这样的国家谁敢去啊?这位外国朋友的反应令笔者惊出一头冷汗。同样,在这个案例中,国内舆论的焦点大多在于警察该不该开枪击毙对方,但是外国读者关注的焦点却是这个国家执法系统是否具有权威性,这个国家的警察是不是训练有素。他们的逻辑其实不难理解:如果一个国家的警察群体缺乏威信和公众支持,那这个国家恐怕是很难让人有安全感的。
雖然这起案件只是一则个案,但是一滴水珠也可以同时折射出太阳的光芒和空气中的雾霾,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发现的眼光。对法律案件报道的分析其实不仅关系到对外传播能力的建设,也关系到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风气的引导,如果没有对内舆论引导的配合、相关政府部门和机构的真抓实干、民众的反思,对外报道再怎么描眉画眼,也很难提升我们的国家形象。对外报道要有突破,除了记者队伍文笔好、语言好、角度巧外,更重要的还是整个社会能够针对一些热点事件做出反思,并在反思中采取行动。只有这样,内外舆论场的互动才能推动中国的长足进步。
直面标签化炒作
因为不了解中国,外媒在解读中国新闻时常常会从他们的思维定式出发做出一些误读,这些误读中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是从某个小切口出发,把与中国有关的人、事、物“标签化”“政治化”。今年以来的例子很多,其中就包括广场舞的报道。体育总局宣布推出12套“标准化”广场健身操舞后,一些喜欢跳舞的老年爱好者表示反对。沸沸扬扬之间,美国《华盛顿邮报》专门以“中国向广场舞大妈宣战”为题播发了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甚至将这一举措比作为四五十年以前推出的八大样板戏。幸好体育总局已出面澄清说这12套广场舞,纯属引导,绝非强制。
为什么外媒会这样反应过度?其实在欧美受众的眼里,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一直是依赖于“大政府,小社会”,政治动员的能力和效果远远超过他们的想象。虽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直在强力推进简政放权,划定政府部门的权力边界,为各类社会参与主体制定负面清单,一些政府部门的手还是伸得太长。否则不会出现一个地方楼塌了,记者去报道,地方领导却抢相机禁止拍摄的行为。这种行为透露了官员背负的压力和恐惧,生怕自己辖区的一亩三分地出个纰漏。其实楼塌总有楼塌的原因,既然楼已经塌了,面对现实,做好救援和信息公开,查找问题是很正常的解决问题之道。为什么要怕要躲?其实就是大政府的意识在作祟,因为有大政府的意识,所以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搞定,在工作中没有对法律和他人权利心怀敬畏,也正是因为有这种意识,官当得累。
如果仔细看这两个案例就会发现,一方面是西方媒体在给我们强加一些政治化的标签,另一方面我们一些官员还没有搞清楚主要精力该放在哪儿,该如何行使手中的权力。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引用《礼记》《论语》详解政府工作报告中“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的表述,他强调纵观中国历史,凡盛世往往都“居敬行简”、轻徭薄赋,政府施政要义,在于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这是非常睿智深远的判断。我们在从事对外报道时,常常会有意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但是特殊性强调得过多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外星人”,一个“外星人”要融入地球人的生活多难啊!所以,从对外传播的策略来看,笔者认为应该多讲共性, 共性多了意味着交集大了,交集大了才意味着可对话的空间才能扩大。
要避免别人把我们的社会治理泛“政治化”,一方面我们要知道简政放权是努力的方向和重点,另一方面也要多报道社会和民间力量的发展,多报道社会各界围绕公众事务进行的协商与沟通。最重要的还是各级政府机关,特别是被李总理喊话的那些不作为或随便作为的处长们,要真的认识到加快政府自身改革、实现放管结合、职能转变的重要性,并且确实行动起来,否则海外媒体和受众对我们的偏见是很难被消解的。
把握中国文化脉动
一个全球竞争力不强的国家是不可能孕育一个强势文化的。中国正处在综合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的上升期,中国的文化也在此刻对西方受众产生了极强的吸引力。但是从新闻媒体的报道来看,海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并不是指我们的传统文化或者东方哲思,而是集中在流行文化上。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传统文化复兴上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如果当代中国人都把复兴中华文化的任务交给祖先,继续急功近利、勾心斗角,利欲熏心,外国读者从当代中国人身上看不到祖先教导的传统美德。除了汉学家们,普通人怎么会对中华传统文化感兴趣呢?
现在,包括Duang,“有权不能任性”在内的各种网络流行词频繁见诸报端,国人对羊年的表述该用绵羊(sheep)还是山羊(goat)的热议,“最强大脑”娱乐节目,中国父母给孩子起英文名的纠结,等等,都会引发境外媒体的关注。这其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越来越多的海外受众对当代中国的文化感到好奇,希望了解这个人口众多、文化多元的庞然大物。透过解析这些流行元素,他们想捕捉中国人的喜怒哀乐,以及国民心态和情结,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现象。以羊年说羊为例,早年我们对圆明园兽首中羊首的翻译用的就是山羊,但那个时候没见哪个海外媒体对此提出异议,羊年也一直被翻译成山羊年,可是现在他们提出山羊在西方文化里一直是和“好色愚蠢”挂钩,是纯正的贬义词,并且试图借此来挖掘中国人的国民心态,这是新现象。
新闻是易碎品,它在国内国外两个舆论场的互动是在分分钟之间转换的,对这两个舆论场进行比较研究,一方面可以让我们的对外报道更有针对性,更贴近海外和国内受众的关切,但更深远的影响还在于一种镜鉴效应,让我们通过两个舆论场的受众对新闻事件做出的不同反应,去发现自己的不足和有待改进的地方。这种改进不能局限在新闻采编的层面,而是应该把这种比较研究的精神扩展到各个部门各个行业的决策者中间,这样我们对自己才会有更冷静的判断,才不会迷失在新闻的易碎性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