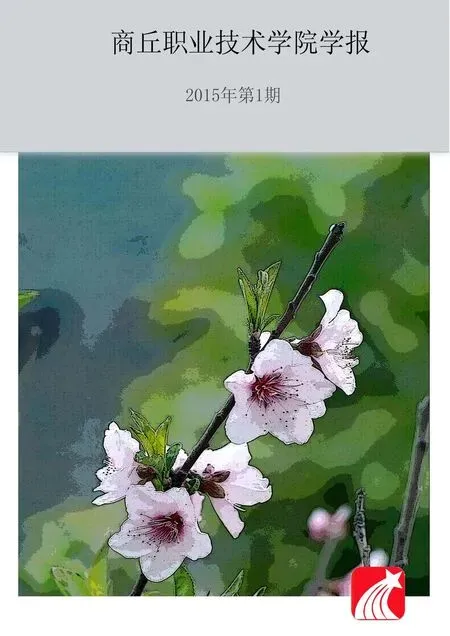论《诗经传说汇纂》之文学倾向
——以《关雎》篇为例
吴 蔚,刘 莉
(1.北京联合大学 应用文理学院,北京 100000; 2.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北京 100000)
论《诗经传说汇纂》之文学倾向
——以《关雎》篇为例
吴 蔚1,刘 莉2
(1.北京联合大学 应用文理学院,北京 100000; 2.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北京 100000)
《诗经传说汇纂》为清代帝王钦定之经学著作,《四库提要》称其“考证详明,一字一句务深溯诗人之本旨”。通过对其中《关雎》篇的分析,可以认为此书以《诗集传》为纲,但并不唯朱子是从;更重考据和实证,对于毫无根据的主观分析能够采取批判的态度;更重文学表现手法的探究。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超出钦定本编定初衷的文学研究倾向和价值。
《诗经传说汇纂》;《关雎》;学术史
《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以下简称《诗经传说汇纂》)共二十卷,序二卷,由王鸿绪主编,于康熙末年御定刻成,雍正五年雍正皇帝亲自作序颁行。作为代表官方思想的钦定经学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此书“考证详明”,“岂前代官书任儒臣拘守门户者所可比拟万一乎?”评价甚高。然后世对此书的评价似非如此:胡朴安的《诗经学》在“清代诗经学”一章中竟然没有提到此书,也未提及王鸿绪其人;夏传才的《诗经研究史概要》在“清初汉学复兴与《诗经》”一节只把此书作为“用皇帝的名义颁行的以宋学为基础的宋汉学通学的《诗经》著作”[1]173,一笔带过;陈国安《论清初诗经学》一文[2]76在略述“清初诗经学”时,罗列了清初治诗经学18名家,唯独没有列入王鸿绪,而只是在此部分末尾提到了他“奉旨”作了这样一本书。本文试图探讨此书的编辑意图和宗旨,并以《诗经》首篇《关雎》为代表,分析其中的文学倾向,探索本书的价值所在。
一、问题的提出:经学?文学?
雍正在《世宗宪皇帝御制诗经传说汇纂序》中称:《诗经传说汇纂》“以朱子之说为宗”,“首列集传,而采汉唐以来诸儒讲解训释之于传合者存之。其义异而理长者,别为附录。折中同异间。”其编排体例为:首列原文诗句,次为朱熹《诗集传》注释,注释下间有诸儒对注文的讲解训释,重点在字词的解释;然后有“集说”,加以选择地汇集了从汉唐以来对本诗句的章句;还有“附录”,收录所谓“义异而理长者”;每篇最后有总论,收录各家对此篇章的评说,还有编者按语。从序言来看,《诗经传说汇纂》以朱熹之注释为宗,其他人的训释多为与朱传相吻合者,但是又开辟了“附录”一栏,收纳与朱传观点不同的言论。《诗集传》是宋学研究《诗经》集大成之作,《诗经传说汇纂》是清代承袭宋学衣钵的一本经学著作是显而易见的。
在序言中,雍正还明确指出了编辑《诗经传说汇纂》的目的:
“朕惟诗之为教,所以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其用远矣。”
“而先王之诗教,借以明国家,列在学官,著之功令,家有其书,人人传习,四始六艺,晓然知所宗尚。”
“我皇考指授儒臣,勒为是编,期以阐先王垂教之意,与孔子删诗之旨。学于是者,有得于兴、观、群、怨之微,而深明于事父事君之道,从政专对,无所不能,则经学之实用,著而所谓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者,亦于是乎。”
从以上序言所述可见,此书编纂的根本目的是“诗教”,具体说来是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希望它能够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诗教”论源于孔子,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学习《诗》三百篇就是要使人归于雅正。这句话成为后世“诗教”论的理论依据。孔子还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可以“感发志意”,可“观风俗之盛衰”,“群居相切磋”,还可以“表达怨情”。既能帮助人们事父事君,具有政治功用,还可以让人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增长知识。继孔子之后,《诗大序》又明确提出了诗歌政治、社会功能。“成孝敬”一句即出自此序:“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强调统治者应当利用诗来教化人民,维护统治者所需要的道德风尚、社会风气,以巩固统治秩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毛诗》被列为官学;唐代孔颖达奉旨作《五经正义》,其中就有《毛诗正义》。从汉代以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诗经》作为儒家经典的政治教化作用。宋代朱熹的《诗集传》也成为当时乃至后世读书人必读的书目。清代统治者也不例外,《诗经传说汇纂》就是用来“列在学官”,“人人传习”以“深明于事父事君之道”的。
对于此书的编辑目的和宗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出了颇为不同的解释和评价:“圣祖仁皇帝天亶聪明,道光经籍,研思六艺,综贯四家,于众说之异同,既别白瑕瑜,独操衡鉴,而编校诸臣亦克承训示,考证详明,一字一句务深溯诗人之本旨,故虽以《集传》为纲,而古义之不可磨灭者,必一一附录,以补缺遗于学术,持其至平,于经义乃协其至当,风雅运昌,千载一遇,岂前代官书任儒拘首门户者所可比拟万一乎?”
从这段评议中,我们看到,《提要》认为《诗经传说汇纂》的编辑宗旨是以“深溯诗人本旨”为要。笔者认为,这句话看似普通,对于诗经学的研究则非同一般。因为作为经学典籍,《诗经》是我国古代统治者进行教化的工具,传《诗》的目的是为了“用之乡人,用之邦国”。因此会强加给《诗经》以封建伦理道德思想,作为政教和德化的必修科目。正因如此,《诗经》的许多真正的篇旨反而被掩盖了。其实,朱熹本人已“初步用文学的观点来研究《诗经》”[1]143,但其本人的理学思想与他对《诗经》进步的研究方法时时产生矛盾,受到制约。而产生于清代的《诗经传说汇纂》如果真如《提要》所述以诗人本旨为务,当是一大进步,对《诗经》的文学研究产生了较大的贡献。
那么《诗经传说汇纂》在实际的编纂过程中究竟遵循着怎样的宗旨呢?经学的,或是文学的?是如《序言》所述,还是如《提要》所述呢?以下就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诗经传说汇纂》中《诗经》首篇《关雎》为例,进行深入分析。
二、《关雎》之分析
《关雎》为《诗经·国风》之始,可冠乎三百篇。孔子曰:“《关雎》至矣乎!仰则天,俯则地,德之所藏,道之所行。大哉!《关雎》之道也。”(《韩诗外传》卷五)历来注家对《关雎》的解说非常重视。因此,对此篇的分析应该具有代表意义。
(一)关关雎鸠、挚而有别与猛鸷非和

到了《诗经传说汇纂》,这一问题有没有突破或改变呢?我们看到在谈到“雎鸠”名称的朱注之后,引用了5则资料:
1.《左传》:少皥氏以鸟名官,“雎鸠氏”即司马的意思;
2.杜预注:对为什么以“雎鸠氏”为官名做出解释,因为此鸟“挚而有别”;
3.陆机:雎鸠为人名;
4.杨雄、许慎:雎鸠为白鷢似鹰,尾上白;
5.郭璞:雎鸠为雕类,今江东呼为鹗,好在江边泜中。
前两则实为一则,而杜预是西晋人,不会没有读过《毛诗》,所以,这样的解释多为引用毛诗,不足为据。后两则实际上否定了自毛诗以来对雎鸠鸟为王雎的解释,认为它不是野鸭或鸥类等性情温和的水鸟,而是一种类似鹰或雕的猛禽,至于有没有雌雄相随的习惯,没有提及。如果承认这一说法,那么“挚而有别”之说就不能成立了,更不用说“后妃”之说。
再看在朱传“挚而有别”之后的一段,《诗经传说汇纂》有4则材料:
1.郑玄:用声训解释“挚”为“至”;
2.欧阳修:认为毛亨之“挚而有别”是偏指一方,重点不在“挚”而在“有别”,“听其声则和,视其居则有别”,并说明这是诗人的取舍;
3.“一家”之说:猛鸷说,“谓雎鸠是鹗之属,鹗自是沉鸷之物,恐无和乐之意”;
4.点明“鸷而未尝狎”与“乐而不淫”之联系。
其中第1、2、3则材料之前都有圈加以隔断,第4则明显与上文语义不符,似是编者自己的语言,但并未加圈。而第1、2、4则材料从观点上看大同小异,都在解释“挚而有别”,只由第3则所谓不指名的一家之说,实与上文杨雄、许慎、郭璞的解释相一致,提出了关雎为猛禽,不像有和乐的生活习性。但这个观点并未展开而深入下去。为什么不指出姓名?为什么欲言又止,语焉不详?恐怕这与从毛诗以来的经学观点相违背,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有关。但是,这些材料的出现,无疑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是对经学解说的试探,或是质疑。但仅此而已。试想,如果沿着“猛鸷非和”的思路探究下去,那么对于《关雎》的解说会是颠覆性的改变,这个改变会使《诗经》从经学走向文学迈出更大的步伐。
(二)淑女、后妃与妾媵
紧接着的一句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对于此句注释的关键在于“淑女”与“君子”为何许人也。毛传曰:“窈窕,幽闲也。淑,善。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这个解释似乎认为“淑女”即“后妃”,“窈窕淑女”即幽闲贞专的好女子,具有后妃之德。所谓“后妃”说,即:“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
朱传则曰:“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称。盖指文王之妃太娰为处子时而言也。”也就是说,淑女并非指“后妃”,而是指未出嫁的女子,只不过这个女子非常贤淑,具有成为后妃的潜在资质。朱传还明确指出这个淑女就是指周文王之妃太娰为处女的时候,说得十分具体,并由此认为,“君子”就是指文王。由此看来,朱传与毛传至少在“淑女”的问题上基本一致,淑女是指后妃本人,只不过朱熹更加强调为后妃为处子之时。
而郑笺及孔疏观点有所不同,他们认为淑女并非后妃,而是于后妃之外的其他淑善女子。笺云:“言后妃之德和谐,则幽闲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谓三夫人以下。”说得非常具体。而孔疏曰:“后妃心之所乐,乐得此贤善之女以配之。君子心之所忧,忧在进举贤女,不自淫其色;又哀伤处窈窕幽闲之女未得升进,思得贤才之与共事。君子劳神苦思,而无伤害善道之心,此是《关雎》诗篇之义也。”二者无非都是说,后妃有德,不仅不嫉妒“淑女”,而且乐得为君子寻此等贤淑女子来配君子,与之共事。由此,“淑女”不是后妃,却能表现“后妃之德”。而“君子好逑”的“好”字,也由读hào,变成了hǎo(郑玄注:好,呼报反),因为,在“淑女”之前既然已经有了“后妃”,又如何成为“好的配偶”呢?这两则解说,《诗经传说汇纂》只编入了“附录”之中,说明并不认同这一观点。
《诗经传说汇纂》所辑资料在此问题上也提供了不同的看法。在“集说”中汇聚了6人的观点:
1.毛苌:观点和朱熹基本一致,认为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
2.程子:观点和朱熹也基本一致,只是突出了“其所忧思在于进贤淑,不在于淫色,无伤善之心也”。最为难得的是,他批判了郑玄和孔颖达的说法。他提出了两条极具说服力的理由。第一是“后人以为,后妃乐得淑女以配君子,配为后妃可称后妃,自是配更何别求淑女以为配”。也就是说,已经得到淑女配为后妃了,为何还要求其他淑女?这和现代人的观点基本一致了。第二是“淫其色乃男子之事,此自关雎之意,如此非谓后妃也”。他的意思是,求淑女是男子的喜好,怎么会成为后妃的事情呢?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说成是后妃为君王求淑女,不嫉妒,真是太荒唐了;
3.黄櫄:他认为“不淫其色乃关雎之义,不足以形容后妃之德”。也就是说,把关雎说成后妃之德实在太过拔高了,充其量也就是普通人能够不淫其色而已。这个理解也把《关雎》从经学的解释拉回普通的文学作品;
4.严粲:认为“关关雎鸠”是“兴后妃德”,与朱子同义;
5.朱善:文王德之“敬”,太姒德之“淑”,仍为朱子解说之补充;
6.黄佐:没有明说支持朱熹或是郑玄的观点,但提出“妇顺内和而家理”,“男教外和而国治”。
由此看来,毛苌、程子、严粲、朱善、黄佐都基本与《朱集传》(《诗集传》)之观点一致,其中程子还对郑玄、孔颖达的所谓嫉妒说进行了批驳。在此诗最后的按语中,编者还专门就“嫉妒说”进行评判,指出“至朱子不主后妃自作,盖因君子好逑之语,以为非众嫔御所可当。且专主一事,其义为狭,论固宏远矣。”而黄櫄的观点却与以上众人有较大不同,虽然仍旧强调“不淫其色”的道德观念,但是已经把《关雎》从后妃之德开始拉回到民歌抒写普通人的实质上来,实为难得。
而纵观全篇的解说,朱子也未免有自相矛盾之处。在首章末尾,朱子总结道:“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参差荇菜,则当左右无方以流之矣。此窈窕淑女,则当寤寐不忘以求之矣。盖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则无以配君子,而成其内治之美,故其忧思之深,不能自已,至于如此也。”上文强调淑女是文王之妃太姒为处女之时,这里又说成后妃求淑女来配君王,以成就自己的“内治之美”,朱子可谓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而第三章的章旨中说“窈窕淑女,既得之则当亲爱而娱乐之矣。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则有以配君子而成内治,故其喜乐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此云”。到底是后妃乐得此女,还是君子乐得此女,抑或二人都乐得此女,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第一章的集说中还有“朱子曰”一段话:“此诗看来是妾媵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侧之事,外人做不到此。”“妾媵”之地位又远不能与后妃相比,那么即使要给君王纳妃那也不是“妾媵”所想之事吧?把这首诗说成是“妾媵”所作就更离谱了。《诗经传说汇纂》所采用的程子和黄櫄的观点,也可以看作间接地对朱子之偏加以修正。
总之,《诗经传说汇纂》中对于“淑女”的身份问题,编者有所顾虑,在按语中称“然亦未尝以郑氏为非也”,并且说明:“今以朱传为宗,而仍附其说于章末,俾后之学者见自有《关雎》诗以迄汉唐诸儒之论,盖如此。”但实际上对“后妃说”和“不嫉妒”的说法提出了一定的质疑,是有鲜明的倾向性的,为还原《关雎》的文学本色给读者提供了线索。
(三)兴、比与兴中有比
“兴”是《诗经》“六义”之一。在对《关雎》篇的解说中,毛传只在开篇第一句之后直接说“兴也”,《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篇案曰:“兴是譬谕之名,意有不尽,故题曰兴。”兴既然是“譬喻”,那么比又是什么?这些解说都很简单,有些语焉不详。《诗集传》对此贡献很大。朱熹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然后又说:“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后凡言兴者,其文意皆放此云。”“雎鸠”即朱子所言“他物”,而文王求淑女以配为后妃即所要引起之词。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君子与淑女相和乐而恭敬就有如雎鸠的挚而有别。实际上,朱子的解释提到了“兴”中含“比”的问题,但他没有明说。
《诗经传说汇纂》在此条之后补充了两则资料,对《诗集传》进行了很好的补充。第一则还是朱子的话:“兴,起也。引起吾意,如雎鸠之挚而有别之物,引起此起兴,犹不甚远。其他亦有全不相类,只借物而起吾意者。虽皆是兴,与此又略有不同也。”此处强调起兴之物可以与引起之词毫无关系,言下之意,此处二者之间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谓关系“犹不甚远”。那么是什么关系呢?依前文所述,其实就是“比”。第二则是吕祖谦的解说:“首章以雎鸠发兴,后章以荇菜发兴,至于雎鸠之和静,荇菜之柔顺,则又取以比也。”他直接道出,雎鸠也好,荇菜也好,都是兴中有比。把前人及朱子未明言者表述出来。在篇末的“总论”中,还引辅广之说:“此皆是兴而兼比。首章以关雎起兴,因以关雎挚而有别为比。二章、三章以荇菜起兴,亦以荇菜为比。但先儒皆取于荇菜之洁净柔顺,而《集传》只言其不可不求者,岂非正以其洁净柔顺之故乎?”此处直接点明了“兴中有比”的问题。
关于“比”,在《诗经传说汇纂》的此篇中也有前人未述之处。对于第三章“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毛传说:“宜以琴瑟友乐之。”郑笺云:“言贤女之助后妃共荇菜,其情意乃与琴瑟之志同,共荇菜之时,乐必作。”但情意为何“与琴瑟志同”,似乎还讲得不透彻。于是孔颖达进一步为之解说:“毛以为后妃本己求淑女之意,言既求得参差之荇菜,须左右佐助而采之,故所以求淑女也,故思念此处窈窕幽闲之善女,若来,则琴瑟友而乐之。”真是越说越离谱,牵强附会,都是为了“后妃之说”能够更为圆满,离国风作为民歌的创作本意越来越远。但是,孔疏最后还说明:“以琴瑟相和,似人情志,故以友言之”,这倒是把琴瑟与友之比拟关系说出来,有一定道理。《诗经传说汇纂》对于孔疏不合理之处没有采纳,而把这一条列在了“集说”当中。《诗集传》只解释了“琴”和“友”的意思,并未说明“琴瑟”与“友之”之间的关系。而在这部分的朱注之后,《诗经传说汇纂》列入了吕祖谦的解说:“友亦乐也。钟鼓有时,而奏琴瑟无时。而不在侧,若朋友然,故曰友。”这一句进一步挖掘了琴瑟的比拟意义,不仅琴瑟相和似友人,琴瑟与人的关系也如同朋友一般。古代文人墨客以琴为友,琴不离身者甚多,此说也极为有理。
总之,《诗经传说汇纂》在《关雎》篇艺术手法的探讨上花费了很多笔墨,对于前人的解说做了大量的补充,把释文的一部分关注点从经学转到文学本身,解释更为合理,更符合《诗经》的本意。
三、结语
通过对《诗经传说汇纂》之《关雎》篇的分析,笔者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于此书的评价是基本公允的。虽然此书为康熙皇帝所钦定,雍正皇帝亲自作序,其经学的目的十分明显,价值取向也没有脱离维护三纲六纪,编纂的主要意图是进行教化,但是编纂者已处处显示出文学研究的思想倾向,使得此本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超出钦定本编定初衷的文学研究倾向和价值。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诗集传》为纲,但并不唯朱子是从。对朱子的解说既有他人的补充和阐发,又有存疑和异说。力图冲出经学的视野,汇集众说,提供崭新的思路,不同的观点亦可见于其间。但又并非无所取舍,优劣杂陈,通过集说、附录、按语,倾向性不言自明;第二,更重考据和实证,对于毫无根据的主观分析,牵强附会的解说训释,能够采取批判的态度,对完全不合情理的经学观点能够大胆进行质疑和批判;第三,更重文学表现手法的分析,对前代未涉及或展开的艺术手法做了大量探讨,艺术分析比重大大增加,对以往解释较少的比、兴等手法有较多的探究。
我们在提到“钦定”经书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有一种心理暗示,即其代表统治者的思想无疑,政治教化目的鲜明,而文学的价值则会打上折扣。但是,不经过阅读和比较是没有发言权的。通过对《关雎》篇之研读,我们让披在《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上的经学外衣逐渐脱落下来,而露出其文学的本来面目,使其在文学的发展历程中记录下自己应该有的一笔。
[1] 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M].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
[2] 陈国安.论清初诗经学[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责任编辑 袁培尧]
Literature Tendency ofTheBookofSongsandLegendsCollective: TakeGuanjuas an Example
WU Wei1, LIU Li2
(1.CollegeofApplicationArtsandScience,BeijingUnionUniversity,Beijing100000,China; 2.BeijingJiaotongVocationalTechnicalCollege,Beijing100000,China)
Thebookofsongsandlegendscollectiveis a Confucian classic of the emperors of Qing Dynasty imperial order, whichQuanShucalled “detailed textual research, every single word or phrase recalled deeply the nature of poet”. By analyzing theGuanju, the author thinks this book takesshijizhuanas the key link, but not completely followed Zhu Xi in textual research and demonstration; more important, the book can adopt a critical attitude for the subjective analysis groundless; and it explores more literary techniques of expression. Therefore, to a certain extent it has literature research tendency and value exceeding authorized version purpose.
thebookofsongsandlegendscollective;Guanju; academic history
2014-12-26
吴 蔚(1972— ),女,湖南长沙人,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副教授,河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史研究;刘 莉(1970— ),女,湖南湘西人,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高级讲师,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I207.22
A
1671-8127(2015)01-006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