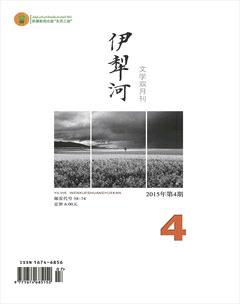旧时味道(外二篇)
李颖超
旁人谈起过年,总有些难忘的回忆,而我打童年开始,就不喜欢过年。因为是家里的老大,下面有妹妹弟弟,所以既不娇生也不被惯养。
总是一进腊月,家里人就开始忙了。
当父母开始蒸馍馍的时候,给馍馍点红点,在花卷上塞红枣,拿把小剪刀在面疙瘩上剪刺猬……这样的美事都是弟妹的,因为好玩。
八岁的我就拖着一个长条大铁盆,用搓板洗全家的被褥、帘帘单单和换洗的衣服,洗衣服的洗涤剂是毛纺厂洗羊毛的清洁剂,家家都用这种洗涤剂,泡沫大得要命,需要用肥皂洗过第二遍,然后淘三遍才能彻底把衣服给洗干净。所以,每到过年,看到小山样待洗的东西我就发愁。
洗完衣服,晾一院子,左邻右舍见了交相夸赞,以至于我长大后,厂里的老人们都愿跟我家结亲,因记得我从小就能干。
等院里冻得梆梆硬的衣物干了后,我的差事就又来了,缝被子。先把被里子在大床上铺好,把棉絮小心搁上去,再将缎子被面铺好拉平,把被里的边均匀折好,穿针引线,戴上顶针我就动工了。开始妈妈做示范,后面就越干越娴熟了。
上师范的三年,因为会缝被子,得了好些实惠。女生请我缝被子,总有小礼物感谢,男生刚开始不找我,他们先找心仪的女生缝,等女生连被子带床单给他缝一起时,便得请我了。
想想还是现在好,一床蚕丝被,一个被套,永远不需要缝被子。
大概十岁的样子,家里搬了更大更宽敞的平房,一溜儿四间,水泥地也变成了砖地。这时候过年,除了洗衣服、缝被子是我分内的活儿以外,因为那该死的砖地,我又有了一项光荣的任务。爸爸通常会丢给我一块麻袋片子,我在盆里倒上洗涤剂,打湿麻袋片儿,蹲在地上一块块地擦砖,等将四间房子的地砖全擦干净后,看到来家的客人不换鞋,我咬人的心都有。
爸爸养花是出了名的,他有本事让所有的对头莲都在正月里开放。地擦干净了,爸又会给我一个盆,我便老老实实地去擦家里绿色植物的花叶子,就是我家橡皮树、龟背竹的叶片,用清水擦完后,还得用鸡蛋清再擦一遍,每当这时候,我都恨不得拔光那些绿油油的叶片。这惨痛的记忆使得我成家后,只喜矮小的绿植,坚决不养橡皮树和龟背竹。
我在干这些活儿的时候,妹妹通常在收拾床底,那时候不管是父母睡的大床,还是我们姐弟三个的小床下面,掀起垂地的流苏床单,床下是满满当当的洗衣盆、水桶等杂物,妹妹的活儿就是把床底下所有的杂物移出来,再把床底下擦干净,然后将一样样杂物擦干净再摆好,所以妹妹成家后没有一张床是可以在底下塞东西的,席梦思带抽屉她都不干,想来收拾床底是她童年时的噩梦。
家里做点心、炸馓子、做沙琪玛是我们比较愉快的时候。妈妈请来单位里能干的回族阿姨,父母和阿姨忙着晾花椒水,用牛奶、鸡蛋和面,爸爸拿出炸馓子的长木棍,我们便知道,这是要炸棍棍馓子了,宽叶馓子需用一个带齿的小铁滚子在擀好的面的边缘走一圈,宽馓子的“牙齿”就成了。炸好了宽馓子往盘里一摆,再把砂糖一撒,诱人极了。判断做馓子手艺的好坏,不用尝,只需看看炸好的馓子的均匀度和上面密密的气泡便八九不离十了。
我家烤的点心也非常好吃,用羊油和面,烤好的点心皮是一层一层的,酥极了。里面的馅更妙,有芝麻、核桃仁、杏皮、葡萄干、糖渍玫瑰花瓣。
做沙琪玛真的是很麻烦,几乎都是用清油、鸡蛋和面,擀好面后油炸,捞出后放在一个大盆里浇上熬好的糖浆,还要在上面用重物压实,最后切块。吃第一口时的那个滋味真是爽透了。
炸翻花馃子的时候,我就派上用场了,爸爸将切好的大小均匀的长方形面皮给我,我把两张叠一起,用刀在中间划道口子,将面皮的头尾从口子里翻过去,花儿就成了,油锅里一滚,出来便是漂亮的翻花馃子了。
炸完馓子的油爸爸通常用来炸带鱼、肉丸子和茄夹辣罐啥的。
等到年三十那天,把所有洗干净的窗帘、沙发套换好,对联贴好。我们姐弟三个一身簇新地跟在爸妈身后去爷爷家。
现在的孩子去爷爷家那都是兴高采烈地,但那时候的我们却是小心翼翼地。
爷爷辈上三兄弟,各自有七个儿女,爷爷是五儿两女。过年时,一大家子人聚齐,妯娌间暗潮涌动,比的是日子的殷实、孩子的学习、教养,那时候,我们敢让父母一时不痛快,他们就能让我们一年不痛快。你什么时候犯了错挨骂时,她都要从年三十这一天的账算起。
大年三十的年夜饭,虽是孩子们坐一桌,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一桌的饭菜,只敢夹自己面前的菜吃,如果你胆敢越过面前的饭菜去夹“别人门口”的菜,一定会有人及时报告爷爷。一桌大人惊讶的眼神会从孩子身上转移到他母亲身上,那滋味不亚于一片小刀子飞过来。
而且所有孩子都要切记,不能说不吉利的话,什么病了、死了通通是忌讳。
物以稀为贵,爷爷的孙子多,所以除了对长房长孙有些偏爱外,对其他孙子孙女都是比较严厉的。
为了讨爷爷一句表扬的话,我们都使劲表现。比如一早起来掏炉灰,然后去煤房子砸好煤块架火,热好洗脸水。再比如扫地、扫院子、择菜,只要是大人一拿什么,你就去抢着做,而且还要做好,这就会被赞一句:这孩子有眼力见儿。被夸得多的孩子在一堆堂姐妹中就有了威信。
最悲催的是有一年,比锅台高一点儿的我看见爷爷在炒豆沙馅,我就冲上去夺下锅铲,那一锅浆糊样的红豆沙呀不断地冒着泡往手上溅,必须快速搅动泡泡才不会跳那么高,一锅豆沙要炒到不粘锅就可以了,因为那次表现好,爷爷说,以后这活儿可以给我干了。打那儿以后,我报仇样的爱吃红豆沙。
小学四年级的春节,妈妈给我买了双时兴的旅游鞋,谁知一进院子大门,爷爷就吊了脸子,毫不客气地对着我说:“大过年的,穿一双孝鞋,还不快换掉。”从那以后,我再不敢戴白帽、穿白鞋子出现在爷爷面前。如今,哪怕是一个洗头的白毛巾,我都要用红丝线在上面缝个小花才用,尽管现在离得远,九十多岁的爷爷看不见,但这份顾忌永远都在。
家里搬了楼房后,没有院子可以施展,父母过年的心劲开始逐年递减,啥东西都可以买来,再不用亲手做了,可再也没有那种甘甜如饴的滋味了。
儿时的我曾经一边擦着砖地,一边和钻在床底下擦地的妹妹发誓,我们长大了一定不让小孩干这些活儿。
这个年,我和妹妹望着各自的儿子,祈求他们少喝点饮料,多吃点主食,祈求他们少上会儿网,多看些书,他们的被子天天都像麻花样的卷着,我和妹妹张了嘴,对视一下又把话咽了回去……
吃年夜饭时,只要他俩吃好了,所有人就都放心了。任何一句表扬都不能让他们像当年的我们那样积极地去表现。
真的不知道,等到两个孩子长大,说到过年的话题,他们会说些什么呢?
家乡情节
每一个城市都有一条繁华的街道,彰显着这个城市的市井民生。童年时,伊犁这条标志性的街道就叫“汉人街”。
我是“汉人街”长大的孩子。我的血管里流着奶茶的芳香和大西北人的豪迈。籍贯中的故乡——天津杨柳青于我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标签。我从小就熟悉的是“汉人街”那热闹的吆喝声、那空气里烤羊肉串的香味……
“汉人街”永远散发着浓浓的生活气息:卖奶皮子的妇人,卖乌斯曼草的少女、卖花帽和英吉沙小刀的巴郎、卖坎土曼的老者……维吾尔族小贩唱歌一般的吆喝着:夏梨木、斯特勒外、红姑娘子、乌斯曼……
我走到哪里,一提起伊犁,便有说不完的话题。她就像一个翩若惊魂的仙子,美得让人喘不过气,让人魂牵梦萦。
伊犁人总是爱这样给客人做介绍:不到“汉人街”不算来过伊犁。
“汉人街”原是一条长约两公里的巷子,道路曲里拐弯,两侧店铺林立,从清光绪年间开始盛极一时。当时聚集在这里的“汉人”大多是跟着湘军“赶大营”(就是挑着货郎担跟着部队走)的杨柳青人。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汉人街”的杨柳青人后裔近年已陆续迁出,仍住在老宅的所剩无几,因此“汉人街无汉人”已成了“伊宁三大怪”之一。
“汉人街”留下了我快乐而天真无邪的童年。爷爷家的庭院紧邻着“汉人街”,那院子是孩子们的乐园。那儿没有鸽子笼似的房屋,偌大的院落里,四周是齐刷刷的白杨树。一条小渠还从院里经过,水渠边上是几棵粗壮的樱桃树,俗话说,樱桃好吃树难栽。可是从小到大,每年我都能吃上那酸甜可口的红樱桃。我和弟妹及叔伯家的孩子们,熟悉各种水果,也是从爷爷家的庭院开始的。春天过了,爬杏树、摘桑葚。那又大又黑的桑葚常吃得我们满嘴乌紫、满手乌紫,然后,举着小手互相追逐、打闹。六月里,樱桃、李子、海棠果就相继成熟了。
夏天,坐在树下,冷不丁的会有熟透的苹果落下来砸在你的肩上。
爷爷家的左邻右舍全是维吾尔族人。而爷爷、伯伯及姑姑们全都能讲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夜色里,总能听见他们和维吾尔族邻居欢快的笑声。邻居们都很喜欢爷爷,谁家做饭缺个西红柿、大葱的,一敲门打个招呼就径自朝地里去摘了。而她们每回打馕,第一坑的热馕总也想着给爷爷送来尝尝。每到过年,从初一开始,陆陆续续的,大人、小巴郎都会来给爷爷拜年。
我最要好的伙伴叫穆妮娜,上小学时,看到她耳朵上挂的耳环,很羡慕,便也想扎耳洞,她给妈妈一说,阿姨竟然大方地告诉我,凡是想扎耳洞的同学都可以来。于是,我们十几个小女孩在她家院里排成一队,阿姨一只手拿着根缝衣针,一只手拿着两粒黄豆,穆妮娜则拿着一团面疙瘩和几根棉绳给阿姨当助手。阿姨先拿黄豆夹住我的耳垂轻捻,一会儿,就没什么感觉了,还没缓过神呢,针已经穿过了,用一小团面疙瘩在棉绳上一粘,在耳洞旁擦点清油,便成了。一会儿工夫,十几个人耳朵上都挂上了面疙瘩,大家摇头晃脑的好开心。
那时候,我最自豪的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朋友到我们家都肯吃我家的饭,这待遇一般的汉族人家是没有的。这都源于爸爸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请朋友在家做客时,他能够把任何一首歌直接用维语唱出来。
当我在洒满阳光的西公园过六一节的时候,当我们被老师带着去飞机场春游的时候,总能看到围成一圈的维吾尔族汉子拎着一瓶伊犁大曲,用一只自行车的铃铛盖子或者剜去内核的新鲜苹果盛着酒,一个个的轮着喝,夜幕降临的时候,一曲曲“黑眼睛”就飘满了伊犁的大街小巷,时至今日,每当我听到“黑眼睛”的时候,就仿佛又回到了童年的时光。
工作以后,我在《伊犁日报》做副刊编辑,每每接待内地报业同行,最怕的一句话是:我不能吃羊肉。
伊犁有天底下最美丽的草场、最鲜嫩的羊肉。
伊犁人的眼睛、舌头通通被惯坏了。
在草原上吃肉,一定要喝马奶子,外地人称之为马奶酒的饮料。这是配套的,马奶子是哈萨克族最爱喝的饮品。
在哈萨克人的毡房里,主人在劝马奶酒时通常会说:“这碗酒,男人喝了嘛,力量。女人喝了嘛,漂亮。两口子一块喝了嘛,较量。”
如果哪位客人在喝马奶子时做出龇牙咧嘴状,我们会从心底鄙视他,还暗骂一句:没有福气的家伙。
到乌鲁木齐工作后,我吃过超市里买的奶皮子,当我把它倒进碗里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天呐!这像冻子似的白色液体是奶皮子吗?
伊犁人吃的奶皮子是纯牛奶烧开后结的那层厚厚的奶油,一层一层地撇出来,装满一个罐头瓶子,买回家就着馕吃,那醇香、那美味,无法言说。
年纪渐长后,我常常回忆起“汉人街”和爷爷家的庭院。我开始有强烈的欲望,想写写“汉人街”和杨柳青人的渊源。
于是,2006年,我的纪实散文《新疆津帮》出版了。在《新疆津帮》这本书中主要介绍了天津商人,也就是杨柳青人在乌鲁木齐、伊犁、古城子、巴里坤等地的创业过程,以及津帮的形成。我在动手写杨柳青人的过程中,看了大量相关的资料,许多人许多事都是我从来不知道的。
津商对于新疆的贡献,不仅在于空前地繁荣了新疆的内外商贸,它还以“百艺进疆”的壮阔气势,带来了新疆百业俱兴的兴盛局面,以津商为首的八大商帮,在多民族杂居的遥远边疆,传播先进的商业理念,向边疆经济注入蓬勃的朝气与活力,极大地丰富了城乡人民的物质生活,创造了古代丝绸之路灰飞烟灭以来的又一次辉煌的商业奇迹,同时也在四大文明交汇的亚洲腹地,掀起了又一次文化融合的高潮。
杨柳青人“赶大营”的影响要远远超过杨柳青年画。他们在新疆形成了“三千货郎满天山”的局面,使当时的天津杨柳青人成为了新疆商业舞台上第一大商帮。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久远的往事渐渐尘封了,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将那些大营客们艰苦卓绝的经历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现在的“汉人街”依然是伊犁最热闹的巴扎,以“津帮八大家”为代表的大十字也依然是乌鲁木齐的繁华地,曾经的杨柳青味道就像雨水渗入沙土一样,表面上它们是消失了,实际上它在土壤里存留着,并且为生生不息的血脉输送着营养。
从报社转到出版社以后,我的家乡情结让我在工作中受益匪浅。
我参与策划编辑的丛书《家住新疆》集中了十位各民族作家的家乡文字,这是一套讲述新疆家园生活的书,是对新疆真实生活的一次可贵言说。
可以说,这是我在这个快餐时代为读者端上的一份营养餐。
一份美食做完,我开始想做大餐了。
在策划30卷本的《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译丛》时,我的朋友狄力木拉提老师给予了我很多帮助,他不厌其烦地帮忙约稿、定稿、传稿,最终,这套丛书在2014年底呈现在读者面前。丛书从组稿到成书犹如漫长的孕期,瓜熟蒂落之时便觉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该丛书收入的作品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蒙古族、锡伯族、俄罗斯族等民族的母语翻译作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囊括新疆十几个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集。全书包括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集、诗歌等,共计680多万字。全面展示了新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总体成就。
少数民族作家用母语写作,可以原汁原味地反映本民族的生活,得心应手地表达本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但很多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因为语言的局限,不能够有效地传播本民族文化,所以,将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翻译成汉文介绍给读者,让读者知道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的喜怒哀乐,这样的了解与沟通多么有必要。
三十册书摆开来便是一道彩虹,这是美编谷雨的创作思路。在这道五彩斑斓的彩虹周围,付出心血的人太多太多。
通过做这套丛书,我有了新的忧虑,老一代的翻译家们日益稀少,像刘宾这样学者型的翻译家青年一代几乎没有,再不抓紧培养,翻译队伍中有可能出现裁判、运动员一体的情况,但愿这不是杞人忧天。
真的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读一读《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译丛》,能静下心来阅读这套书的人,一定是幸运的。
“译丛”忙完之后,我又责编了“名家写新疆”丛书,作者为周涛、沈苇、远人,周涛在他的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士为自己的土地而死,土地是知己者,因为这块土地不光养育了你,这块土地上的人也充分了解了你,最认识你,最抬举你,你不死在这儿,你死在一群根本不理你的人那里干啥?只有新疆的人是你的亲人,死在亲人身边是最好的归宿。”一席话将他与新疆的感情写得淋漓尽致。他说出了这块土地上所有人的家乡情结。
我何其有幸,生在新疆!我何其有幸,能以自己的爱好作为职业谋生!
从一个读书的人变成一个编书的人,真是感谢命运的垂青,这世间,有几个人能够以自己的爱好谋生?看着由我参与策划出来的书籍,很多时候觉得自己很是富足。回首往昔光阴,有一样东西一直陪着我,那就是——书,沉甸甸,贵如金,的确,为文、为书之人的荷包也许永远都不会那么盈满,但我们的生活却因为书而变得有品质。
内心若有明灯,世界没有暗夜。
诗人笔下的新疆
2014年冬天,乌鲁木齐和往年一样,一场场鹅毛大雪盖住了整个城市。大雪之后,又总是温暖的阳光。在我办公桌上,透窗而入的光线,正照在三本刚刚印刷成书的“名家写新疆”系列散文集上。自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策划出版第一辑“名家写新疆丛书”之后,读者就好评不断,因而对第二辑,作为责编,我心里更为谨慎。最终,经过社里审议,选定了周涛、沈苇和远人作为第二辑的作者人选。定稿之后,我意外地发现,这三位作者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他们都是以诗歌在文坛产生影响的诗人。
或许,读者不难发现,诗人写散文和一个纯粹的散文家写散文,有着特别不一样的表达效果。大概是诗人对语言的自我要求更为严格,行文角度也更为出奇制胜,因而诗人的散文更能让人看到字里行间的诗意和新颖别致的视角。当然,不是每个诗人都能写一手好散文,但能够将散文写好的诗人,总是令我不知不觉地更多一份欣赏。
作为一套丛书的组合,周涛祖籍山西,童年时随父母从北京举家迁至新疆。沈苇也是从湖州来到新疆,融入这片“混血的土地”中,远人则是从湘江到新疆的匆匆过客。这种以本土为圆心的对外扩散,也显示出这套丛书的宽广度和包容度。
有人说,读一本书,就是读一个作者和认识一个作者。作为责编,我必须将这三本散文集进行认真地审读、细读和校读。这里我想谈谈对三位作者的认识,通过人,也通过书。
1
第一次见周涛是在他的作品研讨会上,彼时周涛四十出头,不到二十岁的我作为一名涛粉参加会议,只记得笔直高挺的周老师与我握手时,手指修长而干净,时至今日能够让我愿意以“玉树临风”这四个字形容的男人只有中年时的周涛。作为20世纪80年代新边塞诗的代表人物,评论界早有定论。他那些耳熟能详的散文名篇如《稀世之鸟》《巩乃斯的马》《野马群》等,早已烙在我的阅读深处。
当我满怀欣喜地拿到周老师的《冬日阳光》书稿之后,立刻就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在新疆乃至全国文坛,周涛的创作向来便以诗歌、散文为相看两不厌的并峙高峰。这几年,总有人发出“周郎老矣,尚能饭否”的疑问,周涛便以2013年的《一个人和新疆》与2014年末的《冬日阳光》做了回答。这本集子严格说可分四辑,一辑是纯粹意义上的散文,一辑是充满诗意的灵感短章,一辑是人物素描及给他人的作序,最后一辑是周涛接受的各种访谈。不论哪个类别,文字中都可以让读者看到一位著名作家的文学理解和深厚功底。
周涛曾经以诗歌享誉文坛,以散文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在那些纯粹意义上的散文中,周涛贯注的,可以说是他个人对人生的深切感悟,不论是情还是景,最终都走向作者内心的涌动。比如在《帕米尔印象》中,周涛写道,“人一辈子还是应该到帕米尔高原上去体味体味,这比读什么孔孟之道,甚至比读庄子更让人返璞归真,更让人理解人类和自然。帕米尔是一本永远打开的、静谧的书,等着你去读。你可以不读,但受损失的不是它。”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周涛的语言不论是表达内容还是表达张力,都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作为读者,是很容易被这些感性与理性交织而成的文字所感染的。也可以说,周涛的散文魅力也就是在这样的表达中体现出来的。
周涛在他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士为自己的土地死,土地是知己者,因为这块土地不光养育了你,这块土地上的人也充分了解了你,最认识你,最抬举你,你不死在这儿,你死在一群根本不理你的人那里干啥?只有新疆的人是你的亲人,死在亲人的身边是最好的归宿。”一席话将他与新疆的感情写得淋漓尽致。在《大毛拉摆擂台》《新疆的贵族们》《画家克里木》等篇什中,你会一边读、一边笑,一边感佩他对维吾尔族那种发自内心的欣赏与理解。
这本散文集中的其他文种也无不如此,他对人生的真知灼见不是要强行交给读者,而是让读者在他的果断与娓娓道来中不知不觉地接受。甚至在他的访谈中,周涛也用一种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口吻告诉读者和后辈,“文学的第一要素首先是求真,最后才是求善。文学不仅是学识、经验、智慧的产物,更是生命的产物,最高的文学就是生小孩。这是生命里本身带来的,不是仅靠努力奋斗带来的,那叫制造,不是创造。创造是天然产生的,是天然的力量。”我以为,这话里饱含的,是老一代作家留给新一代作家的衷心劝导。它不是从书本上来的漂亮话,而是一个毕生献身文学的大家将自己的全部理解和盘托出。读者从中得到的,我相信绝不是简单的阅读享受,更多的还包括对文学、对生活、对生命深入地理解。
2
认识沈苇也是在很多年以前,一行人一起去伊犁的昭苏采风,让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的诗——像草原上怒放的向日葵,耀眼而热烈。从此,我便加入了苇叶的行列。多年以后,沈苇和我聊起那次采风,提到我去给他买感冒药的细节,而我已不记得了,由此可见,沈苇是一个非常念别人好处的人。1999年我调到乌鲁木齐工作后,大家还保持着在家中待客的习惯,和一堆朋友吃过沈苇做的菜以后,才知道他做文做人做事样样是上得了台面的。
作为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沈苇的诗歌一直在文坛有颇高的声誉。在新疆,不少青年诗人都愿意聚集在沈苇身边,形成令诗坛注目的新疆诗群。在散文创作上,沈苇的才华也有目共睹,其《新疆词典》早成为读者眼中的“新疆指南”。这次列入“名家写新疆丛书”的是其散文新著《西域记》。
沈苇的散文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密度较大。这大概和他的诗有关。有密度的文字也是有力度的文字。沈苇虽是来自江南的才子,但数十年的大西北熏陶,早使他的语言日渐充满雄性。这也形成了沈苇散文独具一格的魅力。
如果说大西北令人视野开阔,那么沈苇的视野也在散文中得到体现。这部散文集的开篇之作《群山谱》就给人开阔之感,也给人致密之感。而且,在散文中,沈苇也充分展示了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想象力,所以他将昆仑譬喻成“诸神的枕头”,这些神来之笔在这本散文集中随处可见。这种语言功夫和他的感受相结合,诞生的就是书中的一篇篇美文。
沈苇的散文的确是美文。它在语言上不仅有奇特的想象,还有丰富的知识含量。在整部散文集中,沈苇对各种事物的由来和引经据典地摘引都信手拈来。尽管摘引不少,但从来不给人掉书袋之嫌,我想原因就在于沈苇特别明白,那些知识性的东西,不过都是为他的表达服务,所以他需要引证时就引证,需要抒发时就抒发,需要历史时就有历史出场,需要现代时就让现代生根……所有这些,无不给读者一种信息量巨大的阅读快感。也正因如此,著名评论家耿占春才指出,“沈苇是一个对生存有着复杂体验的人”。在这部散文集中,沈苇展现的,正是他对生存的种种体验,这种体验,不单纯是他个人的人生体验,更多的是在行文中集中起众生的体验,所以帕米尔在他眼里是天上的,喀什噶尔是西域的天方夜谭,哪怕对动植物的素描,也在沈苇笔下得到活色生香的体验描绘。
大概正是描绘体验,沈苇的文字总是特别开阔。例如在《神树·鬼树》中,他起笔就极富力度地写道,“北方民族,特别是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有一个‘世界生命树和‘宇宙中心树的古老观念。这些民族长期生活在北方原始森林中,崇拜苍天、高山和树木,认为树是天空的支柱、神灵的居所,也是性器的象征、通往上界的天梯。许多神话传说中,树是人类的始母。”这样的开篇给读者横空出世之感,也就更易唤起读者的阅读欲望。它也体现了沈苇在诗歌之外,对散文的独到理解,也是他作为一个诗人对散文文体的富有成效的践行印证。
习惯写作诗歌的人往往习惯语言精练。沈苇这部散文集中就有不少短章,它们就体现了沈苇对语言的打磨,譬如在《放羊人与放牧文字的人》短章中,作者仅用一百二十字便完成,“几年前,在北疆,遇到一位牧民,他去过北京。我问他北京怎么样,他想了想,说:‘北京好是好,可惜太偏僻了。他的回答使我想起阿摩司·奥兹的一句话:‘你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中心。放羊人和放牧文字的人,原来是心有灵犀的兄弟,道出了异曲同工的心声。”
这篇短章在我看来,不仅是体现沈苇对散文语言的打磨贡献,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也正好表明了沈苇作为一个作家的写作态度和认识。
在今天的作家群中,着实需要有更多这样具有认识意识的作家。
3
认识远人,是他2013年8月到新疆文联《西部》杂志社挂职时。在接触之前,就听到有文友说这位来自湖南的诗人到新疆后,每天都在写作。初听时我不以为然,心里也有点好奇,每天都写作的人不多,甚至罕见。职业敏感驱使我进入到他的博客,果然,自他来到新疆之后,就每日不停地写他在新疆看到和围绕他身边发生的一切。我读到他的第一篇文字是《二毛失踪记》,那篇文章的风格立刻把我吸引住了,感觉这位知名的“70后”诗人的确具有颇高的散文创作才华。后来和远人多有接触,我和其他与远人有接触的人一样,很容易便体会到他对文学的激情,也体会到他对写作的全力以赴。此外,远人的记忆力和阅读量都达到惊人的地步,这似乎也保证了他对写作的习惯养成。
这部《新疆纪行》也就是远人逐日写在博客上的“新疆日记”。尽管在整理成书的过程中,远人对文字进行了整理和删改,但全书还是保留了他刻意为之的“日记”痕迹。作为散文一种,“日记体”不那么好写,但“日记”却恰恰能保持最原生态的文字感觉。这部散文集按照远人在新疆的游历过程排列,从他踏上新疆开始,到离开新疆结束,全书构成一部完整的“旅行记录”。正如远人在自序里所言,“没到过新疆的人,大都会把自己渴望去的地方列上新疆二字。吸引人去的理由,既有新疆的广阔,也有新疆的风情。二者构成的期望,是一个一直生活在新疆的人难以体会和想象的。”这句话可以当成远人这部《新疆纪行》的钥匙。全书是以一个陌生人的眼光来面对新疆和描写新疆的。他文字所涉,的确是我们一直生活在新疆的人熟视无睹的种种,但到首次入疆的远人笔下,新疆立刻呈现出一种别样的阅读感受。也可以说,远人的新疆散文其实最令新疆人感到意外,因为他笔下的事物都是新疆人的日常。比如他写到草原和羊时,他笔下出现的文字是“车子终于经过羊群身边。我突然发现,如此多的羊,它们身边竟没有一个牧羊人,在它们周围,除了无穷尽的草原,看不到它们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它们天黑后会到哪里去,甚至,除了我们正在经过的这条水泥公路,看不到羊群走过的是什么样的路。它们似乎一直就在这里,哪怕天荒地老,也不会离去。但我们却在离去。我正在离去,千里跋涉,万里风尘,仅仅只是为了离去,为了看见天涯之外的柔情与美丽,却终不能置身其中。”这样的描述确能使读者感受一个诗人笔尖下的情怀,也充分显示了远人作为一个诗人的敏锐观察力和表现力。
另外,远人在游记中的感慨容易唤起读者的感慨,在那篇《怪石沟的怪石》末段,远人如此写道,“我伸手去摸身边的石头。石头表面无比粗粝,隐隐地从中透出红色。不知那红色是不是石头的血。这些血液也在它们体内流淌了数亿年,只是肉眼凡胎的人看不出石头的血液流动。石头的血看起来凝固,但我相信那些血还在流淌。等我们离去,等一代一代人离去,甚至等人类从地球上彻底离去,它们的血还是会流淌,因为天地永恒,天地不走,它们属于天地,属于时间中永恒的部分。它们不走,是为了见证这世界最终的海枯石烂。”
读着这样的文字,不可能不令读者怦然心动。久居新疆的人会对身边的事物习以为常,而初来新疆的远人用一双诗意的眼睛解读这方陌生的水土时,带给读者的就不止是惊喜了。仅就这部散文集来看,远人更愿意将内心不断沉淀、不断发现、不断走向开阔——而新疆,最大的特色也恰恰就是开阔。
面对这三位诗人的三本散文著作,我想说,因为他们是诗人,所以他们的著作充满了语言的灵性,因为他们是诗人,所以他们的文字充满了鲜活的诗意。
约瑟夫·布罗茨基在“诗人与散文”中这样说道:“谁也不知道诗人转写散文给诗歌带来了多大的损失;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也即散文因此大受裨益。”
新疆,从来就是一块诗意之地。如何表现出它的诗意,在这些诗人的作品中,或许得到了最完满的表达。